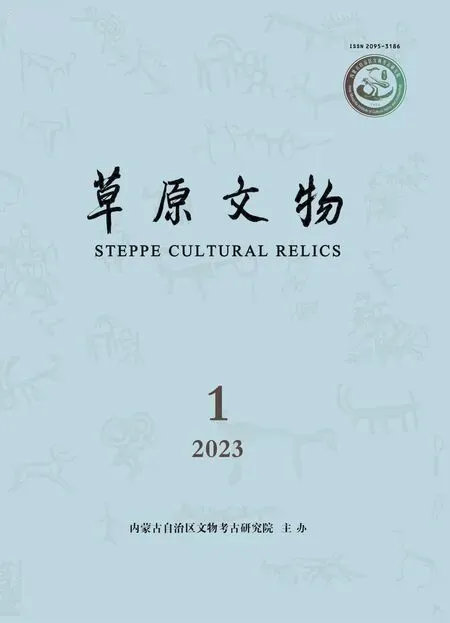2021-2022 年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文物考古發(fā)現(xiàn)綜述
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文物考古研究院
一、解讀內(nèi)蒙古舊石器時(shí)代人類進(jìn)化史
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舊石器時(shí)代遺址經(jīng)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的較多,已發(fā)掘的有呼和浩特四道溝遺址、呼和浩特大窯遺址、烏審旗薩拉烏蘇遺址、康巴什新區(qū)烏蘭木倫遺址、東烏珠穆沁旗金斯太洞穴遺址、扎賚諾爾蘑菇山遺址等。大體建立起了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舊石器時(shí)代文化的發(fā)展脈絡(luò)。近年來,為了進(jìn)一步豐富舊石器時(shí)代考古學(xué)文化內(nèi)涵,對其年代學(xué)、石器制造技術(shù)、早期人類的生計(jì)問題,及深入探討東西方古人類遷移、技術(shù)擴(kuò)散、文化交流問題,對其中兩處重要遺址重新開展了發(fā)掘工作。
1.薩拉烏蘇舊石器時(shí)代遺址
薩拉烏蘇遺址是內(nèi)蒙古為數(shù)不多經(jīng)過科學(xué)發(fā)掘的舊石器時(shí)代遺址(圖一),年代大體在7 萬年至14 萬年,因發(fā)現(xiàn)了目前中國最早的晚期智人“河套人”而聞名。為了紀(jì)念薩拉烏蘇遺址發(fā)掘一百周年,從2021 年開始了持續(xù)地考古發(fā)掘工作,兩個(gè)年度共計(jì)發(fā)掘面積100 平方米。主要發(fā)掘區(qū)為邵家溝灣和范家溝灣兩個(gè)地點(diǎn),采用在文化層內(nèi)細(xì)分操作層的發(fā)掘方法。發(fā)掘深度1~3 米,出土遺物1000 多件,包括動物碎骨1000 余件,包括披毛犀、普氏羚羊、原始牛、馬、河套大角鹿、鴕鳥等,打制石制品200 多件,類型多樣,包括石核、石片、石器和較多的小石片等,另外有零星的燒骨和木炭。范家溝灣遺址點(diǎn)找到了埋藏石器的原生文化層位,最深處發(fā)掘到5 米左右,文化遺物主要分布在第4 層,共出土動物碎骨900余件,多較破碎,打制小型石制品200 余件,另外出土了較多的木炭碎塊和燒骨。該遺址出土了較為豐富的打制石器、木炭、燒骨和動物碎骨,形成了典型的考古剖面,并進(jìn)行了環(huán)境樣品和光釋光測年樣品的采集。

圖一 鄂爾多斯市烏審旗薩拉烏蘇遺址全貌
通過連續(xù)發(fā)掘,為進(jìn)一步開展年代測定和環(huán)境分析等提供了可靠的考古地層剖面,為石器技術(shù)研究和動物考古研究提供了數(shù)量豐富的標(biāo)本,進(jìn)一步推動了薩拉烏蘇地區(qū)古人類生計(jì)方式的研究工作。
2.金斯太洞穴遺址
錫林郭勒盟東烏珠穆沁旗的金斯太遺址為花崗巖丘陵山地洞穴遺址,海拔約1400 米。遺址堆積最厚處近4 米,共分為9 個(gè)層位,主要分為4個(gè)文化時(shí)段,從距今5 萬年左右到青銅時(shí)代,最早的距今約4.7~3.7 萬年,以具有歐亞大陸西部和中亞地區(qū)舊石器時(shí)代中期莫斯特石制品組合特點(diǎn)的遺存為主;距今約2.1~2.5 萬年之間,發(fā)現(xiàn)石制品、動物化石和用火遺跡;第三階段,距今約1.3 萬年,出現(xiàn)了含有細(xì)石葉技術(shù)、兩面器加工技術(shù)、磨制骨器和裝飾品的舊石器時(shí)代晚期晚段遺存;第四階段為含有小件青銅器、陶片、磨制骨器等遺存的青銅時(shí)代遺存(圖二)。

圖二 錫林郭勒盟金斯太洞穴遺址發(fā)掘現(xiàn)場
隨著連續(xù)兩年的考古發(fā)掘,共發(fā)掘40 平方米。2021 年度完成了發(fā)掘區(qū)第5-2 層的發(fā)掘。共清理火塘7 處,僅有發(fā)現(xiàn)于4E 層和5A 層的兩處火塘相對較為完整,主要為挖淺坑堆燒。原生堆積內(nèi)出土有陶片、青銅殘件、裝飾品、骨器、貝殼、石制品、動物骨骼及牙齒等,其中以石制品和動物化石最多。2022 年度對8-6 層的發(fā)掘,出土石制品、動物骨骼及牙齒等,其中以石制品為主。第8 層出土具有明確勒瓦婁哇技術(shù)特征的石片,豐富了研究該技術(shù)的材料。
金斯太遺址處在東北亞重要的地理通道上,5萬年以來不同時(shí)段的石器技術(shù)和文化特征都顯示出與周邊地區(qū)不同程度交流的跡象。后續(xù)的深入研究將構(gòu)建出金斯太先民們在草原地區(qū)5 萬年以來的生存適應(yīng)策略;同時(shí)也可為東西方古人類遷移、技術(shù)擴(kuò)散、文化交流等提供更多考古實(shí)證。
二、內(nèi)蒙古農(nóng)業(yè)文明與早期中國的形成
新石器時(shí)代大約從一萬年至四千年,這一階段我國境內(nèi)形成了六大區(qū)系文化,有北方區(qū)系、中原區(qū)系、東方區(qū)系、西南區(qū)系、南方區(qū)系和東南區(qū)系。這六大文化區(qū)系平行發(fā)展并相互影響,匯聚而成兩條大河文明,其中前三區(qū)系匯流構(gòu)成了夏商周三代的黃河文明,而西南、南方、東南三區(qū)系則最后匯集而成了長江文明。兩者最終共同成就了源遠(yuǎn)流長的華夏文明。
內(nèi)蒙古早期農(nóng)業(yè)文明主要集中在內(nèi)蒙古中南部的黃河中上游地區(qū)和內(nèi)蒙古東南部的西遼河流域。西遼河為出自河北平泉七老圖山的老哈河與出自內(nèi)蒙古克什克騰旗潢源的西拉木倫河匯流而成。這兩條河流在西遼河流域孕育了獨(dú)特而發(fā)達(dá)的早期文明。
1.考古中國“聚落與社會——紅山文化社會復(fù)雜化進(jìn)程研究”課題開展
西遼河流域史前文明自成一體,經(jīng)過百年的發(fā)現(xiàn)與研究,已經(jīng)建立起了自身的考古學(xué)文化序列。至紅山文化晚期還成就了“壇、廟、冢”早期古國文明禮制系統(tǒng)。為了更加深入研究西遼河地區(qū)文明演化進(jìn)程,推動紅山文化申遺工作,2020 年開始啟動該課題。2021 年,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吉林大學(xué)考古學(xué)院、遼寧大學(xué)歷史學(xué)院、赤峰學(xué)院歷史文化學(xué)院等多家單位聯(lián)合開展。
內(nèi)蒙古片區(qū)開展相關(guān)流域的紅山文化遺址考古專項(xiàng)調(diào)查,并初步選擇了松山區(qū)安慶鎮(zhèn)北部的彩陶坡遺址展開發(fā)掘工作。該遺址地理位置接近赤峰市松山區(qū)與翁牛特旗的交界處,為松山區(qū)文物管理所在日常的文物巡查中發(fā)現(xiàn)。遺址總面積約4 萬平方米。2022 年,主要對該遺址不同地點(diǎn)的文化堆積、遺跡分布進(jìn)行初步了解。一共選擇了三個(gè)地點(diǎn),共清理房址12 座,灰坑5 個(gè),灶址1 個(gè)。發(fā)現(xiàn)的一座形制特殊的大房址,由南、北兩室組成,復(fù)原總面積可達(dá)132 平方米(圖三)。北室中部發(fā)現(xiàn)一長方形坑,其內(nèi)部有大量保存較好的炭化橫木鋪設(shè)在二層臺上,其南側(cè)發(fā)現(xiàn)有灶址。推測該房址可能為中心大房址或?qū)儆诰哂心撤N特殊性質(zhì)的遺存。

圖三 赤峰市松山區(qū)安慶鎮(zhèn)彩陶坡遺址房址全景
該遺址屬于西拉木倫河以南區(qū)域紅山文化中小型聚落遺址,2022 年度的發(fā)掘揭露出彩陶坡具有大小規(guī)格不等的房址,應(yīng)與其功能存在聯(lián)系。通過全面細(xì)致的考古發(fā)掘搞清其聚落布局特點(diǎn)、功能分區(qū),或許能為了解紅山社會低等級聚落的運(yùn)行和維系方式提供一條路徑。該聚落房屋的分布、形制等還需要長期的工作去揭示。不同房屋的功能研究也需要繼續(xù)精細(xì)化的發(fā)掘和科技檢測手段的運(yùn)用。
2.“考古中國——河套地區(qū)聚落與社會研究”課題開展
內(nèi)蒙古中南部地區(qū)屬于黃河上中游交界地帶,這里的河流沖刷出的河套平原為農(nóng)業(yè)提供了基礎(chǔ)的土壤、水源條件,加之溫帶大陸性氣候條件,孕育了旱作農(nóng)業(yè)。該區(qū)域?qū)儆谥性瓍^(qū)系的北端,總體上屬于中原區(qū)域文化系統(tǒng),但也存在自身獨(dú)特的北方區(qū)域文化因素。目前該項(xiàng)目已經(jīng)實(shí)施了六個(gè)年頭,后城咀石城作為該課題內(nèi)蒙古項(xiàng)目組的重點(diǎn)發(fā)掘遺址,目前已明確該石城墻體內(nèi)占地約138 萬平方米,城墻延續(xù)長約8 千米,由內(nèi)城、外城及制高點(diǎn)處的城門及甕城構(gòu)成復(fù)雜的防御體系,是目前內(nèi)蒙古中南部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等級最高、規(guī)模最大的龍山時(shí)代石城。
2019-2022 年,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文物考古研究院除了對后城咀石城周邊展開調(diào)查和全面勘探外,重點(diǎn)對城門及甕城部分進(jìn)行了發(fā)掘,累計(jì)發(fā)掘4000 余平方米,揭露城垣、城門、馬面、臺基、墩臺、壕溝、地下通道、墓葬等遺跡五十余處,出土玉器、陶器、石器、骨器等重要器物五十余件。明確了后城咀石城由城門與兩側(cè)馬面組成的主城墻防御體系,呈半月形接于主城墻上的外甕城及壕溝組成第二重防御體系,第三重小型甕城及壕溝組成地面上三重防御體系。此外還發(fā)現(xiàn)了連接第二重和第三重甕城防御體系的地下通道系統(tǒng),最終確立了石城為地上三重防御體系與地下交錯(cuò)相同的通道組成復(fù)雜而嚴(yán)密的防御體系,這也是目前考古發(fā)現(xiàn)的4000 年左右城址防御體系中最為復(fù)雜的(圖四)。其凸出于城外的直入式城門結(jié)構(gòu)與本地發(fā)現(xiàn)的其他城門差異較大,具有中原地區(qū)望京樓、偃師等商代城門的結(jié)構(gòu)特點(diǎn),但整個(gè)從防御體系的出入方式則沿襲了本地曲尺形轉(zhuǎn)折的出入模式。

圖四 后城咀石城甕城發(fā)掘區(qū)全景
對后城咀城門發(fā)掘的同時(shí),對外城東南、西南區(qū)域的墓地也分別進(jìn)行了發(fā)掘。外城西南墓地因水土流失破壞較為嚴(yán)重,斷崖處露出石板墓(圖五)。

圖五 后城咀石城三區(qū)石板墓發(fā)掘區(qū)全景
根據(jù)墓葬形制和出土遺物可見與小沙灣、西岔及對岸的下腦包石城發(fā)現(xiàn)的墓葬一致,為本地龍山時(shí)代墓葬。豎穴土坑的四壁用石板立砌而成,墓底平鋪石板,頂部多為石板平鋪或疊砌而成。墓葬均較窄,僅隨葬有少量石質(zhì)工具及石環(huán)、綠松石、骨笄等。另外東南部的墓地較為特殊,由突出地表3~5 米的土石混筑的高臺組成,根據(jù)墓葬形制及出土遺物可知為戰(zhàn)國時(shí)期墓葬。對其中一處高臺及周邊區(qū)域布方進(jìn)行了發(fā)掘,除了高臺下發(fā)現(xiàn)有墓葬外,空地處也發(fā)現(xiàn)有墓葬。墓葬之間無打破關(guān)系,按照方向不同分為東西向和南北向兩類,其中2 座東西向墓葬位于空地處,墓坑較淺且形制較小,隨葬品僅見骨笄、小件青銅帶鉤等。而南北向墓葬頂部皆有石塊壘砌的長方形封堆,下部為豎穴土坑墓穴,皆有木質(zhì)棺槨葬具,隨葬有典型中原風(fēng)格的銅鏡、銅帶鉤、印章及隨身佩戴的瑪瑙環(huán)等。同時(shí)本年度還對甕城發(fā)掘區(qū)進(jìn)行了三維建模復(fù)原、城門壕溝等遺跡的年代檢測并聯(lián)合國家考古研究中心進(jìn)行了植物考古、動物考古等工作。
后城咀石城地上及地下防御體系,是目前發(fā)現(xiàn)最早的地下防御體系,對早期城市防御體系的豐富與研究又添新材料。此外,出土內(nèi)蒙古中南部地區(qū)最早的玉器,其種類、材質(zhì)與石峁、陶寺和齊家文化發(fā)現(xiàn)的一致,同屬華西區(qū)片狀玉器系統(tǒng),充分展現(xiàn)了內(nèi)蒙古中南部地區(qū)在玉禮、玉權(quán)的文化凝聚力下,在華夏文明一體化進(jìn)程中和早期中國形成階段起到了重要作用。
3.準(zhǔn)格爾旗趙二成渠遺址
該遺址為內(nèi)蒙古中南部地區(qū)一處復(fù)合型聚落遺址。遺址發(fā)掘面積2000 平方米,共清理房址14 座、灰坑30 個(gè)。
根據(jù)所發(fā)掘的遺跡及出土遺物特征可知,分屬仰韶文化中期、仰韶文化晚期、阿善三期文化和朱開溝文化。該遺址所發(fā)現(xiàn)的房址中以F8、F9、F10 最具代表性,此三間房址自北向南排列,F(xiàn)8 為仰韶中期,F(xiàn)10 居住面上發(fā)現(xiàn)的喇叭口尖底瓶則推斷其至少在阿善三期時(shí)才被廢棄。此三間房址依次打破,營建方式一脈相承,反映了該聚落在仰韶中晚期至龍山早期存在延續(xù)性(圖六)。

圖六 準(zhǔn)格爾旗趙二成渠遺址F11
4.準(zhǔn)格爾旗沙日塔拉遺址
該遺址總面積約50 萬平方米,發(fā)掘面積為500 平方米。發(fā)掘房址、灰坑及灰溝、墓葬等遺跡,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骨器、角蚌器等150 余件。房址平面形制有圓形、圓角方形和方形半地穴式。居住面有白灰面、黑土踩踏面和白土踩踏面三種。墓葬均為土坑豎穴式結(jié)構(gòu),平面形制為圓角或弧邊長方形,大型墓葬長3 米以上,小型墓葬長1米以內(nèi)。可分為成人墓和兒童墓。除1 號墓為合葬墓外,其他墓葬均是單人葬(圖七)。除少數(shù)墓葬發(fā)現(xiàn)有葬具朽痕外,多數(shù)不見葬具。遺址內(nèi)出土與朱開溝遺址二、三段相近的器物組合,時(shí)代當(dāng)屬夏代紀(jì)年。重要的是發(fā)現(xiàn)該文化的玉器,種類有玉片、玉璋、玉璜、玉人形器、玉琮、玉箍形器等。此外地表采集有青銅器和冶煉燒結(jié)塊,這些信息為探索河套地區(qū)聚落與社會變遷具有重要價(jià)值。與后城咀遺址出土玉器相結(jié)合,為探索華夏文明一體化進(jìn)程中北方地區(qū)發(fā)展路徑提供了重要線索。

圖七 準(zhǔn)格爾旗沙日塔拉遺址M17
5.巴林右旗烏蘭圖嘎遺址
該遺址為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時(shí)發(fā)現(xiàn),總面積約20000 平方米,發(fā)掘了4000 余平方米。根據(jù)房屋建筑特點(diǎn)及出土遺物可分為興隆洼文化、趙寶溝文化和紅山文化三個(gè)時(shí)期。其中興隆洼文化和趙寶溝文化房址保存相對較好,出土遺物較多,是此次發(fā)掘的主要收獲。尤其是興隆洼文化時(shí)期房址發(fā)現(xiàn)一個(gè)獨(dú)特的現(xiàn)象,在房址中部的灶坑前大多埋有一立置的平底筒形罐,且口略高于地面,罐內(nèi)還盛滿灰燼。這一現(xiàn)象為研究房屋灶坑的使用方式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歷經(jīng)三個(gè)考古學(xué)文化的復(fù)合型聚落遺址,為深入探討西遼河地區(qū)的聚落變遷、人地關(guān)系等提供了豐富的考古資料(圖八)。

圖八 巴林右旗烏蘭圖嘎遺址發(fā)掘全景
6.寧城縣小塘山石城址
該石城揭露面積共計(jì)5000 余平方米(圖九)。石城聚落內(nèi)的房址形制可分為地面式單圈、雙圈建筑,也有部分圓形半地穴式建筑。半地穴式建筑多為圓形,沿穴壁以石塊壘砌(圖一〇)。墓葬多為長方形豎穴,部分利用廢棄的房址建成,有成人及兒童葬。

圖九 寧城縣小塘山石城遺址全景

圖一〇 寧城縣小塘山遺址陶窯
發(fā)現(xiàn)的城門處于城址東南部,與主道路相通。城門結(jié)構(gòu)復(fù)雜,呈臺階狀,前端砌有弧形護(hù)墻石。門址一側(cè)有門垛,另一側(cè)有墩臺。重要的發(fā)現(xiàn)為該遺址出土銅斧、鑿、刀、錐、鏃及銅煉渣等,銅器造型與齊家文化、石峁遺址出土的同類器相近,為探討北方系青銅器的源流提供了重要材料。
7.克什克騰旗塔布敖包遺址
該遺址為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時(shí)發(fā)現(xiàn),總面積2 萬多平方米。因配合基本建設(shè)考古,該遺址已被多次發(fā)掘,曾經(jīng)發(fā)現(xiàn)過屬于西梁文化、夏家店上層文化的遺存。2022 年再一次發(fā)掘有房址、灰坑等遺存(圖一一)。除F1 偏于遺址南部一隅、F6 坐落于西北坡外,其余4 座皆集中分布于遺址東北部,且呈西南—東北向成排分布。房址為圓角長方形半地穴式建筑,面積不大,一般為15~20 平方米。除F2 室內(nèi)保留了豐富的陶器以外,其他房址出土遺物不多。H12 填土內(nèi)發(fā)現(xiàn)人骨1具,人骨的埋藏深度基本接近灰坑開口處。坑內(nèi)出土有石器、陶器、骨器等。這在該文化中是較為常見的灰坑葬。遺址出土陶器以夾砂紅褐陶和灰陶為主,石器可分為磨制石器、打制石器和細(xì)石器,銅器數(shù)量較少,有銅泡、銅鈴等。通過此次發(fā)掘可以確定,分布于塔布敖包山東坡的遺址主體是夏家店上層文化遺存,也屬于該文化分布區(qū)域偏北的龍頭山類型。

圖一一 克什克騰旗塔布敖包遺址
8.阿拉善左旗巴潤別立墓地
2021 年,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文物考古研究院聯(lián)合阿拉善文物保護(hù)研究中心等單位,對阿拉善左旗地區(qū)賀蘭山西麓展開區(qū)域系統(tǒng)調(diào)查工作,并對發(fā)現(xiàn)的巴潤別立墓群進(jìn)行了考古發(fā)掘。發(fā)掘有亞腰形墓葬和半圓形墓葬(圖一二)。該類墓葬皆為地面堆石,剖面呈臺狀,周緣用石塊堆砌成石圍,四角栽立有較大角石,石圍內(nèi)填充大量石塊。封堆長5~10 米不等。石圍西南側(cè)發(fā)現(xiàn)灰堆兩處,封堆填石中發(fā)現(xiàn)有少量殘?zhí)掌笆グ簟⑹频冗z物。封堆中心區(qū)域偏東北處發(fā)現(xiàn)有豎穴墓壙,但不見人骨及隨葬品。另2 座墓葬呈半圓形,剖面呈臺狀,周緣用石塊堆砌成石圍,東北側(cè)石圍平直,垂直栽立有石板,其余部分石圍大致呈半弧狀,石圍有部分缺失,石圍內(nèi)填充大量石塊,石圍及填石均風(fēng)化嚴(yán)重,受力易碎。封堆長3~4米,寬2~3 米,高出地面0.2~0.5 米不等。封堆中出土少量殘?zhí)掌路桨l(fā)現(xiàn)有豎穴墓壙,未見人骨痕跡和隨葬品。

圖一二 阿拉善左旗巴潤別立墓群1 號墓
近幾年來對阿拉善地區(qū)和巴潤別立墓群、敖包圖墓群發(fā)掘,發(fā)現(xiàn)存在亞腰墓與積石墓的組合關(guān)系。與蒙古高原特布希文化基本相同。近年來,我國在陰山地區(qū)發(fā)現(xiàn)了大量的亞腰形墓,以及與亞腰形墓存在文化聯(lián)系的工字形石板墓。這也是目前中國范圍內(nèi)已知該文化分布的最南界。
9.新巴爾虎右旗額爾敦山石板墓群
2021 年,聯(lián)合考古隊(duì)對第Ⅳ區(qū)的3、4 號墓進(jìn)行了持續(xù)發(fā)掘(圖一三),并且對小天山遺址、杭烏拉遺址和阿敦礎(chǔ)魯大遺址進(jìn)行了區(qū)域系統(tǒng)調(diào)查。本年度發(fā)掘的兩座石板墓整體形制與以往相同。墓葬由地上封堆和地下墓壙兩部分組成。周緣栽立有石板框,四角立有角石,角石高聳,石板框內(nèi)填充石塊,石板框外有石塊支護(hù)。墓壙平面呈長方形,口部蓋有數(shù)塊蓋板石,底部與四壁不明顯,內(nèi)部未發(fā)現(xiàn)人骨與隨葬品,東部放置有動物頭骨殉牲等。墓葬東部個(gè)別可見碑狀立石。

圖一三 額爾敦山石板墓群Ⅳ區(qū)4 號墓東部殉牲
根據(jù)這些年來蒙古國境內(nèi)、內(nèi)蒙古草原腹地的調(diào)查和發(fā)掘,不同類型的石板墓分布范圍、年代和文化內(nèi)涵也逐漸明朗。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有著中國北方最廣闊的草原地形,獨(dú)特的地理位置對于探討中國北方和蒙古高原青銅時(shí)代至早期鐵器時(shí)代的游牧文化格局與交流模式、歐亞草原地帶游牧人群遷徙、與周邊地區(qū)農(nóng)業(yè)、漁獵等生業(yè)方式的互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民族交融促進(jìn)共同體意識形成
漢代墓地在內(nèi)蒙古地區(qū)發(fā)現(xiàn)得較多,尤其在內(nèi)蒙古中南部地區(qū)鄂爾多斯高原即“河南地”,分布著城址、長城及其附屬防御設(shè)施,有北方土著民族,也有來自不同地區(qū)遷徙的人們留給這里豐富的遺存。漢末至魏晉,政治統(tǒng)治不穩(wěn)定,這一地區(qū)不同的民族和人群在這里此消彼長留下諸多遺存,也促進(jìn)了民族大融合。
(一)漢魏時(shí)期的民族大融合
1.內(nèi)蒙古中南部漢代墓葬
兩年間因配合基建考古發(fā)掘,發(fā)現(xiàn)的漢代遺存有準(zhǔn)格爾旗廣衍古城(圖一四)、大路鎮(zhèn)南梁圪旦墓葬、鄂托克前旗三段地墓地、和林格爾縣小紅城墓地(圖一五)、和林格爾縣榆林城墓地等,發(fā)現(xiàn)不同類型的漢代墓葬百余座。墓葬形制多樣,包括不同規(guī)模、不同時(shí)段,有豎穴土坑墓、豎穴土坑帶墓道墓、土洞墓、有高大夯土封土堆的土洞墓、磚洞墓、磚室墓等。部分墓葬隨葬青銅車馬明器,大部分隨葬陶器組合除了實(shí)用的甕、罐、壺、釜外(圖一六),也有大的量倉、井、灶、銅帶鉤、印章、銅鏡、漆器等。墓葬形制與隨葬遺物都存在等級制度,但該區(qū)域也發(fā)現(xiàn)有本地的一些文化色彩,如殉牲習(xí)俗、水波紋的陶器裝飾風(fēng)格等,充分展現(xiàn)了兩漢時(shí)期長城沿線地帶社會、經(jīng)濟(jì)和文化面貌的融合現(xiàn)象。

圖一四 準(zhǔn)格爾旗廣衍古城I 區(qū)墓葬區(qū)全景

圖一六 和林格爾縣小紅城墓地M21 出土器物組合
2.涼城縣雙古城兒童瓦棺墓地
涼城縣雙古城為漢代城址,平面呈長方形,城內(nèi)中部有一土墻將古城分為南北兩城,故名雙古城。此次發(fā)掘區(qū)位于西墻外,共清理128 座兒童瓦棺墓葬(圖一七)。這類墓葬是直接放置于地表,用瓦或其他陶器碎片覆蓋,周圍用黏土塊或石塊堆壓。葬具多為板瓦、陶盆、陶罐、陶甑、陶甕及石塊等單獨(dú)或相互組合而成,僅個(gè)別無任何葬具。大多數(shù)墓頂只蓋一層板瓦,個(gè)別覆蓋二至三層,最多有覆蓋六層的。大多尸骨腐蝕殆盡,極少保存有碎頭骨及肢骨。隨葬品極少,僅個(gè)別隨葬有陶或角制飾品,其余隨葬有數(shù)量不等的半兩或五銖錢幣。

圖一七 涼城縣雙古城南區(qū)兒童瓦棺墓地
瓦棺葬是專用于安葬未成年人的一種墓葬形式。該葬俗在新石器時(shí)代至漢代較為流行,以后一直延續(xù)下來。直到解放前,西南地區(qū)一些少數(shù)民族中還保留有這種習(xí)俗。這批瓦棺墓地的發(fā)現(xiàn),為研究漢代長城沿線地帶未成年人喪葬制度提供了一批重要材料。
3.錫林郭勒盟吉呼郎圖匈奴墓群
內(nèi)蒙古境內(nèi)發(fā)掘的匈奴墓葬或墓地有西溝畔墓地、補(bǔ)洞溝墓地、大飯鋪墓地等,而這些墓葬都集中在陰山以南地區(qū)。吉呼郎圖匈奴墓群則位于陰山以北、蒙古戈壁以南的錫林郭勒大草原之上(圖一八)。2020-2022 年,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文物考古研究院與北京師范大學(xué)歷史學(xué)院等單位合作共計(jì)發(fā)掘墓葬44 座。該墓群上部多見有圓形封石堆,墓坑位于封石堆下方,一般為一冢一穴,個(gè)別墓葬為同冢異穴。墓葬結(jié)構(gòu)全部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式,墓坑規(guī)模及深度與封石堆大小成正比。墓葬大部分有木質(zhì)和石質(zhì)葬具。木槨多為框架式架構(gòu),石槨以片石砌筑。木質(zhì)棺槨皆為榫卯拼合而成的長方體,個(gè)別表面可見髹漆,棺外壁有鐵質(zhì)網(wǎng)格形、柿蒂花形裝飾。墓葬盜擾較為嚴(yán)重,出土隨葬品較少,主要包括陶、銅、鐵、金、漆、骨器和動物殉牲等。

圖一八 錫林郭勒盟吉呼郎圖匈奴墓M62 墓葬形制
吉呼郎圖墓群普遍發(fā)現(xiàn)圓形石頭封堆,墓坑南北向,棺頭朝北,木棺用柿蒂形鐵花裝飾(圖一九),隨葬陶壺、陶罐以及牛、馬、羊等葬俗葬制,與漠北地區(qū)匈奴墓葬的特征一致。出土陶器的造型和紋飾,具有典型的匈奴風(fēng)格。墓葬形制、木棺槨及棺木上的飾物、頭部的頭廂結(jié)構(gòu)及出土銅鏡、漆器等源自于同期的漢代文化,反映出該族群與漢文化有著非常密切的互動。

圖一九 錫林郭勒盟吉呼郎圖匈奴墓地出土柿蒂花形棺飾
4.和林格爾縣沙梁子古城
沙梁子古城經(jīng)2019、2020 年兩年的持續(xù)發(fā)掘,發(fā)現(xiàn)了漢代大型建筑臺基,并結(jié)合出土的大量糧食遺存和“萬石”陶盆、陶量等器物,推測其應(yīng)為一座面闊16 間、進(jìn)深2 間的大型糧倉建筑。最早應(yīng)修建于漢武帝時(shí)期,這一時(shí)期漢代在河套設(shè)置郡縣,移民墾殖。該建筑臺基的發(fā)現(xiàn)填補(bǔ)了漢代邊城研究的一個(gè)空白,對研究漢代建筑技術(shù)、西漢王朝對北疆的經(jīng)略以及北方農(nóng)牧交錯(cuò)地區(qū)的生業(yè)方式等具有重要意義。
2021 年對建筑臺基四周繼續(xù)發(fā)掘,發(fā)現(xiàn)其外圍有可達(dá)3 米高的土坯圍墻,臺基東南角發(fā)現(xiàn)有石頭壘砌的三角形護(hù)坡墻。除此之外,在清理建筑倒塌堆積中還發(fā)現(xiàn)北魏時(shí)期房址9 座,這些房址可分為半地穴式和土坯與磚混筑的地面式。半地穴式房屋是直接在倒塌堆積上下挖形成的,而地面式建筑一部分是營建在漢代倒塌堆積之上,另一部分是清理倒塌堆積后再行營建。總之,房屋建筑選址和建筑技術(shù)都較為草率,面積也僅小至四、五平方米。房址內(nèi)出土的碎陶片多見動物紋、網(wǎng)格紋、回字紋等壓印紋飾,具有鮮卑獨(dú)特的文化面貌。漢代高臺建筑與北魏時(shí)期房屋的層位關(guān)系也反映了北魏時(shí)期人們利用漢代城址廢棄建筑臺基營建房屋的事實(shí)。鮮卑和北魏時(shí)期墓葬發(fā)掘得較多,但居址多較難發(fā)現(xiàn),游牧人群的定居遺存較難發(fā)現(xiàn),這也為了解鮮卑人群居住方式、尋找鮮卑人群居住遺存提供了線索。
5.鄂爾多斯市烏審旗瓦則梁漢至北魏時(shí)期墓地
鄂爾多斯市烏審旗無定河鎮(zhèn)瓦則梁漢代遺址位于納林河南岸,該遺址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地表遺物皆為漢代。2022 年因建設(shè)取土,發(fā)現(xiàn)了一批墓葬,此次發(fā)掘13 座。根據(jù)墓葬形制、壁畫及出土遺物可知,其時(shí)代可從漢代延續(xù)至北魏時(shí)期。根據(jù)M11出土典型漢代陶罐、陶壺及明器陶雞、陶狗、陶灶、陶俑、博山爐、陶燈等,推測應(yīng)為漢墓,另外12座墓葬都表現(xiàn)出強(qiáng)烈的北魏風(fēng)格(圖二〇)。墓葬形制均為長斜坡式墓道土洞墓,全長10~12 米。墓道朝向東北,方向在30°~40°之間。墓室平面多呈弧邊梯形,部分墓室存有壁龕,部分墓葬還發(fā)現(xiàn)有壁畫。墓室內(nèi)皆有木棺葬具。出土器物有銀項(xiàng)圈、銀戒指、銅腰帶、銅頭飾、銅戒指、鐵鍑等典型鮮卑文化的遺物。

圖二〇 鄂爾多斯市烏審旗瓦則梁北魏墓葬出土文物
整個(gè)墓地未能全面發(fā)掘,從目前已發(fā)掘的墓葬來看,有成排分布且不見打破關(guān)系的特點(diǎn),墓葬形制和墓向也基本一致,顯然是有整體規(guī)劃意識。然而墓葬所屬年代卻存在差異,推測為同一部族或家族的人群長期生活形成的一處墓地。
6.武川縣壩頂北魏祭祀遺址
呼和浩特市武川縣壩頂遺址自2019開始,持續(xù)至2022 年不間斷地開展考古發(fā)掘與研究,已明確其屬于北魏時(shí)期專為太和十八年(494 年)孝文帝北巡而興建的一座大型祭祀建筑(圖二一)。整個(gè)祭壇為圓形,該祭祀遺存自內(nèi)而外由中心祭壇、內(nèi)環(huán)壕、內(nèi)壝、外壝、外環(huán)壕等五部分組成,總直徑達(dá)96.5 米。該建筑外緣為夯土墻,內(nèi)部填土,形成平臺式圓形壇體,壇體外圍以登壇臺階環(huán)繞。中心臺基底部直徑約34.5 米,頂部直徑約23.5 米,殘高2.9~4.4 米。臺階上下共13 級。對夯土臺北部解剖發(fā)現(xiàn),臺體為平地起建,自下而上逐漸斜收,剖面呈梯形,環(huán)壕內(nèi)發(fā)現(xiàn)有祭祀的動物骨骼,以馬、牛、羊?yàn)橹鳌?/p>

圖二一 武川縣壩頂遺址發(fā)掘區(qū)全景
此類型的祭祀遺跡在華夏文化傳統(tǒng)中綿延至今,在陰山之上發(fā)現(xiàn)的此類遺跡一方面體現(xiàn)了拓跋鮮卑民族對華夏傳統(tǒng)禮制建筑的吸收和傳承,又延續(xù)了北方游牧民族圣山祭祀的傳統(tǒng),是中國古代游牧民族與農(nóng)耕民族之間文化交流與融合的生動實(shí)物見證。
至北齊時(shí),該祭祀建筑被改造為邊堡遺址。將中心祭壇內(nèi)部掏空營建一圈九間房屋,東南方位開設(shè)門道。房址和地層堆積中出土有北齊“常平五銖”銅錢、刻劃有“廣納戍”文字陶盆以及大量的鐵質(zhì)兵器及鐵、陶、骨質(zhì)生活用品等(圖二二)。展現(xiàn)北朝時(shí)期北方邊疆地區(qū)多民族歷史變遷的歷史面貌。

圖二二 武川縣壩頂遺址出土北齊“常平五銖”銅錢
(二)宋遼金元時(shí)期的民族大融合
1.遼上京城址
遼代營建最早,使用時(shí)間最長,地位最為重要的都城。城址由北部的皇城和南部的漢城兩部分組成,平面略呈“日”字形,總面積約5 平方千米。皇城的城墻保存較好,宮城于皇城中部偏東。為了進(jìn)一步認(rèn)識遼上京遺址的布局和沿革,促進(jìn)對遼上京遺址的有效保護(hù),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內(nèi)蒙古第二工作隊(duì)和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文物考古研究院聯(lián)合組成遼上京考古隊(duì),從2011 年開始對遼上京皇城遺址進(jìn)行有計(jì)劃的考古發(fā)掘和研究。通過十余年的考古勘探和發(fā)掘,對城內(nèi)的宮殿基址、宮門、佛寺、佛塔、道路等遺跡持續(xù)發(fā)掘,遼上京考古隊(duì)從考古學(xué)上首次確認(rèn)了遼上京宮城形制規(guī)模,并確認(rèn)了遼上京皇城東向中軸線的存在,極大地推進(jìn)了遼上京布局和沿革的研究(圖二三)。
近兩年主要對西山坡南院山門、后殿、北廊廡配殿以及南院以南附屬院落的中殿、南院南廊廡配殿、南院東北角樓等進(jìn)行了發(fā)掘或試掘,證實(shí)了遼上京城內(nèi)的建筑大多經(jīng)過遼、金兩代先后多次營建,整體院落為南向,院落格局和規(guī)模在遼、金沒有發(fā)生大的改變。出土遺物包括瓦當(dāng)、滴水、板瓦、筒瓦、鴟吻殘塊、磚、彩繪墻皮等建筑構(gòu)件、陶瓷器標(biāo)本、骨料、骨器、鐵器等,還出土了一些泥塑、壁畫和石質(zhì)文物殘塊,時(shí)代主要為遼、金兩代。上述發(fā)現(xiàn)為進(jìn)一步推進(jìn)遼上京遺址的城市考古研究、遼上京與祖陵申遺工作都提供了翔實(shí)的研究資料。
2.遼代墓葬
墓葬皆發(fā)現(xiàn)于通遼市開魯縣東風(fēng)鎮(zhèn)周邊,為新開河與西遼河沖積平原地帶。距西拉木倫河與老哈河西段合流處不遠(yuǎn),距阿保機(jī)的私城龍化州(推測為今通遼市科爾沁區(qū)福巨古城)僅20 余千米。2021 年,在七家子村東南發(fā)掘大型遼代墓葬1 座,為土壙豎穴多室磚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室、耳室及主室組成。前室門道兩側(cè)白灰面上各繪有一契丹人物壁畫,在人物頭部側(cè)上方各有一豎行契丹文字。墓壁青磚壘砌而成,主室頂部為大石塊券頂。西側(cè)墻壁上殘留有少量壁畫。在主室北壁見有平鋪的綠色釉面殘磚。出土遺物較少。隨葬品主要有銅器、鐵器、陶瓷器、石器,另有少量的皮具、木器等。 銅器有鎏金馬帶具、釘及銅錢等,鐵器有斧、釘,陶器有盆、罐、彈丸,骨器主要有鳴鏑等。從墓葬形制和規(guī)模、發(fā)現(xiàn)的契丹文字等推測應(yīng)屬遼代大型墓葬。該墓與2016 年發(fā)掘的金寶屯遼墓相距僅約1 公里,其中發(fā)掘的一座墓的壁畫中還發(fā)現(xiàn)有漢文、契丹文墨書題記,內(nèi)容有“葬□龍化州西□二里”等,為確認(rèn)遼代龍化州的地理位置提供了信息。而另一座墓為綠釉琉璃磚砌制,尸床也為琉璃磚壘砌。墓室四壁原均有壁畫,現(xiàn)僅殘存彩繪蓮花、云紋及人物題材等內(nèi)容。
2022 年,在距離3 千米處的恒源牧場又發(fā)現(xiàn)幾處小型磚室墓,保存基本完整(圖二四)。

圖二四 開魯縣恒源牧場遼代墓葬航拍圖(從左至右M1-M3)
其中一座為長方形豎穴磚砌墓,頂部用大石板平鋪封蓋。東壁有磚砌小耳室,西壁有壁龕,墓葬規(guī)格較小,僅可存放木棺。墓室中央放置一具頭寬尾窄的彩繪木棺,棺外圍有木架。墓主人隨身之物有銀質(zhì)頭箍、摩羯形金耳墜(圖二五)、瑪瑙和銅飾件組成的瓔珞、銅鏡、銅鎏金蹀躞帶、銀鎏金戒指、石牌等遺物。木架上放置有帶木鞘的鐵劍、鐵斧、鐵矛頭、鐵骨朵、樺木箭囊,木棺東側(cè)發(fā)現(xiàn)有鐵鏃、鳴鏑、鐵蒺藜,墓室南部放置一整套鐵甲及包括籠頭、鑣銜、鈴鐺、馬鞍、障泥、馬鐙等在內(nèi)的馬具,用皮質(zhì)系帶和鎏金銅飾件組成。耳室和壁龕內(nèi)隨葬有陶壺、陶蓋罐、鐵釜、漆器等生活用品。另兩座為存有墓道的中型磚室墓葬,由墓道、甬道、墓室組成。墓室為穹窿頂,墓室地面和棺床用長條磚平鋪砌筑,棺床上放置一具頭部高寬尾部低窄的木棺。出土遺物位置與豎穴磚室墓基本相近。木棺內(nèi)有墓主隨身佩戴的金耳墜、瓔珞、銅鎏金蹀躞帶、銀鎏金戒指、銀鎏金臂鞲等,木棺外的木架上放置或懸掛有帶木鞘鐵劍、鐵矛頭、鐵斧、箭囊等武器和工具。墓室內(nèi)不同方位放置有木案及金花銀蓋罐、銅盞托等生活用品,整套鐵甲及馬具,耳室內(nèi)放置陶壺、陶罐、漆器及銅飾件若干。充分反映了契丹人騎馬、游獵的生活場景及崇尚厚葬的葬俗。

圖二五 開魯縣恒源牧場遼代M1 出土摩羯形金耳墜
根據(jù)出土遺物及墓葬形制推測其年代為遼代早期,與近年來在開魯縣發(fā)掘的七家子墓地、金寶屯琉璃磚墓等遼代較高等級的墓葬距離較近,對探討遼代墓葬分布、等級差異、葬儀葬制,尤其是與龍化州城的關(guān)系等學(xué)術(shù)課題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3.遼武安州塔基及周邊考古發(fā)掘
2020 年,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文物考古研究院為了配合遼武安州塔的文物保護(hù)修復(fù)與展示工程,對武安州塔的地宮及塔基進(jìn)行了清理和發(fā)掘,發(fā)現(xiàn)有晚期的紙質(zhì)文書。2021 年,在塔基南側(cè)底部發(fā)現(xiàn)塔基為磚墻包砌在夯土臺基,用平臥磚加白灰砌筑,所用磚多為溝紋磚,墻體外立面刷白灰。目前清理出南墻和東墻的一部分,兩墻相交處,即東南角為直角,由此推測該夯土臺基為方形,邊長約為31.8 米。在南墻外側(cè)發(fā)現(xiàn)有建筑倒塌后的堆積,還有一處倒塌的土坯墻,堆積上有大量的筒瓦、板瓦,以及瓦當(dāng)、滴水等,地表還保留有兩個(gè)門枕石,間距2 米。發(fā)掘面積較小,目前該建筑的整體面貌還需進(jìn)一步發(fā)掘,推測可能為山門一類的建筑物。堆積中出土大量筒瓦、板瓦、蓮花紋瓦當(dāng)和獸面瓦當(dāng)?shù)冉ㄖ?gòu)件,還有鐵飾件、風(fēng)鐸殘片、鐵釘、鐵箭鏃等,也可見少量瓷器殘片。建筑倒塌的堆積上發(fā)現(xiàn)21 座骨灰葬,皆以陶罐為葬具。不見清晰的墓坑,部分周邊用碎磚塊稍加壘砌,罐口覆蓋磚塊。隨葬品很少,個(gè)別發(fā)現(xiàn)有銅錢、骨柄刷等,銅錢多為宋錢。
遼代佛塔發(fā)掘較少,此次因配合文物保護(hù)而開展的考古發(fā)掘工作,對推動遼代宗教建筑的研究、遼代宗教文化、遼金時(shí)期佛教與骨灰葬提供了真實(shí)可靠的信息。
4.準(zhǔn)格爾旗二長渠宋代墓葬
準(zhǔn)格爾旗納日松鎮(zhèn)二長渠新村南側(cè)為宋代豐州城故城。2021 年,在城址西北和東北兩個(gè)地點(diǎn)共發(fā)掘9 座墓葬。墓葬由墓道、甬道、墓室、磚砌尸床等部分組成,墓道有斜坡式、臺階式、豎井式三種。墓葬結(jié)構(gòu)、形制和規(guī)模基本相同。墓葬均為仿木結(jié)構(gòu)磚室墓,墓室及墓壙平面皆呈圓形,磚砌筑的墓室均位于圓形墓壙之中。墓室內(nèi)磚壁等距砌筑仿木結(jié)構(gòu)的立柱、柱頭鋪?zhàn)鳌㈤艽⒋u砌門窗等。葬制為先火化后收集骨灰及未燒盡的骨骼再行埋葬,墓室內(nèi)隨葬明器外,還有陶瓷生活用器、銅錢及宗教用器等。
本次發(fā)掘的9座墓葬位于二長渠宋豐州城北,與2016 年發(fā)掘的4 座墓葬結(jié)構(gòu)基本相同,結(jié)合出土遺物及與城址的關(guān)系,初步認(rèn)定這批墓葬年代為宋夏時(shí)期。
5.興安盟扎賚特旗金代屯堡
興安盟扎賚特旗因文得根水利樞紐工程的開展,連續(xù)三年發(fā)掘了2 座金代屯堡遺址。2021 年發(fā)掘的兩家子堡址,該堡址周長1300 余米,總面積近11 萬平方米,城墻上筑有馬面、角樓等防御設(shè)施,堡門外設(shè)甕城,墻外有護(hù)城壕,其防御設(shè)施完備,防御功能突出,應(yīng)屬于金界壕防御體系的重要軍事防御職能的城堡(圖二六),西北距金界壕約5.6 千米。堡內(nèi)中心部發(fā)現(xiàn)有大型院落建筑基址1 處。在甕城內(nèi)中部發(fā)現(xiàn)平面呈長方形的居住區(qū),有煙道及中心的灶址。出土器物包括陶瓷器、鐵器、石器和骨器等,種類有用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日常生活、修建房屋城墻及打仗所用的各類物品。

圖二六 扎賚特旗兩家子金代堡址全景圖
伊和屯堡址平面呈不規(guī)則四邊形,西鄰綽爾河大回彎處,西北墻利用懸崖,未修筑城墻,崖下為綽爾河。東墻、南墻、西墻為夯筑土墻。東南、南角各設(shè)有角樓,東墻長100 米、南墻長100 米、西墻長70 米。主要對門址進(jìn)行了發(fā)掘,門址位于堡址的南墻中部,單門道,寬約4.5 米。門址墻體為夯筑,寬3~5.6 米,殘高0.8~1.2 米。土質(zhì)為黃褐粘土,較疏松。城墻系一次修筑而成,且使用時(shí)間短或修建后不久廢棄。
這些堡址都是金界壕的附屬設(shè)施,屬金代東北路界壕,修建于金世宗大定年間。從其地理位置、建筑的形制特征可推斷應(yīng)為界壕沿線內(nèi)側(cè)的軍事戍堡。戰(zhàn)時(shí)守邊作戰(zhàn),平日也開展農(nóng)耕、畜牧、漁獵生產(chǎn)等活動,為研究金界壕沿線防御體系、守邊戍兵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有價(jià)值的材料。
6.涼城縣南房子元代遺址
南房子遺址為一處小型元代居住遺址。發(fā)掘2000 余平方米,清理有房址、磚石墓葬、亂葬坑、灶坑、壕溝、灰坑等遺跡三百余個(gè)。遺址保存狀況較差,房址大多僅剩煙道。地層及遺跡內(nèi)出土遺物豐富,主要有陶瓷器、錢幣、金屬器、玉石器、磚瓦建筑構(gòu)件等。出土錢幣包括漢、唐、宋、金時(shí)期。銅器有簪、鐲、戒指、耳飾等;鐵器主要有犁鏵、鐵鋤、礁斗、匜、釘、剪子、刀、馬掌、鳴鏑、矛等;陶器主要是盆、罐、熏爐、陶紡輪、陶球、陶狗和羊等;瓷器主要是白釉瓷,其次是黑釉瓷,也有茶末釉及醬釉瓷器(圖二七)。窯口有磁州窯、霍窯、鈞窯、龍泉窯等,也有少量三彩器和膠胎器,大多為日常生活用品,器足多有墨書的“李”“王”“薛”“張”“栗”“仲”等姓氏;骨器主要有梳子、線軸、骨盒、骨片、塞子等;建筑構(gòu)件主要是方磚、長方磚、筒瓦、板瓦、滴水等。

圖二七 涼城縣南房子元代遺址出土三彩熏爐
該遺址地層堆積較厚,表明其作為元代時(shí)期一處定居時(shí)間較長的遺址,生業(yè)方式應(yīng)以農(nóng)業(yè)為主、畜牧業(yè)也較為發(fā)達(dá),是元代北方長城沿線農(nóng)牧交錯(cuò)地帶村鎮(zhèn)一類遺址的真實(shí)展現(xiàn)。
7.鄂托克旗阿爾寨石窟寺建筑基址考古發(fā)掘
阿爾寨石窟寺位于鄂托克旗草原之上,石窟寺所在紅砂巖山體東西長約200 米,南北寬約70~90 余米,高出周圍地面約80 米,山頂海拔高度為1460 米,是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境內(nèi)發(fā)現(xiàn)規(guī)模最大的集寺廟、石窟、巖刻為一體的佛教建筑群(圖二八)。多年來,對于該石窟寺僅限于對石窟洞窟、崖壁石刻等遺存的保護(hù)現(xiàn)狀、宗教、建筑、藝術(shù)等方面的研究,對其相關(guān)的佛寺建筑、日常生活等鮮有研究。2020 年以來,國家文物局為了全面掌握石窟寺的保護(hù)狀況,系統(tǒng)分析了石窟寺保護(hù)形勢,為科學(xué)制定保護(hù)政策和中長期規(guī)劃奠定重要基礎(chǔ)。全國范圍內(nèi)開展了石窟寺調(diào)查工作,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在此基礎(chǔ)之上計(jì)劃對這處重要石窟寺進(jìn)行了考古發(fā)掘,為深入探討建筑營建年代、延續(xù)時(shí)間、石窟洞窟與頂部建筑的關(guān)系以及當(dāng)時(shí)居住在此的僧侶們的生活等方面提供可靠的證據(jù)。

圖二八 鄂托克旗阿爾寨石窟寺建筑基址發(fā)掘全景
2022 年,對頂部平臺上的建筑基址進(jìn)行系統(tǒng)地調(diào)查記錄后,選擇西南角的兩處建筑基址進(jìn)行發(fā)掘清理工作。其中1 號建筑基址為一處大型回廊院落建筑,坐北朝南,磚木結(jié)構(gòu),東西長23.6、南北寬15 米,建筑面積450 平方米。堆積主要是房屋倒塌和后期形成的堆積。墻體內(nèi)外用長方形單磚交錯(cuò)壘砌,白灰抹縫;墻中間內(nèi)填紅砂巖石塊,上部用與磚同規(guī)格的土坯。主間及次間墻寬1.0、殘高0.30~1.36 米。回廊寬1.90 米,南廊用磚交錯(cuò)鋪地,東、西、北三面回廊將地面直接鑿平。西廊及北廊內(nèi)有殘存的廊柱。主體建筑面闊五間、進(jìn)深三間,面積354 平方米。地面上發(fā)現(xiàn)方座圓形明暗柱礎(chǔ)44 個(gè),地面用磚鋪就,且呈幾何花紋造型。主建筑內(nèi)設(shè)有佛壇及基座,兩側(cè)也均設(shè)有對稱的5 座須彌式佛壇基座。2 號建筑附屬于1 號建筑,規(guī)模較小。為磚石結(jié)構(gòu),僅存基礎(chǔ),坐北朝南。東西長7.60、南北寬4.76、墻基寬0.50、殘高0.40 米。門開于西南角,寬1.10米。西北角有磚砌火炕,長1.95、寬1.10、殘高0.06米。該建筑應(yīng)為僧侶們的生活居址。
建筑堆積內(nèi)出土大量建筑構(gòu)件,主要是磚、瓦、木、石等。有制作塔紋磚、佛像頭髻和佛珠等器具的陶模(圖二九),也出土大量的小型泥塑彩供養(yǎng)繪佛像。生活用瓷器有碗、盤和罐等,部分可確認(rèn)為靈武窯產(chǎn)品,另有銅釜、鐵釜等。另外還出土有景教標(biāo)志的銅牌飾。

圖二九 阿爾寨石窟寺建筑基址出土塔形磚模具
經(jīng)過發(fā)掘,該建筑基址營建年代為元代,是一處保存有完整地基及墻體的回廊式磚木結(jié)構(gòu)的宗教建筑遺址,是內(nèi)蒙古西部地區(qū)元代喇嘛教建筑的典范,為研究阿爾寨石窟寺配套的寺院建筑格局,多宗教文化的交融、宗教建筑技藝以及僧侶的生活面貌等都提供了重要的證據(jù)。
(三)明清時(shí)期的交流互動
1.烏蘭察布市隆盛莊敵臺
隆盛莊敵臺位于隆盛莊鎮(zhèn)東約1 公里處,敵臺東側(cè)3 公里處有雙臺山“大明洪武二十九年”石刻題記。根據(jù)地面保存狀況和發(fā)掘情況得知,敵臺依明長城墻體而建,由中心臺墩、臺基、臺基院落建筑、圍墻、壕溝組成。中心墩臺夯筑而成,整體呈上小下大的覆斗形,邊長7~21 米、高9 米。墩臺建筑分上、下兩層,皆為窯洞式,下層從左向右有三個(gè)窯洞,之間均有過道相通。上下兩層至墩臺頂部都有通道。臺基略呈四邊形,邊長約45 米,臺基現(xiàn)高3~4 米。臺基外圍有一圈圍墻,西北側(cè)依托墻體,西南、東南、東北面建有夯筑院墻。平面近方形,周長約160 米。圍墻內(nèi)發(fā)現(xiàn)房址2 座,有灶炕、排水道等設(shè)施。
隆盛莊敵臺作為明長城(大邊)的重要組成部分與長城墻體同時(shí)建于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由山西行都司主持修筑,是明代北部邊疆地區(qū)防御設(shè)施的重要組成部分。文獻(xiàn)中記載為貓兒莊墩,是明朝與北元政治、經(jīng)濟(jì)、軍事交流的一處重要驛站,對研究明代北疆長城及其附屬建筑敵臺的形制特征及其演變規(guī)律提供科學(xué)資料。
2.準(zhǔn)格爾旗念壕梁明代窯址
鄂爾多斯市準(zhǔn)格爾旗納日松鎮(zhèn)羊市塔村念壕梁社發(fā)現(xiàn)這處明代窯址,是為了配合基本建設(shè)開展的考古發(fā)掘。發(fā)掘地點(diǎn)受限,僅發(fā)掘清理灰坑3 座、窯址1 座。其中窯址為東西向,由窯道、窯門、火膛、窯床、煙道等部分組成,保存較好。窯址所用材料有青磚、土坯,內(nèi)壁涂抹草拌泥,由于長期燒造,呈磚紅色。火膛內(nèi)發(fā)現(xiàn)有燒造完成的器物,有灰陶獸面紋瓦當(dāng)、筒瓦、琉璃鴟吻等。其他灰坑較為規(guī)整,出土有殘鴟吻、瓦當(dāng)、筒瓦、碎瓦片等建筑構(gòu)件,也發(fā)現(xiàn)有陶碗、瓷罐、褐花白瓷等生活用器。
該窯址出土的灰陶瓦當(dāng)、屋脊獸、石灰鴟吻、琉璃鴟吻及灰坑內(nèi)出土廢棄的建筑構(gòu)件和生活用具等,初步判斷為一處以燒造建筑構(gòu)件為主的明代陶窯。念壕梁遺址位于鄂爾多斯高原南部,是晉、陜、蒙三省邊界,其南10 公里即為延綏邊墻,推測該遺址是明代長城沿線居民的陶窯燒造場,為周邊古城居民提供建筑構(gòu)件。
此次發(fā)掘出土的遺物、遺跡是對鄂爾多斯市準(zhǔn)格爾旗地區(qū)明代歷史資料的重要補(bǔ)充,對研究鄂爾多斯乃至內(nèi)蒙古中南部地區(qū)明代考古學(xué)文化、民間建筑形制、陶瓷燒造工藝等具有重要價(jià)值。
近年來,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文物考古事業(yè)蓬勃發(fā)展。自習(xí)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體學(xué)習(xí)時(shí)強(qiáng)調(diào),“要高度重視考古工作,努力建設(shè)中國特色、中國風(fēng)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xué),更好認(rèn)識源遠(yuǎn)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為弘揚(yáng)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增強(qiáng)文化自信提供堅(jiān)強(qiáng)支撐”,考古工作也得到了全方位的關(guān)注。我區(qū)以學(xué)術(shù)課題為目標(biāo)的主動考古發(fā)掘項(xiàng)目也越來越多,時(shí)間軸線越來越長。從幾十萬年的人類進(jìn)化史,隨著石器加工技術(shù)的進(jìn)步,薩拉烏蘇人使用火的能力的加強(qiáng),動物骨頭有被燒灼的痕跡加速了人類的進(jìn)化。一萬年以來,西遼河流域先民們在全新世大暖期的優(yōu)良條件下,發(fā)展起獨(dú)特的西遼河文明,在六千年前后成就了發(fā)達(dá)的紅山文明古國,在三千五百年前后成就夏家店下層文化這樣可與三代文明相媲美的方國文明。河套地區(qū)在整個(gè)黃河文明的影響下,展現(xiàn)出極具北方色彩的以農(nóng)業(yè)為主兼具畜牧的文明模式,成為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分布區(qū)的最北端。四千年前后在長城沿線地帶形成了河套石城文化圈,開創(chuàng)了中國古代防御要素為主的城市建筑發(fā)展模式,為中原地區(qū)的早期城防體系的不斷完善注入了新的元素。秦漢大一統(tǒng)時(shí)期,內(nèi)蒙古地區(qū)經(jīng)歷了戰(zhàn)國至秦漢時(shí)期的開發(fā)經(jīng)營,第一次民族融合就此形成。此后,鮮卑、契丹、女真、蒙古、滿等不同民族在此繁衍、發(fā)展,各民族不斷交流互融,逐漸形成了中華文明一元多支的發(fā)展路徑。這些考古發(fā)現(xiàn)以及展示出來的文化面貌,無不彰顯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和不斷發(fā)展的過程。文化自信首先要做到對自身文化價(jià)值的認(rèn)知和肯定,對中華文明持續(xù)發(fā)展的內(nèi)在基因的繼承和發(fā)揚(yáng)。作為一個(gè)邊疆考古研究單位,我們必須腳踏實(shí)地、守正創(chuàng)新,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更多的實(shí)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