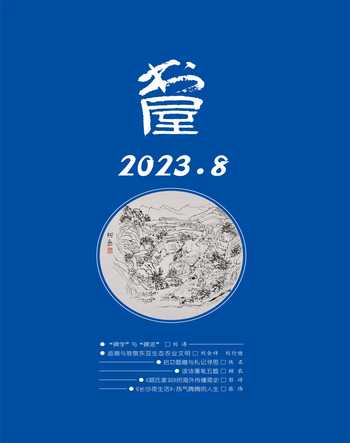佛教的“譬喻思維”
黃俊杰
一
我們研究佛教經典中所見的“譬喻思維”,并分析儒、佛兩家的“譬喻思維”之類型及其所發揮的作用,可以從以下三個問題切入:一、佛教經典中如何運用譬喻(metaphor)?二、儒、佛經典所運用的譬喻分為哪些類型?各自發揮何種作用?三、儒、佛“譬喻思維”對二十一世紀有何啟示?我們先從佛經所運用的譬喻開始探討。
漢代佛教來華,使中土人士開啟了全新的生命觀、宇宙觀與世界觀,這些都是周公、孔子以來中國人所未曾聽聞的論述,對中土的儒家思想帶來巨大的沖擊。從漢末以降,儒、佛論爭及其會通,就成為東亞思想史的重大課題。佛經大量使用譬喻,其言若近,其旨玄遠,誠如《大般若經》云:“廣說譬喻,重顯斯義,令其易了。諸有智者,由諸譬喻,于所說義,能生正解。”《妙法蓮華經》又云:“諸佛亦以無量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辭,而為眾生演說諸法。”但佛經大量使用譬喻的思維習慣,在漢末就引起中土人士之爭議,牟子《理惑論》有以下一段記載:
問曰:“夫事莫過于誠,說莫過于實。老子除華飾之辭,崇質樸之語。佛經說不指其事,徒廣取譬喻。譬喻,非道之要。合異為同,非事之妙。雖辭多語博,猶玉屑一車,不以為寶矣。”
牟子曰:“事嘗共見者,可說以實。一人見一人不見者,難與誠言也。昔人未見麟,問嘗見者:‘麟何類乎?見者曰:‘麟如麟也。問者曰:‘若吾嘗見麟,則不問子矣。而云麟如麟,寧可解哉?見者曰:‘麟,麏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霍解。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老子》云:‘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又曰:‘譬道于天下。猶川谷與江海。豈復華飾乎!《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引天以比人也。子夏曰:‘譬諸草木。區以別之矣。《詩》之三百,牽物合類,自諸子讖緯、圣人秘要,莫不引譬取喻,子獨惡佛說經牽譬喻耶?”
面對中土人士對佛經中的譬喻的質疑,漢代末年的佛教徒就指出中國文化經典如《詩經》《論語》《老子》等都常引譬取喻,以牽物合類,由此支持佛經之引譬取喻。
二
佛教經典運用譬喻的方式,可以歸納為以下四種方式:
第一,佛經常通過講故事來進行哲學論述:中國佛教徒常常閱讀的《百喻經》與《雜譬喻經》就大量使用具體的故事以闡釋佛法之要義;《箭喻經》以人為毒箭所傷,命在旦夕,喻人之求法,刻不容緩。此種譬喻展現東方人經由說故事而進行哲學思辨的思維方式。整部《賢愚經》都通過敘述神話故事而激發讀者思辨道德價值、提煉道德命題。這種思維方式也見于先秦典籍之中,如《孟子》的“揠苗助長”、《呂氏春秋》的“刻舟求劍”、《莊子》的“朝三暮四”等成語,均以具體而特殊的故事為喻,闡釋抽象而普遍的命題。
佛教經典中最為扣人心弦的故事是《雜譬喻經》中的一段神話故事:“昔有鸚鵡,飛集他山中,山中百鳥畜獸,轉相重愛,不相殘害。鸚鵡自念:‘雖爾,不可久也,當歸耳。便去。卻后數月大山失火,四面皆然,鸚鵡遙見,便入水,以羽翅取水,飛上空中,以衣毛間水灑之,欲滅大火……鸚鵡曰:‘我由知而不滅也。我曾客是山中,山中百鳥畜獸皆仁善,悉為兄弟。我不忍見之耳。天神感其至意,則雨滅火也。”
這一段鸚鵡以羽翅取水欲滅火的故事,可以有各種不同的解讀。最常見的解讀是:鸚鵡用心良善,可以感動天神替它滅火。《雜譬喻經》以這一段鸚鵡滅火的神話故事,闡釋一種近于“觀念論”的哲學立場,這種哲學立場主張外部世界的狀況可以因為內在的“心”之起心動念之良善而改變。這一種哲學立場主張“心”對于“物”而言,居于首出之地位;而且,外部世界的運作邏輯受到內在的“心”的運作邏輯的支配而運轉。
第二,佛經常以具體性的事物作為譬喻,以悟入抽象性的義理。《大般若經》以夢境、谷響、光影、幻事、陽焰、水月、變化等作為譬喻,闡釋世間“一切唯有假名”。在藏傳佛教經典中,《現觀莊嚴論》可說是對譬喻的使用最為得心應手的一部論典。《現觀莊嚴論》以大地、純金、初月、猛火、寶藏、寶礦、大海、金剛、山王、良藥、善友、寶珠、日輪、歌音、國王、倉庫、大路、車乘、泉水、雅音、河流、大云二十二種具體事物譬喻“發心”的形象。在恒河沙數的佛教經典中,譬喻的運用不僅源遠流長,而且使閱讀者以譬喻得解,調伏心續,自他圓融,優入圣域。舉例言之,博朵瓦(1031—1105)在《喻法》中以“蟲禮騎野馬,藏魚梅烏食”譬喻暇滿人身之難得。寂天菩薩(685—?)《入行論》以馬喻“菩提心”,以“騎菩提心馬”喻求法精進,以“童嗜刃蜜”喻人之“貪欲無饜足”,以“烏云夜”喻生命中之幽暗,以“閃電”喻佛法,以“劫火”喻覺心,以“沙屋”喻生命之苦短,以“筏”喻人身,以“明月光”喻佛法,以“芭蕉樹”喻心之無所有。宗喀巴(1357—1419)大師在開示“壽無可添,無間有減”時,特別“從眾多喻門而正思維”,以織布、宰殺羊、江河、險巖垂注瀑布、牧童驅逐畜類等,譬喻生命之苦短;以“瀑流水”喻發精進力勿太過熾然或太散緩,而應“恒相續”;以“毒箭”之傷身喻惡行之傷心。凡此種種皆為佛經常見的“引諸譬喻,得知實法”的譬喻思維方式。誠如《大智度論》卷九十一《釋具足品》第八十一上云:“以明心事,故說譬喻,取其少許相似處為喻。”佛經所運用之譬喻,常以少喻多,以“具體性”喻“抽象性”。《華嚴經》曾運用二十一種具體事物來譬喻“心”的不同相狀:
1.應發如大地心,荷負重任無疲倦故。
2.應發如金剛心,志愿堅固不可壞故。
3.應發如鐵圍山心,一切諸苦無能動故。
4.應發如給侍心,所有教令皆隨順故。
5.應發如弟子心,所有訓誨無違逆故。
6.應發如僮仆心,不厭一切諸作務故。
7.應發如養母心,受諸勤苦不告勞故。
8.應發如傭作心,隨所受教無違逆故。
9.應發如除糞人心,離驕慢故。
10.應發如已熟稼心,能低下故。
11.應發如良馬心,離惡性故。
12.應發如大車心,能運重故。
13.應發如調順象心,恒伏從故。
14.應發如須彌山心,不傾動故。
15.應發如良犬心,不害主故。
16.應發如旃荼羅心,離驕慢故。
17.應發如犗牛心,無威怒故。
18.應發如舟船心,往來不倦故。
19.應發如橋梁心,濟渡忘疲故。
20.應發如孝子心,承順顏色故。
21.應發如王子心,遵行教命故。
《華嚴經》使用日常生活習見的事物如大地、弟子、養母、傭作、良馬、大車、舟船、橋梁等,譬喻修行人起心動念應持守的不同的相狀,非常傳神。
《大般若經》中也有一段壯士射箭的故事:“如有壯夫善閑射術,欲顯己技,仰射虛空,為令空中箭不墮地,復以后箭射前箭筈,如是展轉經于多時,箭箭相承不令其墮。若欲令墮便止后箭,爾時諸箭方頓墮落。”
這一段以壯士射箭的故事譬喻修行之人不可間斷,否則前功盡棄。
第三,佛經常運用“同類相比”,也就是隋代慧遠(523—592)法師所著《大乘義章》中所論的“比量”。《法華經》以“火宅”喻生死輪回,以“父親”喻佛陀,以“小孩”喻眾生,以“羊車、鹿車、牛車”喻聲聞乘、獨覺乘、菩薩乘,以“七寶大車”喻一佛乘。這一段譬喻是佛陀巧設方便,讓在火宅中的眾生從希求出離輪回,最后進入“一佛乘”。也以“窮子”喻眾生,以“長者(父親)”喻佛陀,讓窮子從小乘修起,最后進入大乘。
第四,佛經也常常運用“異類相比”,也就是所謂“譬喻量”。例如《法華經》以“藥草”喻眾生根器(小、中、大),以“雨水”喻佛陀所說之法,是在說佛陀教化眾生等無差別,依眾生根器不同,各得饒益。以“險道”喻輪回,以“化城”喻二乘,以“寶處”喻大乘,這一段譬喻說二乘是佛陀化現始眾生脫離輪回、稍事休息之處,大乘方是佛陀引導眾生的真實目的。以“貧人”喻眾生,以“與珠之親友”喻佛陀,以“衣中無價寶珠”喻成佛之善根種子,這一段譬喻是佛陀過去已為眾生種下成佛之善根,但眾生不知,反而成就二乘道。以“轉輪王”喻佛陀,以“髻珠”喻《法華經》一佛乘之說,“王頂上有此一珠,若以與之,王諸眷屬必大驚怪”,以此喻解釋為何佛陀至涅槃前方說“法華”一乘之教。又以“良醫”之詐死喻佛陀示現涅槃相,以“醫子”喻眾生,以“良藥”喻佛法,這一譬喻說明佛陀示現涅槃相是為了使眾生珍惜、信受佛法,實際上如來壽量無盡。
佛經大量運用譬喻,最重要的著眼點在于:眾生苦于“無觀察識”(指眼、耳、鼻、舌、身等五識),所以常常對境即昏,只有“意”識才能思維觀察,所以,佛經就以譬喻來導引“意”識的運作,以譬喻之“名言量”破“無觀察識”。“名言”指名目與言句,通過譬喻而使眾生“于一一法名言,悉得無邊無盡法藏”,從具體性而悟入抽象性。《大般若經》以古印度樂器箜篌作為譬喻,闡釋索解不易的“空性”云:“譬如箜篌,依止種種因緣,和合而有聲生……要和合時。其聲方起。是聲生位無所從來,于息滅時無所至去。”佛經中的譬喻類似道路或橋梁,其作用在于溝通“來源域”與“目標域”,經由譬喻而使聽聞者通達圣教。
但是,佛經中所見“譬喻思維”多以神話故事之方式而進行,與儒家之“譬喻思維”通過“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方式而進行,有巨大之差異。二十世紀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說:“天竺佛藏,其論藏別為一類外,如譬喻之經,諸宗之律,雖廣引圣凡行事以證釋佛說,然其文大抵為神話物語,與此土詁經之法大異。”陳先生的說法,切中儒、佛運用譬喻的方式之不同,儒家聚焦于“此世”,佛教遙契于“彼世”。
至于中國文化經典與佛教經典中之譬喻,所發揮之作用則多種多樣。錢鍾書先生曾歸納為兩類:一曰“兩柄”,二曰“多邊”。錢先生闡釋譬喻所發揮之“兩柄”作用云:“水中映月之喻常見釋書,示不可捉搦也。然而喻至道于水月,乃嘆其玄妙,喻浮世于水月,則斥其虛妄,譽與毀區以別焉。”
又釋“多邊”之作用云:“蓋事物一而已,然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取譬者用心或別,著眼因殊,指同而旨則異;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孑立應多,守常處變。”
錢先生所謂“兩柄”取譬喻所承載正反兩面之寓意;所謂“多邊”指譬喻之一事多義之特質。錢先生言簡意賅,得其肯綮,最有啟發。
三
儒、佛經典中所使用之譬喻可分類為以下幾種類型:1.實體譬喻:如月、火、水等;2.空間方位譬喻:如上、下、左、右等;3.容器譬喻:例如身體作為“納法成業”的容器等。茲分別分析如下:
1.實體譬喻。指以具體實存之事物,譬喻抽象之義理與法意。實體譬喻可以協助聽者或讀者對抽象理念之理解,提供具體的、經驗性的基礎。誠如當代語言哲學家雷可夫(George Lakoff)與約翰遜(Mark Johnson)所說:“一旦能夠將我們的經驗視為實物或物質,我們就可以將之指涉、分類、組合以及量化——并且以此一手段下判斷”。
儒、佛經典中一再地出現有關“月”的實體譬喻。比如說,《論語·陽貨》講:“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以日月之消逝譬喻時間之不可留。《論語·子張》說:“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以月蝕和日蝕譬喻有崇高人格者所犯的錯誤。《中庸》第三十一章“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如日月之代明”,則從正面思考,以日月之輪回譬喻孔子繼踵堯、舜而現于世。
在佛教三藏經典中也有大量的有關月亮的譬喻。在《長阿含經》中,我們讀到“今睹佛光明,如日之初出,如月游虛空,無有諸云翳,世尊亦如是,光照于世間”,世尊就是指釋迦牟尼,如日如月,光照于世間,以日和月來進行“譬喻思維”。
早期佛教經典《雜阿含經》云:“婆羅門白佛云:‘何不善男子如月?佛告婆羅門:‘如月黑分,光明亦失,色亦失,所系亦失。”“不善男子如月”,就是將做壞事的人譬喻為月亮,因為月亮在晚上出現,如同“光明亦失,色亦失”。《雜阿含經》也將善男子譬喻為月:“婆羅門白佛云:‘何善男子其譬如月?佛告婆羅門:‘譬如明月凈分光明,色澤日夜增明,乃至月滿,一切圓凈。”因為做好事的人,也好像月亮一樣掛在天上,人人都可以看到,所以佛經運用月亮的“盈”與“虧”,來譬喻人的“善行、惡行”,以及在輪回中的“升”或者“沉”。
除了常見的“月”之實體譬喻之外,佛經也常使用芭蕉、泡沫等作為譬喻。《大般若經》云:“觀色如聚沫,觀受如浮泡,觀想如陽焰,觀行如芭蕉,觀識如幻事”,以具體的聚沫、浮泡、陽焰、芭蕉、幻事譬喻抽象的“色、受、想、行、識”等“五蘊”,指向“五蘊皆空”“一切法皆無自性”之命題。《大般若經》也以“眾流隨其大小,若入大海同得咸名”,譬喻“布施”“凈戒”“安忍”“精進”“靜慮”等五波羅蜜多,“要入般若波羅蜜多,乃得名為能到彼岸”,以“般若”為“六度”之首出。
2.空間方位譬喻。指以上、下、高、低、遠、近、深、淺等方位進行“譬喻思維”。在儒家經典中,《論語·陽貨》:“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論語·子張》:“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都是空間方位譬喻中使用“上”“下”進行譬喻的例證。針對《論語·子張》章,朱子注云:“下流,地形卑下之處,眾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污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于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朱子指出,《論語》中以“地形卑下”來譬喻人有污賤的行為的時候,那么惡名就都聚集在他那里。這種是典型的以“上”“下”為例的空間方位譬喻。
《孟子》中也出現這種“上”“下”的譬喻,孟子說:“水信無分于東西,無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人性本來就是傾向于善這一面的,這種傾向就好像水自然地會往下流一樣。沒有人要甘于不善,就好像沒有一種水是不往下流的一樣。孟子用水性之“自然就下”譬喻人之“性善”也是一種自然傾向。
佛教經典里面的“上”“下”譬喻就更多了,通常是指一個人經由修行而“生生增上”的這一類譬喻比較多。《雜阿含經》說:“如此人從地而起,得升于床;從床而起,得乘于車;從車而起,得乘于馬;從馬而起,得乘于象;從象而起,得升宮殿。”
講一個人求法修行的歷程,是由下而上的次第,一步一步往上精進。
3.容器譬喻。首先在中、日、韓各國儒家傳統中,人的身體常常被用來作為一種容器。身體是充滿并且展現人的道德修養或者是政治權力的一個場所,而且身體也可以含納社會規范,或者成為個人精神修養一種器物。《孟子·公孫丑上》中說“氣,體之充也”,這個“體”要來充滿“浩然之氣”。“浩然之氣”是什么呢?就是“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要用“義”與“道”來加以支撐,否則這個浩然之氣就會萎縮。而“養氣”充分了以后,就自然會表現在人的言談舉止與手足四肢之上,這就是孟子所謂“四體不言而喻”。公元六世紀時的皇侃著《論語義疏》,解釋“克己復禮”一語說:“言若能自約儉己身,返反于禮中,則為仁也。”就是說,我們閱讀經典,可以使“禮”(也就是社會規范與義理價值)含納到我們的身體里面,在這里顯然是將身體當作一種容器來進行“譬喻思維”。
佛教用身體作為容器的譬喻,可以說無量無邊。《大般涅槃經》道:“凡夫眾生,或言佛性,住五陰中,如器中有果。”人身好像一個器,有一個結果。《佛地論經》云:“世間有情于諳生處,諸根領納色等境界,故名受用,身有運轉,故名身業。”這顯然把身體譬喻為一種“器”,然后用這個器來譬喻“五蘊”,又稱“五陰”。“五蘊”是“色、受、想、行、識”,這種器的功能是領納“色”等外境到我們的“身”中。佛經常常將人的身體譬喻為一種“器”,而要求要領納這個“法”于身心之中。
這種“譬喻思維”在《論語》中也屢見不鮮。《論語·雍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論語》這一部書,最核心的關鍵詞就是“仁”。孔子討論“仁”的時候,并不是對“仁”下一個現代式的定義。孔子提醒他的弟子們要“行仁”,要把“仁”這個德行付諸實踐。至于實踐的方法則多種多樣。《論語·雍也》講到“能近取譬”,能夠從近的事物來取得譬喻的內涵,而想到遠的事物,這是“踐仁”與“行仁”的一種方法。孔子就以“瑚璉”這一種禮器來譬喻他的弟子子貢,《論語·公冶長》:“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子貢的德行可以做宗廟之禮器,禮器就是“瑚璉”。
四
本文以儒、佛經典所見的譬喻互作比較,可以提出以下幾點結論。首先,儒、佛兩者在譬喻的使用上都具有工夫論的色彩。不同于儒家經典中的譬喻常在“政治”脈絡中被運用,佛教經典中的譬喻則常在“修行”的脈絡中被運用。譬喻的作用猶如舟楫,亦如渡筏;猶如道路,亦如橋梁。言近而旨遠,以具體性悟入抽象性。儒、佛運用譬喻的根本目標是幫助經典閱讀者遙契圣人之心,于儒學或佛法獲得勝解,離苦得樂,優入圣域。
其次,譬喻之運用,是一種以故事敘事作為哲學思考之方式,即事而言理,道不離器,影不離形,言近而旨遠,并從具體性悟入抽象性,從“部分”悟“全體”。儒、佛“譬喻思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以譬喻承載不同的意涵,并通過譬喻,而對不同的學法之人或者經典的閱讀者“開權顯實”。這和西方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是不一樣的。儒、佛的智慧不是走亞里士多德式的論述方法,儒、佛走的是一種“譬喻思維”的道路,隨機點撥,皆成教法,達到華嚴哲學所謂“理事無礙法界”,這是儒、佛數千年來最深刻而偉大的智慧。
從儒、佛經典中的“譬喻思維”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的啟示:譬喻的運用,是一種以故事的敘述作為哲學思考的方式。“來源域”通常是比較近、比較具體,可是這一個“來源域”是指向一個比較遠的比較抽象的“目標域”,像看到“山”、看到“水”,就想到“仁者”、想到“智者”;看到“筆硯”就想到“文臣”,看到“甲胄”就想到“武將”等。這是一種儒、佛共通的思維方法,以“言近而指遠”為其特征。用現代的語言可以說,“譬喻思維”是從“具體性”涉入“抽象性”,從“部分”來掌握“全體”的一種思維方法,最具有東方文化的特色。因此之故,今日我們研閱儒、佛經典,不應耽溺在經典多種多樣的譬喻之中,以致玩物喪志,而應該將經典中的譬喻視為津渡或橋梁,經由譬喻而攀登儒、佛經典所揭示的精神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