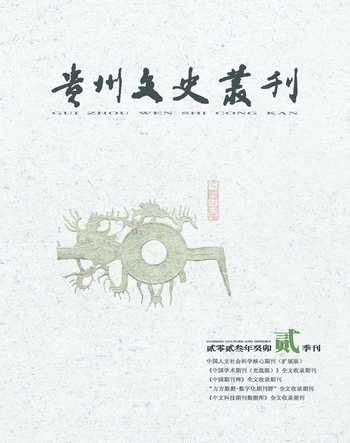歷史時期云南境內的馬種演變與壩區農業轉變
耿金
摘 要:元代以前歷史文獻中多記載云南境內盛產善于奔跑的名馬,從漢代文獻中的“滇池駒”到唐宋時期的“越賧驄”“大理馬”,皆為體型俊美之騎乘馬匹。元明以后,文獻中記載的“云南馬”以善行山路、馱物為主,并最終形成明清時期對云南馬的認知形象。馬種的交替演變,背后的原因是云南壩區農業生產方式在元代以后發生根本性轉變,即壩區由元代以前的畜牧、農耕并重,到元明后以農耕為主,飼養良馬的土地資源農田化,此過程也伴隨著壩區飼養馬匹的民眾因農業生產方式的差異而向山區轉移。農耕經濟對于馬匹役力的使用更強化其馱物功能,故體型略小的“云南馬”在元明以后成為云南地區的主要役力馬種。這一過程隨著清代農耕向山區推進而形成“云南馬”在山區使用普及化,由此改變了云南馬種的分布格局。
關鍵詞:滇池駒 越賧驄 大理馬 云南馬 壩區農業
中圖分類號:K825.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8705(2023)02-34-42
一、引言
元代以前,許多歷史文獻中都有云南地區盛產名馬的記載,無論是漢代的“金馬”形象,還是唐代樊綽《云南志》中記載的可日行五百里的“越賧驄”,以及宋廷曾向大理購買馬匹作為戰馬的記載,都說明歷史上云南地區曾經出產過名馬。這種名馬以“善奔跑、體健碩”而著稱,在云南地區乃至西南地區歷史上的經濟社會發展變化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元代以后,云南地區的名馬記載就較少出現了,被史料記載的馬匹多是體格較小,善行山路,主要用于搬運物資的役力家畜。那么,是云南地區馬匹品種的基因發生了轉變?還是這種名馬自我消亡了?回答此疑問即為筆者撰寫本文之原因。經過閱讀有關史料,筆者認為,這種變化還不能完全從動物自然種群演變史的角度進行解釋,而需要關注其背后農業生產方式轉變的進程、內在驅動因素,以及地方民眾馴養情況等多重因素。
從考古學、歷史學方面研究的成果看,早期云南境內的馬匹品種并非明清時期西南地區普遍使用的小馬。張增琪從考古學的角度進行研究,論證了云南境內早期馬種與北方草原馬種的關系密切;李曉岑對唐、宋時期的云南馬種進行了研究,認為當時云南地區商人販賣給宋廷的馬匹基本為西蕃馬。1但是,已有的研究并未對元代以后云南馬匹為何變化的問題進行討論。除歷史學者的研究外,動物學主要關注歷史上云南境內馬匹的種屬問題,認為歷史上云南地區的馬種是一種中等偏小、具有許多原始性質的單獨馬種。1此外,一些研究者將云南地區的馬種納入到“西南馬”的范圍,并認為“西南馬”有多個母系起源,且與蒙古馬親緣關系較近,部分西南馬起源于普氏野馬或蒙古野馬,2等等。總體而言,已有研究成果大多并沒有解釋歷史上云南馬匹演變的細微過程以及背后的深層原因。對云南壩區農業轉變的歷史過程,仍缺少對其細致轉變過程的研究與展現。本文通過對歷史上云南典型馬種的長時段演變考察,分析云南農業發展史、區域經濟與社會演變史、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史,以期為學界的深入研究提供參考。
二、元代以前的高原名馬
(一)滇池及周邊地區的“滇池駒”
目前所見,歷史文獻中記載的云南地區最早的名馬稱“滇池駒”。“滇池”一詞最早出自《史記》。《史記·西南夷列傳》中記載了古滇國位于滇池之濱,乃楚國將領莊蹻率兵進入滇池流域后,收服整合而成,“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3。而春秋戰國時期的滇國大致到東漢后期就從滇池流域“消失”了。張增祺言:“滇國出現的時間不晚于戰國初期,戰國末期至西漢早期為其鼎盛時期,西漢中期以后開始衰落,西漢末至東漢初在云南歷史上逐漸消失,東漢中期以后滇國已完全銷聲匿跡了。”4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后云南的歷次考古發掘中,春秋戰國時期的滇國逐漸被世人所了解,出土了大量文物,諸如“滇王金印”等,印證了司馬遷記載的可靠性。而在出土的大量古代文物中,馬的形象是比較多的。在兩漢時期的歷史文獻中,也多次出現滇池流域盛產名馬的文獻記載。如東漢光武帝時期,漢廷派劉尚攻打益州郡少數民族頭領棟蠶,獲得馬三千匹;又如《華陽國志·南中志》中記載,諸葛亮平定南中后,令當地提供“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國之用”5。從這些史料中可以看出,歷史上的云南不僅盛產馬匹,而且盛產戰馬。在春秋戰國時期的歷次考古發掘中,云南各地出土了大量鑄有馬匹的青銅器,這些馬匹多數出現在當時的戰爭和狩獵場景中。春秋戰國時期,云南的不少地方都有馴養馬匹之風,在江川李家山墓地中出土一件貯貝器,蓋子上就有馴馬場面,在同一地方出土的青銅器中,還有諸多馬具等。此外,此地出土的戰國時期馬具從制作工藝上看還相對原始,沒有出現絡頭和馬銜等裝飾配件,青銅器圖像中的乘馬人手中有韁繩,但是直接系在馬口中,馬背上也沒有鞍件,僅有較長的坐墊。到了西漢中期,漸漸出現了變化,馬具開始逐漸完善,有額帶、鼻帶、頰帶和咽帶皆備的絡頭,還出現銜、鐮、鏑組成的馬銜,以及鞍墊、攀胸、后鞦、腹帶齊備的馬鞍和相應的帶扣、策子等銅質飾件。進入西漢中晚期后,出現了馬的防護用具“面簾”和“當胸”。同時,在西漢中期,云南境內一些地方的戰馬上已普遍使用馬鐙。在云南發現西漢中期青銅器上的馬鐙圖像,是目前我國也是世界上發現的最早和最原始的馬鐙。張增祺認為,云南早期的居民多騎馬而不乘車,馬具中的攀胸、后鞦齊備的馬鞍與馬鐙都是由當時居住在山地的民族發明的,后來才逐漸向平原地帶推廣。1因此,早期云南境內的馬匹,更多是以作為乘騎之用的戰馬形象出現的。
由上述可知,早期云南地區的馬匹主要作為乘騎之用,以擅長奔跑為主要特點。《華陽國志》中記載了日行五百里的滇池駒:“池(滇池)中有神馬,或交焉,即生駿駒,俗稱之曰‘滇池駒,日行五百里。”2酈道元《水經注》中記載為:“池中有神馬,家馬交之則生駿駒,日行五百里。晉太元十四年,寧州刺史費統言:‘晉寧郡滇池縣,兩神馬一白一黑,盤戲河水之上。”3受此影響,唐代以后的歷史文獻幾乎都記載為“神馬與家馬交,則生駿駒,世稱滇池駒。”4這些記載正如任乃強先生所說,是民間神話傳說,但神話傳說的背后也折射出滇池良好的水土環境為出產良馬提供了自然條件。《南中志》載:“夫馬、龍異類,不可能媾交,何得云龍駒?只緣河湖岸草美,而風浪能激勵馬志,故成良馬種也。”5言下之意,滇池邊的馬匹因當地水草豐美,加之風浪之故,所以能成為優良品種。而滇池流域的“金馬碧雞”神話傳說,也說明當地確實曾經出產過名馬。
(二)越賧驄與大理馬:唐宋時期的云南名馬
唐宋時期,云南地區的馬匹不僅十分有名,而且在當時的軍隊中大量配備,樊綽在《云南志》6中有如下描述:
馬出越賧川東面一帶,崗西向,地勢漸下,乍起伏如畦畛者,有泉地美草,宜馬。初生如羊羔,一年后紐莎為攏頭縻系之。三年內飼以米清粥汁。四五年稍大,六七年方成就。尾高,尤善馳驟,日行數百里。本種多驄,故代稱越賧驄。近年以白為良。藤充及申賧亦出馬,次賧、滇池尤佳。東爨烏蠻中亦有馬,比于越賧皆少。一切野放,不置槽櫪。唯陽苴哶及大釐登川各有槽櫪,喂馬數百匹。7
越賧,又名騰越,在永昌以西,過高黎貢山而后至。唐代稱敕化府,宋代改為騰沖府。8當時的這種良馬主要產于騰沖以東地區,多為雜毛馬,這種雜毛馬稱“驄”,《說文》言:“驄,馬青白雜毛也。”9從歷史文獻看,這是一種毛色黑白相間的馬匹。除瀾滄江以西的騰越地區以外,滇池流域的馬匹質量也很好。當時云南境內的馬匹幾乎都是野外放養狀態,不設馬槽,半野生,只是在大理洱海周邊地區有設槽圈養。這表明在當時的云南,不僅有許多地區產良馬,而且不少壩區有大片野生草場。
到了唐代,云南地區擅長馴養馬匹與騎馬的族群主要是“望苴子”。《云南志》載:“自瀾滄江以西,越賧、撲子,其種并是望苴子。俗尚勇力,上又多馬。”10《云南志》對“望苴子”的情況有詳細記載:“(望苴子)在瀾滄江以西,是盛羅皮所討定也。其人勇捷,善于馬上用槍,所乘馬不用鞍。跣足衣短甲,才蔽胸腹而已。股膝皆露。兜鍪上插犛牛尾,馳突若飛。其婦人亦如此。南詔及諸城鎮大將出兵,則望苴子為前驅。”1筆者從史料中對比分析發現,這種跣足騎馬形象與云南省博物館中的青銅騎馬形象十分吻合。因此,如此質地優良的馬匹自然會被資以軍用。木芹言:“南詔常備軍中有精兵,望苴子為其中之突出者。”2從歷史文獻看,在當時的軍隊中,馬軍是必備的配置,而這些馬軍基本上是寓兵于農,官府不負擔軍隊開銷,遇有戰事則征召參戰。《云南志》卷九言:“戰斗不分文武。無雜色役。每有征發,但下文書與村邑理人處,克往來月日而已。……每家有丁壯,皆定為馬軍,各據邑居遠近,分為四軍。以旗幡色別其東南西北,每面置一將,或管千人,或五百人。四軍又置一軍將統之。”3歷史文獻中記載“每家有丁壯,皆定為馬軍”,在《新唐書·南詔傳》也有類似記載“壯者皆為戰卒,有馬為騎軍”4,即有馬匹的人家可作為馬軍。木芹先生認為,這些軍隊其實由三部分組成:一是常備軍,數目不多,但卻是主力,人數大概常年在三萬左右5;二是寓兵于農部分,平時農耕,并以村邑為單位,以戰時的方式編制起來,農閑加以訓練;三是征調軍,被征服的邊境部族,以開南、麗水及永昌三節度為多,諸如撲子、尋傳、黑齒等。6“望苴子”既尚勇,當地又多良馬,所以成為當時軍隊中的主力。
據史料記載,在當時的軍隊中,馬軍的攻擊力是很強的,訓練也極為苛嚴,既要求熟悉射箭、弄刀、耍槍,還要能記算書寫。在當時的城鎮乃至鄉邑,大都會在空地上立一柱子,農閑時有馬的人就會騎馬圍繞柱子練習刺殺,“每農隙之時,邑中有馬者,皆騎馬于頗柱下試習”7。每年十一、十二月農忙后,兵曹長就帶著文書巡查其境內諸城邑村谷,“各依四軍,集人試槍劍甲胄腰刀,悉須犀利,一事闕即有罪。其法一如臨敵。布陣羅苴子在前,以次弓手排下,以次馬軍三十騎為隊。如此次第,定為常制。臨行交錯為犯令”8。
到了宋代,雖然史料文獻記載較少,但仍有不少中原地區與大理進行馬匹交易的記載。比如,北宋由于有北方遼國的軍事威脅,一直在各地大量購買馬匹用作戰馬,以提高其軍隊的作戰能力。宋廷購買的馬匹主要有兩種,即戰馬與羈縻馬,戰馬主要從陜西、四川、廣東等地購買,而羈縻馬主要產自西南地區,體格短小。9《宋史》載:“故凡戰馬,悉仰秦、川、廣三邊焉。”10北宋時的軍隊戰馬以西北馬最多,其次為川西的馬;南宋以后,陜西馬來路斷絕,所依賴者,川馬、廣馬為主要。11宋代洪邁言:“國家買馬,南邊于邕管(治今廣西南寧),西邊于岷、黎,皆置使提督,歲所綱發者,蓋逾萬匹。”12但由于山路崎嶇,在四川購買的戰馬數量沒有在南邊的兩廣購買的多。據相關史料顯示,宋廷在這兩個地方購買的馬匹,其實大都來自云南。周去非在《嶺外代答》提出,南方諸馬“皆出大理國,羅殿、自杞、特磨,歲以馬來,皆販之大理者也。”1《玉海》也載:“今之買馬多出于羅殿、自杞諸蠻,而自彼乃以錦彩博于大理,世稱廣馬,其實非也。”2這兩條記載,是比較可信的,不僅如此,在這些記載中,還列出了來自大理的馬匹與兩廣本地所產馬匹的區別,稱廣馬出自嶺南者,體格較小,質量不佳,“嶺南自產小駟,疋直十馀千,與淮、湖所出無異”。因此,在市場上交易量價均高,頗受購買者青睞的,更多是質量較佳的大理馬。在當時,大理馬也被稱為“西馬”,文獻史料記載:“大理連西戎,故多馬。雖互市于廣南,其實猶西馬也。每擇其良赴三衙,馀以付江山諸軍。”3從當時的情形看,產自云南的馬匹是直接可以選配到軍隊里的。
宋代云南地區出產的馬匹被視為西南諸馬中的上品,在不少歷史文獻中都有記載,如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就曾提到過大理馬:“出西南諸蕃,多自毗那、自杞等國來。自杞取馬于大理,古南詔也。地連西戎,馬生尤蕃。大理馬,為西南蕃馬之最。”4周去非也曾對當時的南北方馬匹的特點有過評價,他說:“南馬狂逸奔突,難于駕馭,軍中謂之拼命抬。一再馳逐,則流汗被體,不如北馬之耐。”5從整體上看,南馬狂逸奔突,不好駕馭,而且奔跑后容易出汗,耐力不如北馬。但如果遇到南方馬中質量較優者,則北方馬又不可能與之相比,“然忽得一良者,則北馬雖壯,不可及也,此豈西域之遺種也耶?是馬也,一匹直黃金數十兩,茍有,必為峒官所買,官不可得也”6。以此觀之,當時大理的越賧所產馬匹,被認為是南方馬匹中的上品,當地人也將其稱為“座馬”,“座馬,往返萬里,跬步必騎,駞負且重,未嘗困乏,……日馳數百里,世稱越睒駿者,蠻人座馬之類也”7。從以上史料上看,越賧所產之馬,在當時不僅價格昂貴,而且耐力極好,頗受當地人喜愛。
三、元明以后的云南馬匹形象
元代以后,西南地方文獻中關于唐宋時期“名馬”的記載似乎就一下“消失”了。明清時期文獻中記載的云南馬,更多是體型較小、善于奔走山路的馬匹。這讓不少人產生疑惑,為何同樣產于云南的馬,在唐宋時期以善于奔跑見長,到了明清以后卻變成了以善馱運見長呢?通過查閱資料和實地了解,筆者認為,云南地區明清時期以善于馱運見長的馬匹與唐宋時期以善于奔跑見長的馬匹并非同一品種。對此,研究云南馬匹歷史的學者較少有過關注,一般都將早期文獻中記載的滇池駒、越賧驄與后期的西南馬皆視為云南馬。為了不致引起敘述上的混亂,本文將史料所載元代以前善于奔跑的馬匹以本名稱呼,如“滇池駒”“越賧驄”“大理馬”,而將明清以后體型較小、善于山路行走的馬匹稱作“云南馬”,明清以后的文獻所記載的,多是這種善行山路、體型較小的馬匹。
到了元代,馬可波羅從滇池(鴨池城)地區向西騎行十日后到達大理城,他在此行的《行紀》中曾提到,云南洱海流域有一種體形高大的駿馬。當時的大理城屬“哈剌章州”(即明清時期的大理府),馬可波羅到達該州后,在其記載中是這樣描述的:“亦產良馬,軀大而美,販售印度。然應知者,人抽取其筋二三條,俾其不能用尾擊其騎者。尚應知者,其人騎馬用長騎(montent long)之法,與法蘭西人同。”1其中所提到的“抽取其筋二三條”的養馬習俗,正是當地人為了讓馬尾高高翹起而使用的方法。而《云南志》中提到的越賧驄,也是尾高而“尤善馳驟”的。以此觀之,《云南志》和《馬可波羅行紀》中關于大理駿馬的體形描述是很一致的。有學者針對《馬可波羅行紀》中所記馬匹體型描述,指出:“‘大而美之馬,疑為傳寫之誤。廣西高地及云南省中固產健馬,然其軀小而健,故玉耳以為其文應改作多數之馬。”2這種說法或許并不準確。由以上史料可知,元代以前,云南境內的馬匹雖然整體上不如北方馬高大,但體格不算小,而且善于奔跑,完全不是后來有的資料中所指的那種明清時期的體型矮小、善行山路的“云南馬”。認為馬可波羅所見“驅大而美”的馬是記載錯誤,其實是對當時馬匹認知的錯位。
筆者查閱有關史料,歷史上云南境內的馬匹有多個亞種,在動物學分類上將其統稱為“西南馬”。但即使在“西南馬”種屬內,也存在兩種明顯不同的馬種,可能是由于稱呼上的習慣,有的學者將這兩種馬混為一類,將歷史上云南地區的馬匹種類皆視為“西南馬”。李曉岑曾提出,唐宋時期云南境內的“大理馬”屬于西北馬種,并非當時西南地區軀干矮小的“羈縻馬”。“大理馬”不僅軀體高大,當時經常被用作戰馬,還通過貴州等地輸送到廣西市場上出售,成為宋王朝重要的馬匹來源。3這一觀點筆者是認同的,但李曉岑并未解釋宋代以后云南的馬匹為何變成了“羈縻馬”。對此問題,筆者通過分析研究認為,唐代的“越賧驄”、宋代的“大理馬”,都是云南馬的另外品種。動物學的研究也顯示,騰沖境內的騰沖馬應該即為唐代的“越賧驄”后裔,這種馬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調查中還顯示有明顯的草原馬種特征,馬匹體格粗壯結實,頭比較大,體軀較深廣,腹部膨大,四肢粗實,關節明顯,健肌發達。4從目前對云南境內的名馬記載看,漢代至元代是一個連續性階段,而元代以后,這種名馬就逐漸減少了。
明代文獻中仍有提到過這種善于奔跑的馬,不過從馬匹活動區域上看,應當是集中到了滇東的陸良地區。正是由于馬匹活動區域的轉移,歷史上出產駿馬的滇池流域和大理地區,就很少再出現這種善奔跑的名馬的記載了。因此,有關歷史文獻只有在介紹陸良地區民間風俗時,才會提及此種馬匹。有明一代,陸良壩區一直是云南良馬的產地,這是因為當時的陸良壩區有大片的湖泊水域,據景泰《云南圖經志》記載,陸良壩區有被稱為“中埏澤”的湖泊水域,“中埏澤,在州治(陸良州)東丘雄山麓,寬衍六十馀里,有一十八泉注其中,而瀟湘之水5亦入焉。魚蝦甚富。其傍地為牧馬場,而所產多良馬,亦其土地之所宜也”6。這一水域為陸良的馬匹生長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條件。明清以降,隨著當地湖水的逐漸干涸,這種養馬的自然條件逐漸消失了。明代的陸良壩區,是漢族和少數民族共同生活居住的地區,但存在少數民族向山區轉移的趨勢,當地世居的少數民族在史料上多被稱為“羅羅”,當時他們的人口數量占當地人口的絕大多數,他們“居止多在深山,雖高岡磽垅,亦力墾之,以種甜、苦二蕎自贍。又以畜馬為生,牧養蕃息,剔去尾骨二節,謂之雕尾,以此為貴。刻木為鞍而無?,剜木為鐙,狀如魚口”1。此種“風俗”在萬歷《云南通志》中又被原樣記入。2明代的陸良地區與唐宋時的大理地區在養馬方法上基本沒有變化,仍習慣“剔去尾骨二節”。沾益、陸良周邊的民眾與劍川地區的民眾均以養馬為生,在馬的馴養方式上也完全相同。史料記稱劍川山后的民眾“尤為獷悍……與沾益州同俗”3。
在元代及以前的文獻中,我們更多關注的是善于奔跑的馬匹,以“滇池駒”“越賧驄”“大理馬”為主,不太留意善于行走山路的馬匹,這當然是文獻記載的偏向導致的,但文獻記載偏向善奔跑的名馬,證明這種馬無論是在飼養數量還是在利用上,在當時都是很重要的。對后一種馬匹,其實漢代文獻中早有記載,以“筰馬”為代表,只是長期沒有成為文獻記載的重點。《漢書》載:“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筰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4“筰馬”今稱“西昌馬”,軀干較蒙古馬、西寧馬為小,善走山地。5明清時期,這種馬匹在云南山區極為普遍,是山區民眾的主要畜力。在明清以降的歷史文獻記載中,云南境內的馬匹基本上被描述為整體體型矮小,多以“馱馬”出現,善于在山路負重行走。清初劉崑在《南中雜志》中言:“滇中之馬,質小而蹄健,上高山,履危徑,雖數十里而不知喘汗,以生長山谷也。上山則乘之,下山則步而牽之,防顛踣也……上下山谷,皆任騎坐,則百不得一也。而其中又有高大神駿,遠過西馬者,則千不得一也,此種異物,甚為土司所珍,亦甚為土司之累。”6這些歷史文獻記載讓人覺得,云南境內體型較小之馬較多,高大良馬少見。
到了晚清,相關歷史文獻記載中的云南馬,也更多為小馬形象。清末,日本學者鳥居龍藏在云南、貴州考察,在貴州他記錄了當地的馬匹情況:“然貴州、云南所產馬匹,遺傳下古時苗族飼養的特殊能力而不同于普通中國馬匹,這在中國舊方志上也屢有記錄。直到現今,山區的苗族仍都利用馬匹,最適應山間行走。”7“途中與數十匹馬群相遇,僅幾名馬夫帶領,一聲吆喝便都自己行走,頗馴服。一眼看去馬匹非常溫馴,與日本馬大相徑庭。這些馬匹均為馱馬,用于云貴之間的貨物馱運。我曾讀過一些關于中亞或云南周邊的旅行記,知道這些馬的存在。然第一次親眼目睹,卻是在此次旅行中。”8進入云南后,鳥居龍藏對云南府市場上交易的馬匹印象深刻,他說:“(此種馬匹)為云南特有之物產,在中國歷代文獻中,皆記載過去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多飼養馬匹之事,然至今仍普遍飼養。這些馬相比山西馬稍小,較驢大,且性格溫馴,最適合旅行騎乘。無論多么崎嶇陡峭的山路,只要騎上它,就可以通行無阻,可謂是奇珍異寶。”9這些記錄說明,馬匹在當時西南山區民眾的生產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旅行中,鳥居龍藏也多次稱贊了云南馬在山區的行走能力:“山路極險峻,坡面陡急,路邊到處都橫躺著滾下的石頭。在如此崎嶇險峻的山路上,我仍然騎馬而行。并非因自己騎術高超,而是騎乘為云南馬,日本馬是不可能在此攀援的。”10當然,鳥居龍藏記錄中所提到的這種清代西南馬善走山路,與唐宋時期的名馬有所不同。
四、壩區農耕化與役用馬匹的轉變
如上所述,云南歷史上元代以前記載的高原“名馬”,并非明清以后善于行走山路、體型矮小的云南小馬。從馬種上看,前后兩種馬并不存在種群進化關系,各自屬于不同的品種。元代以前云南農業經濟中主要是畜牧業,特別是平壩地區的畜牧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所畜養的馬匹更多被騎乘之用,文獻中所記載的也更多是這種善于奔跑的名馬形象;明代以后,云南文獻中被記載的善走山路、以馱物為主的小馬,其實是另外一種云南馬,上文中所提及的《漢書》中記載的“筰馬”就基本屬于此類馬種。出現這種馬種上的“轉變”,筆者認為,這與元代以后云南的農業經濟轉型有極大關系,隨著壩區農耕環境變化,加之人們對馬匹使用的偏向發生轉變,導致歷史文獻中前期更多記錄的是善于奔跑的高原名馬,而后期更多關注的是善于在山間行走、以馱運見長的云南小馬,即人們對馬匹役用重心的轉變與農牧環境的變化,引起了云南馬匹種群的演變。當然,這種演變并不是指馬匹種群的自我進化,而是由于人們農耕方式與役用馬匹的重心轉變而導致早期善奔跑的馬匹在數量與分布區域上,逐漸縮減甚至是消失了。
元代以前,云南的壩區由于水草條件良好,但農業耕種技術尚未普及,所以民眾大多以畜牧業為生,馬匹是其馴養的主要品種,而且這些馬匹大多數是野外放養,這種優良的畜牧環境,為宋代云南境內馬匹大量進入中原地區奠定了基礎。元代以后,更多先進的農業耕種技術逐步從中原、江南等地傳入,使當地的農業生產模式發生了根本性轉變。
這種生產模式的轉變首先是從滇中、滇東的壩區開始的。以“海”或“海子”的命名為例,這種稱謂最早出現在元代以前的北方地區,1后來卻在云南地區廣泛使用,筆者結合相關史料分析,基本可以肯定,這是大量北方地區的漢族人口進入云南地區從事農業耕種的結果。因此,云南壩區的眾多湖泊,逐步開始以“海”或“海子”命名。到明代以后,這種命名方式已成為了本地的習慣。明代天啟《滇志》中載:“滇俗,潴水處皆稱海子。”2筆者在國家地名信息系統中檢索以“海子”命名的地名,共有四千三百九十五條,其中云南省就有一千五百九十二個,其次是四川省八百一十一個,貴州省五百八十四個,內蒙古自治區三百三十三個,陜西省一百七十六個,山東省一百五十八個,甘肅省一百四十一個,寧夏回族自治區一百一十八個,其馀各省區數量則在個數至數十個不等。從分布地區看,西南“海子”最多,幾乎占到三分之二,尤其以云南最多。在云南境內,“海子”地名主要分布在曲靖市(五百七十九個)、昭通市(三百九十九)、昆明市(一百六十五)、大理州(一百一十九個)、楚雄州(一百一十八個)、文山州(五十三個)、麗江市(三十八個)、保山(二十六個)、普洱市(二十六個)。3可見,云南稱“海子”的地名集中在滇東、滇中及滇西大理、麗江附近。而明代軍事屯墾移民主要集中在壩區,這進一步推進了壩區農耕化進程。而云南南部的傣族先民聚居區,卻很少有以“海子”命名的。
五、結語
綜上,推動歷史時期云南馬種交替演變的,有以下驅動因素:一是壩區由畜牧業逐漸向農耕轉變,農耕與畜牧飼養馬匹形成了資源競爭關系;二是畜牧業向農耕轉變后,對于馬匹使用的定位也出現了轉變,即從用于騎乘向用于馱物轉變。此外,農耕向山區推進,也加速了山區矮小的“云南馬”的普及化,最終形成元代以后,云南馬種利用上的交替演變。元代以前,云南境內的壩區雖有一定范圍的水田農耕,但在農田周邊有大范圍的牧草地帶,這是當時云南境內畜牧業的重要資源;元代以后這種情況急劇變化,特別是明代的移民屯墾主要集中在壩區,使壩區農耕化程度進一步提高。本質上看,元代以前云南境內以畜牧業、農耕業并重,甚至在滇東、滇中、滇西的大片壩區,畜牧業占主導;元代以后隨著壩區農業的開發,明清時期漢族移民的大量進入,確實存在農耕上山的問題,這與前期的山區水田化背景的內在機制有所不同。對于云南境內的土地利用問題,元代以后的壩區農耕化,也直接導致了壩區畜牧資源被壓縮,使得元代以前善于在壩區奔跑、飼養的名馬,到明代以后逐漸讓位于役力使用的馱馬,即所謂善于行走山路、善馱重物的馬匹成為云南馬的典型代表。
The Evolution of Horse Speci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lain Agriculture in Yunnan during the Historical period
Geng Jin
Abstract:The most of the documents before the Yuan Dynasty recorded that Yunnan was rich in famous horses that were good at running, from the "Dianchi Ju" colt in the Han Dynasty to "Yue Dan Cong" and "Dali Horse"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After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Yunnan horses recorded in the literature were mainly "Dian horses", which were mainly good at walking in mountain roads and piggybacks, and finally formed the cognitive image of Yunnan horse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The core factor behind the alternating evolution of horse species is the fundamental change in the mod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the dam area after the Yuan Dynasty, that is, from animal husbandry and farming before the Yuan Dynasty to farming after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and the land resources of raising good horses are turned into farmland, and this process is also accompanied by the transferring of ethnic minorities who raise horses in the plain areas to the mountainous areas because of different farming methods.The farming economy put more emphasis on the burden function of horses, so the smaller "Yuannan horse" became the main service horse breed in Yunnan after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This process promoted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use of "Yuannan horse" in the mountain areas with the advance of farming to the mountainous areas in the Qing Dynasty, which further strengthened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Yunnan horse breeds.
Key words:Dianchi Ju;Yue Dan Cong;Dali Horse;Yunnan Horse;The Plain Agriculture
責任編輯:張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