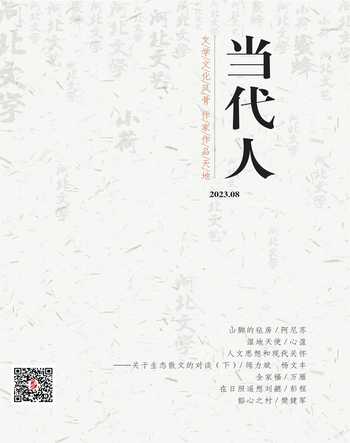童年視角下的創傷與無法拒絕
“生活不是我們活過的樣子,而是我們記得住的樣子。”加西亞·馬爾克斯如是說。沒有哪個作家的寫作之路不受童年記憶的牽絆,而作家對童年的獨特體悟也時常成為他們找尋靈感的重要源泉。在袁予諾的短篇小說《雄雞唱暮》中,身為寫作者的“我”正是選取了童年視角來表達一個關于童年、創傷與拒絕的故事。
雖然“我”在開篇直陳《雄雞唱暮》的文本是一份寫鄰居老王的人物作業,小說卻首先呈現了敘事設置上的精巧。故事以“我”(小鹿)作為第一人稱限知視角,通過牽引一明一暗兩條敘事線索,架構了一個從1976年唐山大地震到21世紀20年代的當下、跨越近五十年的敘事空間。
以“我”出發的敘事明線,從“我”八歲到二十多歲,共分為三個時間層次:第一層是八歲的“我”所在的時間線,講述了“我”從對年逾七十的鄰居老王心懷恐懼,到發現老王性格古怪的秘密,并從情感上逐漸走近老王,與老王的創傷深度共情的故事。在此層次中,小說從八歲“我”的主觀視角出發,對無憂無慮的童年生活、復雜微妙的親子關系以及城市化進程給“我”的生活和心理造成的影響進行了忠實的還原與講述。第二層是成長為一名寫作者的“我”站在二十多歲的當下再次回憶起老王,同時也以一個成年人的視角回望八歲時的自己和那個已經略微有些遙遠的21世紀初,隱藏在八歲“我”的身后書寫著時代的發展變遷、人與人的離合聚散。第三層是文本中點到即止的“成長中的日日夜夜”,說明“我”經常懷著思念和祝福的心情想起老王,起到了增加敘事明線層次感的作用。
以老王出發的敘事暗流,則是從1976年唐山大地震發生到“我”搬離小區的21世紀初,跨度三十年,凝縮了一對因地震痛失多個孩子的夫婦從中年走到暮年的生命歷程,探討了命運的無常以及受傷的人怎樣帶著創傷活下去。在明暗兩條敘事線組成的立體式敘事結構中,作者寫出了創傷的代際傳遞過程,大地震帶來的傷痛不只落在老王一個人的肩上,這些傷痛屬于所有唐山人甚至所有河北人、中國人,成為一個地區的集體創傷記憶,乃至傳遞到年幼的“我”的心頭。同時,立體的敘事結構還容納了作品多義的主題,使得小說觸及了災難與創傷、青春與衰老、誤解與隔膜、城市變遷與故土情懷等諸多哲理向度。
老王的人物形象也在上述敘事空間中得以呈現。作者采用了剝洋蔥式的塑造手法,通過八歲“我”的限知視角,對老王的不同側面進行精準描寫。在“我”眼中,老王從一開始外表病弱衰老、性格高深莫測、家庭關系冷淡,遭受了因大地震青年喪子的不幸命運,到他對鄰里尤其是孩子的默默關愛,再到其奮不顧身從人販子手中救“我”的壯舉,老王的形象逐漸從一個令“我”不愿靠近的怪老頭兒變成了一位令人同情、尊敬和牽掛的長輩,也從肉體的弱者變成了內心充滿善意與溫暖的精神強者。
在形象不斷完整的過程中,老王本人依然孤獨而沉默,沒有什么機會袒露心聲,這也讓讀者不禁想要探究真實的老王究竟是什么樣的。與此同時,作者給老王安排了一只寵物大公雞作伴,它強悍、漂亮、勇敢、有教養,與垂暮、干癟的老王形成了反差但也是一種“對影”,小說題目“雄雞唱暮”也正是老王內心的象征。此外,幼小而生機勃勃的“我”也與行將就木的老王形成了第二重對照。作者精準把握住了兒童對老年人的恐懼,這是充滿無限可能和未來感的年輕生命,對活在創傷之中、散發著腐朽氣息的遲暮生命的誤解,也切近了世人對死亡的恐懼和回避,甚至我們可以理智而殘忍地推斷出在“我”寫出這篇文章的當下,老王很難還在人世。幸而還有“雄雞唱暮”,這是作者的情感選擇與道德立場,也是給讀者的莫大安慰。
在創傷與生死之外,作者還用孩子式的、戲謔幽默中帶有憂傷的筆調寫出了“我”與生俱來的敏銳與個性。作為一名在城鄉接合部跟著爺爺奶奶快樂成長的留守兒童,“我”的內心深處十分抗拒離開老舊小區到城里的新家去生活,這對幼小的“我”來說無異于一種連根拔起。但面對家庭遷移這種大事,孩子的抗拒和反抗幾乎是無效的。在祖輩、父輩懷抱著喜悅的心情為即將進城不停忙碌時,“我”和“我”心中悲傷、不舍的情緒被“非刻意”地無視了。樂景哀情之下,“我”不被理解、不被尊重的心聲叛逆而獨特,此刻哪怕是真心關愛的人之間也會產生隔膜的現實也顯得有些心酸。這是有些人比如老王終究會被時代的列車拋下的殘酷真相,也是城市文明對鄉村文明龐大的籠罩。
(李碩,石家莊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副秘書長,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碩士,主要從事中外現當代小說、敘事學等領域的研究和文藝評論,評論散見于《人民日報(海外版)》《文藝報》《中國藝術報》《河北日報》、光明網、中國作家網等。)
編輯:? 耿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