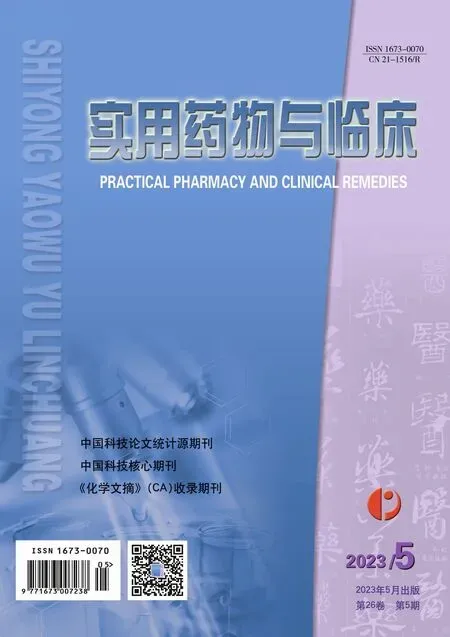1例卵巢癌伴復發性抑郁障礙患者的用藥思考
師亞玲,李 茁,葉軼青
0 引言
卵巢癌是病死率最高的婦科惡性腫瘤,目前卵巢癌的首選治療模式為腫瘤細胞減滅術聯合以鉑類為基礎的化療[1-3]。據報道,在初始治療或鉑敏感復發治療獲得完全緩解和部分緩解后,應用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poly ADP ribose polymerase,PARP)抑制劑維持治療可顯著延長卵巢癌患者的無進展生存期[3]。目前,奧拉帕利、尼拉帕利作為PARP抑制劑已廣泛應用于臨床[4]。惡性腫瘤患者由于術后需長期放化療,導致負面情緒產生,增加了并發抑郁障礙的可能性。治療抑郁障礙的藥物有氟西汀、舍曲林、帕羅西汀等,臨床治療通常需要多藥聯合長期服用[5]。對于卵巢癌并發有抑郁障礙的患者,可能需長期使用PARP抑制劑和抗抑郁類藥物。目前,已有研究證實,部分藥物聯合使用可以通過競爭CYP3A4等代謝酶,導致藥物在體內的血藥濃度發生變化,產生療效增強或者療效減弱甚至治療失敗[6]。針對卵巢癌并發抑郁障礙的患者,PARP抑制劑與抗抑郁類藥物的聯合使用是否產生藥效學之間相互影響,以及對兩種疾病的發展轉歸是否有影響目前尚不明確。本文通過對1例卵巢癌伴復發性抑郁障礙患者的病例進行分析,探討PARP抑制劑與抗抑郁藥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對患者疾病轉歸的影響。
1 病例資料
患者,女,52歲,身高158 cm,體重58 kg,2021年12月1日因“卵巢癌根治術后4月余,要求第6次化療”收治于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婦產科醫院,診斷為卵巢惡性腫瘤IIIC期(高級別漿液性癌)術后、復發性抑郁障礙、睡眠障礙。患者2021年7月行卵巢腫瘤細胞減滅術,為R1理想減滅,術后行5次紫杉醇聯合卡鉑3周療法的化療方案。患者既往有睡眠障礙、復發性抑郁障礙病史15年,現口服坦度螺酮片10 mg/d、帕羅西汀片20 mg/d、氯硝西泮片2 mg/d、米氮平片30 mg/d,現病情穩定。
本次住院第1天,患者一般情況良好,輔助檢查血常規白細胞計數2.3×109/L,血紅蛋白104g/L,血小板計數79×109/L,中性粒細胞絕對值2.0×109/L。腫瘤標志物和CT復查結果正常,基因檢查結果提示乳腺癌易感基因(Breast cancer susceptibility gene,BRCA)已知致病突變。根據血常規結果提示患者骨髓抑制II級。12月2-8日,患者住院期間反復出現骨髓抑制,予以對癥支持治療后好轉。12月9日,患者白細胞計數3.6×109/L,血紅蛋白110 g/L,血小板計數117×109/L,中性粒細胞絕對值2.3×109/L,考慮患者卡鉑化療后骨髓抑制明顯,建議本次化療更換為順鉑,遂行紫杉醇283 mg+順鉑121 mg化療,同時予以護胃、止吐、護肝、補鉀補液等治療。12月11日,患者化療后生命體征平穩,各項檢查正常,予出院。此患者為卵巢惡性腫瘤IIIC期(高級別漿液性癌),在6次含鉑化療后達到完全緩解,考慮其基因檢測結果為BRCA2致病基因突變,根據指南,其維持治療方案可以選擇PARP抑制劑奧拉帕利或尼拉帕利。綜合多種因素,患者選擇尼拉帕利維持治療。患者出院后口服尼拉帕利200 mg/d維持治療至今,門診隨訪期間腫瘤未發生進展,同時患者主訴精神狀態較前好轉,因缺乏精神科醫生的系統評估,所以用藥并未進行調整。
2 討論
2.1 抗抑郁藥與PARP抑制劑之間的相互影響 患者長期使用抗抑郁類藥物,而尼拉帕利與此類藥物之間是否存在相互影響、聯合用藥是否影響藥效或加重不良反應目前尚不明確。臨床常用的抗抑郁藥從作用機制可分為選擇性5-羥色胺(5-HT)再攝取抑制劑、5-HT和去甲腎上腺素再攝取抑制劑、去甲腎上腺能和特異性5-HT能抗抑郁藥等[5-7]。帕羅西汀的代謝酶為CYP2D6,坦度螺酮片、氯硝西泮的代謝酶為CYP3A4,米氮平主要由CYP2D6、CYP3A4及少量CYP1A2代謝[8]。帕羅西汀可以抑制CYP2D6酶,其與米氮平聯用時,可以使米氮平的血藥濃度明顯升高[9]。PARP抑制劑中的奧拉帕利通過CYP3A4代謝,尼拉帕利通過羧酸酯酶代謝[4]。CYP3A4是人體中最重要的P450酶,主要存在于肝細胞的內質網上,許多藥物經由CYP3A4酶催化代謝。當合用藥物存在競爭CYP3A4酶時,藥物的血藥濃度發生變化,導致療效降低或不良反應增加。在一項針對奧拉帕利體外藥代動力學模型實驗中,建議在同時給予強/中度的CYP3A抑制劑時,奧拉帕利應給予減量[10]。因此,患者所用的米氮平、坦度螺酮片、氯硝西泮與奧拉帕利可能競爭CYP3A4酶,影響奧拉帕利在體內的代謝。而尼拉帕利通過羧酸酯酶代謝,與患者所用的米氮平、坦度螺酮片、氯硝西泮之間無相互影響。
據報道,使用帕羅西汀、米氮平、坦度螺酮片、氯硝西泮等藥物可能會引起血液及淋巴系統、免疫系統、內分泌系統和消化系統等不良反應,包括食欲不振、惡心、嘔吐、低色素性貧血等[11]。奧拉帕利和尼拉帕利提示可能會引起血液及淋巴系統疾病、胃腸系統疾病、全身性疾病及給藥部位的各種反應等[12]。有報道,在對奧拉帕利安全信號挖掘中,其不良事件主要包括貧血、惡心、血小板計數降低、食欲減退、中性粒細胞計數降低等[13]。因此,抗抑郁藥與奧拉帕利同時使用,可能會造成不良反應的疊加。
2.2 PARP抑制劑的抗抑郁活性 目前已知PARP家族包括17個成員,其中PARP1和PARP2主要通過堿基切除修復途徑在DNA單鏈斷裂修復中發揮重要作用。有文獻報道了重度抑郁癥患者腦內白質DNA氧化和DNA修復酶的水平,結果表明,堿基切除修復酶 PARP1的基因表達水平在重度抑郁癥患者腦內顯著升高[14]。Szebeni等[15]的研究也表明,抑郁癥患者體內的PARP1和IL-6的表達顯著升高。抑郁癥患者體內PARP1的表達升高,為PARP抑制劑治療抑郁癥提供了理論可行性。Ordway等[16]建立了大鼠抑郁模型,證實PARP抑制劑氨基苯扎胺和5-氨基異喹啉酮在Porsolt游泳試驗中顯示出抗抑郁樣活性。雖沒有文獻直接證實PARP抑制劑奧拉帕利、尼拉帕利的抗抑郁活性,但根據目前的報道推測其可能具有潛在的抗抑郁作用。1篇個案分析報道了尼拉帕利抗抑郁作用的可能性,1例患復發性卵巢癌的女性患者因抑郁障礙長期服用艾司西酞普蘭、丁螺環酮、勞拉西泮,抑郁情緒控制并不理想。患者在使用紫杉醇聯合鉑類方案化療后,開始接受尼拉帕利維持治療,在維持治療期間患者精神癥狀明顯改善,2周后由于尼拉帕利骨髓抑制的不良反應停藥,停藥后患者情緒出現惡化,當再次使用尼拉帕利時,患者情緒好轉,抑郁癥狀明顯改善,且經精神科醫生評估,病情較前明顯好轉[17]。一項針對不同PARP抑制劑的藥代動力學研究,證實尼拉帕利可以跨越血腦屏障,在大腦中表現出良好的活性,為尼拉帕利治療抑郁提供可能[18]。在本案例中,患者口服尼拉帕利后,主訴精神狀態較前好轉,雖未經過精神科醫生的系統評估,但從側面佐證了尼拉帕利具有抗抑郁作用的可能性。因此,現有臨床資料證實,尼拉帕利可能具有抗抑郁活性,但其作用機制仍有待于進一步研究。
2.3 抗抑郁藥對腫瘤的影響 對惡性腫瘤患者,使用抗抑郁藥是否影響疾病的進展尚不明確。有文獻評估了各種抗抑郁藥與上皮性卵巢癌風險之間的關聯,結果表明,使用選擇性5-HT再攝取抑制劑與三環類相關抗抑郁藥時,上皮性卵巢癌的風險降低24%[19]。Lee等[20]的研究表明,選擇性5-HT再攝取抑制劑使用者比非使用者具有較低的腎癌風險,西酞普蘭使用者腎癌風險減少了33%,帕羅西汀使用者腎癌風險減少了25%,證實使用抗抑郁藥可能會降低卵巢癌、腎癌的發生風險。在體外實驗中,氟西汀可以誘導人胃癌細胞的凋亡和自噬,且以濃度依賴的方式抑制癌細胞的生長,推測相對高劑量的氟西汀可用作癌癥的輔助治療[21-22]。有報道,氟西汀可顯著抑制肝癌和非小細胞肺癌的體內腫瘤生長,作用機制為降低與細胞增殖、抗凋亡、侵襲相關蛋白的表達,包括細胞周期蛋白D1、生存素、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基質金屬肽酶9(MMP-9)和尿激酶型纖溶酶原激活劑(uPA)[23]。在動物實驗中,氟西汀增強了阿霉素的細胞毒性(10倍),阿霉素-氟西汀聯合治療可顯著減緩腫瘤進展,同時其他研究證實氟西汀可以使環磷酰胺、多柔比星、絲裂霉素C、長春堿和紫杉醇的細胞毒性增加[24-25],說明氟西汀具有潛在的抗腫瘤和化療增敏的特性。Amit等[26]研究顯示,腫瘤細胞(Jurkat)暴露于高濃度舍曲林或帕羅西汀,會導致細胞活力顯著降低,當與化療藥物聯合使用時,舍曲林顯著增強長春新堿和阿霉素的作用。一項荷瘤小鼠模型中證實了米氮平具有抑瘤作用[27]。另一項研究表明,米氮平通過上調Lin-7C通路來抑制鱗狀細胞癌的細胞遷移和侵襲[28]。Jang等[29]研究了帕羅西汀在人類結直腸癌細胞HCT116和 HT-29 中的潛在抗癌作用,證實帕羅西汀治療降低了兩種細胞系中的細胞活力。通過文獻檢索雖未找到抗抑郁藥對腫瘤進展影響的直接臨床證據,但目前的體外實驗和動物實驗證實,部分抗抑郁藥可以抑制腫瘤細胞的增殖,同時對化療藥物有增敏作用。因此,此患者長期使用抗抑郁類藥物可能對腫瘤結局獲益。
3 小結
通過對本例卵巢惡性腫瘤伴復發性抑郁障礙患者的用藥分析,探討了PARP抑制劑與抗抑郁藥物之間的相互影響,從藥物代謝角度分析,米氮平、坦度螺酮片、氯硝西泮與奧拉帕利可能存在相互作用,與尼拉帕利之間無相互影響。從藥物安全性分析,抗抑郁藥與奧拉帕利、尼拉帕利聯用可能存在不良反應事件的疊加。從現有臨床資料證實,尼拉帕利可能具有抗抑郁活性,但其缺乏大規模臨床隨機對照試驗證實,作用機制仍有待進一步研究。同時研究了抗抑郁藥對腫瘤的影響,根據文獻資料推測此患者長期使用抗抑郁藥物可能對腫瘤結局獲益。因此,在日常工作中我們應該關注合并多種疾病患者的用藥問題,提高藥物治療的有效性和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