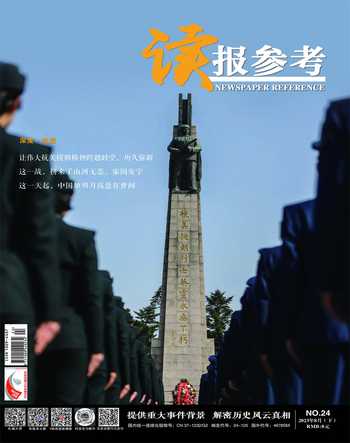尼日爾軍事政變的“表”與“里”
2023年7月26日,西非內(nèi)陸國家尼日爾發(fā)生軍事政變,原本是承擔(dān)保衛(wèi)總統(tǒng)職責(zé)的尼日爾總統(tǒng)府衛(wèi)隊(duì)卻成為發(fā)動(dòng)政變的主角,扣押了2021年上臺(tái)執(zhí)政的民選總統(tǒng)巴祖姆。7月31日,政變軍人又逮捕了執(zhí)政黨180名成員。
尼日爾軍事政變是近年來此起彼伏的西非地區(qū)國家“政變回潮”中的最新案例。此前,該地區(qū)的馬里(2020年8月、2021年5月)和布基納法索(2022年1月、9月)兩國各自在不到一年內(nèi)發(fā)生兩次軍事政變,還有幾內(nèi)亞(2021年9月)軍事政變,幾內(nèi)亞比紹(2022年2月)未遂軍事政變等。
軍事政變?yōu)楹伟l(fā)生
尼日爾政變軍人對(duì)外發(fā)布的政變“理由”是,“尼日爾安全局勢(shì)持續(xù)惡化,政府對(duì)于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治理不力”。而實(shí)際上,這一面上的“理由”折射出的是尼日爾軍方與文官政府間矛盾的日益激化,特別是在國家面臨反恐和安全局勢(shì)動(dòng)蕩以及經(jīng)濟(jì)社會(huì)危機(jī)的關(guān)鍵時(shí)刻。
據(jù)悉,此次發(fā)動(dòng)政變的尼總統(tǒng)府衛(wèi)隊(duì)長奇亞尼將軍,是前任總統(tǒng)的親密盟友,自2007年以來就一直擔(dān)任總統(tǒng)府衛(wèi)隊(duì)長這一要職并在2011年晉升為將軍。
然而近來,奇亞尼與現(xiàn)任總統(tǒng)的關(guān)系日益緊張,且傳出總統(tǒng)巴祖姆想要將其解職的風(fēng)聲。于是,面臨“被解職”危險(xiǎn)的衛(wèi)隊(duì)長采取了先下手為強(qiáng)的策略先“解職”了總統(tǒng)。
除了奇亞尼將軍與巴祖姆總統(tǒng)間的個(gè)人恩怨外,近年來由于西非薩赫勒地區(qū)的反恐形勢(shì)日益嚴(yán)峻,軍方常常抱怨總統(tǒng)對(duì)軍方的反恐支持力度不夠(軍餉及軍備的預(yù)算不足),并對(duì)文官政府的治國能力感到不滿。
可以說,正是這些摻雜了個(gè)人恩怨的種種矛盾,最終點(diǎn)燃了政變引信。
另外,尼日爾政變也與近年來西非地區(qū)國家頻繁政變的傳導(dǎo)和“示范”效應(yīng)有關(guān)。特別是馬里、布基納法索等國此前發(fā)生的政變及其政變軍人最后的成功上位,都對(duì)尼日爾軍人產(chǎn)生了某種程度上的“激勵(lì)”作用。
大國陰影揮之不去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軍事政變?cè)谖鞣堑貐^(qū)的“回潮”,還伴隨著當(dāng)?shù)胤磳?duì)法國勢(shì)力的呼聲上漲以及俄羅斯在該地區(qū)影響力的擴(kuò)大。
西非地區(qū)國家歷史上多為法國殖民地,1960年代取得獨(dú)立后,原宗主國法國仍通過軍事安全、政治外交、經(jīng)濟(jì)貿(mào)易以及社會(huì)文化等“四根紐帶”來維系其對(duì)原殖民地國家的控制。
時(shí)至今日,雖然政治外交、經(jīng)濟(jì)貿(mào)易和社會(huì)文化等三條紐帶已經(jīng)日漸式微,但法國憑借其在西非地區(qū)眾多的軍事基地及自2013年開始在薩赫勒地區(qū)開展的強(qiáng)勢(shì)反恐行動(dòng),希望把法國與該地區(qū)的“軍事安全”這一紐帶再次牢牢系緊。
然而,法國近十年來在西非地區(qū)的反恐行動(dòng)成效不彰。十年反恐,越反越窮,越反越亂,讓當(dāng)?shù)乩习傩崭究床坏桨踩桶l(fā)展的希望。該地區(qū)民眾的反法情緒因此不斷抬頭,而政變軍人也有借“奪權(quán)”將矛頭指向法國,并最終趕走法國駐軍的意圖。
尼日爾總統(tǒng)巴祖姆,就被尼反對(duì)派質(zhì)疑其過于“親法”。因?yàn)楫?dāng)馬里和布基納法索政變軍人上臺(tái)后要法國駐軍卷鋪蓋走人時(shí),是巴祖姆頂著壓力“力排眾議”,同意從馬里和布基納法索撤出的法國軍人部署到尼日爾。
7月30日,上千名支持政變的尼日爾示威民眾包圍和沖擊法國駐尼日爾大使館,焚燒法國國旗,并喊出“法國滾蛋”和“歡迎俄羅斯”的口號(hào)。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歐美國家、聯(lián)合國、西共體以及非盟等國際或地區(qū)組織眾口一詞同聲譴責(zé)尼日爾軍人政變的時(shí)候,俄羅斯雇傭兵組織“瓦格納”集團(tuán)的領(lǐng)導(dǎo)人普里戈任則對(duì)尼日爾政變軍人贊賞有加,稱這一政變是“好消息”。
西共體面臨分裂危險(xiǎn)
1975年成立、共有15個(gè)成員國的西非國家經(jīng)濟(jì)共同體(簡稱“西共體”),是非洲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區(qū)域性經(jīng)濟(jì)合作組織,以加強(qiáng)區(qū)域一體化,促進(jìn)成員國在政治、經(jīng)濟(jì)、社會(huì)和文化等方面的發(fā)展與合作為宗旨,也同時(shí)肩負(fù)著維持西非地區(qū)集體安全與穩(wěn)定的重任。
尼日爾政變發(fā)生后,西共體第一時(shí)間發(fā)聲譴責(zé),要求恢復(fù)尼的原有憲政體制,并很快在7月30日舉行了首腦特別峰會(huì),要求尼政變軍人將權(quán)力交還給原有民選政府。峰會(huì)決定還表示,如果尼軍方未能交出權(quán)力,西共體將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使用武力恢復(fù)該國憲法秩序。
西共體峰會(huì)的決定剛一公布,與尼日爾政變軍人站在一起、處境相似的布基納法索和馬里過渡政府就發(fā)表聯(lián)合聲明,公開表示對(duì)尼日爾的任何軍事干預(yù)都等同于對(duì)兩國宣戰(zhàn)。這一強(qiáng)硬表態(tài)直指西共體對(duì)尼“軍事干預(yù)”的選項(xiàng),是對(duì)西共體強(qiáng)硬“威脅”的“反威脅”。
當(dāng)?shù)貢r(shí)間8月2日晚,尼日爾政變軍人領(lǐng)導(dǎo)人奇亞尼發(fā)表電視講話說,其不接受所有來自西共體的制裁,也不會(huì)在地區(qū)和國際壓力下恢復(fù)總統(tǒng)巴祖姆的職務(wù),不屈服于來自任何一方的威脅。
可以說,無論西共體最終選擇“動(dòng)武”還是“不動(dòng)武”,西共體本身面臨的分裂危險(xiǎn)都已迫在眉睫,西非地區(qū)局勢(shì)也將變得更緊張、更復(fù)雜。
(摘自《工人日?qǐng)?bào)》賀文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