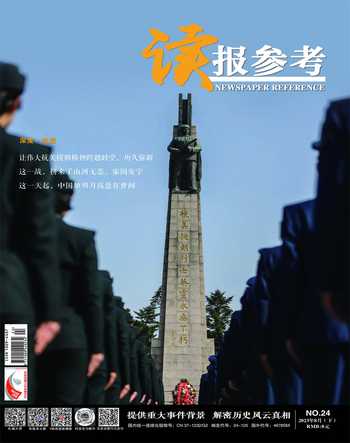躲過了“秦火”的《詩經》
秦始皇焚書,《詩經》首當其沖。今天我們所看到的《詩經》,是由西漢毛亨、毛萇傳下來的《毛詩》,與史籍記載孔子所編纂的《詩》,文辭上是否有不同,編排上是否有變化,甚至篇目上是否一致,這是歷來讀詩者心中的疑惑。最近,湖北荊州一座戰國楚墓里出土的一批竹簡,經過初步整理釋讀,或許可以為我們揭開一些“秦火”之前的《詩經》面目。
古墓之中藏“國風”
長湖,江漢平原上著名的“四湖”之一,也是古云夢澤“縮編”后演化而成的一座長條狀湖泊。長湖的西北角上,就是戰國時期楚國故都紀南城遺址。今天,以紀南城遺址為中心,方圓數十公里范圍內,分布著數以萬計的楚國古墓。
王家嘴是位于荊州市荊州區紀南鎮洪圣村的一處墓地,西距紀南城東城垣約4公里,北接雨臺山古墓群,南瀕長湖。為配合基建項目,2019年至2021年,荊州博物館在這里進行考古發掘。2021年6月,在編號為M798的一座戰國楚墓中,出土了一批珍貴竹簡。經過初步整理和釋讀,考古工作者發現其中一部分可以與今本《詩經·國風》相對讀。
在紙張普遍使用之前,竹木簡牘長期是主要的文字記錄載體。因此,簡牘被認為是學術價值極高的出土文物。一枚簡牘,甚至是其中一個字,往往就可以啟發人們對歷史的重新認知。王家嘴M798號楚墓出土的竹簡,讓我們可以窺見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前“詩”的面貌和《詩經》文本。
據荊州博物館館員蔣魯敬介紹,王家嘴《詩經》竹簡殘斷缺失較為嚴重,最長的約38厘米,最短的不足1厘米。通過拼接和編連,推測大約有300支,整簡長約44厘米、寬約0.6厘米,竹簡簡面右側自上而下有三個契口,部分竹簡的契口還留有編繩殘片,可見原本是編連成冊的。
通過對竹簡的釋讀和編連,初步判斷王家嘴《詩經》可以確認的有150余篇,比今本《詩經》中的《國風》160篇少了幾篇,絕大部分與今本《國風》可以相對讀。比如,1561號簡“雉鳴求起牡,濟盈……”,與今本《邶風·匏有苦葉》可以對讀,今作“濟盈不濡軌,雉鳴求起牡”,詩句順序發生了變化。
值得注意的是,王家嘴楚簡《詩經》中還有少量內容不見于今本《詩經》,可能屬于“逸詩”。據蔣魯敬介紹,現在可以看到篇名的“逸詩”有8首。
荊州博物館王家嘴墓地考古發掘項目領隊肖玉軍介紹,M798號墓是典型的小型東周楚墓,從墓中出土的器物判斷,墓葬年代應為戰國晚期,墓主人為“士”一級。墓葬等級雖然不高,但在墓內出土的竹簡多達3200枚(不計小碎片),推斷原簡數量約為800支。內容除了《詩經》中的《國風》部分外,還有類似《論語》記錄孔子言的《孔子曰》,以及可能為樂譜的竹簡。由于殘斷缺失嚴重,整理難度大,目前只是完成初步的釋文和編連工作。
戰國楚簡是戰國時期楚國用楚文字書寫和流傳的一類典籍,具有重要的考古學和文獻學價值。荊州一帶出土戰國楚簡數量多,保存好,保留了豐富的歷史信息。蔣魯敬說,王家嘴楚墓出土的楚簡《詩經》,在內容、篇章、編排等方面,與今天熟悉的《詩經》有較大差異,為研究先秦時期《詩經》的本來面貌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先秦《詩經》知多少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在先秦時只稱作“詩”,到漢代才成為“經”。春秋戰國時期,《詩》流行于諸侯各國,運用于祭祀、朝聘、宴飲等各種場合,成為當時政治、外交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說:“不學《詩》,無以言。”給予《詩》非常高的評價,并將其作為教材,納入自己的教學體系。《史記·孔子世家》記載,《詩》原本有三千多篇,孔子選取其中可以用于禮義教化的篇章,整理成集,就是三百零五篇。“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孔子不僅刪詩,而且歌詩,使之成為傳誦的經典。
秦始皇燒毀了包括《詩》《書》在內的先秦典籍,使其瀕臨幾乎毀滅的浩劫,給后世留下無限的遺憾。所幸,《詩》是可以吟唱的韻文,便于記憶和流傳,因此在西漢初年得以比較完整地恢復。《漢書·藝文志》說,《詩經》“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漢初《詩》定為“經”,《詩經》成為官方教材。當時《詩》分三家,有《魯詩》《齊詩》《韓詩》,分別由魯人申培、齊人轅固生、韓人韓嬰所創,列于官學。而《毛詩》興起稍晚,一般認為是“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萇所傳,卻沒有被立為官學,只在民間長期傳授。各家之詩大體相同,解讀則已出現明顯分歧。
至東漢時期,《毛詩》取代了“三家詩”的地位,獨立國學,尤其經大儒鄭玄作箋,“宗毛為主”。“三家詩”式微,竟至先后軼亡。唐朝孔穎達奉詔編定《五經正義》,《毛詩正義》被官方認定為標準教材,從此《毛詩》一家獨大。
1977年,安徽阜陽雙古堆一號漢墓出土一批竹簡、木簡和木牘,其中有100多片殘簡內容涉及《詩經》,包括《國風》殘詩65首,還有《小雅》中4首詩的殘句。學者研究認為,阜陽簡《詩經》不同于“三家詩”,也不同于“毛詩”,證明了漢初有多家傳詩的記載。
一些學者推測阜陽簡《詩經》或是楚國流傳下來的一種版本,但是并沒有充分的證據。所以,人們對于秦以前的《詩經》究竟是什么樣,一直茫然無所知。直至1993年湖北荊門市郭店一號墓出土的郭店楚簡中,有部分簡文出現引詩或談到《詩》。1994年上海博物館入藏一批重要戰國楚簡,其中《孔子詩論》記載了孔子對若干詩篇詩旨的理解。清華大學2008年也入藏一批戰國楚簡,有個別與《毛詩》近似的篇章。這些新發現的與“詩”相關的竹簡,更接近“詩”的原貌,給人們帶來對先秦《詩經》的新認識。
真正通過科學考古發現的“秦火”之前的《詩經》文本,除了王家嘴楚簡《詩經》外,還有2015年在湖北荊州市荊州區郢城鎮荊北村發現的夏家臺戰國楚簡《詩》。夏家臺M106號楚墓出土400余枚竹簡,年代在戰國中期,其中有與今本《詩經·邶風》前14篇可以相對讀的內容,這是首次在楚墓中發現《詩經》的抄本。
無獨有偶,2015年安徽大學收藏了一批戰國楚簡,即安大簡。經過整理和研究,其內容涉及《詩經》、楚國歷史、孔子語錄等多個方面。安大簡數量較多,保存也較好,共有1167個編號,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簡文《詩經》。已經公布的資料顯示,安大簡《詩經》包含57篇《詩經·國風》的內容。經湖北荊州文物保護中心取樣進行分析檢測,確認安大簡材質為古代竹材,簡文體現了戰國時期楚地的文字風格,簡的形制與戰國楚簡也較為一致。
荊州王家嘴M798號墓楚簡《詩經》,是繼荊州夏家臺《詩經》、安大簡《詩經》之后,戰國楚簡《詩經》的又一重大發現。除了竹簡外,王家嘴M798號墓還出土了銅鼎、銅壺、銅盤、銅匜等典型戰國晚期楚墓器物,表明墓中竹簡《詩》當為“秦火”之前的《詩經》文本。蔣魯敬說,這是目前經科學考古出土存詩數量最多、文本結構最為完整的戰國楚簡《詩經》抄本,它們呈現了《詩經》的早期文本內容與物質形態,對《詩經》的研究乃至先秦文化研究都具有重大價值。
(摘自《新華每日電訊》皮曙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