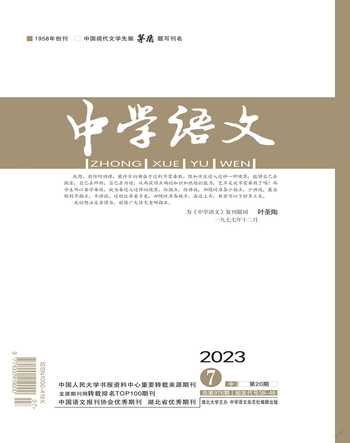高中戲劇教學中劇本創編的實踐與探索
王怡 王韋
摘 要 高中戲劇教學可以指導學生進行劇本創編。挑選經典題材,立足學生成長重新立意;以改編作為任務情境,組織學生基于新的主題對原著進行深度挖掘,建構新的故事邏輯,實現讀與寫的深度互動;當原著不能給新劇本的生成提供足夠支持時,鼓勵學生拋開原著進行重構與創造。
關鍵詞 劇本創編 重新立意 讀寫互動 重構創造
戲劇在《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2017年版2020年修訂》(以下簡稱《課程標準》)和統編高中語文教材中設有相應的教學內容。《課程標準》在“選擇性必修和選修課程學習要求”中指出,學生要“在閱讀鑒賞中,了解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文學體裁的基本特征及主要表現手法” ;“當代文化參與”的學習任務群中指出要“豐富語文學習的方式”,引導學生創建社團,開展戲劇表演等各類語文學習活動。
戲劇是一種集文學、音樂、美術、舞蹈、表演于一體的綜合性藝術形式,因此戲劇教學在高中語文教學方面具有特殊性。我們構建了比較完整的戲劇課程教學環節,為促進學生語文能力的綜合提升和思維品質的發展,在高中戲劇教學中對劇本創編進行了積極探索與扎實實踐。
一、為學生心靈成長與思維發展而選材立意
所有故事和文本都承載著價值觀念,劇本也不例外。學生經過反復讀劇本、背臺詞、排演等一系列環節后,能獲得怎樣的認識和思想情感上的成長,這是在選擇題材、創編劇本之前充分考慮的問題。
學生進行戲劇排演實踐,其實可以直接選用經典劇本,不少學校也是采取直接排演經典劇本的方式進行戲劇實踐的。我們沒有采取這種方式,而是挑選經典題材、素材,重新立意,然后根據新的主題進行戲劇創作改編。采取這種創編方式,正是立足于高中生的特點,“加強語文課程內容與學生成長的聯系”,以“充分發揮語文課程的育人功能”。
高中生處在思維能力迅速發展的階段,他們開始思考人生的目的、價值、理想等問題,很多的社會性情感如社會責任感、正義感、文化認同感等就是在這個階段形成的。經典劇本通常表達特定的時代主題,較少能直接關聯學生的成長生活及他們所關心的問題,而自己立意改編,就能把握主動權,保證劇本所表達的內容與學生的成長生活有關。
同時,堅持在改編基礎上創作,而非完全原創,是因為文學經典作品是經過歷史淘洗而留下的思想文化的結晶,能提供高于學生思維與審美水平的內容,且具備豐富的闡釋空間,能激發學生的思考,形成一種對話的態勢。
2021年選擇魯迅的小說(以《吶喊》為主)作為改編對象。魯迅小說極具時代特色,如何使它與當下的高中生成長生活建立起內在聯系,也是我們思考的重點。《吶喊》的主題是剖析批判傳統制度、文化中陳腐、戕害人們心靈的部分,以啟蒙思想、引領新生。對這樣的作品,如不加引導,學生會覺得時過境遷,與自己無關。而且在教學中,普遍感受到現在的學生比較自我,更多關心個人的發展與價值,而時代與國家的發展,越來越需要年輕人把個人的價值與民族復興、人民幸福聯系在一起,需要他們去擔負歷史使命。所以將主題定為“與我有關”,取自魯迅那句“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的深情表達,以激發學生對于人生價值、個人與社會關系的思考。
二、與經典對話中實現讀與寫的深度互動
劇本創編對學生的閱讀積累和寫作能力的要求很高,它相當于《課程標準》中的選修課程,“應突出差異性和層次性,鼓勵開展個性探究,充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潛能”,“注重學習‘點的深度”。編劇工作是由年級中感興趣且文學修養較好的學生來承擔,由學生進行集體創作。
結合學生的成長需求和真問題確立的新主題,是進行戲劇創編的基礎。所以,學生的編劇需要基于主題,對《吶喊》進行重新思考,梳理出魯迅小說中哪些故事和“與我有關”的主題有關聯。在第一次進行主題闡釋和大綱設計時,編劇學生提供的相關情節和闡釋是:魯迅小說中冷漠的看客形象多持“與我無關”的心態,而狂人極力勸眾人“從真心改起”、不要再吃人,這體現了“與我有關”要改變社會的責任意識,把“與我無關”的部分與“與我有關”的部分組合在一起,就能形成一個有機的發展邏輯。
可以看出,學生理解比較準確,且懂得敘事作品的基本邏輯,但是小說集《吶喊》加上必修教材所學的《祝福》一共15篇小說,學生只找到這樣兩類與主題相關的內容,顯然他們對魯迅小說的理解還不夠深入。當被追問“與我有關”的“我”是誰時,學生也意識到他們找到的這兩種情節中“我”是截然不同的兩類人(一類是農民、幫工、商戶等普通民眾,一類是接受新思想觀念的讀書人),無從建立起連貫的故事發展邏輯。
學生最初的闡釋停留在比較淺表、直觀的層次上。所以,有必要帶著他們再次去魯迅小說中探尋:在阿Q身上,發現了不僅別人的痛苦與我無關,自己的痛苦通過精神勝利法或遺忘法寶也可以變得與自己無關;阿Q想要參與革命,即革命“與我有關”,但他并不理解革命的意義,而只是想改變自身處境、凌駕于眾人之上;《狂人日記》中狂人最初懷疑別人要吃他,這也是一種“與我有關”——“與我性命攸關”,“我”是這種文化的受害者;狂人最后發現“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這是發現“我”和他們一樣也曾是迫害者的“與我有關”,“我”更深刻地認識到這種文化的害處,身處其中的所有人既是受害者也是迫害者。由此學生理解了“吶喊”之迫切,也理解了吶喊者魯迅并不是將自己放在超越群體的絕對清醒、正確、獨立的高位,而是站在人群中,充滿了對被損害而不自知者的同情和理解。所謂“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既是魯迅這種深沉情感的表達,也體現出一種背負使命的自覺。
深入闡釋主題、挖掘素材的工作,一方面讓學生對魯迅小說的形象與思想有了更深刻的認識,進而為魯迅的精神所感動;另一面學生在不同小說中尋找相似或關聯的人物、情節類型,也是一個梳理整合的過程,使他們對魯迅小說的認識,從單個、零散變為類型、整體,發現了其“文本的互文性” ,理解了魯迅剖析社會文化弊病之深廣,思維也就從淺表走向了深層。
在此過程中,學生發現,如果“我”是“狂人”一類接受新思想觀念的讀書人時,就可以出現“與我無關——與我性命攸關——我要改變他們——原來我和他們一樣”這樣一個線性的認識發展過程,并且劇本可以采用雙線敘事結構:用一個狂人式的主人公的成長,串起孔乙己、阿Q、祥林嫂、單四嫂子等人的故事。
可以說,為改編而對原著進行各種維度的梳理閱讀,讓學生找到魯迅多篇小說之間的關聯,對魯迅形成一個較為系統的認識,而且情感上愈發認同魯迅,也更愿意追隨那種“與我有關”的責任使命。這種深入閱讀,也給課本劇改編掃清了障礙、搭起了框架。
經典作品本身就是優質的閱讀材料,能極大地滋養學生的心靈和頭腦,而當我們有了改編原著的任務情境,就更能激發學生閱讀與寫作的動力。同時,以改編任務檢測了學生的理解程度,學習梳理比較的閱讀方法;又以經典文本來幫助積累寫作素材、學習寫作技巧、激發創造性,即以寫促讀、以讀帶寫,在讀與寫的深度互動中,實現讀寫能力的雙重提升。
三、運用文學規律進行重塑與創造
戲劇實踐課程中的劇本創編環節,之所以稱其為創編,是因為這不是對原著或前人劇作進行簡單的組合拼接,而是為表達新主題而進行的重塑、創作的過程,最終形成一部完整、連貫、獨立的劇本。當原著內容,不能給新劇本的生成提供足夠的支持時,要鼓勵學生拋開原著,進行大膽虛構,在此過程中學習文學規律與寫作方法。
上文已提到創編《吶喊》劇本時采用了雙線結構:狂人式的主人公也是穿線人物,所以需要貫穿于劇本的四幕中。著手創作時,學生感到比較困難,因為魯迅小說中寫“受新式教育的讀書人”的故事情節不多,并且像《狂人日記》《頭發的故事》之類小說,是以個人獨白的方式在呈現新式讀書人的內心,具體背景、故事語焉不詳,很難直接轉化成劇本故事。所以我們除了細讀分析原著,尋找可用的語言和情境外,還帶領學生在小說之外的真實歷史中,去尋找原型素材,進行虛構創作。
例如“狂人”可以說是魯迅自身經歷的抽象化、藝術化,那么就以魯迅本人及其經歷為原型,去創造主人公。在小說《藥》里,夏瑜只在眾人的閑談中寥寥幾筆帶出,不能夠支撐創造一個革命者的形象,而夏瑜原型是秋瑾,因是女性,經歷相對特殊,于是又找到和秋瑾同為紹興籍且同年犧牲的辛亥先烈徐錫麟,糅合兩人的性格經歷來塑造夏瑜。與此同時,主人公還需要一位同行者,即和他交心的朋友,這樣他就能通過對話表達出自己的思想認識,這時候我們想到了《吶喊·自序》中跟魯迅討論鐵屋子能否毀壞的金心異,于是設計了主人公的朋友金心異這一角色。這個人物的原型是錢玄同,但是學生不太熟悉錢玄同,于是參考更著名的新文化運動領袖陳獨秀,來塑造金心異的形象。
歷史現實中人們的經驗是所有藝術創作的來源,而這個尋找原型的過程,也正生動地告訴學生,所謂素材積累,不是試圖把別人的故事整個變成自己的作文,而是要根據主旨和敘事的需要,對生活中的相關元素進行提取、重組。這也正是魯迅自己的創作經驗:“人物模特沒有專門用過一個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角色。”這才是把閱讀材料轉化為寫作材料的有效方法。
學生在閱讀中可以很嫻熟地分析人物性格形象。這是一個從形象到邏輯的過程,而創作則讓他們把這個過程顛倒過來,從邏輯出發,最終要施諸于形象,鍛煉學生想象與創造的能力。我們日常的閱讀教學中,很多文學形象分析與賞析被固化成解題思路,學生不是在實踐中去思考其作用價值,很難真正理解并將其變成自己可以學習借鑒的寫作經驗。真正的寫作,既需要有清晰明確的宏觀設計,又要有精準縝密的細節呈現,而這種課本劇創編方式,將讀寫合成一個閉環,引導他們深入規律分析創作,從宏觀到細節多遍打磨,在實踐中提升了語文學科素養。
創編劇本難度大、工程量大,但也給日常教學很多啟發。這種主題闡釋、大綱設計、人物設計、素材改編等內容,完全可以化整為零,延伸到日常的閱讀與寫作教學中。比如在閱讀教學中加入片段改編、續寫、填補空白等微型寫作設計,以檢測學生閱讀理解的程度;在寫作教學中可以提供寫作素材,做規定主題下的改編練習等。而戲劇課程與劇本創編的整體性和情境性則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作者通聯: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