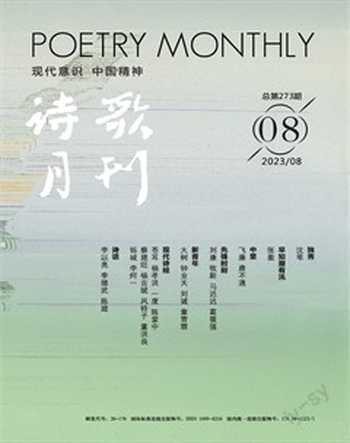猛獸與主角
陳建
20多年前,我寫過一首關于工程師的詩,工程師的狀態被我寫得生猛又憂傷,大意是我可以隨意彎曲、折疊鋼鐵,裝配出一只只非碳基的猛獸,這些猛獸假裝馱著人類前進,隨著我的憂患意識隨時可能反咬一口。實際上,我只是拖拽著鼠標的光標在屏幕上羅列著點、線、圓。當然,從顯示屏的二維世界看過來,我的手勢動作有可能類似畫符,一副妖道作法的狀態。
如此之后多年,我再沒寫過自己職業主題的詩,盡管我依舊生活在畫圖的職業之中。剛工作時,時代正從手繪向電腦制圖轉移,我趕上了那種幾百年傳統的最后幾天——對著大型制圖板“爬圖紙”。但就時間賦予的結果來看,電腦制圖除了出圖量有指數級的提高,工程師依然是手工藝人,依舊付出同樣的禿頂、腰頸椎病、老化散光以及腱鞘炎……
對了,我的職業是:產品研發,這是工牌上標明的。工牌很有意思,戴在胸口,向公司或客戶標示我是誰。在日常生活中,我好像沒發現還有什么別的事物具備工牌這樣的直接性。它直接定義了你的職業,它提供安全感和歸屬感,也兼示隸屬與階級。它是行為模式中規范化的一部分,是法與令最基本的表現形式。陌生的同事間偷瞄一眼對方工牌,然后給出相應的言談舉止,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在工位上時,我時常感到我是一顆活字印刷術的字模,當我的手放在鼠標上時,秘不可知的系統會自動將我使用,構成它需要的句式、產品。朋友們有時候說我的詩設計感很強,反正在褒貶不明的情況下我一般把這當作贊揚。畢竟,我在設計那些猛獸的間隙,在它們一去不返、滿心油膩、偶爾回頭的垂涎瞬間寫詩。
作為一個詩人,或者說作為一個自我定義的職業詩人,我也企圖認為我的工程師職業根本影響不到我的詩歌寫作。畢竟,一方面是按部就班、規則、準確、以產品安全性為第一的藍領設計。另一方面,從詩人的角度來看,世界毫無浪漫,繁復無序,而詩人卻企圖用幾行作品清晰表達這個世界內部的網絡。當然,這種分裂完全合理于人類的常規行為,并沒有異于上班下班這種日常方式更多。
任何有文學藝術傾向的人,都喜歡在自己的作品中按照自己的想法把世界改造一番……編程出專屬于自己的世界。比如我常把人們對利好事物的不懈追求誤讀為笑話,以之幽默我的平衡。十分準確地說是我對那些龐大、天經地義、巨塔一樣的典范缺乏恭敬。面對雕像五體投地的人,我很想扔去一個啃過的蘋果。我旁觀的姿態決定了我總愛在暗處冒點想法,并陶醉于語言中的冒犯。
在40歲那年,我自印了自己第一本詩集《斷常詩》,扉頁上頗為自豪地留下幾個致敬:
謹以此集向拼盡一生,只求一無所獲的先行者致敬
向應有之物,絕不嚴重致敬
向無關指證無限致敬
如今,快要過去10年了,我開始為我的無恥擔憂,畢竟,口號喊得太響了,手上的技術卻有些拉胯,根本配不上致敬。我的朋友游太平先生頗有先見之明,他贊美過:此論出自往圣,賢弟溺得逼真!他是對的,他深諳自我的潛規則,即:每一個較真的詩人,都注定把自己驅向語言的戰場。
1994年的上海,我剛開始寫詩。整整一個冬天,凜冽而微腥的海風中,我自覺行走云端,輕盈而高大,枯燥如水泥地都生動而透明——我深刻懷疑自己因主角的獨特性而被神啟……而事實證明,那與青春有關,與生命的濃烈有關。當然,多年之后,當詩已沾染愛恨情仇、生與死、混亂與秩序、浮腫肉身,我又固執地認為:讓你體驗天空,是為了將你陷入大地。
看嘛,這種自珍自愛多么堅忍不拔,同時充斥著人性的鉆石與污穢。我們給了自己暗示的火箭,以慌亂的加速度來脫離下墜,于是有人當了真,有人拼命滿足它,有人被現實打了兩個耳光后發覺自己是芻狗,有人眼睛睜得更大,有人把它忘了……反正都是一副智商欠缺的人類狀態。
事實上,在通常的職業上滿足自己的獨特性和試圖成為一個更好的詩人在生命層次上又有多少差異呢?想清楚這點,我覺得我終于可以區別于懵懂的本能,雖然其結局并不一定比懵懂舒適。嗯,我其實沒說為什么寫詩的問題。
胡戈·弗里德里希在《現代詩歌的結構》里非常粗魯地說:“不和諧音的張力是整個現代藝術的目的之一。”其實他是在說自波德萊爾以后,抒情手段向現代性技術文明的轉向,在技術化與商業化的文明中,詩歌如何成為可能。然而,米沃什對象征主義引發的詩歌導向非常不認同,他抨擊了現代詩學的一個宗旨——“認為真正的藝術不能為普通人所理解”,最終導致詩歌在“為藝術而藝術”的道路上淪為小丑。
現代性的復雜程度與日俱增,單一的手段和技術很難完成我們的時代復調,相互爭議的語言方式恰恰是詩人們散發的觸角。但基于勇敢的詩人注定要去抵消神圣的律法這一基本事實,必須承認這樣一個顯著特征,即我們所處的文明,在信息量表達上、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上、在生活節奏行為范圍上,我們已與幾千年來的人類不一樣。百年來,新的文明方式幾乎是瀑布一般傾瀉在人們面前,我們的思維、身體在這瀑布前其實呈現了大面積的遲鈍。至于詩,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現代主義興起,詩歌的語言方式從經典的抒情感性移向了復雜的理性構建,這屬于合理的邏輯。我說的不是什么語言上的趕時髦,甚至這都不算時髦,我說的是詩人這種人類古老的職業為何沒有消失,甚至在未來也不會。嗯,我其實也沒說怎么寫詩的問題。
詩人與工程師大概是“本質的自我”與“存在的自我”之間的關系,它們一個與人性特有的東西有關,另一個與生存的物質框架有關。這兩種自我的關系,其實在人類中具有普遍性,它并不因詩人與工程師兩種職業傾向顯得特殊。因為,我們絕大部分人,都處在這樣相似的心理格局與現實框架中,并出于理智、出于責任,去完成自己生命中理所應當的那部分。生存其實本就是精神關系的試驗室。這種試驗大概率上談不上成功,當然也很難定義失敗,它只是一種試驗的進行時,一種呼吸的狀態,且只能用開始或結束來概括。
那么,朋友們認為我的詩有設計感應該是對的,畢竟是一個做設計的工程師嘛。設計的思維方式必然在我詩歌的搭建方式中露出得逞的笑容。其實設計有一個更美好更庸俗的詞語:創作。但我對這個詞天生有些敬畏,這個……還是莫高估自己了。
但設計并不能完全注明一首詩的誕生過程,于我而言,如果一首較長的詩,大約在它的前期是有設計的,但往往隨著詩行的不停增加,建筑物會產生自己的美學需要,甚至開始產生自發搭建新結構的能力,這大概是詩人最幸福也最痛苦的階段,因為你從語言的渾濁中把它打撈起來,它開始長得不像你想象的樣子,但是又是多年后你喜歡的樣子,它是活的,它在你手上擺動、掙脫,將偉大的力反饋給你。
幸運的是,在美學價值上,詩的意外往往會大于標準化的設計。對于工程師,標準有最基本的本能:更簡潔、更高效。標準是工程師最喜歡的工作界限,在這個界限之中,所有猛獸都按程序驅動,規范而無害,猛獸的一切行為都在預設的極致之內。但于詩人,最好的方式是遇見標準,然后再笨拙地翻過去。當然在此之前,詩人嘔心瀝血的,只不過是為了抵達那堵標準圍墻的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