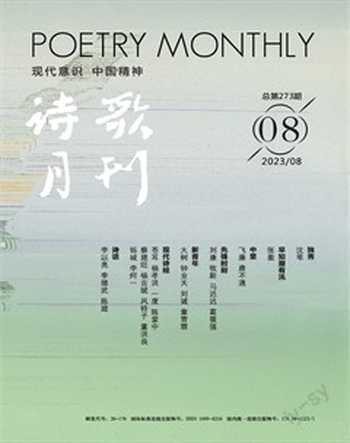青海記
宋長玥
初冬上南山所見
一個人在天上,另一個人也在天上。一個人往西和雪相遇,
另一個人被風吹遠。目之所及,他們經過了青海湖,但悲傷的大地繁錦沒有謝幕。等他們到達黃河沿岸,也許能看見一只放生的羊,和十年前我在黃昏中問路的紅衣老僧。
那些空他們早已經歷。星星打尖的湖泊夜色縹緲,再荒也不為所動。半夜里會有一個人從附近的小鎮醉酒歸來,路邊薄雪泛光,犬吠遙遠。那時我不對自己說苦,現在也不再告訴夜行人所有的痛。
兩人最終會去哪里?我在漏風的帳篷睡過一夜的珠穆朗瑪峰河谷?也許去日喀則黃昏就關閉了木門的寺院?或者在途中走散,為尋找彼此花費一生?
兩個人,其實是兩片狀如人形的白云。
它們飄過南山,高遠的陰影投在大地上。
初冬晴日,上南山
風的右面,是一片荒蕪之地:陽光的孩子們流落山巔,找不見一匹馱動夢的馬。兩只伯勞在樹叢下喋喋不休,不贊美生活,也不詛咒生活。遠方不曾到達,會不會比想象更美。
荒蕪之地
不安靜。
我在風的左面。春天十幾朵花在那里聚會,她們無所顧忌,
有的白得耀眼,有的紅得要命。過了秋天,命運不分好壞,
都在泥土下安身。唯有魂不死不滅,長守南山,靜靜恭迎大雪。
我至今能一一叫出她們的名字,獻給親人的,獻給戀人的,獻給生命的,獻給死亡的。人把心思交給她們,花最后低下頭,
人間更空了。現在,我更思念六月的一只蜜蜂
它在一朵花和一朵花之間奔忙,歸巢,直至累死。
人們嘗到了甜。
在大武
從花朵的唇語中醒來,背負愿望的男人被空馬鞍驅逐。
這片大武僅有的沉靜,那么空,那么遠。他的另兩個自己打開雪山,一個去格曲河背水,一個用三塊石頭支起鍋灶。沒有人知道,男人昨夜獨自走過草原:高過三千七百米的地方,還不能抵達雪線,剛好放得下他不多的生活。
巨大的云朵靜靜滑過天空。每一天都是自己的朝圣。而我終將為他保守一生的秘密:遠方和故鄉,每一個地方都無法讓靈魂安寧;那些灼熱的火,會不會讓他內心清涼。
太陽啊,
我多想聽您叫我一聲:孩子!
阿尼瑪卿山區
一只蝴蝶飛向雪山。一架斑斕的生命戰車,掘開黃金大道開向太陽。九月曠域,白色巨人俯瞰疆土,感到日月煌煌,人間清寂。有深遠的意蘊和不可言說的空無。
不遠,雪豹望著蝴蝶的背影,露出不易察覺的微笑。他縱身躍下斷巖,聽見風暴和擂鼓交混。聽見蝶翅上面有裂帛聲。聽見一塊塊冰川石在大野盛開驚心。
瑪域
月亮爬山,
白銀下雪。
九月在阿尼瑪卿山巔掛起燈籠。花朵旁邊的帳篷,馬鞍尋找騎手,騎風的人把黃金放在心里,把鐵鑄進骨頭。
瑪域,巨浪上的風和空。靈魂貼金,親人只剩下未來。草原打開:那些王,在夢中遇見雪蓮。遇見雪。遇見被鷹帶走的故人。遇見他們被歲月引導,自已修筑自己的祭壇。遇見大野懷抱河床。秋天戴玉,生活含苦。趕路的人翻過山崗,還走在大地上,仿佛太陽的另一個人生。
黃昏,從南山下走過
世界上不止有疲憊的靈魂。
還有男人肩上奔跑的風。
它從南山上下來,在青唐走門入戶。
人類的罪惡和慈愛,兩扇窗口同時打開,它穿過去,想努力保持最初的純凈,但沒有成功。
這一生,我們都會失敗:沒有誰是干凈的,混跡塵世,
一切被時間鍍滿了銹跡。
并非來不及愛:山巔上薄薄的月光,整個夏季吹拂的清風,一次別離和相聚的期待。我們輕易放棄了許多想做的事情,
唯獨沒有祈求命運。就像今夜,月光靜靜站在慈航渡口,我只身匹馬走過南山下面。
宋長玥,青海人,中國作協會員。有作品發表于《詩刊》《人民文學》等,著有詩集、散文集10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