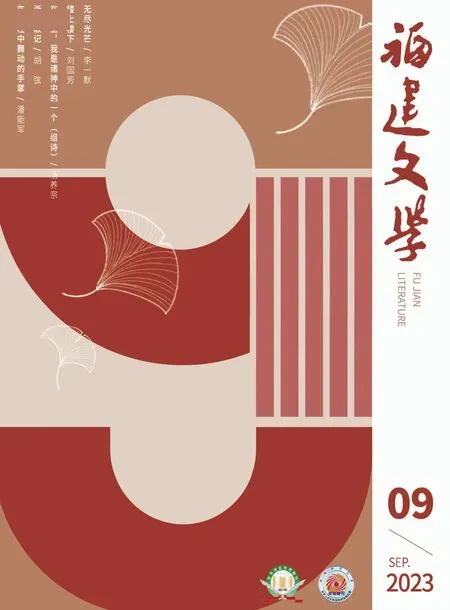外石村邊綠蓁蓁
戴 健
1
1990 年8 月底,從師范學校畢業的我,被分配到富屯溪畔的衛閩學區。我到衛閩學區報到,才知道自己要到外石村完小任教,開始了我的青蔥歲月。那時生活的點點滴滴都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后來,我離開了外石小學,調往其他學校任教。
離開外石小學第30 個年頭的初夏,我再次回到了外石,既感到無比的親切又覺得有些許陌生。記憶中村子東邊有一條沿著稻田邊緣鋪設的沙石路面的馬路,馬路西側是一排土坯房,或以泥墻,或以籬笆圍住院落,均搭著瓜架。整個夏天,瓜架上總是吊著南瓜、葫蘆、苦瓜、冬瓜……而今,曾經的沙石鋪面的馬路已無蹤影,路旁的院落已無當年的風貌,甚至已是一塊空地。外石村部地址還在30 年前的位置,新蓋的二層辦公樓很整潔,設在辦公樓一層的“農家書屋”雖然不大,卻氤氳著濃郁的書香氣——書架上擺放著各類書籍,桌上擺放著書寫用的筆墨、宣紙、鎮尺、硯臺。走出村部,我們順著一個長坡來到古樹林的最東頭。佇立在林間的水泥路上,望著眼前熟悉的景物,特別是向西看到不遠處的小山包——外石小學所在地,我感慨萬千,情不自禁想起第一天到外石小學報到的情景。
那天,我是在衛閩中心小學被外石小學校長接上手扶拖拉機的。手扶拖拉機在沙石路上行駛、蹦跳,而坐在車斗里的我和校長蔡福美,卻如米篩上的米粒跳動,并享受著拖拉機噴出的濃煙、高分貝的噪音和拖拉機行駛中掀起的沙塵。雖然只是不到20 分鐘的路程,可是到了外石村時,我的行李上已沾滿灰塵,用手指篦一篦頭發,指甲間竟然滿是細小的沙粒……我用青澀的目光,度量著嶄新又艱辛的生活。
開拖拉的師傅幫我把行李從拖拉機上取下,朝我咧嘴一笑,點了點頭,牙齒在黝黑發亮臉龐的襯托下格外潔白。拖拉機在學校操場轉了個圈,冒著黑煙跑出校門。
外石小學獨立坐落在外石村西面的一個小山坡上,校門朝東,校園四周砌了青磚圍墻。校園內靠西面蓋了兩棟建筑,一棟是兩層的教學樓,一棟是平房——老師和學生的宿舍。教學樓前是操場,有一簡易旗臺,中間豎立著一根鋼制旗桿;操場北面圍墻前,生長著一排整齊的桃樹。操場上無序生長的雜草,翠綠而葳蕤;桃樹綠葉婆娑,幾只不知名的小鳥在枝間跳躍、歡鳴;幾叢蘆葦的長葉,從圍墻外探進墻內,與桃葉相互輕撫;幾只蘆花雞在墻腳用爪子扒拉著泥土覓食,偶爾抬頭,巡視一番,繼而低頭刨土……面對此情此景我不由得想起宋代釋智圓的詩句:“檐前棲息傍蒿叢,風雨司晨爾有功。”我想,自己會在田園風光、熱鬧與寂寥交織的環境里生活很長的一段時間,但心中卻是火熱的,對三尺講臺充滿了渴望。因為,當時我們能考上師范被稱作“跳農門”,在師范上學不但不要交學費,每個月學校還會為我們發放飯票和菜票,既受村上鄰里的羨慕,自己也感到自豪,極珍惜來之不易的上師范的機遇。
到外石小學的第一次晚餐,我是在校長家吃的。校長是外石村人,在村里有一棟夯土墻、木架構的二層樓房,在學校也有一間宿舍。在淡淡的暮色中,我拘謹地跟隨蔡校長行走在前往他家的路上。從學校通往村里的道路,在村北面的一片狹長的古樹林中間。身材瘦高的校長,邊走邊給我講述這片古樹林的來歷:古樹林不是天然林,而是人工栽種。外石村位于富屯溪畔,數百年前,村子常被洪水洗劫,導致房毀人亡。村民們痛定思痛,決定沿富屯溪畔種植香樟、楓香、桂花樹,在樹木的空隙間栽種箬竹,以防洪水的侵襲。這些樹木成林后,果然阻擋了洪水直接沖擊村舍,保護了村子的平安,被村民稱為風水林。
我指著路邊的一個巨大的樹兜說:“校長,這片防洪林對村子有益,為什么還有人砍伐這里的古樹呢?”
“這里的古樹是不可隨便砍的,”蔡校長是莆田移民,用帶著濃重鄉音的普通話對我說,“只有村里造渡船才能砍伐林中的枯萎的香樟樹,或是香樟樹的大枝丫,其他概不可砍伐。這一鄉俗一直傳承至今沒變。”
之后的三年時間里,我幾乎每天都要在古樹林的泥石路上走上一兩遭,看一看牛兒在林邊悠閑地吃草,聽一聽群鳥無拘無束地歌吟,聞一聞野花浮動的清芳……
2
當年,我在外石教書時,很喜歡散步。那時村里有一條水渠。我每有閑暇便會在渠岸上走走,極為愜意——一路可見水團花、醉魚草、苘麻、萱草、蓼藍、風車草在風中搖曳,彩蝶翩躚,蜻蜓點水;地面匍匐著地菍、鼠曲草、馬蹄金、紅錦草、五行草,各得其所;清澈的渠水里,野生的白條、馬口、鯽魚在嬉戲,優哉游哉。渠邊陰濕處的石塊上,長著水靈靈的苔蘚和石松,總吸引著我駐足伸手去撫摩,瞬間心清氣爽。渠水流至村邊,沿著村子邊緣畫了一個半圓,之后注入富屯溪。村中的男人在渠中汲水澆菜,大嬸、大娘、小媳婦們則在這里浣衣、洗菜,嘰嘰喳喳、嘻嘻哈哈,把日子過得有聲有色,有滋有味。

而今,靜靜地徜徉于村中的小巷間,河卵石鋪就的路面,凝集著過往時光的包漿,厚重而光滑。一座座老厝的墻基,也是由河卵石砌壘而成,一道道縫隙間爬滿青苔,偶或長出一兩株矮小的蕨萁。間或在逼仄的風火墻的夾道間,走過幾只雞,或是跑過一頭伸著舌頭的黑狗,整個村莊顯得恬靜而安寧。水泥路邊的菜園子則是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象——辣椒青翠欲滴,黃瓜的藤蔓上掛滿碩果,紫色的茄子光滑油亮……面對眼前的景致,我不由得想起在外石小學任教時與蔬菜有關的事。
在師范學校學習時,一上完課就可徑直到食堂打飯,而走上三尺講臺后,每餐吃什么菜都得自己操心。外石小學的老師和學生一樣用鋁制飯盒在學校簡陋的食堂里蒸飯,菜則需要各煮各的。外石村沒有菜市場,也沒有圩場,家家戶戶的蔬菜自給自足,偶有豬肉可買。我要吃蔬菜和鮮魚,便要到中心校所在地衛閩購買,那里不但每天有菜買,還有每5 日一圩。因此,只要有空我就騎一輛吱吱呀呀響的自行車,乘渡船過富屯溪,再騎一段坎坷的機耕路,到衛閩趕圩,以滿足口腹之欲。然而,一旦陰雨連綿,或恰逢暴雨,洪水漲溪,通行不便,我便只能到村里的小賣部購袋裝榨菜、散裝紫菜,草草對付一日三餐。
轉眼到了第二年的陽春三月,發生了怪事——有人三天兩頭大清早把新鮮的蔬菜放在我炒菜的桌上。起初,我還以為是其他老師把蔬菜遺忘在我炒菜的桌子上,經過詢問,都說不是他們落下的。沒有得到滿意答案,激發了我尋求真相的好奇心。我經過認真觀察,發現教師辦公室的一扇窗戶正對著我的宿舍,站在窗戶邊就可以將我宿舍前的情景看得一清二楚。
我決定一大早站在辦公室窗邊觀察,解開謎底。那天早晨,我佇立在辦公室窗邊靜靜地等待。只見班上可愛的小不點,背著書包,手上拎著一個編織袋,走到我宿舍窗前,看看左右沒人,迅速掏出袋中的黃瓜和薺菜,放在我炒菜的桌子上,轉身躡手躡腳地離開。體育課自由活動的時候,我找到小不點談心。我微笑地看著她說:“小不點,今天一大早,你來學校做了什么呢?”

“沒有做什么啊!”小不點先是吃驚,轉瞬笑瞇瞇地說,“老師,我是來得早,真的沒做壞事。”
“老師沒有說你做壞事呀,”我笑著提醒道,“那黃瓜、薺菜是怎么回事?”
小不點看瞞不住我,撓了撓頭說,黃瓜和薺菜是她拿來的。她停頓了一下,接著說,同學們把老師沒青菜吃的情況,說給了爸爸媽媽聽,幾個家長一合計,決定輪流讓孩子為我送青菜。聽了小不點的話,我喉嚨發緊,眼睛有些模糊,心里暖洋洋的。
我到幾位同學家中家訪,家長熱情好客。我和他們交流了加強家校聯系,進一步提高孩子們學業成績的話題后,請他們不要再讓孩子為我送青菜了,麻煩。他們卻不依,說:“你一個人離家到我們這兒來教我們的孩子讀書,不容易啊!我們拿一點自己種的青菜給你,只是表達一點自己的心意。你不拿我們自己種的青菜就是看不起種田人。”青澀的我,面對樸實的話語,真誠的表情,純樸的民風,竟然不知如何應對,一時語塞。
家訪回來,學生們依舊送蔬菜到我炒菜的桌上。吃著流淌著泥土一樣質樸情懷的新鮮蔬菜,我只能用倍加努力的教學,回報這份深情。外石的房舍、街巷、山水、田疇,一個個鮮活而樸實的身影印刻進了我的心扉。
而今在燦爛陽光的陪伴下,我重回外石村采風,行走在熟悉而陌生的街巷、阡陌間,我對外石的情感依然如故。
3
從村中的小巷再次步入古樹林邊的水泥路,一棵棵高大挺拔的古樹撲面而來,樹冠如蓋,為我們撐起一片陰涼。古樹林依村傍水,長約1300 米,寬約60 米,面積約118 畝,多少年來,既是外石村阻擋洪水侵害的守護神,也是村民們心中的一種寄托,孩子們的樂園。古樹林中有香樟、楓楊、楓香、苦楝、樸樹、苦櫧、蕈樹、八月桂,不同種類的樹風姿各異,四季韻致不同。
在外石小學教書的3 年里,無論是學生在校的時光,還是校園寂靜的節假日,傍晚只要沒有下暴雨,我都會與幾個學生一起,或踽踽獨行,在富屯溪畔散步,在古樹林里聽鳥兒在濃密的樹冠上咿咿呀呀、竊竊私語,我拍拍手,樹上竟然安靜下來。有時會觸景生情,口占詩詞。一天夕陽西下,一位挑擔的老人在古樹林西頭的渡口想乘渡船前往對岸,卻沒看到渡船,我見景生情,吟詩一首《富屯溪畔獨步》:
躑踏殘霞野草蓬,清風皺水漾歸鴻。
幽然古渡無舟影,攏手高呼一擔翁。
回到宿舍,我意猶未盡,欣然提筆蘸墨,將詩題寫到宿舍的墻上。在寂寥中用筆墨尋找樂趣,生活便有了滋味,有了奔頭。
端午前,古樹下生長的成片箬竹,格外搶眼。細細的箬竹爭先恐后地長出一片片又長又寬的粽葉,翠色欲流。每天清晨都有人踏露采摘箬葉,為端午的粽香飄逸做準備。端午后就進入了汛期。一連幾天暴雨,渾濁的富屯溪水越漲越高,幾乎每年都有一兩次的洪水會漫上古樹林,然而它總是巋然不動,仿佛越被洪水侵襲越強壯,心無旁騖地呵護著外石村。因此,外石村民把它當作村里年歲最長且德高望重的長者敬重,小心翼翼地護衛著它。是的,樹林、河流、鳥兒、魚兒都是有情感的,只要人們真心對待它們,它們也會以自己的方式回報人們。
古樹林四季的美各具千秋。
春天,一場春雨一場暖,雨過枝梢萌新芽。陽春,楓香、楓楊的枝頭滿是新綠,明麗而生意盎然;林間的綠荑已噌噌長長,林畔隨處可見一簇簇的綠茸。香樟在春光的吸引下,也急不可耐地開始零落老葉子,長出新葉兒。知名和不知名的野花盡情綻放,生怕錯過最好的時光。
夏日,一樹濃綠一處景,村樹融合如畫圖。一場晨雨后,我靜靜站立在教學樓二樓憑欄眺望,古樹林霧靄扶搖,外石村上空炊煙裊裊,天地間渾然一幅雋美的水墨丹青。樹林兩端各有一片沙灘。西頭的沙灘如雪鋪陳,潔凈而細膩,有時我會和衣仰躺在沙灘上,什么也不想地望著夕陽西下的天空,匆匆歸巢的鳥兒落入古樹林……古樹林東頭的沙灘與一片河卵石交織在一塊,上面的蘆葦一簇又一簇,不知是沙灘點綴了蘆葦叢,還是蘆葦叢映襯了沙灘,然而它們都是不可或缺的。
秋季,一場寒風一層紅,楓葉紅于二月花。古樹林東頭幾株楓香樹,每到秋天就是這里最有魅力的角色。秋越深,風越疾,楓香枝上的葉子紅得越快,紅得越艷。古樹林東頭橋旁的那棵挺拔又巨大的楓香樹,在天高云淡的天氣里,像高擎的火炬,格外醒目,遠遠就能看得真切。走近看,眼前仿佛被重重紅云縈繞,又如走進色彩斑斕的調色板里,令人驚奇,驚嘆,驚羨。
冬天,一場北風一場寒,葉落成泥更護花。寒風中,放眼望去,大多數古樹的樹冠已然深綠,只有楓香、楓楊的枯葉翩然落地,“化作春泥更護花”。村里的孩子們因為“長尾巴”已躲進洞穴冬眠了,沒有什么可懼怕的,于是一伙伙地在樹林里打鬧、捉迷藏……
而今走進古樹林,古樹林的“古”沒變,它的美卻融入了新元素。古樹林內,圍繞著相逢、相知、相愛、相伴的主題,修建了步道、曲折起伏的棧道,復建了古碼頭。用條石砌筑而成的碼頭,隨勢賦形,樹蔭相掩,水漾石階,樸拙入目,親切滿懷。立于高處放眼量,富屯溪水面格外寬闊,頗為壯觀。順著碼頭石階下至溪邊,伸手撩一撩富屯溪水,涼爽,愜意;看淺水澄澈透明,深水如黛,波瀾不驚的水面下卻是暗流涌動;側耳,我聽到習習的風聲,又仿佛聽到千百年前鏗鏘有力的艄公號子。
古樹林中的210 棵老樹,樹齡最長者已超600 歲,樹齡300 年以上的有33 株。在眾多的古樹中,苦櫧樹生命力極強,心朽了,只剩皮殼也能枝繁葉茂,而它如榛如栗的果實則是村民們的寶貝。每當苦櫧果實成熟時節,孩子們就會三三兩兩去撿拾苦櫧果,拿回家自己放到鍋中炒,起鍋前潑上鹽水。孩子們把炒熟的苦櫧果揣入衣兜,一粒一粒地取出放入嘴,用牙用力一磕,已裂口的苦櫧果便殼仁分離,隨后吐出殼咀嚼果仁,頓時鹽的咸和果仁的苦澀混合在一起,在味蕾上傳遞著孩子們的愉悅……大人們則會將撿回來的苦櫧果實去殼取仁,再將果仁磨成漿,沉淀獲取苦櫧粉。可將苦櫧粉加工成苦櫧豆腐、苦櫧粉絲、苦櫧粉皮、苦櫧糕,既是村民餐桌上的山珍,又是防暑降溫的佳品。
蓊郁的古樹林與富屯溪、水田,形成一塊適應動物棲息的自然環境。因此,古樹林不僅是蝴蝶、青蛙、石龍子等小動物的樂園,還是鳥類的天堂。在這里可遇常見的麻雀、八哥,也可見珍貴的白鷺、紅隼、鴛鴦、戴勝在這里自由自在地生活。
外石古樹林是閩江源頭沿岸今存面積最大的古樹防洪林,是閩江源頭、富屯溪畔最直觀的歷史留存。走進它,我仿佛捕捉到一種美好的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