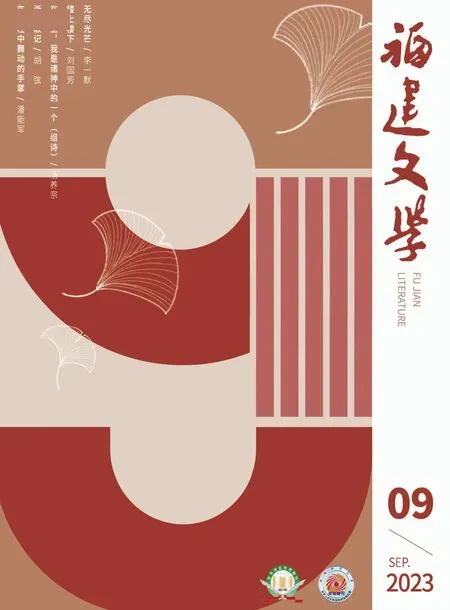經(jīng)驗轉(zhuǎn)換、情感呈現(xiàn)與在地性寫作
——評李迎春長篇小說《故園風(fēng)雨》
趙澤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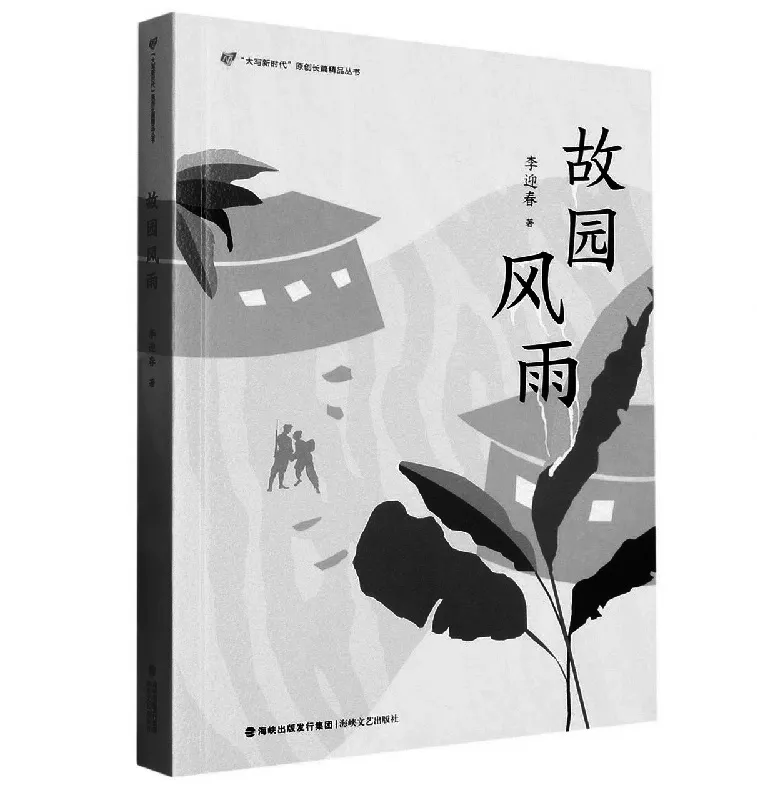
李迎春的長篇小說《故園風(fēng)雨》,以紅色革命老區(qū)龍巖為背景,書寫了閩西人民在歷史巨變中取得革命勝利與和平家園的艱辛歷程。該小說既是對辛亥革命至新中國成立期間波瀾歷史的描寫,也是對革命經(jīng)驗的當(dāng)代轉(zhuǎn)換。同時,作者十分注重情感的呈現(xiàn),多重人物關(guān)系之間流露出令人動容的情感,這種有情的書寫也使得革命題材在當(dāng)代煥發(fā)出應(yīng)有的溫度。而以閩西作為文學(xué)地理坐標(biāo),也使得小說更具在地性寫作的特質(zhì)。我以為,李迎春的《故園風(fēng)雨》不僅為新時代紅土地文學(xué)貢獻(xiàn)了一幅閩西畫卷,同時也豐富并推動了福建文學(xué)版圖的多元多樣化發(fā)展。
1
從辛亥革命到新中國成立,中國的歷史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這是一段啟蒙與革命互相交織的時代,也是血與火鍛造下的歷史。對于宏大歷史與革命經(jīng)驗的書寫,是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一個重要的主題。現(xiàn)代文學(xué)作家中的茅盾、丁玲、路翎、艾青等,他們對革命與歷史的描摹,對于民族、國家與國民的思考,顯示出清醒且深刻的關(guān)切與思索。革命現(xiàn)實(shí)主義題材以及“革命+愛情”的敘事模式,也折射出當(dāng)時作家對革命的態(tài)度以及思考。在十七年文學(xué)時期,革命題材成為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主流。而進(jìn)入新時期后,新歷史小說中的作品多以革命歷史作為背景,更注重挖掘歷史當(dāng)中人的精神主體性。當(dāng)下直接以革命作為推動故事發(fā)展的小說似乎不多見。在李迎春的《故園風(fēng)雨》中,革命成為小說中的主要敘事動力,其中青年一代趙鵬飛、溫潔萍、袁寶清等人成為走向革命的主力軍。同時,作家還塑造了以趙田禾為代表的從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過渡的人物形象。
小說一開始就將時間定格在風(fēng)云巨變的清末民初,隨著武昌起義的打響,一場歷史的突變很快地來到了相對閉塞的閩西山區(qū)。作為家族中留過學(xué)的長孫趙田禾,他思想開放,很早地就投入革命事業(yè)中,在古坊建立了自衛(wèi)隊、藥房與學(xué)校,在醫(yī)療與教育方面為地方百姓提供保障。在這一過程中,他看到了許多軍閥打著革命的旗號去剝削百姓,這也更強(qiáng)化了他想要在各方勢力下保持獨(dú)立性的決心。他對革命也始終保持著一種警惕的態(tài)度,用他的話說:“革命是好的,可我擔(dān)心革命過了頭。唉,只要大家自力更生過好日子了,為什么非要鬧個家破人亡呢?”可以說,獨(dú)立的姿態(tài)使得趙田禾成為多方勢力想要爭取的對象,但他也始終在夾縫中生存,其對于革命的體認(rèn)具有一定的游移性,他本身也是痛苦的。趙田禾的身上“既有作為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一面,也有作為傳統(tǒng)鄉(xiāng)紳守成不變的一面。他的不敢斗爭不敢革命,往往建立在人性理想化的基礎(chǔ)上,具有濃重的烏托邦性質(zhì)”。
雖然,趙田禾本身對革命持有一種距離與警惕,但他明辨是非,在多方勢力的比較中,能真切地感受到共產(chǎn)黨與紅軍是為民請命且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的。因而他始終暗中支持著紅軍以及兒子鵬飛的革命事業(yè),這也顯示出他以及青年一代在國難當(dāng)頭之際,對于民族大義的清晰判斷與深切體認(rèn)。因而對于趙田禾這一中間人物及其過渡狀態(tài)的描寫,既豐富了小說的革命經(jīng)驗,也更加尊重個人在革命面前的主體性與真實(shí)性。從保持距離與懷疑再到逐漸體認(rèn)紅軍,作家寫出了革命經(jīng)驗的多個階段與面向,它使得小說避免落入扁平化人物建構(gòu)的窠臼,顯示出作家對革命的深度思考,也折射出其對于現(xiàn)代革命經(jīng)驗的當(dāng)代轉(zhuǎn)換。
2
革命敘事如何引人共鳴、觸動人心,除了民族大義的彰顯外,有情的書寫同樣重要。在李迎春的《故園風(fēng)雨》中,多重人物關(guān)系之間的情感的鮮明呈現(xiàn),使得革命題材的作品展現(xiàn)出應(yīng)有的溫度。這些情感包含了父子之情、師生之情、夫妻之情,就像是隱于革命敘事下的燭火,看似微弱卻持續(xù)散發(fā)著溫暖,令人讀罷深感動容。
首先值得關(guān)注的,是趙田禾與趙鵬飛之間的父子之情。父與子的情感,其動人之處在于,這種情感有時是矛盾的、對抗的但卻也是深沉的、無言的。趙田禾年輕時,也曾熱血于革命,但后來革命的突變與殘酷使他開始游移與動搖。所以當(dāng)兒子趙鵬飛入黨時,他的反應(yīng)是擔(dān)憂的,他認(rèn)為兒子鵬飛還沒有看到革命的復(fù)雜與流血的殘酷,傳遞出無言的記掛。其后的鵬飛很快就獨(dú)當(dāng)一面,成為獨(dú)立隊伍的負(fù)責(zé)同志,因此當(dāng)二人再見面時,鵬飛甚至覺得父親不夠支持或理解他的革命事業(yè),跟不上革命的步伐。實(shí)際上,父親趙田禾始終支持著兒子的事業(yè),并成為一名“紅色商人”,往蘇區(qū)運(yùn)送一些緊缺物資。最終趙田禾替兒子鵬飛擋下了敵人的子彈,自己倒在了新中國成立前夕。而鵬飛對父親的誤解與不解在失去父親后化為深沉的愛。這是小說中十分動人的場景,表現(xiàn)了父親對兒子無言的奉獻(xiàn)之愛,這種父子之情貫穿于這部小說的始終,突破了一對父子關(guān)系的局限,也濃縮了世間千萬父子之間的情感。
其次,是趙先生與趙田禾之間的師生之情。作為趙田禾的啟蒙老師,趙先生始終將田禾視為己出,趙田禾也在心底將趙先生比作父親,可見二人感情的深厚。當(dāng)趙田禾被多方勢力所牽扯時,趙先生以旁觀者的視角清醒地點(diǎn)出田禾的問題所在:“田禾,做事要果斷。當(dāng)斷不斷,反受其亂。一個小小的古坊,都是親朋好友、宗親族友,千絲萬縷的關(guān)系,編織在一起,你怎么逃得出這人情世故?”趙先生總是在趙田禾困頓之時,為其指點(diǎn)迷津。在趙田禾的心中,趙先生是他的精神之父。更令其欽佩的是,趙先生“雖然沒有見過外面的大世界,但心里卻裝著大境界。趙先生欣賞他對空想社會主義和鄉(xiāng)村運(yùn)動的關(guān)注,更贊成他以實(shí)際行動參與到中國的改造中來”。在趙先生身上,我們看到了傳統(tǒng)的士大夫精神,他們心懷天下大義,目光超拔,思想深具洞見性,也讓我們感受到他們惺惺相惜的師生情感。
愛情則集中體現(xiàn)在青年一代身上。趙鵬飛、溫潔萍、袁寶清三人曾一同去往集美學(xué)村學(xué)習(xí),并共同入黨,投身革命事業(yè),結(jié)下了深厚的友誼。這三人中,趙鵬飛與溫潔萍產(chǎn)生了愛情,最終結(jié)成伴侶。由于革命工作,二人之間只能通過書信來寄托思念。在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誰都無法預(yù)料死亡,書信成了彼此的寄托。書信看似日常,卻在字里行間凝聚了無盡的牽掛。有人說,愛情的本質(zhì)是對抗人的自私,是愛對方勝過愛自己,具有超越性的精神價值。從二人的書信中,我們能真切地感受到這種偉大的愛情力量。文學(xué)是有情的,其不同于哲學(xué)、歷史等人文學(xué)科就在于文學(xué)需要真情實(shí)感,對于情感的描摹與書寫越是真摯,越能夠打通文與人的聯(lián)結(jié),引起讀者的情感共鳴。
3
地理對文學(xué)的影響是巨大的,不同的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會熔鑄于作家的筆端,形成具有地域性特色的書寫,這種影響是潛移默化且深入人心的。“文學(xué)作品中的地理空間,是存在于作品中的由情感、思想、景觀(或稱地景)、實(shí)物、人物、事件等諸多要素構(gòu)成的具體可感的審美空間。它包含了作者的想象、聯(lián)想和虛構(gòu),但是這些想象、聯(lián)想和虛構(gòu)并非憑空產(chǎn)生,而是與客觀存在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空間有著或顯或隱的聯(lián)系。”因而,在烏鎮(zhèn)、湘西、北京、上海、商州、高密東北鄉(xiāng)等地理坐標(biāo)下,無不存在著既具有地域性,又內(nèi)含超越性的優(yōu)秀作家與作品。這是一個文學(xué)與地理相互照亮的過程,地理坐標(biāo)也因作家的書寫而熠熠生輝。
當(dāng)下的福建小說創(chuàng)作不少就擁有獨(dú)特的地理坐標(biāo),呈現(xiàn)出雜花生樹的態(tài)勢。比如,林那北立足于福州寫下了《三坊七巷》《晉安河》《風(fēng)火墻》等,李師江的《黃金海岸》則展現(xiàn)了閩東灘涂由傳統(tǒng)漁村邁向現(xiàn)代城鎮(zhèn)的鄉(xiāng)土巨變,也為他自己以及當(dāng)代文學(xué)找尋到一片嶄新的文學(xué)地理坐標(biāo)。而在李迎春的《故園風(fēng)雨》中,閩西龍巖這一地理坐標(biāo),在近現(xiàn)代歷史中蘊(yùn)含著豐富的紅色革命資源。在龍巖市上杭縣古田村內(nèi),曾召開過具有重要意義的“古田會議”,對中國革命產(chǎn)生深遠(yuǎn)影響。這些成為了作者在地性寫作的最為寶貴的資源。
李迎春的《故園風(fēng)雨》將國內(nèi)大動蕩的歷史背景,凝縮于閩西一隅,其間展示出地方軍閥的割據(jù)與混戰(zhàn)、紅色革命力量的生長以及傳統(tǒng)鄉(xiāng)紳在夾縫中生存等革命背景下的多個狀態(tài)與面向,具有了普遍性和在地性。而這種在地性寫作,在汲取當(dāng)?shù)刎S厚的紅色資源養(yǎng)分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福建的文學(xué)版圖,展現(xiàn)了福建文學(xué)的多元化發(fā)展風(fēng)貌,為新時代紅土地文學(xué)增添了一抹閩西的地方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