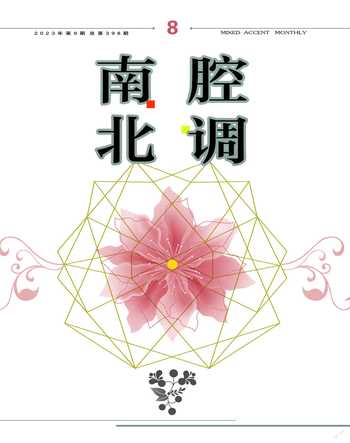“雙線敘事”下的鄉村困境與希望
郭一謹
摘 要:小說《寶水》主要圍繞著明暗兩條敘事線索展開,明線主要敘述寶水村在“鄉村振興”的背景下建設鄉村旅游業的全過程,暗線則深入主人公地青萍隱秘、曲折的私人情感。小說的兩條敘事線索相互交織,一方面反映了當下鄉村發展背后的某種精神痼疾與困境,另一方面又展現了新時代鄉村的新生蛻變與希望。
關鍵詞:喬葉;《寶水》;雙線敘事;困境;希望
喬葉的長篇小說《寶水》問世不久,就先后登上了多個文學好書榜,頗受讀者青睞。作為一位“70后”作家,喬葉此次落筆生根在新山鄉,并與新時代同頻共振,展現了中國現代化鄉村振興的鮮活圖景,也喚醒了無數人心里那份豐饒細膩的情感。
小說依照春、夏、秋、冬的時序衍移,聚焦于中原大地上寶水這個村落,以女主人公地青萍重返鄉村治療“失眠癥”為線索,講述寶水村成功從傳統型鄉村轉變為以文化旅游業為特色的新型鄉村的故事。小說透過“歸鄉者”青萍的目光和思考,寫出了當下鄉村背后的沉疴痼疾、精神困境,并以樸素的筆調,在生動瑣碎的家常中娓娓道出新時代鄉村的新生蛻變、綿延不息。
一、一明一暗的雙線交織
《寶水》有著獨特的敘事手法,不是由單一的明線牽引著讀者,而是有明暗兩條敘事線索。明線緊緊圍繞著寶水村展開,講述寶水村在新時代的背景下完成鄉村轉型的故事,主人公青萍正是這一過程的參與者、見證者、推動者。與此同時展開的另一條敘事線索是青萍的“病”,作品展現了她的原鄉記憶的“隱痛”留存以及重返鄉土的“療愈”過程。明暗雙線交織貫穿全篇,共同推動著故事的發生與發展。
小說開篇即介紹了中年喪夫的主人公青萍因長期受到嚴重“失眠癥”困擾,提前從“象城”報社退休,為休養身心,便應老朋友老原之邀,來到其老家寶水村協助經營由原家老宅改成的旅游民宿,開始在寶水村一年的生活。小說便由此借著青萍的眼睛和心靈,體察著寶水方方面面的肌理層次。寶水村民在鄉村建設專家“孟胡子”、鄉村干部劉大英、秀梅等人的引導、帶動下發展鄉村旅游業,從“孟胡子”來村里設計圖紙、進行局部改造,到青萍替老原接管民宿,籌建“村史館”等工作,人物在明面上直接介入寶水村的變革成為小說的明線。
在寶水村的鄉村旅游業由“亂”到“治”的發展過程中,各家有各家的“生意經”。在鄉村轉型經歷“陣痛”之時,村民們紛紛獻言獻策,積極解決激增的客流導致的有關堵車和停車、生活垃圾的處理、公共衛生服務等問題,大家做好食品安全與保障,和游客打好交道,做到既保障服務又保持盈利。與此同時,寶水這個當下的新農村,也已然進入短視頻時代,青萍和村里的“三梅”共同經營的抖音賬號“寶水有青梅”將富有特色的鄉村生態,通過互聯網媒介平臺呈現在更多的遠方客戶面前,寶水村成功地從傳統型鄉村轉變為以文旅為特色的新型鄉村。
同時不能忽略的是,小說的暗線從故事的開頭就“埋”上了:
“若是明天出門,我今晚八點就會吞下安眠藥,洗漱完畢,兢兢業業地上床臥著,像母雞孵蛋似的,巴望著能順利地孵出一點兒毛茸茸的睡意。能睡著一會兒算是運氣好,睡不著就是分內。”[1]
小說的暗線正是由青萍嚴重的“失眠癥”所勾連起的一系列隱秘、曲折的私人情感。青萍由奶奶一手帶大,童年生長于和寶水村同屬懷川縣的福田莊,十幾歲時隨父母來到“象城”讀書。奶奶和福田莊對她而言,既意味著溫暖、親密、自由的童年經歷,又構成自卑敏感的少女在都市目光的打量下最想洗去的鄉村印記。青萍的奶奶愛“維人”,也擅長“維人”,在福田莊的語境里,“維人”,意指“對各種人脈資源的經營繕護”[2]。從她記事起,甚至在父親出生之前,奶奶“維人”的長繩就已經開始編織,依靠著奶奶“維人”,小門小戶的地家在福田莊支撐起相對穩固的地位,也保留住了起碼的體面。奶奶一輩子所遵循的農村倫理與處事法則,以剪不斷的人情往來的方式,牽縛著在“象城”工作的父親,困擾著城市出身的母親,最終釀成了家庭的悲劇——父親在幫福田莊七娘的兒子借體面的紅色“桑塔納”婚車的途中發生車禍,意外喪生。在青萍看來,來自福田莊的所有麻煩都寄生在奶奶身上,福田莊等于奶奶,奶奶就等于福田莊。多年來,村里人無數次托在“象城”工作的父親幫忙辦事,而奶奶的滿口答應、從不拒絕,讓青萍感到憤怒。她無法理解為什么奶奶非要給父親帶來這么大的麻煩,并把他拖進深淵、陷阱里。父親的死,更是直接導致青萍與奶奶之間難以消除的情感裂痕,而老家福田莊也成為她最深刻和最疼痛的記憶。在城市核心家庭懼怕的“人情線”里所包含著的付出、壓力與束縛之下,奶奶的“維人”被誤解為一種為了維系自家在村里的面子、地位、虛榮心與實際利益的“私心”。即便青萍在“象城”結婚之后,這種城鄉之間的沖突與糾葛所帶來的巨大創傷,也未在平淡的婚姻生活中得以撫平,且伴隨著丈夫的去世更加難以愈合。對鄉村生活既眷戀又怨恨、既懷念又恐懼、既親近又疏離的復雜情感,以嚴重的失眠、多夢的精神病癥長久地折磨著她。
在小說的暗線敘事上,青萍的“病”以及微妙的情感變化并非以順敘展開,而是作為記憶或夢境的“碎片”穿插在寶水四時流轉、晨昏相繼的日常生活里。她實實在在地生活在寶水村里,與村民朝夕相處,變成寶水鄉村式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式的“鄉村農民”。青萍在參與寶水村事務、和村民共同經營民宿的過程中,不得不切實地解決農村生活中的具體問題甚至大小摩擦,因而需要不斷地調動其從奶奶、父親和福田莊村民那里所獲得的鄉村生活的經驗與知識。她能從寶水的“老祖槐”聯想到小時候自家院子里的槐樹,從跛腿的光輝身上看到自己叔叔的影子,從要強得令人心疼的小女孩曹燦身上突然照見童年的自己……在陪九奶睡覺時,能突然從她身上嗅到自己奶奶那種熟悉的、令人安寧的氣息,“仿佛在這一刻,穿越到了福田莊的老宅,穿越到了小時候”[3]。更重要的是,青萍在寶水所體味的鄉村生活,混合著溫厚與無奈、情理與計算的人情世故,最終構成她理解奶奶為何如此重視地緣、親緣的傳統鄉村情感根據。在寶水,她遇到了大英,遇到了秀梅、青梅、雪梅,更遇到了九奶——這位年輕時和自己奶奶有過交情的老人。也是在和九奶相處的日子里,她才徹底地認識了奶奶,明白了奶奶為何熱衷于“維人”,最后她也成為奶奶——為寶水村的人情瑣事忙碌著。“我在寶水村做到這些分外之事,在本質上好像就是對福田莊的彌補性移情。”[4]她曾經在福田莊所抗拒的一切,在寶水卻逐漸自然而然地接受著、包容著。她重新回到了真實的鄉村結構內部,理解了鄉村世界的行為邏輯,進而也重構了“人與我”“城與鄉”之間的關系。
二、難以言傳的沉疴痼疾
一直以來,“鄉村”作為一個積淀著種種社會問題的龐大群體,許多作家紛紛把目光投注到這個難以回避的社會群落中,喬葉也是如此。她的中篇小說《最慢的是活著》通過“我”的視角講述隱忍、勤勞卻深受中國男權主導文化壓抑鉗制的奶奶的一生;長篇小說《拆樓記》的敘述者“我”帶著城市知識分子的目光審視鄉村的落后與愚昧,并懷著一顆悲憫之心看到了鄉村背后的生存困境。
《寶水》延續著這一話語,小說以主人公青萍的視角,展現她原鄉記憶的隱痛以及這背后所暗藏的種種鄉村困境、沉疴痼疾。青萍奶奶的“維人”,從表面上看是傳統鄉村生活中維系鄰里關系的紐帶,實際上折射出的卻是鄉村背后的某種生存艱難。青萍的爺爺在兵荒馬亂的年月里從了軍,奶奶一邊勤謹恭敬地侍奉著公婆,同時又提心吊膽地盼候著爺爺。在那個年代,奶奶作為鄉村生活中的弱勢存在,不是被人摘走剛剛變紅的棗子,就是被偷走垛得整整齊齊的柴火,日子過得如履薄冰,卻沒有實力撲上去與對方撕個高低。新中國成立后,本以為很快就可以過上安生日子,爺爺卻不幸在解放大西南的戰爭中犧牲,從此奶奶成為“光榮烈屬”,獨自撫養著年幼的父親和剛剛出生的叔叔,正是因為得到了鄰里鄉親們的不斷幫扶,日子才漸漸好了起來。在某種程度上,奶奶的“維人”是鄉村底層最無奈的生存之道。而當父親大學畢業,在“象城”立定腳跟后,奶奶更是抓住這個出息了的長子繼續她的“維人”,一件一件地給村里人辦事,這也是在進行道義上的人情回報。
在福田莊,“最會講理”的奶奶正是憑借著在家長里短中寬解人心的本領和在“象城”工作的父親對鄰里鄉親源源不斷地幫扶“維住了人”,使得地家成功處于村里的“上層”。“人情似鋸,你來我去。”[5]這是她的嘴邊話。奶奶看重的是“你來我去”里的割舍不斷的情感紐帶,這是鄉村生活的基本倫理要求,既是回饋與報償,也是預支和交換,更是相互依靠、信任、包容的共同體生活。對于奶奶和福田莊來說,重點是“你來我去”,然而對于青萍的小家庭而言,重點卻是“人情似鋸”。“被鋸”,就意味著無窮無盡的疼痛。即便父親已經接受過大學教育,也無法擺脫這種強大的舊式鄉村倫理。他被來自福田莊的各種復雜人情線捆扎著,陷入泥潭似的深網,在以奶奶為中心的傳統鄉村生活邏輯的要求下一件件地給村里人辦事,甚至最終喪失性命。然而從某種程度上看,父親的死卻是他作繭自縛、自作自受,是“自殺”:早年間青萍叔叔結婚時,父親主動借來一輛“破天荒”的吉普車當婚車,由此便在村里開了頭,“找婚車”便成為村民心中父親能辦到的重大事件之一。起初只是吉普車,后來發展成小轎車,最后甚至挑起了顏色,必須要紅色的小轎車。在青萍看來,如果當年叔叔結婚時父親沒有借那輛吉普車,便不會有之后的幫七娘的兒子借紅色“桑塔納”,他做的這些也許是為了討奶奶歡心,也許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也許兩者兼有之。但他已經死了,一切都不得而知。
在小說的敘述上,父親、奶奶、福田莊,構成青萍隱秘、疼痛的原鄉記憶,她曾經拼命從福田莊逃離到“象城”,在城市中漂泊,追求著事業、金錢、欲望,但無論她多么努力地融入,其外在和心靈都無法徹底地與故鄉割裂,都被深深打上了原鄉的隱痛烙印。一次偶然的機會,青萍來到寶水生活,并在田間勞動中不斷地進行舊日回溯,在植物菜蔬里平復了內心的傷痛。在一年四季的更替中,她聯結起上自老人九奶、下到青年香梅等農村女性的歷史記憶和生命經驗,也見證了寶水的綿延不息與新生蛻變。但與此同時,隨著青萍一步步深入村民生活,寶水村的“暗面”也借著她的眼睛和心靈凸顯了出來。
寶水村主任兼支書劉大英性格直率潑辣,表面上看大大咧咧沒有城府,實際上凡事拿捏得當,進退有余。然而,大英強悍干練又聰慧狡黠,卻承受著女兒嬌嬌“怕見生人”的癔癥帶來的難言之痛。嬌嬌的病來自早年間進城打工時遭到侵犯后難以愈合的精神重創。村里孩子沒上過多少學,心思又簡單,到城里打工多不適應,精神病便成了近年來周圍村莊里最常見的病癥。美麗風情的香梅長期遭受著丈夫七成的家暴,但她沒有選擇大眾化的婦女保護渠道,而是以青萍難以想象的方式秘密謀劃、反戈一擊。她先是私會初戀男友,后是設局致七成摔傷腿腳,趁機對他大打出手。“不是不報,時候未到”[6],香梅選擇了用以暴制暴的方式,而非知識分子式的維權,維系著他們之間恐怖的、平衡式的婚姻。
小說看似筆調溫和,實際上觸及鄉村的某些共性、重大的問題,如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的矛盾沖突、留守兒童的困境、家暴等。小說包含著鄉村生活的種種真實質感,同時也迂回地呈現出農村的另一個“切面”。《寶水》在敘事雙線的互相交織、牽制下折射出當代鄉村的種種難以言傳的沉疴痼疾,無論是福田莊的奶奶、父親,還是寶水村的嬌嬌、香梅,都反映出鄉村背后的某種生存艱難和精神病態。喬葉以真實但不尖銳的方式揭露鄉村存在的切實問題,在她的筆下,鄉村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精神困境的存在地。
三、生生不息的鄉土希望
“鄉村”一直以來都是文學的重要表現領域之一,文學史上也誕生了諸多表現農村題材的優秀文學作品,比如《故鄉》《創業史》《平凡的世界》等。近年來“鄉村振興”的國家發展戰略,“無疑需要以文化作為支撐,才能使社會各界在形成共識、凝聚人心和整合力量的同時,進一步強化農村文化建設”[7]。時移世異,如何用文學形式反映新時代中國鄉村的巨大變化,重新發現鄉村生活的審美價值,開拓出文藝新境界,是新時代文學從業者需要探討的課題。
與《最慢的是活著》《拆樓記》等作品不同,《寶水》的出色之處就在于喬葉在批判鄉村沉疴的同時,更有著對鄉村空間溫情的懷戀以及對鄉村發展的憂思和展望。小說沒有從概念、觀念出發,而是實實在在地潛入農村生活深處,寫活了人物,寫足了細節,呈現出新山鄉生存與振興的時代故事與當代鄉村建設發展的可能路徑。
初到寶水,青萍并不愿意真正進入鄉村內部,因為父親間接死于“人情”,所以她對鄉村的“人情”社會充滿了偏見,她只想當一個寶水村的“旁觀者”,不過度介入寶水人的生活,又不過于冷漠。起初她慶幸自己是個“外人”,然而寶水村的四季變化與自然風光,撫慰著她的心靈,也緩緩地改變著她的想法,漸漸地她也時常覺得自己在“里子”里了。在鄉村里“悠”著,和村民一起“扯云話”“挖茵陳”“吃懶龍”“數九肉”“打艾草”,聽九奶講她和老原爺爺的情感往事,了解她對心上人堅貞的守望和踐諾,包括九奶最后的離世和“喜喪”,這些日常的村事和鄉間生活、傳統的風俗與民間文化,都在改變著她的故鄉記憶,并在潛移默化中療愈著她。“對于青萍而言,故鄉福田莊承載了她的創傷記憶,如同一個噩夢般的存在。寶水則是一劑良藥,帶給青萍寶貴的治愈感。青萍年少時,不理解村里人為何值得她奶奶付出,而她十幾歲時的困惑,直至四十幾歲時才在寶水村得到了解答。”[8]通過在寶水的療愈,一個原本對生活心灰意冷的中年女人,最終和比認識丈夫還早、給自己介紹過對象的老朋友老原在九奶“你倆好了沒有”的牽線下“身不由己”,成為戀人。至此,青萍完全成為鄉人眼中“寶水村的女人”,真正地在“里子”里了。
在小說的文本鋪陳中,作者用四季更替的方式講述著寶水的故事,不厭其煩地書寫著鄉村的自然風景與風土人情。在寶水,招呼客人到自家吃飯不用四碟八碗,就是添碗水添雙筷子的事;誰家殺只雞,殺只鵝,都會叫上鄰居一起熱熱鬧鬧地吃上一頓;前來支教的研究生周寧和肖瑞為村里的孩子開辦“性教育”知識講座;誰家有困難需要幫忙,能搭把手的事就絕不冷漠——正如九奶所言:“人在人里,水在水里。活這一輩子,哪能只顧自己。”[9]這句話道盡了人與人之間最本質的情感和聯系。
作為“美麗鄉村示范項目”的寶水村,新綠初萌,春花初綻,水清路暢,屋舍整潔。寶水村民在“孟胡子”、大英等領導班子的帶領下,通過民宿民居、高效農業、戶外拓展、旅游經濟等各種途徑,優化了農村環境,提升了服務意識,不僅讓村民擁有了更加幸福的居家生活,也讓游客獲得了更加美好的鄉村體驗。寶水村的面貌日新月異,發展突飛猛進,希望的種子在寶水的大地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當然,舊的鄉村文化倫理道德、農民傳統的生活方式和思維習慣,和新時代背景下的“美麗鄉村”建設,每天都會發生意想不到的糾葛、矛盾與沖突。散漫的生活習慣、利己主義、追逐華麗裝飾的心思與崇尚自然、淳樸、清潔、爽朗、高效、有序的鄉村建設的沖撞、抵抗與纏繞,都在寶水時時發生。青萍、大英、 “孟胡子”、楊鎮長、王主任、老原等人都參與到了這項事業中。除此之外,青萍還負責籌建寶水村“村史館”等工作,這些都讓她真實見證了新時代城鄉之間的流動、互動、碰撞與融合,感受到了新時代“美麗鄉村”建設的艱難、曲折和復雜。
在《寶水》中,作者幾乎完全摒棄了“陽春白雪”式的辭藻,而是選擇大量使用河南方言土語,比如處理人際關系叫“維人”、聊天叫“扯云話”、喜歡叫“景”、夸人出色叫“卓”……這些土話作為喬葉“獨特的母語”,更帶著淳樸、溫度與感情。這些方言的介入,大大激活了小說的動感,也使得小說帶著濃郁的泥土氣息,顯得更加“接地氣”。喬葉的老家在河南焦作,因此她把位于太行山深處的寶水村作為小說寫作的核心,在《寶水》中,喬葉給鄭州另起了一個名字叫“象城”,老家焦作叫“予城”。“予”是人稱代詞,相當于“我”,《寶水》中的敘事角度就是第一人稱“我”,而“象”和“予”合在一起,就是“豫”。如喬葉所言:“我‘敝帚自珍地喜歡著《寶水》里的這些地名。人到中年,離家鄉越來越遠,而寫作卻有回歸跡象,故鄉的根一直跟隨著我。”[10] 為了寫好《寶水》,喬葉經歷了長期的“跑村”和“泡村”,走進真實的鄉村生活現場,深入鄉村生活內部,和村民生活在一起,如此才寫出了鄉村振興的艱難和復雜,以及在這艱難性與復雜性中產生或成長的各個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
結 語
生活的“寶水”是天然的恩賜。小說名字“寶水”一語雙關,既是村名,也包含了生活是創作的寶貴源泉的含義。喬葉經歷了長時間的“跑村”和“泡村”,積累了大量鮮活有趣的素材,由此才寫出了新農村建設、新山鄉振興的出色之作。與此同時,“水象征著特別寶貴的民間力量,就像寶水村民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可以爆發出很多智慧和努力,很像山間的泉水,可能特別細小,但是匯聚起來就能成江成河。”[11]
《寶水》通過一明一暗的雙線敘事,寫出了當下鄉村的困境與希望。鄉村固然是某種精神困境、沉疴痼疾的存在地,但小說也借著地方風情、文旅資源豐盈了失落的鄉土精神。在某種程度上,被荒廢了的農村重新恢復活力,吸引著更多青年人回到農村發展,這既寄托了喬葉對中國新農村發展的期望,也開啟了一種鄉村新書寫的可能。
參考文獻:
[1][2][3][4][5][6][9]喬葉.寶水[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2:6,189,278,345,195,350,417.
[7]饒曙光,蘭健華.共同體作為方法:鄉村振興主題電影的高質量發展路徑[J].長江文藝評論,2021(03).
[8]顧學文,沃佳.“新鄉土小說”系列訪談︱喬葉:“巨變”原是在生活中點滴發生的[N].解放日報, 2023-02-25(05).
[10]張帥.喬葉:虛構寫作 抵達現實[N].大公報,2023-04-03(B1).
[11]李喆.喬葉:誠實地去傾聽,樸素地去寫[N].北京青年報,2023-01-09(B01).
作者單位:寧夏師范學院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