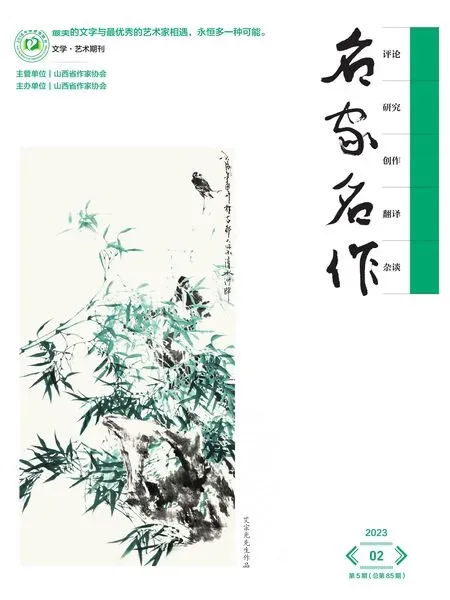從《文心雕龍·程器》看劉勰的文人人才觀
王開慧
《程器》是《文心雕龍》的最后一篇,從形而下的角度探討了文人人才的構(gòu)成要素。劉勰認為,文人人才應當是《周書》中所說的“梓材”之士,“梓材”,劉勰給出的解釋是“樸斫成而丹雘施,垣墉立而雕杇附”,即良木涂上紅漆,墻壁筑成后加以粉飾,既要求有使用價值,又能夠有所粉飾裝點。所以,理想的文人也應當如同“梓材”一般,“貴器用而兼文采”,即能兼顧器用與文采,這樣的文人形象無疑與儒家對文人“文質(zhì)彬彬”的要求一脈相承。劉勰在《程器》中對這種文人人才又在德行、個人能力與現(xiàn)實目標三個方面進行了深入探討。
一、德行“無玷”
劉勰首先討論了道德修養(yǎng)與文人的關(guān)系。劉勰的論述從對魏文帝“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的反駁開始。魏文帝在《與吳質(zhì)書》中說:“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jié)自立。”古今文人大都不顧小節(jié),道德上有瑕疵,這種批判是對整個文人群體的批評,因為曹丕后來稱帝,他的這一“文人無行”論也就流傳甚廣。劉勰順著魏文帝的文人“不護細行”論進行了具體的舉例,他說:“相如竊妻而受金,揚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修廉隅,杜篤之請求無厭,班固諂竇以作威,馬融黨梁而黷貨;文舉傲誕以速誅,正平狂憨以致戮;仲宣輕銳以躁競,孔璋愡恫以粗疏;丁儀貪婪以乞貨,路粹餔啜而無恥;潘岳詭诪于愍懷,陸機傾仄于賈郭,傅玄剛隘而詈臺,孫楚狠愎而訟府。”司馬相如、揚雄等文士確實德行有虧,但緊接著他又進行了反駁。他說:“文既有之,武亦宜然。”不只是文人,武將也同樣有道德瑕疵,“至如管仲之盜竊,吳起之貪淫,陳平之污點,絳灌之讒嫉”,這就從對象上對魏文帝的“文人無行”論提出了反駁。劉勰特別舉了孔光和王戎的例子,前者身為丞相卻獻媚于寵臣,但這并不損害他一代名儒的名聲;后者位列三公,賣官納賄但不妨礙他仍是竹林七賢之一。二者因為身居高位,即使同樣存在道德瑕疵,不能滿足儒家對君子的要求,但身后的名聲卻未受損害。究其原因,劉勰認為是“名崇而譏減”的緣故,人們出于“避禍”心理,很少對身處上位者進行譏諷,以免給自己帶來危險。此外儒家的“為尊者諱”傳統(tǒng)也是原因之一。
劉勰為文人群體進行了辯護,他在前文說“文既有之,武亦宜然”,不僅文人群體有道德瑕疵,武將也有,又在后文說“蓋人秉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難以求備”,人非圣賢,孰能無過,不能求全責備。他仍舉出了六位道德上“無玷”的文人榜樣,“若夫屈賈之忠貞,鄒枚之機覺,黃香之淳孝,徐干之沉默”,屈原、賈誼忠直專貞,鄒陽、枚乘機警,黃香極孝順,徐干沉靜淡泊。“豈曰文士,必其玷歟?”文士群體中確實存在德行有虧的人,但并非所有的文士都必然有道德瑕疵,沒有缺點的文士同樣也是存在的,追求道德上的“無玷”仍應是文士們的目標。《程器》開篇的“貴器用而兼文采”受“文質(zhì)彬彬”說的影響,篇末的“達則奉時以騁績,窮則獨善以垂文”則與孟子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一脈相承,可以看出《程器》的指導思想仍是儒家思想。儒家一直是將德行作為君子的立身之本,劉勰雖有不平之語,但并無離題之意,道德上的“無玷”仍是劉勰心目中理想文士應當具備的。
需要看到的是屈原、賈誼等六位文士不僅在道德上“無玷”,在治國理政與文學素養(yǎng)上同樣也毫不遜色,屈原除了是偉大的浪漫詩人之外,還有作為三閭大夫,掌管楚國內(nèi)政外交這一政治家的身份;賈誼創(chuàng)作的《過秦論》《論積貯疏》《陳政事疏》等政論文至今仍在流傳,顯示出他過人的政治眼光;鄒陽的《上吳王書》《于獄中上梁王書》、枚乘的《上書重諫吳王》顯示出身為臣子的直言敢諫;黃香既有文名又勤于國事;徐干以文才受曹操推重。可以看出,劉勰在樹立文人典范時,除了德行之外,現(xiàn)實的政治才干同樣是其看重的,這就引出了劉勰“以成務為用”的主張。
二、“學文以達政”
劉勰隨后提出“蓋士之登庸,以成務為用”,文人被提拔重用,是以他能參與政治生活、處理軍國大事為準則的。他說:“魯之敬姜,婦人之聰明耳,然推其機綜,以方治國。安有丈夫?qū)W文,而不達于政事哉?”魯國的婦人敬姜尚且能夠以織機來比喻治理國家,哪有丈夫?qū)W文,卻不能治理國家的呢?換句話說就是,丈夫?qū)W文,卻不能以自己的才學參與國家政治運作,比未接受過教育的婦女還要不如。由此可以看出,“以成務為用”,學文而“達于政事”在劉勰看來是對文人的一種基本要求,是文人學文的根本目的。他所撰《文心雕龍》中自《明詩》到《書記》有二十篇文體論,除文學類文體外,劉勰還集中總結(jié)了應用類文體的文體特點,如詔、策、檄、移、章、表、奏、議等,這類應用文體是文人參與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從中可以看出他對“成務”的重視。
以“成務”為目的,劉勰強調(diào)“貴器用而兼文采”,但“器用”與“文采”孰輕孰重,我們可以從劉勰對揚雄、司馬相如的態(tài)度得出答案。劉勰提出“彼揚、馬之徒,有文無質(zhì),所以終乎下位”。揚雄、司馬相如以寫作鋪張揚厲的辭賦見稱于世,內(nèi)容上以描寫自然景觀的秀美和皇家園林的美麗富饒為主,形式上“勸百諷一”。劉勰認為,這樣的作品缺乏實際內(nèi)容,是“有文無質(zhì)”的,在他看來創(chuàng)作這樣作品的文士是本末倒置的,如果沒有政治才能,創(chuàng)作只為討主上歡心,這樣的文人只是“文學侍從”,而非真正的文士。由此可見,“器用”與“文采”,在劉勰看來,文采當居次要地位。
對于揚雄、司馬相如“有文無質(zhì)”的評判,是劉勰對所處時代深刻思考之后的總結(jié)。劉勰所處的齊梁時代,受東晉玄學思想影響極深,《明詩》中有言:“江左篇制,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忘機之談。”致力于政務的心志被人恥笑,陶然忘機的清談反而大受推崇。受此影響,“近代詞人,務華棄實”,《明詩》中有言:“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這正是對齊梁文壇的生動寫照,形式上求新、求奇,一味追求華辭麗藻,使文學走向一種極端,文壇被這種虛華的風氣所籠罩,而缺少現(xiàn)實的內(nèi)容。劉勰對此是持批判否定態(tài)度的,他創(chuàng)作《文心雕龍》就有改革文風、指導文人寫作的目的,因此他提出的“成務為用”也就具有了現(xiàn)實的價值。
能夠做到“士之登庸,成務為用”的,劉勰舉了庾亮的例子,“昔庾元規(guī)才華清英,勛庸有聲,故文藝不稱;若非臺岳,則正以文才也。”劉勰認為,庾亮憑借自己出色的處理政事的才能,得以受到提拔重用,但即使不做官,他也能夠憑借文采而被稱揚。據(jù)《晉書·庾亮傳》記載,庾亮因才德受晉元帝禮遇,被提拔做官,元帝即位之后,庾亮被任命為中書監(jiān),中書監(jiān)是一個十分靠近權(quán)力的中心位置,庾亮的文學才華也被劉勰多次禮贊,如《才略》中有言:“庾元規(guī)之表奏,靡密以閑暢。”言庾亮的表奏文思細密從容暢達,《章表》篇中有言:“……庾公之《讓中書》,信美于往載。序志顯類,有文雅焉。”贊揚庾亮的《讓中書》寫得溫文爾雅,遠勝于前代同類作品。這就與揚雄、司馬相如形成了鮮明對照,充分說明擁有處理政事的能力和才干對于文士的重要意義。
劉勰又對“成務為用”提出更進一步的要求,不只是學文而能達于政事,并且要“文武之術(shù),左右惟宜”,既要為文,又要能武。“文武之術(shù),左右惟宜。郤縠敦《書》,故舉為元帥,豈以好文而不練武哉?孫武《兵經(jīng)》,辭如珠玉,豈以習武而不曉文也?”他認為,無論文人、武士,都應像郤縠、孫武一樣兼有“文武之術(shù)”,不因為通曉其一,而有所偏廢。如此文武全才,才有建功立業(yè)、“奉時以騁績”的可能。這有現(xiàn)實因素的考量,正如前文所述“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誚”,將相得以加官晉爵的機會相較文士更多,歷史上憑借文采而得以重用的文士多屈居下位,而憑借武功得以晉升的則更易名顯聲揚。同時,劉勰的這一考量具有超出時代的意義,六朝審美更多地追求柔美纖秀,“傅粉何郎”“看殺衛(wèi)玠”等典故廣為流傳,表明這個時代追求的是一種陰柔之美。顏之推說:“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持,郊郭之內(nèi),無乘馬者。周弘正為宣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常服御之,舉朝以為放達。至乃尚書郎乘馬,則糾劾之。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復性既儒雅,未嘗乘騎,見馬嘶噴陸梁,莫不震懾,乃謂人曰:‘正是虎,何故名為馬乎?’其風俗如此。”在家國動蕩之際,陰柔、孱弱的文人顯得不合時宜,基于此,劉勰提出“文武之術(shù),左右為宜”,要求學文達于“政事”就顯示出了拯救時弊的重要意義。
三、“奉時以騁績”
“以成務為用”是從文士自身的努力方向著眼,而從客觀的角度出發(fā),真正文人中的人才,應當是能夠“緯軍國”“任棟梁”,于國家有益的人才,并且要“達時奉時以騁績”,取得一定的功名和地位。雖然劉勰也提出“窮則獨善以垂文”,但“獨善以垂文”只是相較于“達時”的退而求其次之舉,是無可奈何的選擇。他認為,最理想的情況仍是在政治上有所成就,既有聲名又有地位。前文提到的庾亮正是符合這一要求的文士,既有政治才能又有文采,因此能夠身居高位,建功立業(yè),如他這般的文人才是劉勰心目中理想的文人典范。而這一理想文人形象與劉勰先祖劉穆之的形象有相似之處。
劉穆之為南朝劉宋開國皇帝劉裕的謀士,在劉裕稱帝前一直為其出謀劃策,深得其倚重,他幫助劉裕矯正法律,改變政治風氣,升任尚書左仆射后,總掌朝廷內(nèi)外事務。劉穆之在劉裕稱帝前三年去世,宋武帝劉裕即位后,追贈他為南康郡公,謚號為文宣。《宋書》記載,劉穆之幼年時家境甚為貧寒,屬于低等氏族,在東晉門閥氏族社會里,高門氏族可以輕易憑借蔭庇進入仕途,但如劉穆之一般的低等氏族要想入仕進取則會困難得多。但出身并沒有成為劉穆之入仕道路上的阻礙,他憑借個人出色的政治才能與極高的文學素養(yǎng),受到劉裕的賞識,最終輔佐劉裕成就大業(yè),《宋書》記載他“為一代宗臣,配享清廟”,足見其成就。劉穆之正符合劉勰“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的要求,他能夠“發(fā)揮事業(yè)”,“奉時以騁績”,受到開國皇帝的賞識,贏得生前身后不朽的名聲。可以看出,劉勰對于理想文士人格的追求正是從他先祖出發(fā),加以描摹刻畫的。從個人“成務為用”的才能出發(fā),不僅使自己得到高官厚祿,贏得不朽名聲,而且能夠獲得皇帝的賞識,能夠“緯軍國”“任棟梁”,有利于國家,如此才是劉勰心中理想的文士典范,是文人的最高追求,《程器》結(jié)尾的“豈無華身,亦有光國”,內(nèi)涵即在于此。
對于如何成為這樣的文士典范,劉勰也提出了努力的方向,“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發(fā)揮事業(yè);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楠其質(zhì),豫章其干”[2]。想要實現(xiàn)“緯軍國”和“任棟梁”的宏愿,需要做到以下兩點。
一是“君子藏器”,器即是前文提到的“德行無玷”和“成務為用”,德行上沒有錯誤缺點,同時“貴器用而兼文采”,既具備處理現(xiàn)實政治事務的才能,又兼具文采,有“文武之術(shù)”,如此便做好了可以建功立業(yè)的準備。上文提到的劉穆之,雖出身低等氏族,卻能在年少時苦讀儒家經(jīng)典,博覽多通,滿腹韜略,文化素養(yǎng)高,加之長期在戰(zhàn)爭中學習軍事,讓他具備了基本的軍事才能,這就為他受提拔做好了準備。
二是“待時而動”,德才兼?zhèn)涞奈氖坎灰欢ň湍芙üαI(yè)、封侯拜相,這其中還有“時運”發(fā)揮著重要作用。“窮”與“達”是不同的“時”,有人終其一生,未必能得到“時”,但只要有“器”,有才德傍身,即使無時運,也能“窮則獨善以垂文”,以著作傳世。而一旦時來運轉(zhuǎn),便可“達則奉時以騁績”,實現(xiàn)文士的最高理想,既“華身”又“光國”,建功立業(yè),澤加于民。這顯然與儒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之說是一脈相通的。
四、結(jié)語
劉勰在《程器》中探討了理想中的文人形象應當是什么樣的。總體來看,他對理想文士的要求離不開儒家思想的影響,他要求道德上“無玷”,學文要以“達政”為目的,同時有“文武之術(shù)”,能為“緯軍國”“任棟梁”服務,于國家有所貢獻,最終能夠建功立業(yè),“達則奉時以騁績”,取得名聲和地位,既能“華身”又可“光國”。劉勰認為,這樣的文人才是符合儒家要求的“梓材”之士,是文人的最高理想追求。可以看到,劉勰的人才觀沒有做形而上的泛泛之談,而是從實際出發(fā),強調(diào)文人的使用價值,為身懷抱負的文人提供了一條現(xiàn)實的通行路徑,這對封建社會的文人士大夫們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值得思考的是,劉勰的人才觀對于當今的大學生同樣具有參考價值,大學生應注意個人修養(yǎng),從實際出發(fā),提升個人能力與文學文化素養(yǎng),從這個路徑出發(fā)才能成長為對社會有益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