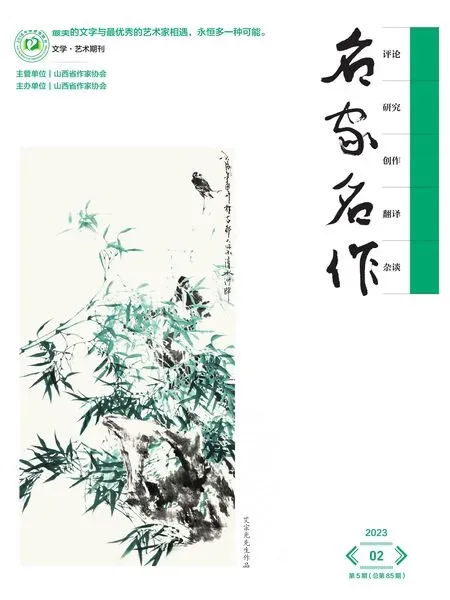蘇軾題跋藝術思想分析
孔祥云
本文首先從《蘇軾文集》入手,對其中與題跋有關的內容進行分析,明確開拓題跋這種全新的文體方向以及題跋發展過程中,蘇軾題跋具有的重要意義。自從佛教傳入我國之后,經歷了魏晉南北朝以及隋唐五代時期的大規模發展,并在宋朝統治者的追捧、百姓的需求、佛教人士的宣揚下,逐漸與道家和儒家融合發展。因此,許多宋代文人及作品受到儒釋道三教融合的影響,其中蘇軾就是一位典型代表,他將三教的系統理論充分滲透到題跋的藝術風格、思想內涵、審美情趣中,并受到其知識水平、自身閱歷、思想道德、文化素養等眾多因素的影響。在研究蘇軾題跋藝術思想的過程中,對宋朝文化思潮、蘇氏家學、蘇軾個人稟賦、蘇軾建立題跋藝術思想的背景、基礎及題跋藝術的魅力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深入探究,明確了蘇軾題跋對后世文學的影響,分析了蘇軾題跋藝術的繼承與發展,以及蘇軾題跋藝術思想的感染力與藝術地位。
一、蘇軾題跋藝術的思想特征
(一)情真質美
蘇軾題跋內容涉及政治、民生、游歷、參禪論佛、文學主張等幾類主題,與同時期題跋創作頗豐的大家相比,歐陽修題跋以考證為主,王安石以人物傳記為主,而蘇軾的題跋則多為有感而發,以抒寫性情為主,因體裁而宜,生發議論、敘述、抒情,故其情真。無論對親人的深情回憶或懷念、對友人的肝膽情義還是對底層勞動人民的同情,抑或不同觀點和主張表達,則因其情真,深顯意長。
對于蘇軾題跋藝術具有的“質美”思想特征而言,主要體現在題跋創作是否能夠遵循必要的規范,蘇軾題跋思想不僅承認了其有“法”可依,而且不完全受“法”的約束。蘇軾曾在潁州留任時,與趙令疇、陳師道共同拜訪歐陽棐、歐陽辯兄弟,并作詩“夢回聞剝啄,誰乎趙、陳、予”。對此,趙令疇認為,詩的句法較為新穎,之前從未出現過此種方法;而歐陽辯卻認為,之前已經出現過此種方法。“長官請客吏請客,目曰‘主簿,少府、我’。”雖然僅是生活細節,但反映出蘇軾積極尋找不斷豐富詩詞句法的事實。總體而言,蘇軾對“法”給予了高度重視,是遵循規范的表現,其本就是對“質”與“美”的重視。
(二)形神兼備
在蘇軾的后半生,對柳宗元的詩極為喜愛,借“味”品評柳宗元的詩,將“人食五味”的普通日常活動與藝術鑒賞進行充分整合。吃喝作為人們最基本的生理活動形式,能夠讓人們直觀地感受到食物的酸甜苦辣。蘇軾認為題跋創作與人們品嘗到的酸甜苦辣咸類似,但又在五味之上。因此,需要借助一定的藝術修養,對食物的“形”充分把握,對“神”精準定位,這樣才能使藝術創作實現“形神兼備”,就如同人們日常“吃五味”一樣簡單。此類論述不僅能夠使蘇軾題跋“形神兼備”的思想特征得到突出體現,而且借助此類極具獨特性的思考方式,能夠開拓藝術發展新局面,并且以此為啟發,對藝術的文人趣味以及審美特性進行重點強調[1]。
(三)法度自然
一名胸有成竹的藝術創作者,即使能夠充分掌握事物的原理,也未必能做到在藝術創作中表現“自然”,這就是“道”的問題,也就是技巧。當藝術創作者缺乏高明的創作手法時,即使再優秀的思想也無法得到充分表達,只能在內心了解“自然”的道理,卻難以通過具體藝術形式進行詮釋,無法“應手”,只能“得心”。因此,真正的藝術創作不僅要重視“道”的問題,還要擁有能夠詮釋“自然”的技巧,蘇軾曾多次在題跋中提到這一道理,要求“技道合一”,這樣才能使創作的作品實現“自然為文”的高超境界。這不僅是蘇軾放蕩不羈、天真率性的外在表現,更是其內心自然的流露,以及毫無掩飾、順乎天性的思想情感[2]。
(四)本色蘊藉
在蘇軾以人物為主的題跋中,對目標對象特點的描寫十分細致、飽滿,而抒情類的題跋中,以抒發懷才不遇的憤怒、追憶先賢親友、感慨人事變遷和時光流逝為主,這些情懷都是蘇軾發自內心的情感。比如,在《書子由〈超然臺賦〉后》中,蘇軾不僅對蘇轍的文章進行了評價,而且還對文章創作提出了“詞理精確”的一般要求和“體氣高妙”的美學要求。從結構層面來看,這篇文章雖然只有三句,但蘇軾利用“有不及吾”“吾所不及”說明了“天姿所短”,利用“詞理精確”“體氣高妙”說明了“殆兩得知,尤為可貴”。這樣的結構方式不僅用簡短的文字突出了文章的簡潔峭拔之姿,而且還能將自身在文學創作中的獨特感受與人生體驗巧妙融入評價中[3]。
二、蘇軾題跋藝術思想特征形成的內部原因
(一)無為之道對蘇軾題跋藝術風格產生的影響
“道”是一種能夠將自然全面概括的概念,從根本來看,只有窮盡了所有,才能真正認識“道”,但人是無法窮盡所有的,因此,在《日喻》一文中,蘇軾認為“道可致而不可求”。在對“致”進行詮釋的過程中,蘇軾列舉了游泳的例子,即使對水的沉浮原理以及游泳要領多么了解,不經過實踐,永遠無法真正學會游泳,只有日與水居的人,才能自然而然地學會游泳。從中能夠看出,從認知角度出發,無法得水之“道”,只有一個人達到身心自然而然地與水契合的境界,才能實現。將人心靈的虛靜與人生體驗、認知實踐進行充分整合,對記憶方面的修煉給予高度重視,使人在體驗中增長知識、提升直覺、豐富技藝,從而達到身心與“道”的結合,實現相忘之至的自由境界[4]。
(二)仁者之儒對蘇軾題跋創作動機產生的影響
在蘇軾的幼年和青年時期,受到了儒家經典的熏陶,從小便立下了“奮力有當世志”的遠大志向。成年之后,蘇軾認真學習經史子集,對儒家經典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由于蘇軾遵循從實用出發的創作風格以及自身嚴謹的治學態度,所以他對儒家經典的解讀有其獨到見解。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中,蘇轍曾這樣評價蘇軾:“初學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蘇軾的老家在四川,蘇軾對眉州當時的學術風氣“貴經術”、重視“西漢文字”進行了點評,其中不乏儒家思想對蘇軾產生的濃厚影響;蘇軾的父親是一名對儒家經典非常重視的儒士,將效仿儒家先賢作為追求方向,蘇軾在父親身上學到了處世態度,并將其充分融入題跋作品中[5]。
(三)禪宗之理對蘇軾題跋審美情趣產生的影響
在研究禪宗對蘇軾題跋藝術思想產生的影響時,要重點分析蘇軾與僧人之間的交往。蘇軾一生共與130 多名僧人交往,有詩文記載的人數多達80 人,在與這些僧人的交談中,僧人的禪宗思想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蘇軾的題跋藝術思想。雖然蘇軾閱讀大量禪宗經典的時間較晚,但其接觸禪宗的時間卻比較早,13 歲時,蘇軾便已開始閱讀佛經,在22 歲游歷成都時,與惟度、惟簡成為一生摯友,為蘇軾踏上求佛之路提供了指引。蘇軾在被貶黃州時,僧人道潛特意趕來與其同住,被貶惠州時,道潛也受其牽連無奈還俗。蘇軾之所以一生能夠與佛界較為親近,主要是因為其能夠超越世俗的利益糾葛和是非算計,這種情感滲透在蘇軾題跋中,是世人望塵莫及的[6]。
三、蘇軾題跋藝術思想特征形成的外部原因
(一)宋朝文化思潮對蘇軾題跋產生的影響
在北宋初期,與題跋文化有關的內容較少,文人創作題跋的局面尚未打開,即便如此,依然存在一部分令人驚喜的題跋創作成果。比如,擁有“北宋三大家”稱號之一的董源的題跋代表作《拂林圖跋》、張錫的題跋代表作《唐韓干馬性圖跋》等,雖然缺乏成熟性,但突破了北宋時期題跋藝術領域空白的瓶頸。在北宋中期,題跋藝術迎來了爆發式的發展浪潮,歐陽修創造了題跋藝術發展史“三個第一”,即第一個正式提出“題跋”文體形式、第一個大量創作“題跋”作品和第一個出版題跋專輯的文人。而受歐陽修的影響,蘇軾則是將題跋藝術的發展推向了另一個巔峰,他一生共創作題跋作品679篇,許多題跋作品沒有固定風格,短小精悍,自然灑脫,涉及的內容較為廣泛[7]。
(二)蘇氏家學對蘇軾題跋生成思想產生的影響
蘇軾的父親蘇洵極其反感擺弄詞藻的文字游戲,認為文章要情感真實、內容生動豐富,他的文學思想在當時是先進的,使得少年蘇軾的文學創作起點極高,影響了蘇軾的一生。蘇軾為人坦率真摯,在與人交往的過程中,能夠打開心扉,但卻不善于自我保護,因此,成就了他與眾多文人不同的胸襟和人品,使其創作的題跋具有永恒魅力。蘇氏家門具有教子成才的家風,特別是在伯父考取進士之后,對蘇軾產生了較大影響,在年幼的蘇軾心中埋下了報效國家、安心治學的種子。蘇軾母親為人寬厚、性格果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在教育理念方面,母親不僅要求蘇軾背誦傳統經典,而且特別重視對蘇軾的啟發和教育,這也影響了蘇軾的一生[8]。
(三)蘇軾個人天賦對蘇軾題跋藝術魅力產生的影響
在中國的文化發展中,眾多文人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其中,蘇軾便是一個如百科全書一般的全能人才。蘇軾精通歌賦、詩詞、題跋,擅長養生、美食、書畫、建筑,熱衷于醫療、慈善、民生,能夠將三教融會貫通,在各個領域皆有建樹,人們稱為“文豪”。蘇軾的一生雖然仕途坎坷、充滿挫折,但其不恃才傲物,能夠隨遇而安,拒絕隨波逐流,在經歷了種種磨難之后,仍然積極面對各種困難。即使仕途不順,蘇軾也能做到廉潔守法,造富一方。蘇軾的政治忠貞與當時的社會格格不入,但是其憑借率真的本性,使千百年后的現代社會依然給予其高度評價。每個人所遭遇的不幸,沒有一件是毫無意義的。也正是這些坎坷,為蘇軾提供了最優質的藝術養分,使其藝術思想能夠真正融入題跋中[9]。
四、蘇軾題跋藝術思想對后世產生的影響
作為題跋藝術的集大成者,蘇軾對宋朝以及后世發展產生了較大的影響,眾多文人相繼投入題跋創作中,其中對蘇門學士、南宋周必大等人的影響最大。后世人們從相關作品中積極搜集蘇軾題跋的藝術精華,通過與自身優勢的充分整合,為題跋藝術的創新發展提供積極助力,使文化藝術得到繁榮發展。[10]
蘇軾題跋藝術思想能夠從文化層面入手為當代文藝理論學科的全面構建提供幫助,加強對蘇軾題跋藝術思想中“形神之美”“自然之美”“本色之美”的深入研究,明確蘇軾題跋藝術思想與三教思想的融合渠道與碰撞點,對不同門類的文化藝術具有針對性的指導價值。蘇軾在詩、詞、書、畫、文等眾多領域,都為后人留下了豐富的藝術創作理論,能夠為當代文藝理論實現創新發展提供積極支持[11]。
五、結語
蘇軾題跋藝術思想特征主要包括情真質美、形神兼備、法度自然、本色蘊藉四個方面。在此基礎上,本文從無為之道與蘇軾題跋藝術風格、仁者之儒與蘇軾題跋創作動機、禪宗之理與蘇軾題跋審美情趣、宋朝文化思潮與蘇軾題跋生成的社會背景、蘇氏家學與蘇軾題跋生成思想、蘇軾個人天賦與蘇軾題跋藝術魅力這幾個角度出發,對蘇軾題跋藝術思想特征形成的內部動因與外部動因進行詳細分析,系統梳理了蘇軾題跋藝術思想對后世產生的影響,為豐富當代文藝理論基礎、促進文學藝術理論進一步完善提供了積極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