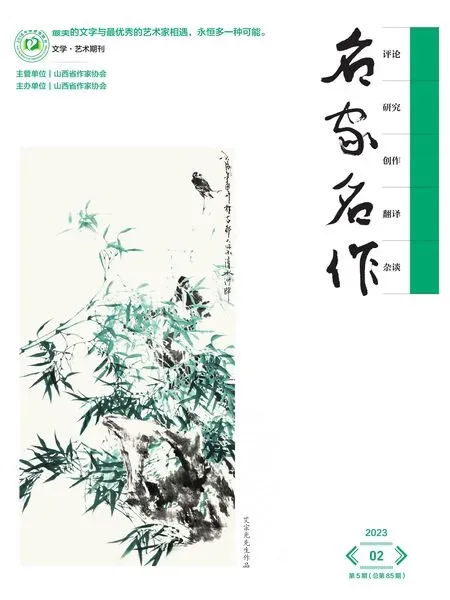余承堯山水畫與五代兩宋山水畫的比較
傅燦斌
一、余承堯藝術概貌及所處時代的特點
余承堯是一位學者型畫家,他的山水畫因以峭拔、闊大、整飭、厚重、飽滿的獨特的風格與特有的高度,折射出特有的時代精神而雄視千古、享譽世界。19 世紀的中國山水畫雖有那個時代的課題,比如思想觀念延續樸學的精神,但總體上離四王的傳統不遠。19 世紀末20世紀初是一個風起云涌的時代,明末清初以來本來就務實的民族精神在追求富國強民的內在自覺下更加務實了,表現在書畫界中大約有這四種傾向。一是對書畫有變革的訴求。正如傅抱石所說,時代變了,思想變了,畫法不得不變。二是尋求外來先進文化藝術以補陳舊的傳統繪畫局面,甚至欲借洋畫以革中國畫的熟悉的傳統面孔。這種思潮以康有為、陳獨秀、徐悲鴻、林風眠等人為主要代表。三是畫面由原來的文靜內斂的品質向運動的氣勢靠攏,并且繪畫表現的載體也由傳統造型的理想性、簡約性、筆墨的抽象性向現實生活靠攏,這一特點以任伯年、黃賓虹、傅抱石、潘天壽、石魯、陸儼少為代表。這一派總體上具有較強的文化本位主義的意識,他們的變革靠傳統內部的自覺來進行。四是折中派,以嶺南畫派為代表。將西洋畫寫實的光影效果引入畫面,并與中國畫傳統的筆墨相結合,形成一種非傳統非西洋的山水畫風格。在以變革為主題的20 世紀下半葉的山水畫領域中,李可染最能代表與囊括以上四種特點。就20 世紀下半葉的山水畫創作而言,如果說李可染稱得上成功者,那么李可染之外便不能不提余承堯。二人的山水畫都是密體,具有可比性,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最能夠代表中國20 世紀文化中的思想觀念發展程度的圖像化形態。這里要提出的是,余承堯的成功在于他是無師自通的。
余承堯少年時期就已經開始作詩填詞,這為他深厚的文史知識素養的形成奠定了基礎;青年時期,負笈東瀛學習軍事,養成了博學強記的能力。56 歲開始學畫,三年形成自己的風格,畫到第八個年頭,首次辦展大獲成功,一舉成名。當時華人世界里最有名的收藏家、書畫鑒定家王己遷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為筆墨再好一點就是王蒙第二。可是,他未必看得上王蒙。這固然與他的時代感受與時代課題有關。他認為元代之后的山水畫留白太多,甚至認為畫面的結構不夠硬朗。五代北宋的山水畫在他看來還是太空,不夠充實。對比畫史,唯有五代兩宋的山水畫,以其尚質實、崇理性似與余承堯遙相呼應。但是,余承堯所處的時代、所面臨的時代課題、所崇尚的價值傾向與五代兩宋已經不一樣了。以下從運筆、構圖、造型意識、色彩意識、作者所處時代的觀念意識五個方面對余承堯的山水與五代兩宋山水作一簡要的對比,希望能在比較中看出兩者的不同以及余承堯的山水畫對20 世紀的中國畫壇的貢獻。
二、余承堯山水畫與五代兩宋山水畫的比較分析
以荊浩、李成、范寬、許道寧、郭熙、李唐為代表的五代兩宋山水畫作代表了五代北宋文化再造時期的文化精神的圖像化形態。本文將以他們作為參照,與余承堯作比較。
(一)運筆方式不同
南齊謝赫的“六法論”在“氣韻生動”的條目下緊接著就是“骨法運筆”。唐人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里指出:“氣韻本乎游心而歸于運筆。”氣韻固然是中國繪畫表現的目的性內容,這種目的與內容則是通過運筆得以實現的。中國畫以裝飾性、平面性作為它的基本特點,因代異而權變,歷千祀而彌新,這大約是中華民族的思維模式。從6000 年前的半坡文化遺址的彩陶紋、余姚河姆渡陶豬紋到商周時期的青銅器紋樣,到漢代畫像石、畫像磚乃至唐宋元明以來的傳統繪畫都共同延續著這一特點,即便是在近百年西學東漸的背景下,凡欲發揮中國畫固有的重神采、重表現力的優點,則裝飾性、平面性特點還應正視并加以發揮。在山水畫的傳統中,樹木的表現、山石的皴法、云水的造型都由運筆來傳神寫照。運筆有虧則物象精神凋敝、神采黯淡。可見運筆在中國畫中的重要意義。五代時期荊浩有一篇《筆法記》說明了筆法的內在意涵及重要意義。其中提及運筆有四勢,謂筋、肉、骨、氣。荊浩的總結顯然啟示了畫面所透出的品格及所蘊含的信息量需要由相應的運筆得以實現。由此可見,運筆就實現完整的繪畫而言是關鍵環節。
余承堯也像傳統的多數畫家一樣強調畫家需要重視書法修養,書法修養以運筆為基石,若畫家書法修養有虧欠則繪畫的表現力是要受限的。以運筆為核心要素的中國山水畫的筆墨已經有深厚的傳統了,從五代兩宋的荊浩、李成、范寬、郭熙、王詵、李唐、馬遠、夏圭的作品看,中鋒、側鋒、干皴法、斧劈皴、豆瓣皴、雨點皴、披麻皴、礬頭皴已經出現,枯樹叢樹皆有極生動的表現力,提按頓挫、粗細對比、枯濕濃淡的交互可謂盡其靈而足其神。可以說五代兩宋的任何一位大師的山水畫都已經積淀了非常豐富的運筆經驗,具有豐富的表現力。相比而言,余承堯山水畫的運筆反而簡單一些,他有自己的技法,他的技法統一在整體的構造之內,是為畫面的構造效果服務的。換言之,他是以盡量簡約的運筆技巧表現畫面的整體宏大構造。
另外,與五代兩宋諸家相比,余承堯山水畫的運筆相對來說是偏向瘦硬的。我們讀他的畫語錄可知,他是在批判傳統山水畫流于空疏,未能很好地表現出現實生活中所見到的豐富充實、明朗的山水,他決心要畫出他人未畫過的山水畫。在這樣的認識的驅動之下,他的山水運筆偏向小筆。小筆的好處是便于積墨,便于分析性塑造,畫面的整體效果在分析性的筆法中實現。在整體效果的推進中又能夠保證局部畫面關系的可讀性、可分析性。
與余承堯的畫面相比,五代兩宋的運筆反而更具有審美意義,而余承堯的山水運筆則更像是技法與手段,是一個服務于整體效果的局部,其美感需要將運筆放進畫面的整體之中始能體現出來。
(二)構圖方式不同
構圖就是謝赫“六法”畫論里的經營位置,也就是繪畫中的布局。構圖就像寫文章的謀篇布局,關系繪畫作品的成敗。構圖到了宋元之后和畫家個人風格的形成與作品的辨識度的達成有著緊密的關聯。尤其是在近代美術創作中,構圖直接影響著畫家的圖式風格的辨識度。在眾多的美術作品中,構圖語言缺乏辨識度,是缺乏個人特點的表征,在繪畫創作里是不算成功的。構圖與繪畫作品本身的成敗及繪畫風格的形成有著最緊密的關系。成熟的畫家都有屬于自己的圖式語言,讓讀者一眼可以辨認出作品的所屬。余承堯在56 歲開始動筆作畫前,研究過中國傳統的山水畫,他覺得中國自古以來的山水畫面留白太多,而且畫得不像,所表現的不似真實生活的那種充實飽滿的美感,那種郁郁蔥蔥的生機。于是他決心要畫自己所見的真實的山水。他視角獨特,不迷信傳統的見識,崇尚以真實世界為依據的價值取向,所以他的起點已經大異于眾多山水畫家,這一見識使得他與宋元以后的絕大多數畫家拉開很大的距離;他研究山水頗重視對地質學的研究,這使他的創作又與傳統型的畫家拉開了很大的距離;再者,他自青少年以來就重視文史的修養,能寫一手可觀的詩詞,從早年到晚年,書卷不離手,并且告誡后輩作畫需要多讀書。我們由其年譜可知,其在47 歲時就修完了二十四史的功課,由此可見,其文化見識是高于同時代的絕大多數畫家的。文化見識為他的創作提供了判斷力的前提條件。以上三點“優勢”為他獨特的繪畫構圖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余承堯的構圖充實飽滿,他的畫面圖式在留白上往往比較克制。其多數畫作往往頂天立地,只在畫幅的上面部分留出一小塊天,或畫中的水與少面積的房屋留白。其構圖的圖式語言極具現代感的幾何造型特點,這是宋人所未見的。
(三)造型意識不同
造型意識就是處理或塑造畫面物象的意識,造型亦是涉及物象的構造手段。不同風格、不同時代的畫家,其造型往往都有自己獨家擅長的“秘笈”,以充分表現其審美意識。
造型意識具有時代性與個人性的特點。在余承堯的意識里,他的創作要力矯空疏之弊,即便是山腳、沙洲、遠山,都以疏密輕重不等的小筆來塑造,使畫面物象關系顯得實在而豐富。
另外,余承堯的造型具有現代意識。許多人第一眼見到余承堯的山水畫就會馬上想到五代兩宋的山水畫。這完全是因為余承堯山水畫的充實飽滿、峭拔雄偉的氣象。可是稍微細心觀察便可發現余承堯畫與五代兩宋畫在造型特點上是不一樣的。五代兩宋的山水畫在造型上非常重視對畫面造型位置、物象特征進行推敲。這一點從當時的繪畫與畫論是可以得到印證的。余承堯的畫面也是嚴謹的,他的嚴謹程度與五代兩宋山水的傳統各有其長又各不相同。從大的方面講,如果說五代兩宋的山水畫類似歐洲古典主義繪畫的話,那么余承堯的繪畫課題就相當于歐洲現代繪畫之父塞尚以古典主義的理性秩序消化了近代繪畫的光色要素,而以全新的觀念與面貌拉開了歐洲現代繪畫的序幕。古典主義繪畫是將畫面結構隱藏在畫面的物象里,而現代繪畫是將畫面結構作為內容表現在畫面的視覺效果中,使觀眾在看畫時就能直接感知到畫面明確的結構關系以及由明確的結構而投射出的畫面形塊結構的力度感。余承堯僅憑其對生活的感受與對美術史的感受就能在其作品中表現出時代的精神。他在中國美術史與五代兩宋以來的山水畫中的地位與塞尚之于歐洲繪畫的地位是非常相似的。具體表現在畫面中的是明確的幾何意識以及表現出的有意味的造型趣味。
(四)色彩意識不同
色彩是繪畫的手段也是目的。余承堯繪畫的用色類似印象主義繪畫的點彩。他的設色方式與北宋趙伯駒、趙伯骕以及王希孟的表現方式都不同。北宋的青綠山水著色一般以赭石為底,從山腳開始,往上則逐漸染不同色差的石綠與石青而呈現出寶石般的美感。相比之下,余承堯的設色山水則少了舊程式的套路,而多了寫真的意味。他的用色一反傳統的模式化,幾乎每一幅畫的設色都要表現出不同季節不同時間段“真實”的色彩情調。其色彩的微妙處、濃郁處、華麗處皆是傳統青綠山水所不能比擬的。
(五)時代觀念意識不同
我們讀金觀濤、劉青峰《中國思想史十講(上卷)》可以認識到人類文明的背后一般是有價值取向性的,它會通過各個時代的思潮來影響人們的文化生活。中國繪畫史上每一個時期的作品背后往往會有其時代思想觀念的影子,不同時代觀念下的山水畫,其時代的課題也會不一樣。通過對歷史文獻進行分類研究、概括總結,是可以追溯到那個時代思想觀念、價值取向的傾向性的。限于篇幅,本文先不作思想觀念關鍵詞的演繹研究。但需要指出的是,當我們想了解余承堯與五代兩宋的山水畫之間的根本差異性在哪里時,對其時代的思想觀念、價值傾向是不可忽視的。五代兩宋的思想觀念的時代課題正是接著魏晉玄學與佛教中國化的背景。唐朝以來為了提高社會生產力、維持社會秩序、維護民族生存的社會文化意識的重建,使知識分子中間長期醞釀社會思潮。這種思潮從傅奕、韓愈辟佛到宋明理學的形成,背后的思想觀念影響了山水畫家思想觀念的形成以及繪畫創作。同理可知,中國文化在經歷陽明學末流,日趨空疏而不能夠實現經世致用的功能,終于在晚明清初逐漸形成氣論哲學與樸學,以克服陽明心學末流帶來的流弊。整個社會在這種務實的思想意識的統攝下,山水畫也不知不覺會有“務實”的特點。這種“務實”的精神早期是將宋明理學中的天理體現在具體的應事之中,到了后期,天理二字逐漸不提,只在現成物質的世界中解決現實問題,而北宋那種高遠悠渺的天理似乎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余承堯的繪畫最能夠表現出這種思想觀念的特點,而有別于五代兩宋在天理世界觀下的藝術境界。
三、結語
綜上所述,余承堯山水畫與五代兩宋山水畫在運筆、構圖、造型手段、色彩意識、大時代的思想觀念背景等方面都具有顯著的差異,正所謂“時代變了、思想變了,繪畫不得不變”,從明末清初以來,中國思想界發生過巨大的變遷,山水畫界總體上是沿著宋元傳統在變革,直到晚清民國才有明顯借鑒西畫的課題。但是從某種意義上說,明末清初以來注重實在的氣論哲學思想觀念的山水畫界,到余承堯才算是真正形成了與其時代哲學精神和思想觀念相匹配的山水畫,這也是余承堯山水畫對中國山水畫的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