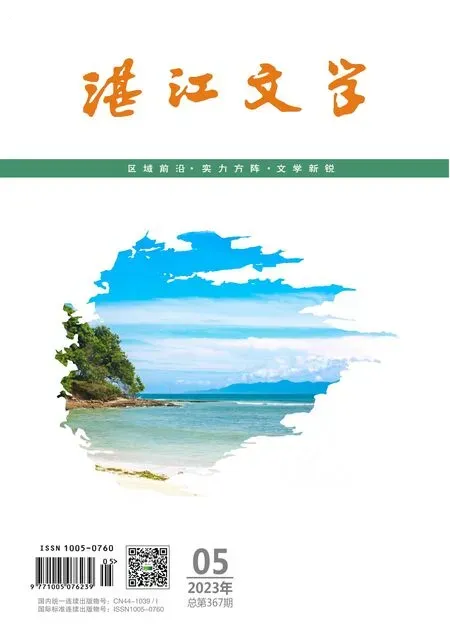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組章)
◎ 張首濱
消 暑
三伏天的陽光灼熱似火,
仿佛空氣都在燃燒。
我坐在一棵古樹下喝著老普洱,左右只一人,喝一壺少一壺,喝一壺得一壺,茶的功效如何?解渴,醒神。別的我不了解,利尿很明顯,去方便一次也是一次小解脫——
對這等情況,我不怕絮煩,大俗即是大雅。
自己做自己的活兒無束縛也是一樂,樂即涼快。
就在我自語時,枯枝不枯處,一個不知從哪來的蟬,眼里無天下,心中無一個我吱吱地唱著。我抬頭靜靜望一下,周圍一片云淡風輕。
對此我不想去打擾,
它亦是在自己做自己的事——念經消暑。
一個熟人
“這里雨都這樣嗎?”
“不一定,這得看是什么季節。”
“這個季節都這樣嗎?”
“差不多,但也有例外,有時也看天的情緒。”
“是這樣啊!”
一個長相像外鄉人的人,真的是外鄉人,但他是我的一個老友。什么叫老友?
就是以前經常在一起飲酒作詩,縱論天下事的那種。他來這里是路過,要去的地方,在哪里他也不知道。他說了幾遍,下一步要到一個沒有人的地方做一個人。我不知道他說的那個地方在哪里。就說:“今天喝點酒吧,一是給你接風洗塵,二是暖暖身子,去去濕氣。”他沒有反對。
雨十分的纏綿,若有若無地灑落著,
不時有踩踏泥漿的腳走過,濺起的水比雨大。
“這雨什么時候能停?”他坐在靠窗的位置問。
“說不好,看云象,應該還要下兩天,這樣的雨以前下過。”我經驗的回答。
他沒有再說啥,一臉的憂郁和天空中的云差不多,只是更凝重。
“菜上齊了,喝酒吧。”我轉正話題:“今天老友相會,高興,我們要多喝點。”
說完我先干了這一杯,并由衷地感慨:“歲月太快了,一晃我們十幾年沒見了。”聊起無常的人生,在啥時都有滄桑。他端起酒杯,也一干而盡。接著只見他粗糙的嘴唇囁動,像是對我說,也像是對自己說:“這雨這么下,絲絲縷縷的,肯定有什么在里面。”
他說的那個什么,指的是天上的,還是地上的?
我沒有問。周圍都在悄無聲兒。
這一頓酒飯的時間,他的眼睛老是盯著雨不放。
春已來了,怎么還不知道
天氣變化無常,寒潮是一個去另一個來。
今天我路過街邊花園,只見草木被上一次寒潮傷害的慘象仍在,左一片黃焦焦,右一片黑黢黢,令人不忍賭。
此刻一枚像雪片一樣的雪,在我身旁悄然飄落。
二月這個時間點下雪,也是有的,并不為怪。
可是過一會兒,它又飛起,翩躚得有模有樣,我頓時感覺到——那真的不是雪,雪怎么會落下又飛起?
對此我有些自責,春已來了,怎么還不知道。
是一個熟識的陌生人
我和孩子一起去散步。旭日在前面冉冉升起,我們走在這座城市的一條靜觀大道上,道的兩邊是做綠植的三角梅。
三角梅花開的時節,正是現在。一種姹紫嫣紅的景象,搖動在清風里。
我們一邊走一邊賞觀,也一邊呼吸著其特有的芳菲。這時迎面走來一個人,面目平常,向我打個招呼:來啦。
我回答:你早。隨后各奔東西。
早晨是好的。空氣新鮮,四周安謐。
我們充滿朝氣,大步向前走。突然孩子問我:剛才那個人是誰?
這一問我倒是一愣,有點懵。因為我不知道他是姓甚名誰。
說真的,我只知曉那個人也是一個散步的。無奈,只好告訴孩子:是一個熟識的陌生人。
這支風
這支風來時沒有說要到哪里去。
哪里也不去就到這里。
這支風來,可以這么來,也可以那么來,怎么來都是風來。來了有沒有歸處,暫且不論,來時沒有跟誰打過招呼,坐下來也沒有向誰訴說什么需求,看著挺孤獨的。
這支風來了,即保持著一個沉默,仿佛在等待一個什么,那個什么會是一個怎樣的什么?神鬼不在,弄不清楚。一個疑問解決不了一個問題,那就是了另外一個問題。
這支風會不會是在等另一支風,
準備一起做一個不是風的事。
那樣我怎么也做不到
每天睡覺前,我都會這樣:先把一只水杯放在床頭柜上,以便隨時拿來解渴;再打開一本書,去閱讀里面的動靜。
可是今天起身不慎,把水杯碰掉地上。“砰”的一聲,杯子和水都碎了。我隨之從床上也掉下來,手按在一塊碎的玻璃碴上,鮮艷的血頓時痛了出來。
我掉下床,是為了救那只杯子。
杯子沒有救起,手又受了傷,我凝視一地的悲傷,心想,如果杯子落地時,能冷靜地觀察一番,再做收拾,血就不會這樣流出來,痛也不會叮在手上。
可是,眼看著水杯掉下,而無動于衷,那樣我怎么也做不到。
只是要掛上一頂摘下的帽子
一手握著錘子,一手拿著釘子,在嗵嗵鑿的過程中,他十分享受,那種對事物的專注和力的發揮。
如釘子吃力,他會毫不猶豫地猛鑿幾錘。如釘子松動,墻皮崩裂,他會另選一處,或往釘眼里塞一節木棍,反正是讓釘子深入并牢固,這是一種有思想的行為。
今天他選準一個點,是房內距離窗戶遠些的一面墻上,要鑿下一顆釘子。一手扶著釘子,一手揚起錘子,他像帶著階級的仇恨一樣地狠。一下又一下鑿著。
打得墻一陣一陣發顫。打得墻發出的聲音不像墻的。他為啥這般?不為別的,只是要掛上一頂摘下的帽子。
好像就是在給一個人看
夕陽西下,天空飄著晚霞。
在一條屬于寂寞的地平線上的那個人。如一棵秋后沒有葉子的樹,紋絲不動。這不動也許是無風,或許有其他原因。
此刻此景,孤獨不孤獨,我就不說了。我在不遠處,看那個人已有半個時辰了,
只見他在望著那漸漸淡去色彩的晚霞,十分地專注,在看什么呢?不得知。
不過那晚霞,好像就是在給一個人看。
它也有人心的紫
在邁出鑲嵌在墻中的門時,日落西山,我提著一串話,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一路撒落著葡萄籽。這個時辰不算早,也不算晚;霞有一抹掛在樹梢上,有點嬌羞,有點醉,像初戀的色彩。
在這里不說這些了,人已中年,
對葡萄的感覺應該是一樣,不一樣的是情懷。
吃不到葡萄都說葡萄是酸的。
烏鴉也算是一只鳥,從我的背身處飛來,動作皆黑,在做黑里拿出一串串的鳴叫。那叫聲在屬于空中的上面滴落,做葡萄的模樣。
葡萄自有自己的味道。暮色蒼茫,在這個季節之外,從另一頭歸來的我,懷揣西風,投足在什么時候都會有彎曲的路上,對明處和暗處的響動說:葡萄不像別的東西,它也有人心的紫。
挺有意思的事
我在臺下看戲,臺上大幕有懸念地拉開,先看到的一點兒亮,是燈光,舞臺總缺少陽光而不缺少燈光。接著是背景,這背景不是某某人身后的權勢,背景不大,景深很淺,一眼就看到底。
可是景后是一面墻,
墻后是什么?
不可得知,那已是這出戲之外的事。
這時有人出場,人一登臺就變成人物,拋一句響亮的話,另一個人物把話接住,也扔一句同樣差不多的話,這叫對話。對話的語言一般不是老百姓家里常用得著的俗話,都是經過藝術加工的語言。我聽得似懂非懂,但不影響關注戲情;因為不時有人挺像樣地從唱腔鏗鏘中出來。
這個在別處,
是不容易看到的。
說起戲,聊起來還有些尷尬,說真的,我樂花些銀兩在臺下坐穩,并肯把自己的脖子梗得酸痛——只是為看一眼想看清楚而又看不清楚的。
這件事是不是挺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