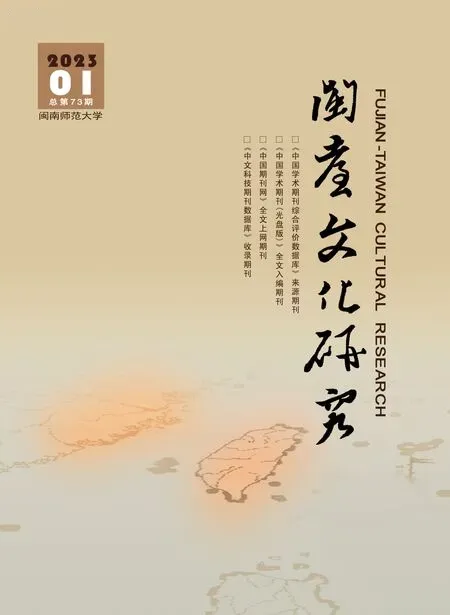《選贈和齋詩集》:乾嘉時期臺南公共文化空間的詩體書寫
肖慶偉
(閩南師范大學文學院,福建漳州 363000)
在經歷明鄭、清初順康之后,至乾嘉年間臺灣文學開始崛起,文人聯吟結社是其重要標志之一。在臺灣詩社發展史上,如果說海外幾社和東吟詩社是明清之際大陸宦臺文人主導的產物,那么乾隆、嘉慶年間的引心文社則完全是由臺灣文人發起和主導的詩社,其核心是陳廷瑜。引心文社產生于清臺灣縣(今臺南市),經歷了一個從最初的民間文社發展成為官方書院的過程。通過陳廷瑜的《選贈和齋詩集》,我們得以了解引心文社群體的基本面貌,以及這個群體對臺南公益事業的關注和書寫。引心文社及《選贈和齋詩集》都尚未引起學界關注。因此,本文擬就引心文社的演變、群體概貌及公共事業的詩體書寫進行探討,以期有助于了解崛起之初臺灣文學的面貌。
一、從引心文社到引心書院
引心書院,位于臺灣縣寧南坊呂祖廟,乃由引心文社演變而來。《續修臺灣縣志》卷三記載:
引心書院,初為引心文社,在寧南坊呂祖廟。嘉慶十五年(1810)拔貢張青峰、優貢陳震曜、增生陳廷瑜等議定課期,生童月二次,監以紳衿。束修課費多出監生黃拔萃手。[1]
引心文社最初是郡邑文人詩藝切磋之所。至嘉慶十四年(1809)前后,逐漸成為生童準備儒學考試的讀書之處,由張青峰、陳震曜、陳廷瑜等人議定課程和學制,生童學費則由黃拔萃捐助。但引心文社何時成立,史志并無明確記載。考《選贈和齋詩集》所錄張青峰《贈陳握卿丁巳年改建南社文昌閣》[2],是集中可考時間最早的一首詩,題云“丁巳年”,即嘉慶二年(1797),或可表明此時已有文社活動。
引心文社之所以能變為引心書院,主要原因是當地的南湖書院已經廢棄,生童缺少讀書之處。彭煥勝說:“引心書院:府城地區(臺南市)南湖書院棄置后,因文教需要而新增。”[3]
嘉慶十八年(1813),引心文社正式改為引心書院,即由民間文社演變成為官方書院。《續修臺灣縣志》卷三:“(嘉慶)十八年,知縣黎溶與拔萃及各紳士商改為臺灣縣書院,黎自捐銀五百元,拔萃亦再捐銀五百元,又捐埔地一所。”[4]黎溶,號秋帆,廣東番禺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舉人,署澎湖通判。嘉慶十五年,以賢能調知臺灣縣。[5]嘉慶十八年,在知縣黎溶的倡導下,引心文社改為引心書院。
但在黎溶調任臺灣知縣之前,引心文社已經開始向書院的方向發展了。嘉慶十二年(1807),張青峰等修建呂祖廟,《續修臺灣縣志》卷五:“呂祖廟:在東安坊。祀純陽子呂洞賓,唐進士李巖也。嘉慶九年(1804),以清江浦靈應,編入祀典。初,東安坊準提寺側有祀像,嘉慶十二年拔貢生張青峰等修建,改今名。”[6]修建呂祖廟,目的就是為了向生童讀書提供更好的環境和條件,同時也是為變成官方書院奠定基礎,因此,當黎溶調任臺灣知縣后,就有了和“各紳士商改為臺灣縣書院”之事。
《選贈和齋詩集》錄魏爾青《贈陳握卿己巳年引心書院首唱結社月課春秋祭祀》一詩,題云“己巳年”,即嘉慶十四年,是引心書院月課首唱之年,即為引心書院成立之時。又曾濬成有詩《贊和齋陳先生總理引心書院十三年》《庚辰歲來郡考試,閑步引心書院,詣文昌寂凝壇,及準提寺、呂祖廟,見其棟宇堅牢,門屏鞏固。規形體制,迥異昔時。詢諸守院人,稔知陳君廷瑜勤勞董修,從事十三年,不厭不倦,方得遹觀厥成。余聞而心慕之,不揣鄙詞,歌以為贈》。“庚辰歲”,即嘉慶二十五年(1820)。從己巳到庚辰,共十二年。陳廷瑜總理引心書院十三年,當從己巳前一年即嘉慶十三年(1808)算起,意謂截至嘉慶二十五年,陳廷瑜牽頭管理書院已達十三年之久。
此后,引心書院續有擴建。《續修臺灣縣志》卷三:“(嘉慶)二十五年知縣姚瑩捐生息銀一千元,又歲撥充鯽魚潭戶銀二百元,前后置業充用。其掌教聽紳士擇請,官課縣自延師校閱。至道光三年(1823)冬,經紳士張青峰等查得前知縣高大鏞亦捐銀五百元,赴學僉稟移查,并請建書院以廣育人才。當即準縣復,查明此項系交拔萃具領有案。”[7]姚瑩,字叔明,號石甫,又號展如,安徽桐城人。嘉慶十三年進士,二十一年謁選,得閩之平和,次年調龍溪。二十四年,調知臺灣縣。道光元年,移署噶瑪蘭通判。[8]嘉慶二十五年及道光三年,引心書院的建設繼續得到了官府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其運行體制:“其掌教聽紳士擇請,官課縣自延師校閱,”意謂官學和私學并行,體制可謂靈活,有利于發揮官府和民間舉辦教育的積極性。
道光末年,引心書院已廢,直到光緒十二年(1886),知縣沈受謙選址重建,稱蓬壺書院。丁紹儀《東瀛識略》卷三:“臺灣縣書院一,曰引心,已廢。”[9]《臺南市志》卷七《人物志》:“(沈受謙)光緒十年四月,移知臺灣縣。縣舊有引心書院已廢,受謙因就赤嵌城址立蓬壺書院,置山長,豐備膏火,以給諸生。”[10]另址重建,已經不是原來的引心書院了。
二、《選贈和齋詩集》所錄詩人考略
在引心文社向引心書院發展的二十年間,臺灣縣府城地區始終活躍著一個詩人群體,可稱為引心文社群體。幸有《選贈和齋詩集》以詩存人,我們得以了解這個群體的基本情況。《選贈和齋詩集》凡收41人69首詩,且所收詩人大多為臺郡人士。這個群體的中心是陳廷瑜。
1.陳廷瑜及其兄弟五人
陳廷瑜,字握卿,號和齋,清臺灣縣(今臺南市)人,嘉慶年間為臺灣縣學增生,生卒年無考。家境富裕,時有善行,“同縣(臺灣縣)諸生陳廷瑜字握卿,亦修學宮,舉行祀典,輯縣志,建引心文社以勵后學。又請禁紙牌,正淫祠,禁錮婢,著《與善錄》以勸。”[11]
父陳繩其。郭紹芳《奉贈和齋悉焚父券》詩序云:“和齋父,陳君繩其翁。”
陳廷瑜少時進入縣學讀書。章甫作詩《賀陳握卿游泮》:“白沙理學世傳芳,擷藻猶留翰墨香。五色筆花新吐艷,三條燭火看搖光。揚髻出海經鯤化,振翮摩天極鳳翔。珍重姮娥親種桂,秋來攀與少年郎。”首二句白沙理學,謂其家學源自明代理學家陳獻章。中間四句連用“五色筆”“三條燭”“鯤化為鵬”“振翮遠翥”四個典故,贊其才華橫溢,志向遠大。末二句預言其將來必定能蟾宮折桂,高舉進士。本詩體現了章甫對一個青年讀書人的激勵和期望。
陳廷瑜渡海到福州參加了鄉試。薛邦揚《送陳握卿秋闈》詩云:“三鳳聯飛出海東,劈開云路直摩空。紛披五采文章爛,橫掃千軍氣勢雄。玉筍班名馳北闕,金花帖字捷南宮。程途此去渾無限,買得輕帆扇好風。”“三鳳聯飛”,謂陳廷瑜和他的兄長廷珪、廷璧一同參加鄉試。“金花帖”,是希望廷瑜能高中進士,“玉筍班”,是希望他能入朝為官。但這次考試失敗了,否則,《續修臺灣縣志》“舉人”一欄就應該有陳廷瑜的名字了。
陳廷瑜結婚生子。蘇繼朋有《季春賀門人陳廷瑜新婚》四首,其一云:“笙歌滿院醉香風,翠繞珠圍燭影紅。百兩在門星在戶,瑤池春暖戲雙鴻。”寫出了婚禮的熱鬧和喜慶。從詩題可知,蘇繼朋還是陳廷瑜的老師。婚后,陳廷瑜連得五子,陳震曜有詩《賀握卿兄桐月舉第一子》,李連升有詩《賀陳握卿梅月舉第二子》,韋廷保有詩《賀陳握卿陽月舉第三子》,許玉章有詩《賀陳握卿梅月舉第四子》,章采有詩《賀陳握卿舉葭月第五子》。據王漢申《陳握卿以長子繼嗣五弟,題以善之》一詩可知:陳廷瑜將長子過繼給了五弟廷瑚;薛云征《陳握卿以第五子繼嗣四弟,題以善之》一詩則知:陳廷瑜將第五子過繼給了四弟登科,得到時人的稱贊。
嘉慶十二年知縣薛志亮開局續修臺灣縣志,陳廷瑜分任采輯。
輯《選贈和齋詩集》,并由章甫編訂,嘉慶二十一年(1816)章甫為作《選定同人贈和齋詩序》,序云:“吾黨贈歌,老夫編次。”嘉慶六年(1801)游廷元也為之作《書箑序》。
存詩三首:《鹿耳春潮》《竹溪寺》《紅毛城》,見《選贈和齋詩集》,《全臺詩》據此收錄。
兄弟五人:
長兄廷珪,字錫卿,臺灣縣學廩生。存詩三首:《法華寺懷古》《鯤身漁火》《月池》,見《選贈和齋詩集》,《全臺詩》據此收錄。
二兄廷璧,字孚卿,乾隆五十五年(1790)恩貢。嘉慶十一年(1806)蔡牽之亂,以守城功授六品職銜。[12]存詩四首:《赤嵌夕照》《鯽魚潭》《竹溪寺》《鳳岫春雨》,見《選贈和齋詩集》,《全臺詩》據此收錄。
四弟登科,字一卿,臺灣府學諸生。《全臺詩》第四冊《陳登科》;“陳登科,清嘉慶年間(1796~1820)人士。臺灣府學諸生,生平不詳。”據《選贈和齋詩集》,可增補其字。存詩四首:《嵐翠亭閑詠》《春日游鯽魚潭》《翠屏夕照》《掃墳口占》,見《選贈和齋詩集》,《全臺詩》據此收錄。
五弟廷瑚,字夏卿。據《選贈和齋詩集》可補其字。存詩八首:《鹿耳觀瀾》《竹溪寺》《泮池荷香》《翠屏夕照》《鯽魚潭》《塞婦詠》《新月》(二首),見《選贈和齋詩集》,《全臺詩》據此收錄。
2.陳震曜。字煥東,號星舟,嘉義人,后居郡治。和陳廷瑜、張青峰等共同發起引心文社。事見連橫《臺灣通史》卷三十四《列傳六?鄉賢列傳》。
嘉慶十五年,以優行貢太學,召試。歷署建安、閩清、平和等縣教諭。道光五年(1825)監理福建鰲峰書院,助修《福建通志》。道光六年(1826),任同安縣訓導。道光十二年(1832),張丙起事,隨軍渡臺,辦理團練撫恤諸務。曾主鳳儀書院,參與纂修《彰化縣志》。道光十七年(1837)任陜西寧羌州州同,在任十余年,有政聲。道光三十年(1850),因病返鄉。咸豐二年(1852)卒于家,年七十四。著有《小滄桑外史》四卷、《風鶴余錄》二卷、《歸田問俗記》四卷、《東海壺杓集》四卷,皆佚。
今存文《天赦云記》一篇,見周璽《彰化縣志》卷十二《藝文志》;存詩《賀握卿兄桐月舉第一子》一首,見《選贈和齋詩集》,《全臺詩》據此收錄。
3.薛邦揚。字垂青,臺灣縣寧南坊人。乾隆年間郡廩生。
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圍困郡城,陳邦揚募義兵抵抗,日久食盡,典房屋計千金以濟。帥兵數十戰。第二年五月,敵大至,官軍義兵合力抵御,邦揚沖入敵陣,為亂炮擊中,墜馬而死,時年二十八歲。事見《續修臺灣縣志》卷三《學志?行誼》本傳。“又林爽文案臺灣縣義民薛邦揚、陳天宗等四百八十一名……例得祀旌義祠。”[13]
存詩《送陳握卿秋闈》一首,見《選贈和齋詩集》,當為陳邦揚乾隆五十一年前作。
隨著對軌道交通鋪軌精度要求的不斷提高,目前已有武漢、廣州、西安、南京等城市采用更高精度的CPⅢ測量取代基標測量來指導軌道鋪設工作。本文主要針對當前軌道交通建設工程發展的新要求,通過借鑒在高鐵上已經應用成熟的CPⅢ測量技術分析研究城市軌道交通CPⅢ測量中的若干問題,將其同城市軌道交通工程的特殊性結合起來,研究確立CPⅢ控制點點位在地鐵隧道環境中的最佳布設位置、控制點觀測方式以及城市軌道交通CPⅢ網的合理精度指標。
4.張青峰。臺灣縣人。乾隆五十三年(1788),因林文爽之亂,軍功,授八品職銜[14],同年拔貢[15]。與陳廷瑜、陳震曜共同發起引心文社并議定課期(前引)。嘉慶十二年曾修建呂祖廟(前引)。存詩《贈陳握卿丁巳年改建南社文昌閣》一首,作于嘉慶二年,見《選贈和齋詩集》,《全臺詩》據此收錄。
5.林師圣。臺灣縣人,嘉慶元年(1796)恩貢[16]。存詩《跋陳握卿與善錄》《聞和齋陳三兄在大崑麓莊截筩化字率此寄贈》三首,見《選贈和齋詩集》,《全臺詩》據此收錄。
6.林啟泰。乾隆四十六年(1781)歲貢[17]。存詩一首:《贈陳握卿己巳年董修寂凝壇呂祖廟》,見《選贈和齋詩集》,《全臺詩》據此收錄。
7.潘振甲。臺灣縣人。乾隆五十一年舉人,軍功加六品銜。[18]嘉慶十年(1805)十一月,海寇蔡牽來犯,至翌年敗退,振甲以守城功,授六品銜。振甲作《乙丙歌》記蔡牽之亂,詩序云:“乙丑(1805)十一月十三日晦,海寇蔡騫(即蔡牽)來臺入滬尾港,溝通南北陸路騷擾,至丙寅(1806)二月初七日始去。”
嘉慶十二年知縣薛志亮開局續修臺灣縣志,潘振甲任分纂,《續修臺灣縣志》卷二《憲紀李思敏傳》即為振甲所撰。嘉慶十五年,有詩《贈陳握卿庚午年呈禁廟宇積弊》,見《選贈和齋詩集》。
8.郭紹芳。臺灣縣人。嘉慶三年(1798)舉人。[19]章甫門生,章甫有詩《門人郭紹芳秋闈獲雋》,當為門人郭紹芳嘉慶三年中舉后,章甫致賀之作。
嘉慶十二年知縣薛志亮開局續修臺灣縣志,郭紹芳任分纂,《續修臺灣縣志》卷二《知縣魯鼎梅傳》《解文燧傳》《穆和藺傳》即其所撰。
嘉慶二十一年,作《半崧集跋》。章甫《半崧集自序》作于嘉慶二十一年,郭紹芳跋語當作于本年。
存詩二首:一是《雁門煙雨》,見《續修臺灣縣志》卷八《藝文三》;二是《奉贈和齋悉焚父券》,見《選贈和齋詩集》。
9.黃汝濟。臺灣縣人。嘉慶五年(1800)拔貢,軍功加六品職銜。[20]嘉慶十二年知縣薛志亮開局續修臺灣縣志,黃汝濟任分纂。《續修臺灣縣志》卷三《學志?行誼》中的《鄭其仁傳》《陳名標傳》《王化成傳》,及卷四《軍忠軍官》中的《魁德傳》《潘國材傳》,皆為汝濟所撰。存詩二首:一是《重陽日同友人游海會寺席上分韻拈得禪字》,見《續修臺灣縣志》卷八《藝文三》;一是《贈陳握卿壬戌年邀眾呈禁南北義塚積弊勒石示文于城前》,見《選贈和齋詩集》。
10.洪坤。臺灣縣人。府學廩生。嘉慶十二年知縣薛志亮開局續修臺灣縣志,洪坤任校對,《續修臺灣縣志》卷首《續修職銜》:“校對:候補州判拔貢生黃纘、府學廩生黃本淵、府學廩生洪坤、黃殿臣。”
存詩二首:一是《游竹溪寺》,見《續修臺灣縣志》卷八《藝文三》;一是《贈陳握卿己未年邀眾呈禁字紙牌捐建敬圣樓崇祀倉圣人》,見《選贈和齋詩集》。
11.陳玉珂、陳肇昌、吳成謨。嘉慶七年(1802),臺郡拔貢生李宗寅、生員陳廷瑜、陳震曜、陳玉珂、陳肇昌、吳成謨等人上呈《義塚護衛示禁碑記》。[21]
陳玉珂,臺灣府人。陳廷瑜侄。嘉慶二十四年(1819)舉人。[22]嘉慶十二年,作詩《贈握卿叔丁卯年采訪續修臺灣縣志》,見《選贈和齋詩集》。
陳肇昌,臺灣縣人。生員。存詩《贈握卿弟丙寅年呈禁扮妝武圣神像》一首,據詩題,當為陳廷瑜從兄。詩見《選贈和齋詩集》,《全臺詩》據此收錄。
吳成謨,臺灣縣人。生員。存詩一首:《初,郡中魁堂會社無匾,丙寅陳君握卿建朱子祠、修敬字堂,顏曰:中社書院,以郡外有南北社,此中立也》,見《選贈和齋詩集》,《全臺詩》據此收錄。
12.林奎章。臺灣縣人。生員。軍功加六品職銜。嘉慶十二年續修臺灣縣志,分任采輯(前引)。存詩二首:《重游鯽魚潭》,見《續修臺灣縣志》卷八《藝文三》;《送陳握卿歸東瀛》,見《選贈和齋詩集》。
13.張文雅。臺灣縣人。武舉。以從剿桶盤棧功,用千總。[23]存詩一首:《贈陳握卿己巳年董修南社文昌閣》,《全臺詩》據此收錄。
以上考得引心文社成員19人,其余22人無考,但其大多為臺灣縣人。從考得成員來看,雖然他們的身份不高,或舉人,或貢生,或生員,但他們是一群在臺灣本土成長起來的文人,反映了自康熙統一臺灣以來文人接受儒學教育的實際情形。
三、《選贈和齋詩集》:臺南公共文化空間的詩體書寫
《選贈和齋詩集》凡收41 人69 首詩,大體可分為兩個部分:一是贈陳廷瑜詩47 首,二是陳廷瑜昆季五人詩作22 首。前者主要記錄了陳廷瑜的公益行事,后者則主要描寫當地自然景觀。陳廷瑜鄉試失敗,只好返回家鄉臺南,回歸家庭生活,并以增廣生的身份倡導和參與當地的公益文化事業建設。《選贈和齋詩集》以詩歌創作的形式記錄了這一歷史事實。
(一)書寫陳廷瑜參與修繕臺灣縣學、文廟諸事
嘉慶二年,陳廷瑜改建南社文昌閣,張青峰《贈陳握卿丁巳年改建南社文昌閣》詩云:
城南奎閣半塵埃,百六年來復盛開。萬丈文光齊北斗,千尋紫氣貫三臺。環山聳翠鐘奇品,積水拖蘭育妙才。堪羨后昆能濟美,先人曾此舊登臺。
“城南奎閣”,即指奎光閣,亦名文昌閣,又稱敬圣樓,《續修臺灣縣志》卷三:“敬圣樓在大南門外,祀文昌……嘉慶二年鳩眾改建(生員陳廷瑜、生員今拔貢黃汝濟、職員吳春貴、歲貢生韓必昌等任其事)。”[24]“丁巳年”即嘉慶二年,陳廷瑜、黃汝濟等人牽頭改建敬圣樓。“城南奎閣半塵埃”,寫改建前的情形。“堪羨后昆能濟美”,贊賞陳廷瑜等能在前人的基礎上發揚光大。
嘉慶四年(1799),陳廷瑜邀眾捐建敬圣樓崇祀倉圣人,洪坤《贈陳握卿己未年邀眾呈禁字紙牌捐建敬圣樓崇祀倉圣人》詩云:
煌煌圣跡煥班彪,萬世師尊永不休。此輩昧良供縱博,多君嫉惡視為仇。犯科畫像懸書魏,重道藏文敬字樓。紀績臺陽年己未,芳名千古海疆流。
《續修臺灣縣志》卷三:“敬圣樓……(嘉慶)四年,增祀倉圣。”[25]并未明言何人提出增祀倉圣人(造字圣人倉頡),但通過本詩可知,己未年即嘉慶四年,陳廷瑜倡導了這一行為,可補志乘不足。嘉慶九年,陳廷瑜修建臺灣縣學文廟,林瓊《贈陳握卿甲子年董修臺灣縣學文廟》詩云:
丹楹刻桷漸消磨,振起規模壯若何。俎豆千秋森肅穆,宮墻萬仞蔚嵯峨。前徽渺渺遙相繼,盛典煌煌肯放過。奎閣聿新文廟煥,瀛壖善舉獨君多。
臺灣縣學,位于東安坊。《續修臺灣縣志》卷三:“嘉慶九年,知縣薛志亮、教諭鄭兼才率諸紳士捐修,費用不足,林朝英獨任之。”[26]并未提及陳廷瑜是否參與修建縣學,但從林瓊贈詩可知:“甲子年”即嘉慶九年,陳廷瑜參與了臺灣縣學的修建,“奎閣聿新文廟煥,瀛壖善舉獨君多”,修建了文昌閣和文廟,稱贊了陳廷瑜的“善舉”。
嘉慶十一年,陳廷瑜興建魁星堂垣墻,張鳳祥《贈陳握卿丙寅年興建魁星堂垣墻》詩云:
特隆祀典羨開元,繼美端須賴后賢。七點文星齊射斗,一枝彩筆獨凌天。門墻何止觀瞻壯,靈爽從教赫濯傳,愧我無能堪附驥,空隨瞻禮樂年年。
《續修臺灣縣志》卷三:“魁星堂,在西定坊……(嘉慶)十一年,巡道慶保捐貲議改建。議成,興修倉圣堂居中,前為魁星堂,東為朱文公祠,西為敬字堂(貯字紙灰,舉人郭紹芳、生員陳廷瑜復與韋啟億倡捐成其事),統曰中社書院。”[27]可見:“丙寅年”即嘉慶十一年,在巡道慶寶倡議興修魁星堂的事件中,陳廷瑜、郭紹芳等參與了其中“敬字堂”的修建。而從張鳳祥贈詩中,我們知道:魁星堂的圍墻是由陳廷瑜修建的,這一點,縣志并未提及。本年,吳成謨《初,郡中魁堂會社無匾,丙寅陳君握卿建朱子祠、修敬字堂,顏曰:中社書院,以郡外有南北社,此中立也》詩云:
古社今銜署此君,關中特立振斯文。沂公惜字崇前圣,朱子傳閩證夙聞。地薄西南雄學海,堂開左右慶連云。春秋二仲頻馨薦,善氣時來滿院熏。
三、四句分別用宋代王曾惜字、朱熹閩中理學喻指敬字堂和朱子祠。而從本詩可知:陳廷瑜同時參與了敬字堂和朱文公祠的修建。
嘉慶十四年,陳廷瑜再次修建南社文昌閣。張文雅《贈陳握卿己巳年董修南社文昌閣》詩云:
奎樓仍舊制,補葺復巍然。振起文光見,重修斗氣聯。才真能繼美,事實可光前。遙踵先人步,端資此象賢。
“己巳年”,即嘉慶十四年,時隔十二年之后,陳廷瑜再次修建文昌閣。《續修臺灣縣志》未載此事,據此可補志乘不足。本年,陳廷瑜還修建了呂祖廟。林啟泰《贈陳握卿己巳年董修寂凝壇呂祖廟》詩云:
聿新輪奐耀神光,布地金沙普化長。獨秉丹誠為首唱,從今過廟重純陽。
呂祖廟是引心文社的聚集之地。《續修臺灣縣志》卷五:“呂祖廟,在東安坊。祀純陽子呂洞賓,唐進士李巖也。嘉慶九年,以清江浦靈應,編入祀典。初,東安坊準提寺側有祀像,嘉慶十二年拔貢生張青峰等修建,改今名。十四及二十五年,俱黃拔翠、陳廷瑜、韋啟億捐修。”[28]“獨秉丹誠為首唱”,見其“首倡”之功。
嘉慶十九年(1814),陳廷瑜修建中社奎樓。曾濬成《題贈和齋甲戌年董建中社奎樓》詩云:“衡文大憲素尊神,海外奎樓擬聿新。同事諸賢多袖手,惟君應命獨勞身。鳩金構得規模峻,制器圖成俎豆陳。自是瀛堧羅斗宿,長教翰墨永生春。”《續修臺灣縣志》未載此事。“同事諸賢”二句,見其修建奎樓之勤。
從嘉慶十三年到嘉慶二十五年,陳廷瑜參與了臺南準提寺的修建。曾濬成有一首七絕專寫此事,詩的題目較長,但因記述了陳廷瑜參與修建的整個過程,故茲錄于下:
準提寺創建已百余載,供奉準提佛母并諸神佛,為比丘尼住持焉。后尼死失及星散,闃其無人,香火蕭條,只存前后二殿。雖有北畔店屋,作本寺香資,然亦典質人家矣。而寺宇坍塌,爐冷煙銷,偶至其地,令人生寥落之感。嘉慶十三年,增生陳廷瑜等倡議重修。次年即捐資,贖回北畔店屋,修葺前后兩旁寺宇,及所倒壞店屋齋舍,香火始復。迨二十二年,再小葺戶牖瓦甍,佛座神居,頗稱安穩。二十五年,復捐資重修各殿堂,妝塑佛像,修置神龕,補造器物,又復燦然可觀焉。嗚呼,寺觀盛衰,關乎氣運,惟賴善信君子,敦行不怠,維持調護,以興衰而振廢。自茲以往,將見香煙馣馤,燈彩輝煌,較前尤盛焉,因作詩以志之。
從倡議重修、捐資贖回店屋,再到修葺寺宇殿堂、妝塑神像、購置器物,陳廷瑜主導了修建準提寺的全過程,故而曾濬成以詩贊之:“一片忠誠衛佛門,幾番首倡葺祗園。浮屠七級思功德,自覺芳名萬古存。”
(二)書寫陳廷瑜參與續修臺灣縣志之事
宋代以后,方志大興,至明清二代尤盛,康熙十一年(1672),詔各郡縣分輯志書,以備編纂《大清一統志》之需;雍正年間,頒省、府、州、縣六十年一修之令。臺灣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設一府三縣,修志之事始盛。康熙二十四年(1685),首任臺灣知府蔣毓英纂《臺灣府志》;康熙五十六年(1717),《諸羅縣志》纂成;康熙五十八年(1719),《鳳山縣志》纂成;康熙五十九年(1720),王禮《臺灣縣志》纂成。
在王禮《臺灣縣志》的基礎上,乾隆十七年(1752),魯鼎梅《重修臺灣縣志》纂成,嘉慶十二年,薛志亮開局續修臺灣縣志,三人的身份均為清政府任命且由大陸赴臺的臺灣縣知縣。縱觀三部臺灣縣志,參與編纂的臺灣本土文人呈現增多之勢,體現了臺灣本土文人知識水平的整體提高及參與公益文化事業的積極性。《續修臺灣縣志》卷首《續修職銜》:
總裁:升授鹿港海防兼北路理番同知、臺灣縣知縣薛志亮。
總纂:嘉義學教諭謝金鑾、臺灣學教諭鄭兼才。
分纂:舉人分發山西知縣洪禧、軍功加六品職銜舉人潘振甲、舉人郭紹芳、軍功加六品職銜拔貢生黃汝濟、軍功加六品職銜歲貢生韓必昌。
采輯:軍功加六品職銜歲貢生游化、邑增廣生陳廷瑜、嘉義學增廣生陳震曜、軍功加六品職銜邑生員林奎章、府學生員林珅、鳳山學生員王瑞、邑廩膳生員林棲鳳。
總理志局事:候補郎中拔貢生吳春貴。
校對:候補州判拔貢生黃纘、府學廩生黃本淵、府學廩生洪坤、黃殿臣。
由上可知,從總裁到校對,共20人參與續修臺灣縣志之事,除薛志亮、謝金鑾、鄭兼才三人外,其余17人都是臺灣本土文人。又《續修臺灣縣志》卷首《凡例》:
至其參稽實跡,賴于群士,非能臆為也。故山水則得之游化,城池則得之陳震曜,街里、橋渡則得之黃汝濟、林珅、林奎章,而參諸陳廷瑜;海道補注則得之林奎章,海口、港汕則訪諸旌士陳啟良,祠宇、寺院則林珅、王瑞、林奎章共詳之,而陳廷瑜之力居最;行誼、節孝則得諸洪禧、黃汝濟、韓必昌、陳廷瑜之聞見者為多,而林奎章、王瑞、林珅、黃本淵并有力焉;恤政則得之韓必昌,學田則得之陳廷瑜,屯田、屯番則得之陳震曜;軍志則黃汝濟之輯錄獨多,而并得之王瑞、林棲鳳;列傳分稿,則洪禧、韓必昌、黃汝濟、潘振甲、郭紹芳也,藝文之收采,則韓必昌之力而勷之者黃汝濟。其他旁見互參,諸多補助。悉書其大略于此,俾無忘其勞焉。[29]
由上可知,參與實地考察的共有19人,較之《續修職銜》,多出陳啟良和黃本淵二人。而在19位臺灣本土文人中,潘振甲、郭紹芳、黃汝濟、陳廷瑜、陳震曜、林奎章及洪坤都是引心文社成員,可見,續修臺灣縣志,引心文社實乃功不可沒.故陳玉珂《贈握卿叔丁卯年采訪續修臺灣縣志》詩云:
邑志臺陽闕續編,多君采訪紀遺箋。文章道德千秋在,節孝忠貞一日傳。五十余年詳事實,十三閱月告成篇。他時太史輶軒過,無事停車訪舊賢。
首二句謂續修邑志,陳廷瑜分任采輯。三四句贊其道德文章、節孝忠義。五六句揭十三月完成續修之事。末二句謂陳廷瑜必將青史留名。
(三)書寫陳廷瑜參與修繕引心書院、主持月課諸事
從引心文社的發起到引心書院的修繕和管理,陳廷瑜都傾注了大量的物力和人力,這在《選贈和齋詩集》中也多有體現。曾濬成《贊和齋陳先生總理引心書院十三年》詩云:
引心院建十三年,惟日孜孜為勸賢。講席宏開陶偉器,文壇結構選青錢。群才喜得登云路,主席欣看入月仙。藝苑書勛名可久,歌詩祝頌樂無邊。
勾勒出陳廷瑜孜孜勸賢、陶冶俊才的寬廣胸懷,也見出青年才俊登云入月之喜。曾濬成還有一首詩《庚辰歲來郡考試,閑步引心書院,詣文昌寂凝壇,及準提寺、呂祖廟,見其棟宇堅牢,門屏鞏固。規形體制,迥異昔時。詢諸守院人,稔知陳君廷瑜勤勞董修,從事十三年,不厭不倦,方得遹觀厥成。余聞而心慕之,不揣鄙詞,歌以為贈》,也寫到陳廷瑜董修引心書院之勤,詩云:
三教回環氣運開,文壇佛座接仙臺。憑依在德昭靈應,蘊藉為功達化裁。慧眼時觀龍軸降,靈符畫引鶴書來。百年故址今殊昔,董倡奇勛實偉哉。
“庚辰歲”,即嘉慶二十五年。“百年故址”二句稱贊了陳廷瑜“董倡”引心書院的奇功。
《選贈和齋詩集》還寫了引心書院的月課。魏爾青《贈陳握卿己巳年引心書院首唱結社月課春秋祭祀》二首,詩云:
結社春秋祭祀慇,丹爐點化課詩文。惟君默契神仙意,樂道飄然迥出群。
最好無虛結社名,奇文共賞對花評。香風引發心中隱,一筆揮云奠太清。
“己巳年”,即嘉慶十四年,引心書院成立。“課詩文”“奇文共賞”是書院的主要教學內容。稱贊結社首唱以“春秋祭祀”為月課之題,未負結社之名。
(四)書寫陳廷瑜社會治理方面的諸多善舉
陳廷瑜家境富裕,時有善行,《選贈和齋詩集》對此作了大量書寫。
首先,焚燒債券,免除債務。郭紹芳《奉贈和齋悉焚父券》詩序云:“和齋父,陳君繩其翁,輕財重義,南北村莊,郡城商賈,多有所借貸。積欠帳項,連編累牘。父沒,和齋悉焚之,曰:無致子侄輩多事。”詩云:“弓冶箕裘志不紛,況于財帛等浮云。千金弗索甘灰燼,百卷全教付火焚。自是承先銷舊恨,豈惟市義化殘文。高門自此多余慶,世好相安盡在君。”父親生前重義輕財,南北村民、城里商戶,都向其借貸。父親死后,陳廷瑜將所有賬單燒毀,免除所有債務。如此善舉,實屬不易。
其次,建言保護南北義塚。黃汝濟《贈陳握卿壬戌年邀眾呈禁義塚積弊勒石示文于城前》詩云:
山鬼跳梁慣逐群,奇橫何不畏蒼旻。拽牌盜石為生計,穿穴謀金趂落曛。刬草牧牛荒古塚,移尸賣地廢孤墳。多年積弊君除禁,城北城南勒示文。
“壬戌年”,即嘉慶七年,《義塚護衛示禁碑記》:“據拔貢生李宗寅、生員陳肇昌、陳廷瑜、趙新、王瑞、陳震曜、朱登科、吳成謨、陳玉珂、陰陽生魏巽巖等呈稱:‘臺郡南北義塚,概系沙土浮鬆,全賴蔓草滋生,根連固結,以資護衛。近有樵夫牧子,在該墳塚鋤割草薪,放牲踐毀,刨取沙土,妄肆蹂躪,漸至墳土摧殘;一經霪雨,水注沙流,恒有塚穿棺現之虞,已堪憫惻!更有一種奸徒,綽號‘山鬼’,膽將牌石、墳磚偷挖盜賣,甚至開棺盜物,或遷骸別瘞,將穴筑窨轉售。種種慘傷,殊難言喻’。”[30]義塚,是埋葬無主尸體的公共墳地,無人看管,時間久了,便出現樵夫割草為薪、牧子放任牲口踩踏,乃至“山鬼”挖墳盜物、筑穴轉售等現象,于是,陳廷瑜等人呈文知縣,[31]建言保護南北義塚,后來知縣準予勒文示禁。黃汝濟贈詩即真實反映了這一事件,并表達了對陳廷瑜的贊譽之情。
第三,革除廟宇積弊。陳肇昌《贈陳握卿丙寅年呈禁扮妝武圣神像》詩云:
后漢忠貞第一人,千秋名義賴猶新。誰家混列梨園譜,我輩如臨金闕身。竊恐當場渾作假,致教流俗認為真。惟君獨懼傷風化,一舉偏令畏圣神。
“丙寅年”,即嘉慶十一年。武圣,即關羽。關帝信仰是臺灣民眾的重要信俗之一,針對民間戲曲演出中將關羽過分妝扮如同宮殿之身的現象,陳廷瑜呈文請求下令禁止,以免有傷風化。又潘振甲《贈陳握卿庚午年呈禁廟宇積弊》詩云:
巍巍肅穆梵王宮,頹廢如今不古同。赤腳野仙盤殿上,裸身羅漢踞廊中。遂令寶帳香煙歇,漸覺銀燈燭影空。重振賴君除積弊,揮毫一掃舊腥風。
“庚午年”,即嘉慶十五年。“赤腳野仙”“裸身羅漢”,喻廟宇被裸身赤腳之人侵占,以致煙火香滅,因此,陳廷瑜呈文請求下令禁止,廟宇乃恢復如初。
第四,為鄉鄰排憂解難。張維光《郡北之南莊舊有古更路,莊人侵占數十年,適乾隆己酉陳君握卿詣七莊,為之清出,時有爭訟橫逆百余事,悉聽其勸解,眾皆悅服。陳君回郡,七莊老幼送程十里》詩云:
處己謙虛世莫京,南莊鼎重藉聲名。一朝清理功非偶,數載欺凌氣自平。舊典于今猶恪守,成規終古不紛更。芝蘭氣味薰人醉,莫解情緣送遠程。
“乾隆己酉”,即乾隆五十四年。古更路被莊人侵占幾十年的難事,被陳廷瑜一朝解決,且“眾皆悅服”,見其公心,也見其影響力。又賴河光《鳳邑大昆麓莊內,福德祠前一帶基地被莊眾侵占百余年,耕作菜園,開池筑廁,嘉慶乙亥,陳廷瑜首唱捐貲,勸解莊人為之清出,眾皆悅之》詩云:
開疆樂土百余年,穢惡何堪瀆廟前。欲壯神光三尺地,更增物色一番新。堂開凈域英靈普,社有馨香福澤綿。幸得成裘將腋集,庶幾鄉曲荷安全。
“嘉慶乙亥”,即嘉慶二十年(1815)。福德廟前的一塊土地被莊民侵占百年之久,莊民在此種地種菜、挖坑筑廁,陳廷瑜帶頭捐款,勸解莊民清理整治,還福德祠一個干凈整潔的環境。又賴純光《鳳邑傀儡山腳有溪曰排律,其水甚大,長流不絕,原水路從北而出外溪。突于嘉慶乙亥年溪門大塌,水勢直沖,各處田園,幾變滄海。大昆麓,陳君廷瑜莊業也。適瑜到,即倡捐金貲,勸勉番仔侖北、旗尾、埔頭三莊,均同捐金。令佃人累石筑堤,闊一丈余,長五六丈。于是各處田園,無致被水沖陷,亦全無派累佃農分毫。故莊人喜之,而作此詩》詩云:
為障狂瀾累石頭,保全廬井免橫流。何虞疊載懷襄患,且慶豐年黍稻謀。不是捐金資倡始,安能決水易田疇。他時結伴堅堤上,須把蘇公姓字留。
“嘉慶乙亥”,即嘉慶二十年,陳廷瑜到自己的田莊——鳳山縣大昆麓,正好遇上傀儡山腳下的排律溪突然漲水,沖破溪門,各處田園眼看受損,當即倡議捐款,快速筑起一道石堤,田園免遭沖陷。“不是捐金資倡始,安能決水易田疇”,肯定了陳廷瑜首唱捐金的作用,而且認為應該在石堤上刻上陳廷瑜的名字,就像杭州西湖的蘇堤那樣。
無論是修繕縣學文廟,還是為鄉鄰排憂解難;無論是續修邑志,還是書院月課,處處體現了陳廷瑜“與善”的家族傳統及其“淑世”的家鄉情懷,正如林師圣《跋陳握卿與善錄》二首之一所云:“聚首相親數十年,曾披著述輯成編。承家歷歷名言在,淑世昭昭雅訓傳。說備東平心最樂,談賅司馬德為先。從教海外遵鴻誨,與善應多積善緣。”
上述詩歌都包含了時間、地點、事件三要素,敘事性極強,風格質樸。章甫《選定同人贈和齋詩序》:“爰有同人,是真知己。與居善室,共筑詩壇。曲自稱高,直遏青云之響;和休云寡,齊聯白雪之詠。或葉律而諧音,聲聲入古;或裁紅而暈碧,色色生新。玉本無瑕,何須錐琢;金原有耀,轉望沙披。吾黨贈歌,老夫編次。駢詞弁簡,竊登風雅之場;錦組聯絲,補入金蘭之簿云爾。”說出了崛起之初臺灣詩歌質樸的基本面貌。
注釋:
[1][4][7]謝金鑾、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卷三《學志?書院》,《臺灣文獻叢刊》第140種,臺北:臺灣經濟銀行研究室,1962年,第166頁。
[2]陳廷瑜:《選贈和齋詩集》,《臺南文化》1953年,第3卷第3期。下引詩歌同出此本。
[3]彭煥勝:《臺灣教育史》,高雄: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第144頁。
[5]黃典權、葉英、賴建銘:《臺南市志》卷七《人物志》,臺南市政府編印,1979年,第245頁。
[6][28]謝金鑾、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卷五《外編?寺觀》,《臺灣文獻叢刊》第140種,第342頁。
[8]黃典權、葉英、賴建銘:《臺南市志》卷七《人物志》第二章,第222頁。
[9]丁紹儀:《東瀛識略》卷三《學校》,《臺灣文獻叢刊》第2種,臺北:臺灣經濟銀行研究室,1958年,第29頁。
[10]黃典權、葉英、賴建銘:《臺南市志》卷七《人物志》第二章,第246頁。
[11]《國朝孝義錄?陳廷瑜》,《福建通志臺灣府》下冊,《臺灣歷史文獻叢刊》,臺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第853頁。
[12][16]謝金鑾、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卷三《選舉?恩貢》,《臺灣文獻叢刊》第140種,第194頁。
[13]《壇廟》,《福建通志臺灣府》,臺灣歷史文獻叢刊,臺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下冊,第113頁。
[14]謝金鑾、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卷三《學志?軍功》,《臺灣文獻叢刊》第140種,第227頁。
[15]謝金鑾、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卷三《選舉?拔貢》,《臺灣文獻叢刊》第140種,第196頁。
[17]謝金鑾、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卷三《選舉?歲貢》,《臺灣文獻叢刊》第140種,第203頁。
[18][19]謝金鑾、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卷三《選舉?舉人》,《臺灣文獻叢刊》第140種,第192頁。
[20]謝金鑾、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卷三《學志?軍功》,《臺灣文獻叢刊》第140種,第228頁。
[21][30]黃典權:《臺灣南部碑文集成》下冊,《臺灣文獻叢刊》第218種,臺北:臺灣經濟銀行研究室,1962年,第437頁。
[22]《選舉?舉人》:“嘉慶二十四年(己卯)魏本唐榜:臺灣府陳玉珂、黃龍光(改名驤云,道光己丑進士)、淡水廳郭金茂、臺灣陳泰階。”《福建通志臺灣府》,《臺灣歷史文獻叢刊》,臺南:臺灣文獻委員會,第700頁。
[23]謝金鑾、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卷三《學志?軍功》,《臺灣文獻叢刊》第140種,第228頁。
[24][25][27]謝金鑾、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卷三《學志?崇祀》,《臺灣文獻叢刊》第140種,第161頁。
[26]謝金鑾、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卷三《學志?學宮》“縣儒學”條,《臺灣文獻叢刊》第140種,第149頁。
[29]謝金鑾、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卷首《凡例》,《臺灣文獻叢刊》第140種,第14~15頁。
[31]謝金鑾、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卷二《政志?縣官》,《臺灣文獻叢刊》第140種,第102頁:“周作洵,河南商城人,辛卯副榜。(嘉慶)五年二月任。降調。”嘉慶八年七月,薛志亮任臺灣縣知縣,故嘉慶七年陳廷瑜呈文知縣,當指周作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