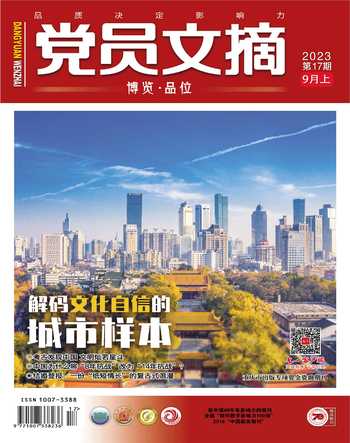解碼文化自信的城市樣本
王明浩 王永前 李勇等
北京:文脈千秋鑄京華
世界名城北京,有3000多年建城史、870年建都史,文脈悠悠、綿延不絕,它不僅見證了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更彰顯出中華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蘊。
文脈綿延 弦歌不輟
“金溝河上始通流,海子橋邊系客舟。卻到江南春水漲,拍天波浪泛輕鷗。”
元代詩人楊載筆下元大都的海子橋就是今天坐落于地安門外大街的萬寧橋。那時節,京杭大運河漕運碼頭擠滿了南來漕船,船工號子十里聞聲,橋畔人聲鼎沸、行人往來如織。
在來自歐洲的旅行家馬可·波羅眼中,這里無疑就是世界上最繁華的大都市,“全城地面規劃如棋盤,其美善至極,未可宣言”。
一座城市的歷史文化是風范的展示、風韻的表達、風貌的象征。
正是元大都“前宮后市”的規劃格局為今日北京的城市面貌奠定了基礎——布局宏偉莊嚴、空間合理有序。
從高空俯瞰,北京中軸線穿越故宮,形成一個“中”字;而它與北京城市的另一軸長安街,形成了一個“十”字。
這條中軸線隨城市發展不斷向外延展。北延線上,中國國家版本館大氣恢弘,彰顯中華文化神韻;南延線上,大興機場形似鳳凰展翅,歡迎八方賓客。
聯通東西的長安街沿線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進程同步:新首鋼見證無與倫比的冬奧盛會、城市副中心發展蹄疾步穩……
城市軸線,中正和合。城市發展,蓬勃興旺。
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故宮學研究所所長王軍認為,作為東方城市的杰出代表和偉大結晶,北京城直溯中華文明淵源,展現了驚人的文化連續性。
這里的每一方街市、每一處山水、每一道天際輪廓線,都在延續著城市的歷史記憶,浸潤著生長于斯的人民。
開放包容 美美與共
6月3日,夜幕降臨,雄壯的《紅旗頌》交響樂響徹八達嶺長城上空。這是俄羅斯指揮家捷杰耶夫率馬林斯基交響樂團為熱情的聽眾們傾情演繹。
古長城、交響樂、紅旗頌……各具特色的文化符號共同呈現出文化交融的獨特魅力,彰顯出北京開放包容的文化形象。

故宮午門
置身北京城,這類因文化交融碰撞而迸發的“光彩”隨處可見。
在亮馬河“國際風情水岸”,美麗的濱河夜景廊道已是夜游北京的“打卡地”;曾是老北京市井煙火代表性區域的隆福寺地區煥新重生,中外文化交融的創意藝術體驗空間成為新增的一抹亮色;位于宣西大街原順承門內的繁星戲劇村院里,湯顯祖和莎士比亞兩位戲劇大師的銅像相向而立,似乎在交流著各自對文化與藝術的理解……
“北京有一大批老百姓耳熟能詳的文物古跡已經成為新興城市文化地標。”來自非洲加蓬的寶拉已在北京工作14年,她覺得,“北京的文化能讓各種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覺得回味無窮”。
融匯古今、聯通中外。
北京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得更明白、用得更精彩,讓“中國節”變成“世界節”,讓中國元素在世界舞臺煥發光彩。
上海:海納百川譜華章
文化是城市的靈魂。黨的誕生地、初心始發地上海,在傳承與創新中推進文化自信自強,凝心聚力建設人民城市。
“一大紅”:百余年芳華依舊
這抹“一大紅”,永不褪色。
上海市黃浦區興業路76號,中共一大會址。石庫門小樓,烏漆木門、雕花門楣、朱紅窗欞,歷經百余個春秋卻芳華依舊。
一旁,新天地街區流光溢彩,與中共一大紀念館構成開放型、街區型文化空間。今時今日,這里已成為越來越多年輕人心中最具魅力的城市文化地標。

上海市楊浦濱江人民城市建設規劃展示館
《共產黨宣言》首個中文全譯本在這里出版,《新青年》《共產黨》《向導》等革命報刊在這里創辦,《國際歌》在這里被翻譯成中文……
“紅色,是上海最鮮明的文化底色。”歷史學家、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熊月之說。
以中共一大會址為中心,向西約800米,老漁陽里,中共發起組成立地;向北約1000米,輔德里,中共二大會址;向南約500米,成裕里,印刷《共產黨宣言》首個中文全譯本的又新印刷所舊址……在城市的版圖上,600余處紅色資源,如繁星遍布。
這抹“一大紅”,穿越時空、歷久彌新。
舊址遺跡成為黨史“教室”,文物史料成為黨史“教材”,英烈模范成為黨史“教師”——上海創新表達方式、走進年輕人群,讓紅色資源亮出來、活起來。
這抹“一大紅”,融入城市血脈,成為延續城市記憶、感召時代新人的強勁能量。
龍華烈士陵園里,陳延年、陳喬年、趙世炎、彭湃、何孟雄等烈士墓前鮮花簇簇,今人寫給英烈的書信層層疊疊。字里行間,情真意切。“我們始終如一,走在你們所選擇的那條正確道路上”;“多希望你們能看到今天的上海”……
“一江一河”:時代潮競涌奔騰
“七一勛章”獲得者、紡織工人的優秀代表、92歲的黃寶妹在黃浦江邊工作生活了一輩子,見證了上海工業文明的發展演變。讓她耳目一新的是,老廠房如今成了博物館、咖啡廳、黨群服務中心等公共空間。
匯入黃浦江的蘇州河自西向東,九曲十八彎穿過城市心臟地帶。河岸一座半島上,1933年建成的上海啤酒廠灌裝車間已改造為環保主題公園,向市民游客講述著蘇州河的前世今生。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在保護中更新、在更新中保護,近年來,“一江一河”已有近百公里的岸線貫通開放,上海城市形象隨之一新。
最好的江景奉獻給市民。一條新的生活“秀”帶上,曾經的祥泰木行,成為楊浦濱江人民城市建設規劃展示館;黃寶妹工作過的國棉十七廠,現在則是游人如織的上海國際時尚中心……
“一江一河”競涌奔騰,文化力量催動城市生機。
歷史、當下和未來,在一批批新型文化空間中交匯融合、滋潤人心。
都市繁華很近,“詩和遠方”不遠。人們可以在被譽為“林中玉石”的上海圖書館東館,將“夢境森林”化作閱讀景觀;也可以在朵云書院滴水湖畔的“最美書店”,看日出日落……
透過一件件文物,感受中華文明的深厚底蘊,從中汲取文化自信的力量——各處博物館和美術館內外摩肩擦踵、熙熙攘攘的人群,才是這座城市文化畫卷中最亮眼的“主角”。
弘揚開放、創新、包容的城市品格,堅定文化自信,踐行人民城市理念,上海正加快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不斷創造新的榮光。
重慶:文潤山城氣自華
重慶,山環水繞、江峽相擁,人文薈萃、底蘊厚重。這座歷史文化名城迄今已建城3000余年,孕育出巴渝文化、三峽文化、抗戰文化、革命文化、移民文化等。
古風新韻:成就獨特魅力
清晨,山城巷,67歲的市民周英碧吃過一碗面,在家門前的巷道里擺上兩張桌子。她在這里住了幾十年,退休后開了家“周姐小吃店”,賣冰粉、涼蝦、小面、酸辣粉等小吃,向來巷子拍照“打卡”的游客講這里的故事。

重慶山城巷
山城巷面江臨崖而建,是重慶唯一一條以“山城”命名的街巷。臨江的石梯步道一邊是壯觀的長江大橋、高聳的樓宇大廈,一派現代氣象;另一邊則是傳統吊腳樓民居、百年宅邸老建筑,以及“擺龍門陣”的老街坊、吃著火鍋看川劇變臉的游客,留住過往時光。
一座座老建筑、一段段石板路、一棵棵黃葛樹,仿佛一扇扇歷史的記憶之門。
對于跨越歷史長河的文化遺產,重慶人特別珍愛。
從事石窟文物修復近30年的陳卉麗,正帶領文物修復團隊,對世界文化遺產大足石刻寶頂山圓覺洞的頂部進行加固。
“當看到修復好的千手觀音造像金光再現的那一剎那,我覺得所有的艱辛付出都有了回報。”陳卉麗說。
重慶奉節有“詩城”美譽,我們從詩仙李白“朝辭白帝彩云間,千里江陵一日還”的背后知道了它,更從詩圣杜甫“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的名句中感受著它——歷代文人墨客在此留下眾多優美的詩篇。
古風與新韻水乳交融,歷史與現代守望相擁,成就重慶魅力。
紅巖精神:塑造山城氣質
“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1940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孩子劇團”在重慶唱響《黃河大合唱》。這歌聲唱出民族精神、氣魄和力量,激發了廣大同胞同仇敵愾、抗戰圖存的決心。
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徐悲鴻、冰心……抗戰時期,一大批文化名人輾轉來到山城,并創作出大量名作名篇。從來沒有一個時期、一個城市承載了如此多的大家,他們用滿腔憤怒與熱情投身抗日救亡運動之中。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抗戰文化運動在重慶蓬勃發展,傳遞著中華民族不屈的意志、必勝的信心。
“紅巖上紅梅開,千里冰霜腳下踩……”
重慶歌樂山烈士陵園,在蒼松翠柏掩映中顯得莊嚴肅穆。相距不遠的渣滓洞、白公館監獄舊址,見證了革命志士進行的英勇斗爭和偉大犧牲。
重慶是紅巖精神的發源地,紅巖精神植根于重慶悠久的歷史文化和光榮的革命傳統,植根于偉大建黨精神,是最具辨識度的重慶人文精神標識,“傳承弘揚紅巖精神,就是不忘昨天的苦難輝煌,無愧今天的使命擔當”。

“朝天”之志:打造開放高地
長江南岸南濱路,中西合璧的歷史建筑群組成重慶開埠遺址公園,見證著重慶近代開埠歷史。
重慶,曾是長江上游最早開埠通商的港口之一。位于長江、嘉陵江交匯處的朝天門,曾是老重慶17座城門中規模最大的一座。朝天門碼頭,商賈云集,是過去乘船出川的要道。
早在1889年,以開采煤礦發家的重慶奉節人鄧徽績遠渡日本經商,與人合辦了一家名叫森昌泰的火柴廠,兩年后,他把整個工廠搬到中國,在重慶建立森昌火柴廠。《重慶開埠史》記載,這是長江中上游地區第一家近代民營工廠。
1922年末,29歲的盧作孚從重慶朝天門碼頭登船沿江而下,尋找救國答案。他在上海、南通拜會了黃炎培、張謇等人,考察教育和實業,堅定了發展航運、實業救國的信念。
重慶是一座移民城市,開放包容是這座城市典型的文化特征。走出閉塞盆地、沖出峽江的進取心,伴隨著這座西部山城的歷史。
如今,朝天門依然是重慶通江達海的開放之門。自朝天門碼頭順江向東,一座國際化的內河多式聯運樞紐港果園港,正日夜不息運轉。重慶從內陸腹地走向開放前沿,新觀念在形成、新資源在匯集、新樞紐在牽引。
納百川、破夔門,向大海。新時代的山城重慶,正以前所未有的文化自信風貌,奏響高水平對外開放新樂章。
揚州:江河交匯育文昌
這里處江河交匯之地,望運河帆影、枕長江濤聲;這里有歷代文人墨客留下的無數名篇,“煙花三月下揚州”令多少人心向往之。
水運水韻,文脈滔滔
由長江入運河,瓜洲古渡、運河三灣、瘦西湖……“運河十二景”串珠成鏈;揚州市中心,始建于明代的文昌閣重檐攢尖,仍是城市地標;園林修造、古琴制作、雕版印刷等傳統非遺活躍在街巷間……詩畫揚州,古今輝映。
萬里長江東流,千里運河縱貫,距離揚州主城僅30分鐘車程的瓜洲古渡,正位于兩條中國黃金水道的十字交匯點上。唐代鑒真東渡曾五過瓜洲,北宋王安石也曾“泊船瓜洲”。
“開邗溝,筑邗城”,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以邗溝溝通長江、淮河兩大河流。自此,春秋筑城,漢置郡國,隋通運河,唐開港埠,至宋元烽火,明清興衰,揚州幾度富庶繁華,歷盡廢池喬木。

揚州何園
“這是一座通史式的千年名城,興衰與大運河息息相關。”知名運河文化學者顧風說。揚州曾憑借漕運之利成為“南北要沖,百貨所集”。
昔日南糧北運,如今南水北調。位于江蘇揚州的江都水利樞紐,一塊刻有“源頭”字樣的石碑靜靜矗立。每年,有數十億立方米長江水從這里輸出,潤蘇北、濟齊魯,送至千里之外的華北地區。
水運水韻,脈動千年,生生不息。歷盡滄桑的大運河揚州段,不僅從未斷航,更以前所未有的賁張活力,肩負新的使命。
古城煥新,近悅遠來
有著千年歷史的東關街上,市民杜祥開用自家平房與天井打造出“祥廬”,小橋流水,亭臺假山,錦魚暢游,匾額楹聯。
晚明時期,文人計成在揚州寫下造園寶典《園冶》,首次總結出中國傳統自然山水式造園“雖由人作,宛自天開”的理想。
2500多年的建城史,為揚州積淀了豐厚的文化遺存。古街老巷縱橫交錯,串起了名勝古跡,也收藏市井風情。
早上“皮包水”,品嘗揚州早茶、蟹黃湯包、大煮干絲,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晚上“水包皮”,體驗“揚州三把刀”沐浴、修腳、采耳、美發等非遺技藝,享受揚州人的精致生活……
“一曲廣陵散,絕世不可寫。”魏晉時期的嵇康以善彈此曲而著稱于世,在中國音樂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舊唐書》記載:“天下文士,半集維揚。”據不完全統計,唐代有150多位詩人寫下吟詠揚州的詩篇超過400首,讓這座城市充滿詩情。
如今,站在瘦西湖熙春臺遠眺,綠樹、碧水、青瓦勾勒出的優美曲線,將人們的視線帶向天際;入夜,一場大型沉浸式夜游,更令人們徜徉在“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的畫意之中。
唐代詩人張祜筆下的“十里長街市井連”,盡顯昔日揚州的開放繁榮。今天,大運河、長江水文化的包容與開放化作人文交流紐帶、經貿發展動能。
依水而建、緣水而興、因水而美,走過2500多年,揚州依舊與江河血脈相連,光彩更勝往昔。
(摘自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