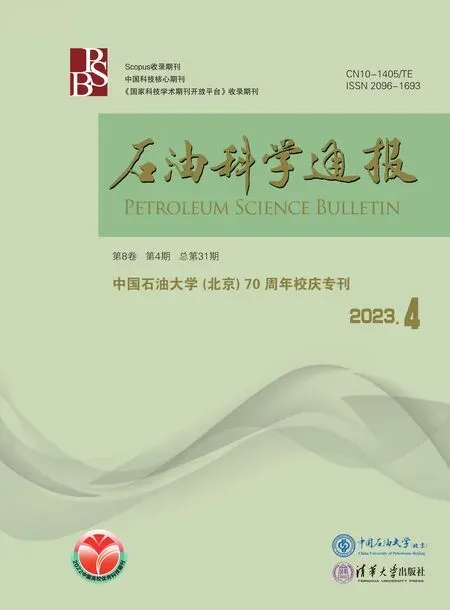中國碳捕集利用與封存技術應用現狀及展望
李陽,王銳,趙清民,方欣
1 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728
2 中國石化石油勘探開發研究院,北京 102206
0 引言
二氧化碳捕集利用與封存(CCUS)是指將CO2從能源利用、工業過程等排放源或大氣中捕集分離,并輸送到適宜的場地加以利用或封存,以實現CO2長期封存或轉化利用的過程,是實現CO2減排的有效技術手段,也是我國實現“雙碳”目標的關鍵技術路徑。CCUS技術和產業鏈發展涉及煤炭、石油、天然氣、新能源等能源生產領域,以及電力、化工、鋼鐵、水泥、建筑、交通等多個行業,與社會、經濟、政治等各個方面息息相關。CCUS與化石能源深度耦合,能夠實現碳基能源有效脫碳,保障以傳統化石能源為基礎的工業產業可持續發展;CCUS與可再生能源、氫能、生物質能等新能源耦合,能夠構建多能互補新模式,實現零碳、負碳能源供給體系變革,保障新型能源體系穩定運行;CCUS與化工、鋼鐵、水泥等工業產業深度融合,能夠有效推動傳統產業的提質升級,催生低碳、零碳、負碳新產業和新業態,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對經濟社會發展和“雙碳目標”的協同推進具有重要意義。
1 CCUS 發展歷程及其貢獻
CCUS是由CCS發展而來,為了應對氣候變化,1977年CCS的理念首次被提出,即將CO2捕集,防止排入大氣中。上世紀90年代,麻省理工學院發起成立碳捕集與封存技術計劃倡議。1996年挪威政府實施了全球首個CCS項目-Sleipner咸水層封存項目。進入21 世紀,CCS日漸受到國際社會重視[1]。2001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ⅠPCC)開展CCS專題報告研究。2005年,ⅠPCC正式給出了CCS定義,是指將CO2從工業或相關能源產業的排放源中分離處理,輸送并封存在地質構造中,長期與大氣隔絕的過程[2]。為了推動減碳技術和產業發展,2010年國家科技部提出加強以“U”為中心的技術研發,通過利用減排增匯,CCUS的理念目前已被國際社會廣泛接受。2020年以后,隨著全球主要經濟體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和碳中和目標的提出,CCUS步入快速發展軌道,CCUS新技術、新理念不斷涌現,CCUS技術的內涵進一步拓展,一是更加注重全生命周期的碳固定和封存;二是注重碳的資源化利用,以用減排;三是不僅包含人為排放的CO2,也包括大氣中的CO2捕集利用與封存。目前,CCUS發展成為一個新的理論和技術體系,需要新的理論和技術支撐。
國際機構對CCUS碳減排貢獻進行了評估。ⅠPCC在《ⅠPCC全球升溫1.5 ℃特別報告》中指出,2030年CCUS的減排量為1 億~4 億t/a,2050年CCUS的減排量為30 億~68 億t/a[3]。國際能源署(ⅠEA)2050 年全球能源系統凈零排放情景預測,2050年全球碳捕集量為76 億t/a,可持續發展情景預測,2070年全球實現凈零排放,CCUS是第四大貢獻技術,累積減排貢獻達到15%[4]。國際可再生能源機構(ⅠRENA)深度脫碳情境預測,2050年CCUS貢獻約6%的年減排量,減排量為27.9 億t/a[5]。2023年,伍德麥肯茲公司發布預測報告指出,CCUS技術將至少貢獻全球碳減排量的15%。我國學者對中國凈零排放情景下CCUS減排貢獻也進行了評價,2060年碳中和情景,CCUS年減排量約10.41 億t,累積減排貢獻為14.6%[6]。上述評估結果表明,CCUS已成為國際公認的減碳途徑之一[7]。
我國實現“雙碳”目標時間緊,碳減排強度大,CCUS對我國“雙碳”目標實現更為重要。我國能源結構以化石能源為主,2022年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費中占比82.5%,能源相關碳排放量大,同時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排放量在近期仍將增加;我國制造業占GDP比重較高,單位GDP能耗強度和碳排放強度高,因此,必須采用組合技術體系保障“雙碳”目標實現。CCUS可助力化石能源清潔化利用,使化石能源與新能源實現競合關系;可推動電力、鋼鐵、水泥等行業的綠色低碳轉型,成為我國實現“雙碳”目標的重要技術支撐,也是必然選擇。
2 國內外CCUS 發展趨勢
隨著全球碳減排行動的推進,主要國家和經濟體紛紛加快CCUS技術和產業研究,推動CCUS技術和工程示范快速發展,并出臺了多項支持政策[8-26]。
從技術發展來看,第一代以化學吸收劑為主的捕集技術能耗和成本進一步降低,國家能源集團錦界電廠15 萬t/a碳捕集技術再生能耗小于2.4 GJ/t CO2。第二代離子液體、相變吸收劑等新型捕集溶劑研發進展順利,加壓富氧燃燒、燃料源頭捕集等新一代捕集技術試驗成功。從技術成熟度來說,化學溶液吸收技術已進入商業應用階段,其他多處在工業示范階段。此外,直接空氣捕集CO2技術和生物質能碳捕集技術也取得重大進展,美國石油公司 Occidental正在開發全球最大的直接空氣捕集設施,預計每年將從空氣中捕集100 萬t CO2;英國生物質能發電公司Drac計劃建設全球最大的BECCS項目,年捕集800 萬t CO2。
在輸送技術方面,CO2管道輸運已完全實現商業化應用,國外已建成近萬公里的CO2長距離輸送管網,多數以超臨界態輸送為主。我國二氧化碳輸運以低溫罐車為主,CO2管道輸運尚在起步階段,2023年6月中國石化建成109 km CO2管道,中國石油、延長石油等企業也正規劃建設多條CO2管道。CO2管道輸送是目前國際上大規模長距離碳運輸的最經濟有效的方式,據ⅠEA預測,2050年全球CO2輸送管道總長度將達到20 萬km。
在地質利用方面,驅油封存、浸鈾采礦技術已進入商業應用階段,咸水層封存目前處于示范階段。CO2驅油封存是目前最為經濟可行的埋存方式,美國驅油封存項目每年注入約6000 萬t CO2,其中約30%來自工業氣源。隨著技術發展,CO2地質利用領域不斷拓展,天然氣藏、常規油藏、殘余帶油藏、致密油氣藏、頁巖油氣藏、水合物及地熱資源等都成為CO2應用的新領域。在CO2資源化利用方面,CO2制備化學產品和化學材料、利用光合作用合成甲醇燃料、CO2合成人工淀粉等各種資源轉化技術均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其中CO2制備化學品和礦化利用技術發展相對較快,多數已開展工業示范,但轉化效率和能耗較高。
從全球示范工程建設來看,截至2022年9月,全球捕集能力10 萬t/a以上的CCUS項目達到196 個,比2021年增長44%,捕集能力達到2.44 億t/a,較2021年增長63.4%[27]。目前全球新規劃或建設的項目規模大都在300 萬t/a以上,500 萬~1000 萬t/a的集群化項目快速增加,處于規劃或建設中的CCUS集群項目共有24 個,主要分布于北美、歐洲和亞太地區。典型的CCUS集群有美國墨西哥灣休斯頓Ship Channel CCUS產業集群、荷蘭鹿特丹Aramis CCS產業集群、挪威Longship CCS產業集群等,具體見表1。近期,中國也啟動CCUS集群項目建設,項目規模從400 萬t/a增加至2000 萬t/a(含在建、計劃項目),中國海油聯合埃克森美孚、殼牌等在大亞灣開展海上千萬噸級CCUS集群項目,中國石化聯合殼牌、寶武、巴斯夫在中國華東地區開展開放式千萬噸級CCUS集群項目。以CCUS樞紐為中心,多方參與構建CCUS產業集群,形成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CCUS發展新模式,是未來CCUS產業化發展的主流方向[9-12,26-27]。

表1 國外典型CCUS集群項目Table 1 Typical CCUS cluster projects
碳市場、碳稅、碳金融等碳定價機制迅速發展。歐盟碳市場碳價從50 美元/t增長至90 美元/t,北歐四國碳稅價格更高至70~140 美元/t。近期,歐盟碳邊界調節機制法案(CBAM)立法通過,針對碳排放水平較高的進口產品征收相應的費用或配額,這將極大促進區域CCUS技術發展。美國聯邦政府2008年出臺45Q法案,近期通貨膨脹抑制法案強化了45Q補貼力度(見表2),使得美國CCUS項目基本都具有經濟性。美國也制定了碳邊境調節機制法案《清潔競爭法(Clean Competition Act),簡稱CCA》,對進口商品征收二氧化碳排放費用,并將收入提供給發展中國家。總體來看,歐美發達國家正積極推進碳關稅。我國陸續出臺了系列雙碳政策,大力推進CCUS技術研發與示范,構建CCUS產業鏈。截至2023年5月,我國CCUS相關政策文件共有76 項,涉及規劃、意見、通知、標準、路線圖等方面。隨著碳達峰碳中和“1+N”政策體系的建立,CCUS政策工具類型逐步豐富,行業應用逐步拓展,CCUS政策體系初具雛形[28-31]。

表2 美國通貨膨脹抑制法案稅收抵免額度Table 2 US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tax credits
3 我國CCUS 技術及工程示范進展
我國CCUS技術快速發展,形成了碳捕集、利用與封存全流程技術體系。已形成不同濃度排放源的CO2捕集技術,在煤電、石化、水泥及鋼鐵等行業開展了大量示范應用;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和延長油田在多種類型油藏開展了CO2驅礦場試驗,取得了好的效果,形成了二氧化碳驅油與封存配套技術體系,并建立了封存安全性評價、監測及全生命周期評價技術;化學轉化及生物利用技術快速發展,部分CO2合成液體燃料、化工材料技術及CO2礦化轉化技術已經實現示范應用。整體來看,我國CCUS進入規模化應用階段(圖1)。

圖1 二氧化碳驅油封存全流程技術體系Fig.1 Technical system for CO2 oil displacement and storage
在工程示范方面,截至2022年底,我國CCUS項目(含規劃)近100 個,已投運項目的二氧化碳捕集能力約400 萬t/a,CO2注入封存能力200 萬t/a。已投運項目以工業示范和小型試驗為主,規模普遍偏小,多在10×104t/a以下,但正在建設或規劃的項目規模逐漸增大,其中中國石化已建成我國首個百萬噸級捕集、輸送、驅油、封存全流程示范工程,項目覆蓋石油地質儲量2562 萬t,預計注入約1000 萬t CO2,提高采收率11.6%。中國石化于2021年7月5 日啟動建設齊魯石化-勝利油田CCUS示范項目,2022年8月,示范項目投產運行。
齊魯石化-勝利油田CCUS示范工程形成了全鏈條技術體系。在碳捕集環節,建成100 萬t/a化工尾氣二氧化碳回收利用裝置,通過低溫精餾技術回收煤氣化裝置尾氣中的高濃度二氧化碳,開發余熱回收、余壓回收等技術,提升能量利用效率,降低捕集能耗10%。在輸送環節,建成超臨界CO2長距離輸送管道,管道全長109 km,最大輸氣量170 萬t/a,管道設計壓力12 MPa,形成超臨界壓力密相輸送技術。在二氧化碳驅油與封存環節,形成高壓混相驅油技術、全過程CO2驅前緣數值模擬及動態調控技術,提高全程混相程度,擴大波及系數,實現增油和封存最大化;形成多種產出氣回收利用技術,產出氣全部回注地層,實現CO2的循環利用和全生命周期碳封存。在監測環節,形成地質、工程安全性評價技術,實現斷層、儲層、蓋層、井筒及地面工程安全性評價;建立了空天地三介質一體化監測體系,實現對地下斷層蓋層的應變、井筒完整性、土壤、大氣、地下水、地面變形、植被等環境介質實時動態監測。
齊魯石化-勝利油田CCUS示范工程是我國第一個百萬噸級CCUS全流程項目,也是石化產業零碳產業鏈構建示范項目,為石油石化產業上下游一體化協同發展探索了一條有效途徑,標志著我國CCUS技術和工程示范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對有效提升我國碳減排能力、搭建“人工碳循環”模式具有重要意義,將有力推動國家“雙碳”目標實現。
4 我國CCUS 面臨的挑戰及發展方向
4.1 我國CCUS面臨的挑戰
“雙碳”目標背景下,加速CCUS產業規模化發展勢在必行,但我國CCUS產業發展仍面臨諸多挑戰。
一是關鍵技術亟待突破,大規模全鏈條技術體系尚待形成。低濃度排放源捕集技術能耗和成本較高,驅油封存協同優化技術和咸水層規模化應用配套技術還不成熟,化工利用和生物利用技術轉化能耗高、轉化效率低,封存安全性評估、監測技術及量化核查評價體系還未建立,直接空氣捕集技術、生物質能捕集封存技術、玄武巖快速礦化封存技術等前沿顛覆性技術研發力度不足,基于不同應用場景的全鏈條技術體系、技術模式有待創新,特別是大規模CO2捕集利用技術體系。
二是CCUS成本較高,與其他減排技術競爭優勢不明顯。我國煤電示范項目加裝捕集裝置后,捕集每噸二氧化碳會增加140~600 元的運行成本,而據國際能源署統計,直接空氣捕集成本高達800~2300 元/t,2022年我國碳市場平均價格僅為55 元/t。
三是已建成工程示范規模小(除齊魯石化-勝利油田示范工程外),全產業鏈布局不完善。國內已有CCUS示范項目多為點對點的單一碳排放源中小規模示范,單環節CCUS項目占比達到87%以上,缺乏全流程一體化及面向多種碳排放源的多技術組合的工程示范,制約了CCUS技術迭代升級及產業化發展。
四是政策生態建設不完善。近年來,國家陸續發布了CCUS相關的政策法規文件,約61%為國家科技規劃類,將CCUS技術作為前沿儲備技術重點資助;27%為雙碳相關政策或指導意見。總體來看,這些政策文件主要以引導性為主,支持各大研發機構或企業開展技術研發和工程示范,對企業不具有強制約束力。同時,國家還未出臺CCUS補貼激勵政策和推動CCUS產業發展的專項政策。2022年我國啟動了全國碳交易市場,但CCUS并未納入交易范圍。
4.2 我國CCUS產業發展方向
CCUS具有較長的技術創新鏈和產業鏈,需要從技術研發、封存中心、產業融合和方法學等多個方面協同推進,加速推動產業發展。
①加強CCUS全技術鏈研究,突破利用關鍵技術
碳中和目標下,CCUS需要構建新的理論和技術體系,降低能耗,提高效率。圍繞CCUS各環節關鍵科學問題,開展全創新鏈的基礎研究,特別是突破“C”和“U”的理論和關鍵技術瓶頸。聚焦捕集動力學和熱力學機制問題,研發針對低濃度排放源的新一代吸收劑、膜分離和膜吸收捕集技術,近期力爭捕集再生能耗降至2.0~2.2 GJ/t,捕集成本降至200~250 元/t,遠期捕集再生能耗降至1.5 GJ/t,捕集成本降至150 元/t,支撐大規模捕集。聚焦提高轉化效率和降低轉化能耗關鍵問題,推進化學高值轉化技術、生化高效固碳技術攻關。加強前沿技術的交叉融合,如捕集轉化一體化技術(圖2),通過微觀尺度上碳捕集和碳轉化的能量耦合,降低CCUS整體能耗;加強化學轉化與生物轉化融合,實現高品質液體燃料及化學品可持續綠色制造。聚焦二氧化碳地質封存利用地下空間、安全性及成本3 個關鍵問題,開展關鍵技術攻關,支撐地質封存利用工業化應用。

圖2 捕集-轉化一體化技術Fig.2 Integrated capture-conversion technology
②源-匯優化的含油氣盆地驅油封存中心建設
我國含油氣盆地具有多個油氣藏及大量咸水層資源,具有規模利用和封存的潛力,據評價可封存萬億噸CO2。同時我國含油氣盆地分布范圍廣,具有良好的源-匯匹配性及油藏驅油和咸水層封存的工程化優勢。應圍繞含油氣盆地,強化源匯優化,加強樞紐建設,建設驅油封存中心,形成捕集-輸送-封存利用產業集群。2030年在渤海灣盆地、蘇北盆地、松遼盆地、鄂爾多斯盆地、準噶爾盆地等區域,建成3~5 個百萬噸級CCUS全流程示范項目,注入能力1000 萬t/a;2050年圍繞含油氣盆地建成億噸級CCUS集群樞紐,推動全產業鏈的快速發展,實現大規模的封存利用。
③加強CCUS與產業的深度融合,構建工業零碳/負碳產業鏈
工業產業直接碳排放約占全國總排放量的39%,加上間接使用的電和熱的碳排放,占比高達60%~70%,因此,工業領域的深度減排是實現“雙碳”目標的重要領域,需加快構建低碳或零碳產業鏈。我國具有完整的工業體系,產業間協同減排優勢顯著,通過CCUS與能源體系及工業過程全流程的深度耦合,形成以全生命周期碳足跡為核心的跨行業、跨環節、跨空間的協同減碳機制,構建新的碳循環利用一體化的產業模式,打造產業集成、相互補充、協同發展的零碳負碳產業鏈。
④開展CCUS方法學研究,形成CCER機制
CCUS技術涉及捕集、運輸、利用與封存多個環節,全流程碳排放包括直接排放、間接排放及逸散排放等,同時地質封存的安全性及地質封存量的核實和量化,都給CCUS方法學研究帶來挑戰。要針對CO2捕集利用與封存的不同場景,開展核算邊界、排放源、核算方法等研究,建立不同情景下的碳足跡模型,形成CCUS方法學。將CCUS項目納入我國自愿減排機制,推動CCUS項目獲得碳減排量,提升項目經濟性,支撐CCUS項目規模化效益化發展。
5 結論
(1)CCUS是實現“雙碳”目標的關鍵工業技術,我國已初步具備CCUS技術規模化應用和產業化發展的基礎,建成了首個百萬噸級齊魯石化-勝利油田CCUS全流程示范工程。
(2)“雙碳”目標背景下,加速CCUS產業規模化發展勢在必行。CCUS具有較長的創新鏈和產業鏈,要加強CCUS全創新鏈的理論、技術研究,加快含油氣盆地驅油封存中心建設,加強技術與產業的深度融合,構建工業行業零碳/負碳產業鏈,加強CCUS方法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