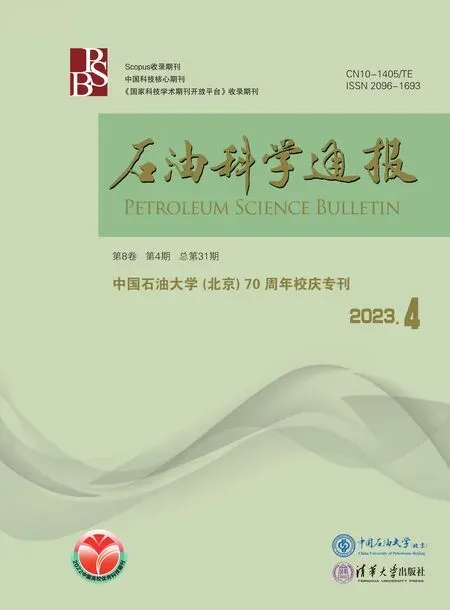裂縫性地層橋接堵漏技術發展綜述與展望
孫金聲,楊景斌,白英睿,呂開河,王金堂,王韌
1 中國石油大學(華東)石油工程學院,青島 266580
2 中國石油集團工程技術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102206
0 引言
我國石油和天然氣消費需求逐年增長,油氣供應對外依存度居高不下,2022年我國原油對外依存度71.2%,遠超50%的國際安全警戒線,天然氣對外依存度40.2%,嚴重危及國家能源安全。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調研勝利油田時強調,能源的飯碗必須端在自己手里;二十大報告中強調要“加大油氣資源勘探開發和增儲上產力度”。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對石油天然氣需求仍將強勁增長,加大國內油氣資源勘探開發力度是保障國家能源安全的重大戰略,高效開發超深層油氣是保證端好能源飯碗的當務之急。
我國深層超深層油氣資源總量達671 億t油當量,占油氣資源總量超34%,目前探明率僅為17%。近年來,我國油氣開發深度從深層逐漸拓展到超深及特深層,不斷突破有效資源保持深度下限。塔里木、四川、渤海灣等盆地相繼探明超深層油氣,開辟了增儲上產新戰場(圖1)。目前,攻克萬米超高溫高壓油氣開采技術與裝備已被列入2020—2035年國家油氣科技重大專項戰略規劃,中石油、中石化在“十四五”期間規劃部署了數百口8000~10000 m超深—特深井,正在實施萬米特深層勘探計劃,開啟了超深—特深層油氣開發的序幕。
超深層地質條件復雜,普遍發育多尺度裂縫甚至溶洞,工程環境苛刻,鉆井工程復雜事故多。裂縫性井漏是超深層鉆井過程中最常見且難以治理的工程復雜事故之一,已成為制約我國超深油氣地層鉆井提質增效和勘探開發進度的“攔路虎”(圖2)[1]。據統計,全世界井漏發生率占鉆井總數的20%~25%,每年用于堵漏費用高達40 億美元[2];美國、加拿大等北美地區碳酸鹽巖、頁巖等油氣藏鉆井過程中發生惡性井漏的井數約占鉆井總數的40%;中東地區碳酸鹽巖裂縫性油藏鉆井過程中發生惡性井漏的井數占比超過30%,井漏損失時間占比超過50%[3]。我國油氣鉆井工程同樣面臨井漏難題,據中國石油集團油田工程技術服務公司統計,近年來中石油國內和海外區塊鉆井復雜事故總損失時間中,井漏導致的損失占比均超過70%,每年井漏損失時間超3500 天,年均直接經濟損失超40 億元(圖3)。塔里木油田2019—2021年完鉆的320口井中,有275 口井發生漏失1646 井次,水基鉆井液漏失量超21 萬m3,油基鉆井液漏失量超3.6 萬m3,經濟損失巨大。因此,裂縫性地層井漏已成為制約油氣勘探開發進度的世界性難題。

圖2 裂縫性地層井漏示意圖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leakage in fractured formation

圖3 中石油集團鉆井事故復雜損失時間分類統計Fig.3 Classification and statistics of complex loss time in drilling accidents of CNPC
裂縫性地層井漏理論與技術研究方面,以經典的“應力籠”理論為基礎,國內外學者相繼提出了“裂縫封尾”、“阻滲帶”、“強固環”等理論,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系列鉆井液承壓堵漏技術[4],對于小尺度裂縫漏失地層取得了較好應用效果,但是針對裂縫性惡性漏失地層的一次堵漏成功率仍然較低,堵漏方法難以復制[5]。隨鉆堵漏技術類似于人為建立“人造井壁”屏蔽環,可提高井壁正反方向的承壓能力,可以適用于復雜構造地層,裂縫發育地層等低承壓條件的地層[6]。常用的隨鉆堵漏技術有橋塞隨鉆堵漏技術,物理法隨鉆堵漏技術,化學法隨鉆堵漏技術等[7]。雖然,許多堵漏技術已經被開發或應用于石油鉆井工程中,總體來說,鉆井堵漏還存在諸多問題。由于井漏發生情形的復雜性和難以預見特性,依然缺乏行之有效的堵漏材料和方法,而且堵漏一次成功率低。中石油塔里木庫車山前地區巨厚鹽層漏失段一次堵漏成功率低于40%(圖4);川渝地區二開斷層水基漏失段一次堵漏成功率低于10%,三開裂縫地層油基漏失段橋堵和水泥的一次堵漏成功率分別僅為16%和10%(圖5);中石化順北地區志留系裂縫性漏失地層的一次堵漏成功率低于25%;沙特阿拉伯Ghawar油田二疊系Khuff組裂縫性地層的一次堵漏成功率低于20%。

圖4 塔里木庫車山前鹽膏層堵漏成功率統計Fig.4 Statistics of successful plugging rate of salt paste layer in Kuqa Mountain front,Tarim

圖5 川渝頁巖氣井三開油基堵漏效果統計Fig.5 Statistics of oil-based plugging effect of three openings in Sichuan-Chongqing shale gas Wells
橋接堵漏是解決裂縫性地層井漏問題的有力手段之一,在塔里木、西南、長慶等地區的應用比超70%,美國90%的井漏均采用橋接堵漏來處理[8],在全球油氣井堵漏范圍內的應用占比超65%。橋接堵漏材料按其形狀可分為3 大類,即顆粒狀材料、纖維狀材料和片狀材料。其中,顆粒狀材料在堵漏過程中卡住漏失通道的“喉道”,起“架橋”作用;纖維狀材料在形成封堵層中縱橫交錯,相互拉扯,起懸浮拉筋作用;片狀材料在堵漏過程中主要起填充作用[9]。利用不同形狀及尺寸的橋接堵漏材料與鉆井液復配在裂縫內架橋、堆積和充填,形成阻斷流體壓力傳遞和流體介質通過的裂縫封堵層,具有致密結構和高承壓能力特征[10-11]。但常用的橋接堵漏材料粒徑與地層漏失通道尺寸的匹配性差。由于重力沉降、縫內沖刷、井筒壓力波動等因素的影響,在裂縫寬度較大、縱向延伸較高的大裂縫,尤其是溶洞中不易駐留,高溫穩定性不佳,導致封堵層承壓能力低。因此,研發具備抗高溫、強級配、高穩定性等一體化特性的功能型堵漏新材料,揭示其裂縫堵漏機理,可為深層裂縫性地層堵漏提供新材料、新機理和新方法借鑒。
綜上,高效堵漏材料及其作用機理等基礎研究的創新和突破,是提高超深層橋接堵漏一次成功率的關鍵,也是當今國內外的攻關熱點。基于此,本文對裂縫性地層橋接堵漏技術進行了詳細的綜述,概括了橋接堵漏材料的分類、作用機理以及橋接堵漏配方的設計方法和組成,闡述了提高裂縫性地層橋接封堵層穩定性的機制和承壓堵漏機理,厘清了橋接封堵層的形成、破壞和結構演化機制。同時,展望了裂縫性地層橋接堵漏技術的發展前景,為保障我國超深層油氣安全高效鉆井提供理論支撐,對于加快超深層油氣開發進程、保障國家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義。
1 裂縫性地層橋接堵漏材料研究現狀
隨著油氣勘探開發向深層—超深層拓展,鉆井過程中遇到的地質條件愈加復雜,裂縫性井漏問題異常突出,惡性漏失頻發。橋接堵漏方法具有材料來源廣、成本低廉、現場施工工藝簡便等優點,受到了國內外相關領域學者的廣泛關注。
1.1 橋接材料分類及作用機理
堵漏材料是實現堵漏成功的基礎和關鍵。堵漏材料對鉆井液漏失條件和漏失類型的適用性決定了其作用效果。國內外專家學者相繼研發了橋接類、高失水類、可固化類、吸液膨脹類和柔性凝膠類等多種類型的堵漏材料。目前,橋接堵漏材料是油田現場普遍使用的一種堵漏材料,橋接堵漏材料的類型、幾何及力學性能等對封堵層的承壓能力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橋接堵漏材料是由顆粒狀、纖維狀、片狀等惰性材料按照一定的質量比和粒度級配形成的復合堵漏材料。常用的橋接材料有核桃殼、碳酸鈣、纖維、云母片等。孫金聲[1]認為橋接堵漏材料的作用機理主要是通過在漏失通道內架橋、拉筋、堆積、填充等作用形成致密的封堵層,適用于滲透性或漏失不嚴重的地層。許成元等人[12]研究了橋接堵漏材料在裂縫中的動態封堵性能,認為裂縫封堵層的形成可分為滯留階段和封堵階段,如圖6 所示,滯留階段通常經歷橋接結構的形成—破壞—改造,最終趨于穩定,封堵階段是后續進入裂縫的堵漏材料在穩定橋接結構的基礎上快速堆積并持續壓實,形成裂縫封堵帶。Amanullah等人采用椰棗核研發了系列橋接顆粒狀堵漏材料,對2 mm縫寬裂縫的承壓封堵能力達10 MPa以上[13]。康毅力等人[14]通過分析核桃殼、碳酸鈣等橋接堵漏材料的形貌、粒度分布及力學性質等建立了深井超深井鉆井橋接堵漏材料高溫老化性能評價方法和指標體系,認為橋接堵漏材料高溫老化失效是深井超深井裂縫封堵層結構破壞并在儲層段發生重復性漏失的一個重要因素。目前關于橋接堵漏材料的研發以剛性材料為主,主要研究剛性材料的粒徑、形貌、強度等關鍵參數對橋接堵漏效果的影響規律,對于熱固性樹脂等功能型橋接材料,國內外學者也開展了探索性研究。
針對裂縫性地層漏失通道大、常規橋接堵漏材料堵漏效率低等問題,立足“剛性材料架橋+柔性材料固化充填”思路,結合熱固性樹脂固化前變形能力強、固化后強度高等應用特點,在鉆井液堵漏領域具有廣闊的應用前景。Lv等人制備了一種水下高溫慢固化的環氧樹脂堵漏體系(圖7)[15],可以很容易地穿過模擬地層裂縫,并在120 ℃條件下進行固化,固化后的環氧樹脂具有良好的抗壓強度,能夠有效封堵裂縫,可應用于油氣鉆井過程中的鉆井液堵漏。Batista等人使用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醇酯改性的聚酯樹脂作為堵漏材料[16],具有較高的抗壓強度和較低的粘度,在封堵棄井和補救作業中具有良好的應用。Knudsen等人制備了一種熱固性樹脂堵漏劑,成功地處理了中東海上氣田井中的稠油泥漿漏失[17]。Maryam等采用纖維改性的聚丙烯進行堵漏,該堵漏材料在玻璃轉化溫度以上可實現自適應、自黏結封堵漏失通道,在0.2 inch的裂縫中承壓能力高達5 MPa,性能優于常規堵漏材料[18]。王在明采用雙酚A環氧樹脂、酮亞胺、偶聯劑KH550 和硬脂酸鈣等合成了一種膠黏材料[19],將其涂覆在橋接堵漏材料上,可形成具有自固結特性的堵漏劑,在110 ℃溫度固化后抗壓強度達高到4.6 MPa。

圖7 水下高溫慢固化環氧樹脂堵漏劑制備過程示意圖[15]Fig.7 Schematic diagram of preparation process of underwater high temperature slow curing epoxy resin plugging agent[15]
針對常用化學堵漏劑抗溫性能差、承壓封堵能力弱,無法有效封堵深層復雜漏失地層的問題,王建華等人制備了一種油基鉆井液用改性樹脂抗高溫防漏堵漏劑[20],在180 ℃高溫條件下對寬裂縫漏失通道的封堵承壓極限達到6 MPa,可滿足高溫高壓漏失地層中的鉆井液堵漏目的。Li等人采用連續乳液聚合法制備了丁苯乙烯樹脂/納米SiO2(SBR/SiO2)復合材料,分析了SBR/SiO2的分散和封堵機理(圖8)[21]。該研究為解決鉆井過程中油基鉆井液造成的井筒失穩和儲層損害提供了一條途徑,通過添加堵漏劑可在頁巖地層中形成致密濾餅,減少流體漏失。郭鋼等人通過改性環氧樹脂形成了液態堵漏樹脂體系[22],具有低黏、易注入、固化時間可控、耐壓強度高等特點,在長慶油田鎮A井及華B井套管堵漏作業應用效果良好,為油田穩產增產提供一條新的技術途徑。陳大鈞等人對以環氧樹脂和酚醛樹脂復配物為主體材料的堵漏劑進行了改性研究[23],改性后的環氧-酚醛樹脂堵漏劑固化時間可控、強度高,具有較好的抗高溫老化性能以及化學穩定性能,對巖心孔隙的封堵率在98%以上,對巖心裂縫的封堵率在80%以上。賴小林等人研制了一種新型雙網絡吸水樹脂堵漏劑[24],具有很高的抗壓強度和很好的韌性,能夠長期耐受150 ℃高溫,可用于深井超深井堵漏作業。

圖8 丁苯乙烯樹脂/納米SiO2 復合材料分散性和堵漏機理示意圖[21]Fig.8 Schematic diagram of dispersibility and plugging mechanism of butadiene resin/nano-SiO2 composites[21]
1.2 橋接堵漏配方設計方法
橋接堵漏配方設計應優先考慮與漏失通道尺寸相匹配的粒度分布。橋接堵漏材料及其配方粒度分布的獲取方法有實驗測試法和粒度分布函數預測法。國內外學者圍繞裂縫性地層堵漏配方設計開展了大量研究。Vickers考慮粒度分布特征值D90、D75、D50、D25、D10與最大縫寬的關系,提出了指導堵漏配方設計的Vickers準則[25]。Whitfill認為粒度分布均值與平均裂縫寬度相當時封堵效果最優,提出了堵漏配方設計的D50準則[26]。Razavi提出了基于雙峰特征的最優累積粒度分布方程,用于指導裂縫封堵配方設計[27]。Lee開展了單裂縫封堵過程CFD-DEM模擬,基于堆積效率和無量綱漏失速率指標,對比了具有單峰和雙峰粒度分布特征的堵漏配方封堵裂縫效果的差異[28]。Mehrabian等針對井周組合寬度裂縫性漏失,提出了多峰粒度分布堵漏配方設計方法[29]。朱金智等人基于單一橋接堵漏材料粒度分布實測數據,提出了采用分段三次Hermite插值法預測橋接堵漏材料及配方粒度分布的新方法[30]。基于分段三次 Hermite插值法的新方法對橋接堵漏材料配方粒度分布的表征更加準確,堵漏配方的預測累積粒度分布曲線與實測數據高度吻合,不需要預先設定粒度分布函數形式,且適用于具有多峰粒度分布的顆粒物料,可用于預測不同配比顆粒混合物的粒度分布。康毅力等人開展了室內2 mm裂縫封堵實驗,優選出了有效的橋接封堵材料,形成了封堵層優化配方,最終提出針對毫米級裂縫的堵漏材料優化組合,認為對毫米級裂縫進行架橋封堵的最優材料組合為剛性顆粒、彈性粒子與纖維材料,其形成封堵層示意圖如圖9 所示[31]。唐文泉等人優選了高強度架橋材料、填充材料和纖維材料,按1/3~2/3 架橋理論確定不同材料的粒徑范圍,按SAN-2 工程分布理論確定了各種粒徑的體積配比,形成了抗高溫高強度交聯堵漏配方[32]。李峰等人優選了剛性顆粒、柔彈性顆粒和有機纖維材料等不同類型的堵漏材料,優化了1~4 mm不同開度的裂縫堵漏配方,承壓能力達8 MPa[33]。根據國內外學者的研究,封堵不同裂縫和孔隙尺寸,需要對多種材料的粒徑及其體積進行設計。然而,現有的深層裂縫性地層堵漏配方設計方法主要以粒度分布為指標,僅考慮了裂縫封堵致密性,無法兼顧裂縫封堵承壓能力,未實現裂縫封堵層力學-幾何結構協同優化,導致深層裂縫性地層堵漏效果常難以復制,一次堵漏成功率普遍偏低。

圖9 剛性顆粒、彈性粒子與纖維材料形成封堵層示意圖[31]Fig.9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ealing layer formed by rigid particles,elastic particles and fiber materials[31]
1.3 橋接堵漏配方組成和應用
準確快速預測堵漏材料及其配方粒度分布是橋接堵漏配方數字化、智能化設計的關鍵。許成元等人提出的堵漏材料定量評價優選方法,可系統評價堵漏材料幾何、力學和化學參數,實現對堵漏材料定量評分和快速優選,如圖10 所示[34]。采用優選材料所形成的配方封堵承壓能力大于15 MPa,并在塔里木盆地深層裂縫性儲層2 口井堵漏現場試驗驗證了該方法的可靠性,有效提高了裂縫封堵效果。暴丹等人通過不同類型抗高溫堵漏材料的粒徑級配和濃度控制,優化得到了不同裂縫開度的抗高溫致密承壓封堵工作液配方,其高溫封堵承壓能力≥10 MPa,最高可達15 MPa[35]。王書琪等人研究出了一套適合不同地層不同漏速的高密度橋接堵漏配方,在卻勒101、群6 井堵漏和提高地層承壓能力,施工5 次,一次成功率為100%[36]。張沛元等人采用橋接堵漏材料由細到粗、濃度由低到高的邊配邊注的逐級漸進法施工,有效提高了堵漏成功率和減少重復井漏的可能性[37]。現場應用該方法施工6 口井、7 井次,成功率為100%。目前,雖然國內外專家學者相繼建立了深層裂縫性地層堵漏材料定量評分模型,并形成了橋接堵漏材料定量評分優選方法,但是常規橋接堵漏配方仍以漏速大小來決定堵漏材料粒度、濃度及注入量,易發生堵漏漿全部漏失或大顆粒封門現象,堵漏成功率不高或出現重復井漏。

圖10 深層裂縫性地層堵漏材料關鍵性能參數及定量評分優選圖[34]Fig.10 Optimization diagram of key performance parameters and quantitative scores of plugging materials in deep fractured formations[34]
橋接堵漏是解決裂縫性地層井漏問題的有效方法之一。利用不同形狀及尺寸的橋接堵漏材料,以不同濃度與鉆井液復配,通過堵漏漿流動過程中在裂縫內架橋、堆積和充填,形成裂縫封堵層。但常用橋接堵漏材料與裂縫尺度級配性差,現有技術無法準確反映地下裂縫尺度,因而難以科學優選橋接堵漏材料的粒徑范圍,導致橋接材料與裂縫尺度級配性不強,易在小裂縫入口“封門”或在大裂縫內“難駐留”。
2 裂縫性地層橋接封堵層穩定性研究現狀
裂縫封堵層細觀結構穩定性控制著宏觀結構承壓能力,進而影響工作液漏失控制效果。裂縫封堵層的結構穩定性是決定漏失控制效果的關鍵因素。國內外學者圍繞裂縫封堵層結構穩定性,分別在裂縫封堵層結構特征、堵漏材料性能參數提取、裂縫封堵層細觀結構表征、裂縫封堵層承壓失穩機理等方面開展了大量研究。
2.1 橋接封堵層力學穩定性研究現狀
裂縫封堵層是由堵漏材料組成的離散顆粒物質體系,裂縫封堵層結構研究已成為防漏堵漏理論與技術發展的重要方向。關于裂縫封堵層結構特征,康毅力等人認為地層承壓能力強化理論主要包括應力籠、阻滲帶和強固環理論,提高地層承壓能力的最終目的是建立井筒液柱壓力與地應力場和地層壓力場的平衡(圖11)[38]。裂縫擴展與延伸、滲流效應和地層壓力衰竭是弱化地層承壓能力的主要因素。閆霄鵬等人明確了承壓過程裂縫封堵層強弱力鏈演化特征,基于網絡科學方法提取了裂縫封堵層細觀力鏈網絡,揭示了裂縫封堵層結構失穩細觀力學機制,如圖12 所示[39]。關于堵漏材料性能參數提取,Aston等人提出“應力籠”加固井壁方法,該方法要求堵漏材料需具有一定的抗壓強度,以確保裂縫封堵層形成后能夠支撐裂縫張開[40]。Xu等人通過數學模型和對堵漏強度和堵漏效率的模擬,確定了堵漏材料的關鍵力學參數,建立了考慮剪切破壞的裂縫封堵強度模型,并采用計算流體力學和離散元耦合方法對裂縫封堵效率進行了模擬,提出了一種優化材料選擇的綜合方法[41]。Kang等人提出了堵漏材料磨蝕粒度降級測定方法,探討了堵漏材料磨蝕粒度降級主要控制因素[42]。關于裂縫封堵層細觀結構表征,Yan等人基于顆粒物質力學理論,考慮裂縫封堵層結構剪切失穩模式,引入光彈實驗法研究裂縫封堵層結構,提出了裂縫封堵層細觀結構表征光彈實驗法[43]。關于裂縫封堵層結構承壓穩定性方面,Kumar等人指出,鉆井過程反復漏失的主要原因是裂縫閉合或張開導致的裂縫封堵層結構破壞[44]。Xu等人考慮了裂縫封堵層摩擦失穩和剪切失穩模式,建立了裂縫封堵層強度模型[45]。盡管目前國內外專家對裂縫封堵層結構穩定性研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是由于缺少對超高溫高壓條件下承壓過程裂縫封堵層動態細觀力學參數提取與細觀結構演化的精細刻畫,裂縫封堵層結構失穩細觀力學機制尚不明確,橋接材料在裂縫內架橋堆積,在井筒與地層壓差作用下形成擠壓封堵層,其結構強度易受井筒壓力波動等因素影響而降低甚至“潰散”,導致堵漏失效。

圖11 封堵層的多尺度結構及力鏈網絡[38]Fig.11 Multi-scale structure and force chain network of the plugging layer[38]
2.2 橋接封堵層高溫穩定性研究現狀
隨著油氣資源勘探開發領域的不斷拓展,逐漸走向陸地深層超深層、海洋深水深層、高溫地熱以及干熱巖等復雜高溫地層,而常用的堵漏材料難以滿足超高溫環境的需求。因此,超深層高溫環境給橋接堵漏帶來了更為嚴峻的挑戰,對堵漏材料的抗溫能力、抗壓強度、穩定性及漏層滯留能力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Yan通過對橋接封堵層顆粒間力的分析,描述了封堵層的多尺度結構(圖13)[46]。結合裂縫性儲層的地質特征和鉆井作業特點,提出了封堵帶結構穩定性的表征方法。熊正強等人通過對橋接堵漏材料抗溫性能篩選及不同堵漏材料粒度匹配研究,以剛性顆粒、礦物纖維、變形顆粒、屏蔽降濾失材料及高溫保護劑為原料研制了一種抗200 ℃高溫隨鉆堵漏劑GPC-200,具有良好的抗高溫封堵性能[8]。段永賢等人研制了一種超深水平井架橋顆粒堵漏材料CQ-GXJQ,該堵漏材料具有粒度可調、抗高溫、機械強度高等優點,可作為剛性架橋粒子用于超深水平井橋接堵漏技術中[47]。李家學等人研制的惰性、抗高溫、高強度、不規則顆粒狀剛性顆粒堵漏材料,使用隨鉆封縫即堵技術在迪那地區應用后相比于鄰井漏失量減少73.6%,漏失次數減少67%[6]。為了提高隨鉆堵漏劑的抗溫性能,也有選用抗高溫填充變形材料作為主要原料,采用一定的加工工藝制備抗高溫隨鉆堵漏劑。例如,王富華等人以廢橡膠制品為主要原料,經脫硫改性以及配合活性劑與增效劑制備了一種抗150 ℃高溫橋接型防漏堵漏劑LD[48]。王先兵等人利用果殼具有的柔韌性、硬度高、抗高溫以及變形性好等特點,先后以杏仁殼、多種天然果殼為主要原料,經初級粉碎、脫脂、干燥、超微粉碎及造粒等加工工藝研制了新型抗溫達160 ℃的隨鉆堵漏劑 ZTC-1[49]。目前國內外研究表明,橋接類堵漏材料資源豐富,但隨著高溫高壓井的不斷增多,需要采用抗溫性能更優的橋接堵漏材料,如礦物纖維、抗高溫橡膠顆粒、彈性石墨、抗高溫吸水樹脂變形顆粒等,通過粒度匹配及各組分加量比例調節,研制耐高溫隨鉆堵漏劑。

圖13 橋接封堵層的多尺度結構穩定性[46]Fig.13 Multi-scale structural stability of the bridging plugging layer[46]
2.3 橋接封堵層穩定性評價方法
裂縫封堵層的結構穩定性,是決定漏失控制成敗的關鍵因素。大多數的封堵失效和重復漏失都與封堵層結構失穩有關。徐江等人采用新型裂縫封堵評價裝置對橋塞封堵裂縫的動態過程進行了分析,探索了橋接堵漏材料在裂縫中的封堵規律,揭示了粒度連續分布的橋接堵漏材料在裂縫中形成多級封堵層現象[7]。蘇曉明等人提出了封堵層氣蝕剪切失效概念,構建了封堵層氣蝕剪切失效的物理模型,并借助顆粒物質力學理論,對封堵層氣蝕剪切失效過程進行了深入研究,揭示了封堵層氣蝕剪切失效機理,如圖14 所示[50]。許成元等人采用耦合計算流體力學-離散元(CFDDEM)方法模擬了裂縫封堵層結構形成過程,采用自主研制的表征封堵層細觀力鏈網絡的光彈實驗系統模擬了裂縫封堵層結構承壓演化過程,揭示了裂縫封堵層結構形成與演化機制,形成了堵漏材料優選與堵漏配方設計新方法[51]。李松等人應用有限元法模擬了封堵層對裂縫變形、井周切向應力及裂縫尖端應力強度因子等裂縫變形因素的影響,探索了封堵層存在下的裂縫變形行為,量化了封堵層對裂縫變形程度的影響[52]。Yang等人研究了纖維濃度、長徑比、直徑、密度、剛度、旋光度、泊松比等因素對頁巖孔隙封堵效率的影響[53],建立了基于纖維的離散元流固耦合封堵模型,闡明了納米纖維在頁巖孔隙中的動態遷移和封堵過程。邱正松等人[54]采用計算流體力學-離散元耦合方法對橋接顆粒運移和封堵的微觀過程進行了研究,明確了顆粒形狀、楊氏模數、粒徑分布和流體動力粘度對架橋效率的影響。Pu等人采用計算流體力學-離散元方法建立井筒-裂縫模型,研究封堵液在裂縫中的流動特性[55]。該模型特別考慮了井壁與堵漏漿之間的相互作用,認為封堵層的演化過程可劃分為4 個階段。同時,封堵層的初始結構主要為雙球橋,封堵層的形成位置和隨后的施工速度分別取決于顆粒大小和濃度,優化顆粒組合可以有效提高封堵層的結構穩定性。

圖14 不同流場中封堵層結構及剪切失穩過程示意圖[50]Fig.14 Schematic diagram of plugging layer structure and shear instability process in different flow fields[50]
目前,提高橋接封堵層的高溫和力學穩定性是提高堵漏成功率的關鍵,抗高溫和高強度是超深層鉆井堵漏材料的必備性能之一,現有果殼、纖維等常規橋接材料高溫易碳化或降解,封堵層長期穩定性能較差,復漏風險高,難以滿足日益增多的深層鉆井堵漏需求。因此,研發具備抗高溫、強級配、高穩定性等一體化特性的功能型堵漏新材料,揭示其裂縫堵漏機理,可為深層裂縫性地層堵漏提供新材料、新機理和新方法借鑒。
3 裂縫性地層橋接承壓堵漏機理研究現狀
堵漏材料在裂縫壓力下進入裂縫中,通過架橋、堆積、充填實現對裂縫性地層的封堵,橋接作用是形成封堵層的關鍵,橋接封堵層的形成破壞演化及不同堵漏配方中處理劑的相互作用將直接影響到封堵層的致密性和結構強度,從而影響承壓穩定性,明確裂縫性地層橋接承壓堵漏機理,對于堵漏材料研發和封堵配方設計意義重大。
3.1 橋接堵漏材料封堵理論
目前關于堵漏材料架橋封堵的粒度設計理論或規則較多并且不統一。比較常用的堵漏材料架橋設計的理論和規則有:1/3 架橋理論、屏蔽暫堵理論、理想充填理論、D50規則、D90規則等。針對孔隙和小尺度裂縫,Abrams等人提出了適用于封堵孔隙型地層的1/3架橋理論[56]。國內學者對“1/3 架橋理論”進一步發展提出了“屏蔽暫堵理論”,認為當架橋粒子與儲層孔隙平均孔徑的1/3~2/3 匹配時,地層孔喉處的橋堵最穩定[57]。繼承經典的“屏蔽暫堵”理論,呂開河等人提出了基于微裂縫地層儲層保護的預交聯凝膠顆粒鑲嵌暫堵機理和自適應堵漏機理[58]。“1/3 架橋理論”及“屏蔽暫堵理論”已在防漏堵漏與儲層保護領域取得了不少的應用成果,但在某些情況下,并不能達到一種最佳的堵漏和儲層保護效果。國內外學者應用顆粒堆積效率最大值原理并依據大量試驗的結果,提出了對暫堵劑顆粒尺寸進行優選的“理想充填理論”。認為當顆粒累計體積分數與粒徑的平方根成正比時,顆粒的堆積效率達到最高,可實現顆粒的理想充填[59]。對于中-大尺度裂縫的架橋封堵,張金波等人以“理想充填理論”和“D90規則”為基礎,充分考慮了對不同尺寸孔喉的暫堵,提出了一種有利于對中、高滲透儲層實施暫堵和保護的新方法[60]。
在橋接承壓堵漏機理方面,邱正松等人提出通過合理的顆粒類型、粒度級配與濃度控制,剛性顆粒、彈性顆粒、纖維材料等協同封堵裂縫,形成具有“強力鏈網絡”的致密承壓封堵層,可顯著提高地層承壓能力[61]。孫金聲基于封堵實驗和顆粒物質力學方法研究表明,橋接封堵層的形成過程經歷從慣性流、彈性流到準靜態流的顆粒流態變化過程,揭示了封堵層形成的本質及破壞的驅動能量,提出了鉆井液防漏堵漏顆粒優選規則[62]。許成元等人以顆粒物質力學為基礎,構建了裂縫性地層封堵層失穩模式,同時考慮地層高溫、高壓和高應力條件,建立了裂縫性地層堵漏材料定量評分模型,指出堵漏材料、傳遞力鏈顆粒群或顆粒團簇、裂縫漏失通道中裂縫封堵層3 個尺度構成了裂縫封堵層的多尺度結構[63],鏈接微觀堵漏材料性質和宏觀封堵層承壓性能的橋梁為細觀力鏈網絡結構(圖15)。目前橋接材料承壓堵漏機理的研究主要集中的剛性顆粒材料之間的力學作用方面,對于柔性材料作用機理研究較少,尤其是關于剛柔復合材料在裂縫內的堵漏機理研究較少;此外,沒有涉及堆積過程的橋接顆粒形貌甚至化學形態變化,因而無法解釋包含化學或相態變化的橋接承壓堵漏過程。

圖15 橋接封堵層微觀結構和失穩破壞模式結構[63]Fig.15 Microstructure and failure mode structure of bridging plugging layer[63]
在化學凝膠承壓堵漏機理方面,羅平亞院士(2007)提出了針對裂縫性惡性漏失的“隔斷式凝膠段塞堵漏機理”,其核心是裂縫中凝膠應當“流得進、沖不稀、停得住、排得開、填得滿、隔得斷、抗得住”[64]。Sweatman研究表明,存在于凝膠段塞中的從井筒至地層的壓降,使得作用在裂縫尖端的壓力降低,防止裂縫擴張,因此應強化凝膠自身以及與裂縫壁面之間的膠結強度,提高壓降窗口[65]。白英睿(2015)發現實現聚合物凝膠對地層孔縫成功封堵的前提是:“聚合物凝膠壩”自身內聚力及其與孔縫壁面的粘滯力之和大于“膠壩”封隔前后地層的流體壓差(圖16)[66]。狄麗麗指出預交聯膨脹性凝膠顆粒主要通過“架橋堆積、吸液膨脹、擠壓充填”機理對漏失通道進行封堵[67]。王中華等認為凝膠顆粒具有“變形蟲”特征,會在漏失壓差作用下在孔縫中向前變形蠕動,直至在窄縫處產生架橋、堆積、變形封堵,防止裂縫中壓力傳播和誘導擴展[68]。目前化學凝膠材料承壓堵漏機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下交聯凝膠的承壓封堵和地面交聯凝膠顆粒的膨脹變形封堵等方面,漏失通道內凝膠材料的運移、充填、堵塞等機理研究有待深入研究。

圖16 聚合物凝膠壩及凝膠粒子封堵機理示意圖[66]Fig.16 Schematic diagram of polymer gel dam and gel particle plugging mechanism[66]
綜上,國內外研究者們通過分析堵漏材料在裂縫中的運移、充填過程,形成了系統的適用于孔隙或小裂縫的封堵機理,這些理論的出現對于孔隙或小裂縫中橋接堵漏材料的粒度級配及體系配方優化起到了指導作用。但針對深井中大裂縫中高地應力環境下承壓能力不足的封堵層失穩機理研究仍不足,需要針對大裂縫性漏失地層重新厘定堵漏材料的粒度級配設計理論和方法。
3.2 橋接封堵層的形成、破壞和結構演化機制
橋接封堵層的形成、破壞和演化過程直接影響到封堵層的強度。許成元等人采用耦合計算流體力學-離散元模擬了裂縫封堵層結構形成過程,指出架橋概率是決定封堵層結構形成和裂縫封堵效率的關鍵因素(圖17)[51]。同時,基于顆粒物質力學理論,探索分析了摩擦失穩和剪切失穩2 種封堵層結構破壞形式。張韻洋等人研究認為力鏈的數量和強度是形成穩定封堵層的關鍵[5]。當封堵層數量足夠多且足夠強時封堵層更為穩定。邱正松等人基于裂縫封堵微觀結構受力分析,探討了封堵層失穩破壞形式,提出了將堵漏材料粒度降級率、表面摩擦系數、剪切強度、堆積孔隙比等作為評價封堵失穩的特征參數[61]。康毅力等人分析了低承壓能力地層致漏機理,概括出應力籠、阻滲帶和強固環3 種地層強化理論,建立了不同理論指導,明確了弱化地層承壓能力的主要因素[38]。但是在目前的研究中對于封堵層形成過程中的受力情況及破壞過程的失穩形式的研究尚淺,缺少有效的堵漏材料在演化過程中的評價指標及高效優化設計方法。
橋接堵漏材料的類型、組合、配比、濃度對于封堵裂縫性地層是否能成功封堵漏失層位至關重要。馮永存等人以CFD-DEM數值理論為基礎,研究了顆粒濃度、顆粒級配對于橋堵效果的影響(圖18),認為橋堵顆粒濃度存在著一個“橋堵窗口”,低于“橋堵窗口”下限不能實現有效封堵,而高于這一“窗口”對橋堵效率影響不大[69]。康毅力等人評價了剛性顆粒、彈性粒子以及纖維3 種封堵材料協同堵漏效果,指出在協同封堵過程中,剛性顆粒起到骨架作用,彈性粒子起到增加摩擦力作用,纖維材料起到充填作用[31]。邱正松等人基于微觀顆粒物質力學“強力鏈”基本原理,揭示了基于微納米尺度的鉆井液致密承壓封堵機理,給出了鉆井液強化致密承壓封堵優化設計方法,即通過合理的顆粒類型、粒度級配與濃度控制,剛性顆粒、彈性顆粒、纖維材料等協同封堵裂縫,可形成具有“強力鏈網絡”的致密承壓封堵層,顯著提高地層承壓能力[70]。材料的外形和性能直接影響到封堵層的強弱,Kumar等人分析了材料的圓度、凹凸度等對封堵層的影響,認為將碳酸鈣與彈性石墨碳(RGC)材料結合使用可以有效地提高地層的完整性[44]。但目前大尺度裂縫中橋接堵漏機理研究主要基于不同類型剛性顆粒材料之間的堆積充填作用,以剛性力學結構演化為主,對于功能型橋接材料發生熔融形態變化等而引發的物理化學協同作用的研究較少。

圖18 堵漏顆粒粒徑對漏失裂縫出口漏失速率及橋堵位置的影響[69]Fig.18 Influence of plugging particle size on leakage rate and bridge plugging position at leakage fracture outlet[69]
4 結論與展望
裂縫性地層井漏是制約超深層油氣鉆井的關鍵“卡脖子”難題。橋接堵漏是一種常用且較為見效的堵漏方法,但目前常用橋接堵漏材料抗高溫性能弱、材料粒徑與裂縫尺度級配性差、裂縫中顆粒堆積橋接封堵層穩定性不佳,導致裂縫封堵無效或復漏風險高,難以滿足日益增多的超深層油氣鉆井堵漏需求。因此,裂縫性地層橋接堵漏要想獲得成功,堵漏材料的級配和濃度必須滿足3 個條件:一是堵漏材料要“架得住橋”;二是堵漏材料要具有“嵌入”、“填充”作用;三是橋堵漿要有“滯留”和“掛阻”效果。所以,建議未來應根據漏失和堵漏機理建立可視化模型量化堵漏材料粒徑與裂縫尺度的匹配性,進而確定堵漏材料與裂縫漏失通道的級配關系,同時研發具有裂縫空間形態自適應特性的橋接堵漏材料。
現有基于架橋、充填和堆積理論的裂縫封堵機理,主要反映裂縫封堵層幾何結構形成機制,無法描述封堵層力學結構形成和承壓演化規律,無法解釋封堵層承壓能力不足的根本原因。現有以粒度分布為主要指標的深層裂縫性地層堵漏 配方設計方法,主要考慮了封堵層幾何結構的致密性,無法有效兼顧封堵層力學結構的承壓穩定性,亟待建立基于裂縫封堵層幾何-力學結構協同優化的裂縫封堵新方法。因此,厘清微觀堵漏材料性質—細觀力鏈網絡結構—宏觀封堵層承壓性能關聯機制,搭建起微觀堵漏材料性質與宏觀封堵層力學性能的橋梁,對創新和完善深層裂縫性地層封堵理論與方法具有重要的科學意義。
提高超深裂縫性地層堵漏成功率的關鍵在于提高三維裂縫中橋接封堵層的穩定性,強化封堵層內部以及封堵層與裂縫壁面之間的力學結構是提高封堵層穩定性的基礎。超深層、超高溫、高壓和高鹽等復雜地質條件下,常用橋接顆粒間的物理架橋堆積作用形成封堵層的力學穩定性受井筒與地層之間的壓差作用影響大。使用熱固性樹脂堵漏劑作為功能型橋接材料與常用橋接材料復配使用,在超深裂縫中可通過高溫固化作用將常規橋接封堵層由物理堆積體變為物化固結體,使之免受井筒與地層之間的壓差作用影響,不僅可以顯著增強橋接封堵層內部的力學穩定性,而且可以增強封堵層與裂縫壁面之間的力學作用,提高封堵層在裂縫中的駐留能力,進而提高橋接堵漏一次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