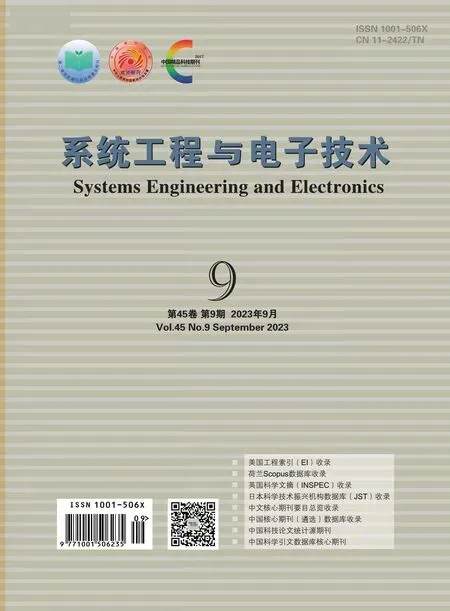基于逆濾波處理的雷達干擾效果在線評估方法
李 瑞, 朱夢韜, 李云杰
(北京理工大學信息與電子學院, 北京 100081)
0 引 言
近年來,先進體制雷達逐步向智能化方向發展,其反對抗能力得到了極大提升,促使雷達對抗方開始研究構建包括態勢感知、干擾效果評估、自適應干擾在內的閉環認知對抗系統[1]。干擾效果評估是認知對抗系統實現閉環的關鍵環節,只有準確地評估,才能及時準確地反饋干擾實施的效果,從而進行干擾策略和參數的優化調整[2]。因此,非合作條件下的干擾效果評估及干擾參數優化已經成為雷達對抗研究領域的一個熱點問題。
干擾效果評估是指在對雷達實施干擾后定性或定量評價雷達受到的損傷或破壞的過程。傳統的干擾效果評估多為合作式評估,需要雷達方提供一定實驗數據,以雷達對應系統功能或性能作為評估指標,依照一定評估準則對評估指標在受干擾前后的數值進行數學計算和分析來實現。評估常用的效能評估準則包括功率準則、信息準則、效率準則、時間準則等,具體的評估計算方法主要包括評估因子法、模糊綜合評估法和智能評估法等。不同評估指標和方法在具體應用中可以組合使用,如文獻[3-4]均在采用智能評估法的同時充分發揮了評估因子法、模糊綜合評估法的優勢。
在真實對抗作戰場景中,對抗方只能根據己方可以偵察感知到的雷達發射信號、波束轉換、平臺機動等多方面因素進行干擾評估,因此需要研究非合作條件下的干擾效果評估方法。文獻[5]提出了非合作式干擾效果評估的必要性、判定標準和具體方法,通過對比在干擾實施前后偵察接收到的雷達發射信號變化,結合先驗知識進行間接評估。Ou等根據干擾前后截獲的雷達信號的脈沖幅度和數據率的變化,以截獲信號的幅度累積量作為特征統計量,設計了基于顯著性檢驗的自屏蔽干擾效能評估檢測器[6]。文獻[5-7]中具體的評估計算過程,均是根據偵察到的雷達發射信號的變化情況分析得出雷達參數、狀態、模式等不同層次的評估指標,經過綜合計算間接評判干擾效果。上述研究所給評估方法的指標計算過程十分依賴專家經驗和戰前情報,且偵收的雷達發射信號幾乎是唯一的評估信息源,攜帶反映雷達系統內部真實狀態的信息量有限。因此,研究能夠定量感知雷達系統內部各環節的狀態在干擾前后變化情況,實現高可信信息支撐的非合作在線干擾效果評估方法非常必要。
逆處理是通過研究系統外部行為或表現逆向推理系統內部細節的方法。Kalman早在1964年發表的文獻[8]中就研究了逆最優控制問題,目的是確定給定控制策略的成本準則是最優的。近年來逆處理問題在多個領域引起了關注。在人工智能領域,逆強化學習是典型的逆處理問題,即在給定策略或觀測行為的條件下逆向推斷智能體的獎勵函數[9-17]。在電子對抗領域,Krishnamurthy在文獻[14]中以具有波形優化能力的認知雷達為對抗對象,首次提出利用微觀經濟學中的顯示偏好理論檢驗雷達是否具有認知能力,并在具有認知能力的情況下估計雷達方波形優化的效用函數。文獻[15]基于上述逆強化學習方法提出了對抗自適應雷達系統的處理框架,提出利用逆濾波處理可以估計雷達方的最優估計和傳感器精度以實現逆跟蹤。
經典的逆濾波問題主要討論的是如何通過貝葉斯濾波輸出的狀態后驗估計濾波輸入或傳感器精度[16]。從1979年開始,就已經有專家學者對線性高斯狀態空間模型下的Kalman濾波的逆濾波問題進行了研究[17-19]。文獻[16]針對線性高斯狀態空間模型下的兩類問題進行了探討,針對已知狀態后驗為真實后驗和狀態后驗帶有噪聲的兩種情況分別提出了對應的逆濾波算法。文獻[20]討論了離散的隱馬爾可夫模型(hidden Markov models, HMM)下的逆濾波問題,提出了基于聚類算法的逆HMM濾波算法。文獻[21]中討論了逆HMM濾波在電子對抗領域的應用,通過逆濾波估計所對抗的目標雷達濾波輸出及其后驗分布和傳感器精度,可為對抗系統自適應干擾提供參考基礎。文獻[22]研究了針對Kalman濾波、粒子濾波[23]等逆濾波處理在對抗自適應雷達系統方面的應用。上述研究均說明,通過逆濾波處理可以獲取雷達濾波輸出及其狀態后驗估計,為非合作對抗系統實現相應的干擾效果評估提供了新的途徑。
本文基于針對雷達系統進行逆處理的思路,設計了一種基于逆濾波處理估計雷達跟蹤誤差,進而實現非合作干擾效果在線評估的方法。以對抗方針對導引頭雷達實施距離門拖引干擾(range gate pull off, RGPO)進行自衛為例,仿真驗證了所提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1 針對雷達系統的逆處理
1.1 雷達系統逆處理框架
如圖1所示,雷達系統可由信號收發、信號及信息處理、資源調度、波形優化模塊組成。信號收發模塊經過天線實現雷達發射信號和回波信號的發射和接收,信號處理部分實現如脈沖壓縮、恒虛警率(constant false alarm rate, CFAR)檢測及目標跟蹤濾波等處理,資源調度和波形優化可通過如強化學習等方法實現雷達系統自適應資源調度和認知波形優化。
對抗方對雷達方進行逆分析處理時,可根據分析對象在雷達系統中所處位置,模塊化映射為慢時間域的逆波形優化和逆資源管理、快時間域的逆信號處理等3個功能模塊。逆波形優化模塊可以基于接收雷達信號序列的參數測量結果,對雷達方的發射信號波形優化目標函數進行反演分析,支持干擾效果評估和干擾策略優化,具體可利用逆強化學習的方法實現;逆資源管理模塊可基于雷達方系統行為序列觀測結果,對雷達方的資源管理調度目標函數進行反演分析,支持干擾策略優化,資源管理逆分析也可通過逆強化學習方法實現;逆信號處理模塊可以基于接收雷達信號變化或者雷達平臺機動變化,即時對雷達方信號或信息處理對應關鍵節點狀態進行推理,如本文研究的根據雷達平臺空間量測逆濾波處理實現雷達目標跟蹤中的跟蹤誤差估計,進而實現干擾效果評估和干擾策略優化。其中,雷達平臺空間量測可由載機自身搭載的有源探測系統或外部輔助探測系統、或通過偵干探通一體化技術支持得到[24-25]。
1.2 逆濾波處理實現雷達跟蹤誤差估計


圖2 目標跟蹤濾波算法原理圖Fig.2 Principle of tracking filter algorithm
具體來說,雷達濾波過程如下所示:
xk~Pxk-1, x=p(x|xk-1),x0~π0
(1)
yk~Bxk,y=p(y|xk)
(2)
πk=T(πk-1,yk)=p(xk|y1:k)
(3)

(4)



圖3 雷達對抗中的逆濾波問題建模Fig.3 Inverse filtering problem modeling in radar countermeasures
(5)
針對距離假目標、速度假目標、距離拖引干擾、速度拖引干擾等旨在破壞雷達跟蹤精度的干擾樣式,可以利用對雷達跟蹤誤差的估計實現非合作條件下的干擾效果在線評估。
2 雜波背景下雷達濾波算法的逆濾波處理
針對噪聲、雜波環境、多目標、目標機動等不同應用場景,研究者針對性地提出了許多雷達跟蹤濾波算法。不同雷達濾波算法需要推導與其匹配的逆濾波處理算法,文獻[14-16]在給出逆濾波處理概念時,已針對基本Kalman濾波算法的逆濾波過程進行了討論。考慮末制導雷達導引頭在實際攔截攻擊機動目標時會遇到有雜波信號的場景,本文針對可以適用雜波背景的PDA濾波算法,推導了對應的逆濾波處理方法。
2.1 逆PDA濾波算法
PDA濾波算法是標準Kalman濾波結合概率數據關聯思想的一種跟蹤濾波算法,能夠很好地解決雜波場景下的目標跟蹤問題[26]。
PDA濾波的目標狀態模型為
xk+1=Axk+wk,x0~π0
(6)


(7)
式中:C為量測矩陣;vk~N(0,Rk)為量測噪聲;Rk為量測噪聲協方差矩陣。
(8)
濾波誤差協方差如下:
(9)

(10)
雷達可根據上述濾波結果和某些預制函數選擇其動作為uk[22]。若雷達方為雷達導引頭,該動作可以是基于線性二次型高斯(linear quadratic Gaussian, LQG)理論設計的最優制導律,即雷達導引頭的加速度狀態。若雷達方為認知雷達,則該動作可以為雷達波形設計或資源管理動作,即雷達系統的發射波形或資源分配結果。對抗方在噪聲中觀測到的雷達方動作ak如下:
(11)

將式(7)代入式(8)可得
(12)
由式(10)可得
(13)

(14)
式中:PD為檢測概率;PG是n維量測落入波門內的概率;與雷達方相同,PD和PG根據專家經驗得出[27]。將式(14)代入式(12)可得對抗方逆PDA濾波模型的狀態方程為
(15)
由狀態方程式(15)和量測方程式(11)可知,逆PDA濾波模型是一個線性高斯模型,可采取與標準Kalman濾波類似的方法進行逆處理。為了便于描述,將對抗方逆濾波使用的狀態矩陣、控制矩陣、狀態過程噪聲、量測噪聲如下所示:
(16)

(17)
式中:Σk|k-1=AΣk-1AT+Qk;λ為雜波密度;a、b、c為3個計算因子,可根據文獻[28]查表得出。則
(18)
根據上述推導,對抗方實現逆PDA濾波的輸入為雷達動作的帶噪量測,輸出是雷達方對對抗方運動狀態的估計的最優估計,處理流程如圖4所示。

圖4 逆PDA濾波算法流程圖Fig.4 Diagram of inverse PDA filtering algorithm
與圖4對應的具體逆濾波實現步驟如下。

步驟 3狀態預測。
預測雷達對目標狀態的最優估計:
(19)
預測對抗方逆濾波的誤差協方差:
(20)
步驟 4狀態更新。
對抗方逆PDA濾波增益為
(21)

(22)
更新k時刻的濾波協方差:
(23)
步驟 5k=k+1,跳轉至步驟2進行下一時刻處理。
2.2 仿真分析
2.2.1 仿真設置
在二維平面內進行仿真,雷達始終位于坐標原點,在雜波背景下利用PDA濾波對目標的距離、速度信息進行濾波跟蹤。目標初始位置為[5 km,8 km],并以100 m/s的速度沿x軸負方向做勻速直線運動,仿真中時間間隔為Δt=1 s,總時長為100 s。

假定雷達濾波檢測概率PD=1.0,波門大小隨濾波過程中的新息協方差變化,PG=0.999 7。具體的雜波生成參考文獻[29]中的方法,雜波量測在關聯波門內服從泊松分布。
對抗方在雜波下利用逆PDA濾波算法估計雷達對目標運動狀態的估計,進行100次蒙特卡羅實驗,通過計算均方根誤差和均方根誤差均值對逆PDA濾波算法估計雷達對目標運動狀態估計的準確性進行評價。距離均方根誤差(root mean square error,RMSE)及其均值計算公式如下:
(24)
(25)

2.2.2 仿真結果及分析
(1) 不同對抗方量測噪聲下的仿真實驗
對抗方量測噪聲均方差取rus={5,10,30},仿真實驗結果如圖5所示,仿真中λ為0.000 1 s/m。

圖5 不同rus下的逆濾波RMSEFig.5 Inverse filtering RMSE under different rus
由圖5可知,對抗方量測噪聲均方差的大小會略微影響算法的收斂速度,但在10幀后均收斂到穩定值,說明雜波下逆PDA算法具有時效性。通過對比收斂后的RMSE可知,當雜波密度固定時,量測噪聲均方差越大,逆濾波估計的誤差越大。
對抗方量測噪聲均方差以1為步進遍歷0~100區間,所得平均RMSE如圖6所示。

圖6 不同rus下的逆濾波平均RMSEFig.6 Inverse filtering average RMSE under different rus
由圖6可知,當rus為0時,逆濾波AVRMSE最小,隨著rus的增大,AVRMSE越來越大,但當rus增大到100時,距離AVRMSE仍然較小,小于1.5 m,速度AVRMSE則始終小于1 m/s,說明雜波下逆PDA濾波算法估計雷達最優估計的誤差較小,準確性高。
(2) 不同雜波密度下的仿真實驗
對抗方量測噪聲均方差rus=10,雜波密度取λ={0.000 1,0.000 5,0.001},仿真所得逆濾波距離和速度RMSE如圖7所示。
由圖7可知,雜波密度越大,逆濾波算法的收斂速度越慢,且逆濾波的估計誤差越大。當雜波密度為0.000 1時,算法收斂速度最快。當雜波密度為0.000 5時,在15~20幀距離速度RMSE才收斂,收斂后距離速度RMSE均大于λ=0.000 1時的實驗結果。當雜波密度增大到0.001時,算法的收斂速度最慢,收斂后的RMSE最大。
圖8為以0.000 1為雜波密度步進值,在不同雜波密度下實驗所得AVRMSE結果。由圖8可知,雜波密度越大,距離和速度的平均RMSE值越大,即逆濾波估計的誤差越大。

圖8 不同λ下的逆濾波平均RMSEFig.8 Inverse filtering average RMSE under different λ
綜上所述,雜波下逆濾波估計準確性與對抗方量測噪聲和雜波密度有關,量測噪聲均方差和雜波密度越大,逆濾波估計誤差越大,但當rus和λ在正常范圍內,逆PDA濾波算法能夠以較低誤差估計雷達方對目標運動狀態的估計,因此可以利用對雷達最優估計的估計對雷達跟蹤誤差進行逆向計算,為非合作條件下的干擾效果定量評估提供依據。
3 基于逆濾波處理的距離拖引干擾效果在線評估方法
RGPO干擾是典型的可通過增大雷達跟蹤誤差,逐漸引偏雷達致使雷達重新搜索的干擾樣式,本節以RGPO干擾為例,設計通過逆濾波處理實現對抗方對雷達跟蹤功能干擾效果的在線評估和干擾參數的實時優化。
3.1 RGPO干擾原理
RGPO干擾是最有效的欺騙干擾方法之一。典型的RGPO干擾的實施過程分為捕獲期(停拖期)、拖引期、關閉期3個階段[30]。假設拖引期進行勻速拖引,上述過程可用如下所示:
(26)
式中:v1為真實回波所代表的目標運動速度;v2為對抗方拖引干擾的拖引速度;t1為停拖期時長,t2-t1為拖引期時長;TJ為一個拖引周期。
RGPO干擾的效果與拖引策略有密切關系。若拖引速度太快則可能由于雷達方的距離跟蹤系統難以及時響應,導致干擾信號脫離雷達跟蹤波門,或被雷達抗干擾環節識別,導致干擾失敗,若拖引速度太慢可能導致拖引期結束仍未將雷達跟蹤波門拖離真實目標回波信號,干擾也會失敗。傳統的RGPO干擾往往利用情報分析實現制定干擾策略,在作戰過程中按照固定策略實施干擾。且對干擾是否成功的判別,也只能在一個干擾周期結束后通過狀態識別判斷雷達是否進入搜索狀態來進行判定或根據多次試驗數據計算拖引成功率進行干擾效果評估,無法在一個干擾周期內對干擾效果進行在線評估,并實時調整干擾策略參數[30]。
3.2 基于逆濾波處理的RGPO干擾效果評估
本節設計的基于逆濾波處理對RGPO干擾效果進行在線評估,并根據評估結果動態調整干擾策略的方法總體流程如圖9所示。

圖9 基于逆濾波處理的干擾效果在線評估原理Fig.9 Principle of online evaluation of interference effect based on inverse filter processing
(1) 雷達距離跟蹤誤差估計

(2) 距離跟蹤誤差突變點檢測
針對距離門拖引干擾,雷達方可以通過跟蹤波門移動速度變化率的分析識別拖引干擾,然后采用記憶跟蹤波門等方法對抗拖引干擾[31],造成拖引干擾失敗。為了利用距離跟蹤誤差進行干擾效果判定,本文根據距離拖引干擾原理定義了圖10所示的3類突變點:① 起拖突變點:假設停拖期干擾信號能夠成功捕獲距離波門,A點時刻進入拖引期,拖引干擾開始起效,雷達距離跟蹤誤差會發生第1次突然增大,將該點稱為起拖突變點。② 成功突變點:拖引期出現起拖突變點后,雷達跟蹤誤差將持續增大。如果跟蹤波門在B點時刻被成功拖離真實目標回波,雷達跟蹤誤差將發生第2次突然增大,將該點記為成功突變點。③ 失敗突變點:如果在拖引期實施過程中,由于拖引速度過大沒有拖走跟蹤波門或干擾被雷達成功識別,雷達在C點時刻重新鎖定跟蹤上目標本體,雷達跟蹤誤差會突然減小,記該點為失敗突變點。

圖10 勻速RGPO下雷達距離跟蹤誤差變化Fig.10 Radar range tracking error change under constant-speed RGPO
跟蹤誤差突變點檢測方法設計如下。
(27)
進入拖引期后,若從k0時刻開始連續累計Δkt個時刻點誤差斜率均值比前一時刻誤差斜率均值的增長量大于閾值γe1,則將k0+Δkt-1時刻記為突增點,記該時刻為k1,從k1時刻開始重新計算距離誤差均值,即
(28)
若在拖引期首次檢測出突增點則為起拖突變點,若在檢測出起拖突增點后雷達跟蹤誤差持續增大,并第2次檢測出突增點,則為成功突變點。
突降點檢測與突增點檢測方法類似,對估計跟蹤誤差曲線斜率進行記憶,計算曲線斜率均值,當從某一時刻開始連續Δkt次誤差均值減小量大于閾值γe2,則檢測為失敗突變點。
(3) 干擾效果在線評估及策略調整
基于突變點檢測結果,可以對干擾成功/失敗及成功/失敗時刻的干擾效果進行評估,并根據評估結果調整干擾策略。干擾效果評估結果及干擾策略調整措施如表1所示,其中Ⅲ型失敗是由于拖引速度過大導致在拖引初期干擾信號就脫離跟蹤波門或被雷達抗干擾識別,其余類型原因見上文。需要指出的是,在線干擾策略調整是一個多要素約束條件下的受限優化問題,由于本文重點為基于逆濾波處理的干擾效果在線評估方法設計,在干擾策略調整方面做了簡化處理,即根據評估結果直接對拖引速度及關機時間做出調整。

表1 干擾效果在線評估結果與策略調整關系Table 1 Relationship between evaluation and strategy adjustment
4 仿真驗證
4.1 目標建模
本文仿真驗證以主動尋的制導雷達導引頭作為雷達方,體制為脈沖多普勒雷達,雷達導引頭基于LQG控制理論[32-33]確定的最優制導律帶來的雷達位置狀態變化,作為雷達方動作。本文假設該雷達量測已由載機自身搭載的有源探測系統或外部輔助探測系統或通過偵干探通一體化技術支持得到。

(29)
式中:amx、amy、amz表示雷達導引頭在各方向上的加速度分量;系數C1,C2,C3分別如下:
(30)
式中:tgo表示飛行器剩余飛行時間;N為導航比。由式(29)可知,在該制導律影響下,導彈運動特性與彈目距離、導航比、飛行器剩余飛行時間有關,且在導航比及剩余飛行時間一定的前提下,導彈在x、y、z各方向上的運動加速度隨跟蹤距離的增大而增大。

4.2 仿真場景
具體對抗仿真在二維平面空間內進行,場景為空-空對抗,導彈迎頭攻擊載機目標,雷達對目標進行距離、速度跟蹤。以雷達初始位置為坐標原點建立直角坐標系,導彈初始飛行速度為[400 m/s,500 m/s],目標初始時刻位于[1 000 m,1 000 m],沿x軸負方向做勻速直線運動,速度為200 m/s。
雷達在雜波中利用PDA濾波器對目標進行跟蹤,距離波門寬度為脈寬的整數倍,脈寬μ=5×10-6s。目標檢測概率PD=1,目標落入波門內概率PG=0.999 7。假設波門最大跟蹤速度vmax=700 m/s。對抗方采取自衛式距離門干擾,假設干擾在停拖期可以成功捕獲距離跟蹤波門,干擾參數設置如表2所示。

表2 距離拖引干擾參數設置Table 2 Range pull-off parameter setting
仿真中雜波體現為關聯波門內的虛假測量點,雜波生成方式與第2.2節相同,仿真中每幀Δt=0.01 s。
實驗從以下3個方面評價本文干擾效果評估方法的有效性和適用性。
(1) 在線干擾效果評估結果的正確性。若雷達方的真實情況與干擾方在線干擾效果評估結果相同,評估正確,反之評估錯誤。
(2) 在線干擾效果評估的時效性。采用干擾方得到評估結果時刻t1與導引頭真實受影響時刻t0間的延遲Δτ=t1-t0,評價該方法的時效性。
(3) 雷達跟蹤誤差估計的準確性。由于干擾效果評估以跟蹤誤差估計為基礎,因此跟蹤誤差估計RMSE能一定程度反映干擾效果評估的準確性。采用拖引期內干擾效果評估過程中的雷達跟蹤誤差估計RMSE值,評價對抗方對雷達跟蹤誤差估計的準確度,具體計算方法如下:
(31)

4.3 結果分析
(1) 不同拖引干擾參數下的干擾效果評估
圖11~圖14所示為拖引速度為vj={50,200,500,700}m/s條件下的四組干擾效果評估結果,實驗中設置導引頭導航比N=10,雜波密度λ=0.000 1 s/m。

圖11 Ⅰ型失敗干擾效果評估曲線圖Fig.11 Interference effect evaluation curve for type I failure
圖11所示為干擾效果評估結果為Ⅰ型失敗時的干擾效果評估曲線,由圖11可知,當拖引速度為500 m/s時,真實和估計跟蹤誤差曲線均在2.38 s時檢測到失敗突變點,判斷干擾失敗,說明當前拖引速度過大,導致被雷達抗干擾模塊識別或由于速度過大使得干擾信號脫離跟蹤波門。圖12所示為Ⅱ型失敗的干擾效果評估曲線,可看出拖引期只檢測到了起拖突變點,說明當前50 m/s的拖引速度太小,不足以使真實回波脫離雷達跟蹤波門。

圖12 Ⅱ型失敗干擾效果評估曲線Fig.12 Interference effect evaluation curve for type Ⅱ failure
圖13所示為Ⅲ型失敗的干擾效果評估曲線,可以看出當前拖引速度過大,初始時刻就被雷達抗干擾失敗或干擾信號脫離跟蹤波門或拖引速度超過雷達最大跟蹤速度。如圖14為判定結果為成功的干擾效果評估曲線,可看出在拖引期相繼檢測到起拖突變點和成功突變點,說明當前200 m/s的拖引速度可以成功將雷達距離波門拖離目標回波。

圖13 Ⅲ型失敗干擾效果評估曲線Fig.13 Interference effect evaluation curve for type Ⅲ failure

圖14 成功干擾效果評估曲線Fig.14 Successful interference effect evaluation curve
表3所示為拖引速度取50~700 m/s的7組實驗結果。由表3可知,不同拖引速度下干擾效果定性評估結果均正確,與真實干擾結果相同。

表3 不同RGPO參數下干擾效果評估結果Table 3 Evaluation results of interference effect under different RGPO parameters
當拖引速度過小,如50 m/s時,干擾效果評估時延為0 s,這是由于判定依據為直到拖引期結束還未出現成功/失敗突變點,因此判定時刻為拖引期結束時,沒有突變點檢測引入的時延。當拖引速度取100~500 m/s時,干擾成功/失敗的判定均是由于在拖引期檢測到成功/失敗突變點,因此會引入突變點檢測的必要時延,即突變點檢測中累計判斷時長,仿真中設定檢測中累計判定次數為Δkt=3,因此時延為0.02 s。當拖引速度為700 m/s時,由于拖引期過半還沒有檢測到起拖突變點,則沒有由于突變點檢測引入的時延,但實際上從進入拖引期開始干擾便失敗,而判定時刻為拖引期中期,因此判斷時刻延遲拖引期時長的一半。此外通過分析距離跟蹤誤差估計的RMSE值可知,盡管相比于第2.2節中無干擾下的估計RMSE有所增大,但如表所示,該范圍內的RMSE增減未對干擾效果評估的正確性及時效性產生影響。
(2) 不同對抗方量測噪聲的干擾效果評估
在拖引速度vj=200 m/s,雷達導引頭導航比N=10的基礎設置下,令觀測噪聲均方差rus取0~100的8組數值,可得如表4所示的實驗結果。
由表4可知,當量測噪聲均方差在0~100內時,干擾效果定性評估結果均正確。干擾效果評估時延和跟蹤誤差估計RMSE會隨對抗方量測噪聲均方差的增大而增加。當量測噪聲均方差較小時,干擾效果評估時延的來源僅為突變點檢測中的累計判斷時長。
當量測噪聲均方差為10時有如圖15所示的仿真結果。

圖15 干擾效果評估曲線(rus=10)Fig.15 Interference effect evaluation curve (rus=10)
由圖15可知,此時成功突變點變得更加“不明顯”,需等到誤差斜率均值增大到一定閾值才可判定成功,因此當量測噪聲均方差大于10時,評估時延不僅來源于突變點檢測中的必要時延,還包括由于突變點“不明顯”導致的檢測滯后。且該時延隨著量測噪聲均方差的增大而增加,對應的跟蹤誤差估計RMSE也會增大,當時延增大到一定程度后,將導致在拖引期內始終未檢測出成功突變點,判定干擾失敗,導致評估結果錯誤。經實驗,當量測噪聲均方差在正常范圍內時不會出現上述情況,因此能保證干擾效果評估的正確性。
(3) 不同雷達動作參數下的干擾效果評估
在拖引速度vj=200 m/s,對抗方量測噪聲均方差為rus=0.1 m的條件下,改變雷達動作參數,在本節所設置的仿真場景中主要體現為雷達導引頭的導航比,令導航比從0.1增大到5進行如表5所示的7組實驗。

表5 不同雷達動作參數下干擾效果評估結果Table 5 Evaluation results of interference effect under different radar action parameters
由表5可知,雷達導引頭導航比越大,干擾效果評估時延和跟蹤誤差估計RMSE越小。當雷達導引頭導航比小于1時,評估時延和跟蹤誤差估計RMSE稍大,但仍能保證評估結果的正確性。當導引頭導航比大于1時評估時延小于1 s。且導航比只需大于3即可保證干擾效果評估方法沒有除突變點檢測必要時延外的其他時間延遲,保證干擾效果評估的強時效性。
綜上所述,本文所提出的基于逆濾波處理的RGPO效果評估方法適用于不同拖引速度下的RGPO效果評估。干擾效果評估的正確性、時效性及距離跟蹤誤差估計準確性與對抗方的量測噪聲和雷達動作參數有關。隨著量測噪聲均方差增大和導航比的減小,干擾效果評估的時間延遲和跟蹤誤差估計RMSE增大,增大到一定程度可能導致干擾效果定性評估結果錯誤。經仿真實驗可知,當對抗方量測噪聲均方差小于100,雷達導引頭導航比大于0.1時,干擾效果評估結果均正確。且當量測噪聲均方差小于30,雷達導引頭導航比大于等于1時,在干擾效果評估結果正確的基礎上,可保證干擾效果評估的強時效性和距離跟蹤誤差估計的準確性。
(4) 基于干擾效果評估的距離拖引干擾策略調整仿真實驗
本實驗驗證如本文第3.2節所述的距離拖引干擾策略改進方法,仿真設置初始拖引速度為500 m/s,結果如圖16所示。

圖16 干擾策略調整過程的干擾效果評估曲線Fig.16 Interference effect evaluation curve of the interference strategy adjustment process
由圖16可知,仿真開始以500 m/s的拖引速度進行首次干擾,于2.4 s檢測到失敗突變點,判定干擾失敗,根據策略調整方案需要停止拖引并減小拖引速度。減小拖引速度為400 m/s后開始實施第2次干擾,但此時拖引速度仍較大,導致干擾信號在5.22 s再次脫離雷達距離跟蹤波門,對抗方在5.24 s檢測到失敗突變點并停止干擾。再次減小拖引速度到300 m/s后實施第3次干擾,在8.7 s時檢測到成功突變點,判定干擾成功。由圖16可知,在第1次干擾周期內基于干擾效果在線評估結果調整干擾策略后進行了第2次拖引干擾,并在第2次拖引干擾周期內根據本次評估結果調整拖引速度參數及關機時間,實施第3次距離拖引干擾后干擾成功。本實驗表明,本文所提方法可實現非合作對抗過程中的干擾效果在線即時評估,并通過在線調整策略達到成功干擾的目的。
5 結束語
本文針對非合作雷達干擾效果在線評估問題,提出了基于逆濾波處理的干擾效果在線評估方法并基于此對干擾參數進行實時優化。本文首先對逆濾波處理估計雷達跟蹤誤差問題進行建模,推導仿真了雜波背景下雷達濾波的逆濾波處理算法。然后,基于逆濾波處理提出了適用于破壞雷達跟蹤狀態的干擾類型的干擾效果在線評估方法。最后以針對導引頭雷達的自衛式RGPO為例,仿真驗證了該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本文所提干擾效果在線評估方法是通過逆信號處理實現雷達系統更多內部狀態感知和推理的一次有益探索,但在對抗條件方面作了相應假設并在干擾策略調整方面做了簡化,后期將在更寬松的假設下對更多雷達內部環節的逆處理方法開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