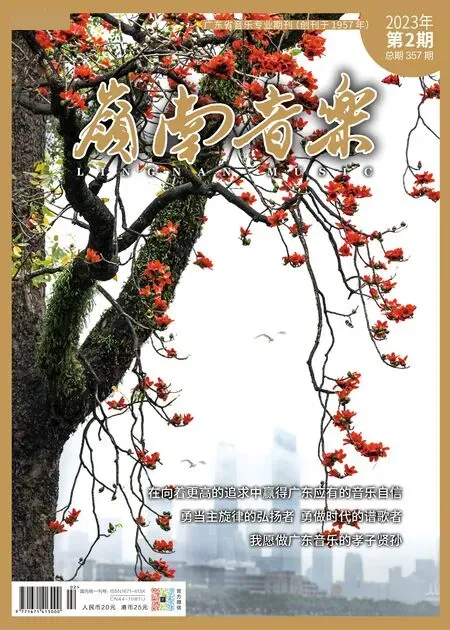儒家樂教釋義
文|張小雨
中華文明,素有禮樂文明之內涵,禮樂并舉、優于政刑是其一貫的文化特色與制度特點。中華文明相較西方文明的一大區別,便是在較早時期就意識到音樂所具備的道德屬性與教化價值,并自覺將其作為培養國家意識形態的方式,最終促使中國呈現出“禮樂之邦”的文明樣態。音樂很早便成為古代中國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突出表現在儒家禮樂教化的觀念中。儒家繼承發揚了周代禮樂制度的基本精神,并通過人文化與內在化轉述,構建出其獨特的教化主張。而以往對儒家禮樂教化的研究,往往重禮輕樂,本文則要直面樂教之內涵與現代價值。
1.儒家樂教的內涵
儒家樂教,簡單來說,便是“以樂為教”。它是將音樂和舞蹈作為一種教育方式,通過開展一系列音樂活動,從而在無形中影響參與者的情感志向、價值觀念、行為習慣,并使其逐漸符合于教育開展者的期望,是一種面向人內心情感道德塑造,充分利用藝術資源的綜合性教育模式。故與今日的素質教育、藝術教育相近。但是,儒家樂教觀念中“樂”這一概念,與今日世人常說的藝術教育中的“音樂”,其實并非完全同義,而是有著較為獨特的內涵。與此類似,儒家樂教觀念中的“教”,也不能完全等同于今日世人常說的“教育”。《禮記》《周禮》《禮儀》被儒家統稱為“三禮”,它們共同構成儒家四書五經中的“禮經”,主要記載儒家的禮樂思想。《禮記》又分為“大戴禮”與“小戴禮”。“小戴禮”的《樂記》篇,是目前已知的文獻中,論述儒家音樂哲學、樂教思想最為系統、成熟的著作,它在開篇便說:“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①儒家嚴格區分了聲、音、樂三者。所謂聲,是人之內心在外物影響下產生波動,并以發聲方式將其展現出來,從而實現內外互通的一種音響形式。它處于較為低級的階段,人與動物皆能發出并接收,類似于鳴、叫、吼等。音則是人在聲的基礎上,運用一系列樂器與演奏方法,將聲復雜化、節奏化、旋律化所形成的,是唯獨人才能創作、演奏與鑒賞的,類似于今日的歌曲。樂則是儒家理想中的有德君子,將音配合上舞蹈要素,并灌注深刻道德內涵創作出的一種綜合性藝術形式。其在藝術結構、思想境界等方面都大大超越音與聲。儒家語境中的樂涵蓋了音樂、舞蹈、故事創作、角色塑造、舞臺布景、服飾設計等,可以理解為上古時期幾乎所有藝術門類的綜合載體。這意味著,聲、音、樂三者處于一種既相互連接,但又有所區分的維度。從根源來看,它們皆來自人內心對外物影響的反映,人通過復雜程度不同的聲音形式來表達內心之動,從而產生了聲、音、樂三者。但是,三者之間不僅存在組織結構上的繁簡之別,更具備思想價值上的高低之差。接著,《樂記》說:“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②儒家認為,音(當然也就包括聲)僅是人內心對外物所施加影響的機械式反映,雖然音已經蘊含一定的曲調旋律、審美因素,但并未體現出人作為一種具備道德倫理的生物對情感進行節制的能力。因此,只有蘊含了道德情感要素、能體現情感能發而中節,并具備教育他人屬性的樂,才能“通倫理”——體現人類社會的倫理準則。這才是一種區別于動物鳴叫的、只屬于人類的藝術形式。所以,只有君子才能制作、鑒賞樂,也只有樂才具備成為教育客體進而影響民眾主體的條件。那么,儒家樂教思想當中“樂”的這一概念,就并非俗稱的音樂,而主要是指自上古流傳下的諸位圣賢、君主所作之雅樂,其主要內容是歌頌圣王之德行。儒家樂教,便是利用這批樂舞中所蘊含的道德倫理觀念來教化民眾,從而實現其道德提升的教育行為。所以,樂教本質上是一種道德倫理教育,它最為關注的是音樂的藝術形式與思想內涵對人內心精神、情感的正面塑造作用。在音樂作為一種藝術必須具備美的形式外,更加強調它必須符合善的原則,要以樂舞的形式美、精神善在無形中影響聆聽者的內在世界,使之能祛惡揚善。最后,《樂記》說:“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③與當下“為藝術而藝術”的觀念極為不同,儒家將組成音樂的要素——樂器規模、曲調旋律、演奏技藝、表演水準、指揮能力等,視為“樂之末節”——細枝末節,轉而最為關注樂曲唱詞中蘊含的中心思想是否符合道德倫理原則、是否能為他人進德修業提供理論啟示,以及旋律曲調是否能“中正平和”,即幫助聽樂之人維持、鞏固一種平和的情感狀態。因為儒家政治體系,根基于其血緣宗法等級制度,由國家根據不同人之間的血緣親疏、地位高低、職業性質、年齡長幼等客觀差異建立起一套制度安排,從而起到區別親疏貴賤、調和不同階層、使人各司其職而互不侵犯的政治目的。禮教,便是將這一制度體系以教化形式推行,使民眾之言行得以規范,從而維護國家的基本秩序。但如果僅有禮教,則可能走向人人疏遠、不相愛護的尷尬局面。所以,需要樂教從人人共通的情感基礎出發,通過組織音樂活動,實現不同階層之間人們的情感共鳴、團結友善。這種教育形式能更加便利地實現教育目的,因為它將原本抽象而干癟的說教以生動活潑的形式呈現,令百姓更易于接納。樂教與禮教在地位與作用上恰好能形成互補,禮樂教化自古便是維護社會和諧的政治形式。
在此禮樂一體教化制度中的樂教,與當下藝術教育中的音樂教育,便存在本質區別。因為現代音樂教育的重點,是培養學生在聲樂、器樂等方面的表演能力與鑒賞、創作能力。儒家則將樂之德性放在首位,而視器樂演奏、聲樂歌唱為“樂之末節”,它不過分注重技藝培養,僅將其視為相關從業者的職業技能教育和童子初學的通識性教育。單純的音樂教育,只是將音樂視為一種藝術門類,意在培養主體對這一藝術客體的鑒賞、演奏、創作能力,而樂教作為一種“教化方式”,實則是將音樂作為培養主體社會性道德倫理的工具。它必然要賦予音樂在藝術之外的道德內涵。所以,儒家樂教中“教”這一概念,不僅僅代表教育,更是教化。《說文解字》釋教字云:“教,上所施下所效也。”④又釋化字謂:“化,教行也。”⑤段玉裁注曰:“教行于上,則化成于下。”⑥從文字學角度來看,教化是已臻于道德至善境界的圣王對普通民眾施加的一種正面道德引導。圣王將其道德意識以諸多形式彰顯出來,目的在于使百姓受到感化,也能實現道德進取,最終達成“移風易俗”的社會治理目的。這便是《周易·賁卦彖傳》中的“文化”,以禮樂這一可知、可見、可感的“文”(外在),來感化民眾那不可見的“質”(內在)。張汝倫先生曾說:“中國人對文化的理解最簡單地說,就是以人文教養來培養人的高尚人格和精神品性,所謂‘禮樂教化’,也就是明確表現在這種以培養人格造就文明社會為目的的文化中,禮樂起著核心的與基本的作用。”⑦可見,樂教不可能僅是一種藝術培訓或職業教育,而是以國家為主體、以樂為載體、以民眾為客體、以人格塑造與文明社會為目的所進行的一種綜合性教育。儒家所謂的“德”“君子”等概念與其道德倫理思想、哲學理論、政治建構密不可分,樂教便是根基于儒家的整個哲學體系。儒家樂教思想,本質上是儒家對如何利用樂舞來開展教化、提高民眾道德倫理境界的理論思考。它是儒家的宇宙論、人性論、教化論和政治哲學思想,在認識、分析、利用樂舞時的具體結果。現代音樂教育,重在培養人對音樂藝術自身的理解、運用、鑒賞水平,實際是一種美育。儒家樂教,則重在以音樂為媒介,實現道德倫理思想、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及情感觀念的傳播,實際是一種德育。因此,不能簡單地將儒家樂教理解為古代的一種音樂教育模式或是現代音樂教育產生前的原始形態,從而利用某些藝術研究方法與途徑進行闡述,必須從儒家哲學思想這一整體背景出發,特別是從情感觀、修養觀、功夫論、政治教化論等途徑入手,充分考察其生成與發展,才能真正將其掌握。
2.儒家樂教的消失
儒家樂教繼承自西周“王官六藝之學”,它開端自孔門樂教,但一毀于秦政,二毀于東漢末年的亂世,三毀于魏晉時期,上古雅樂應在南北朝后便逐漸消失了。雖然后世有多次嘗試恢復樂教的舉措,但總體上看,此類活動主要局限于官方音樂層面,即宮廷樂、廟堂樂得以恢復,而教化樂卻一蹶不振。所以,我們大體上可以認為,由官方組織的、面向民間的雅樂教化活動,在東漢末年就基本宣告結束了。可是,主體內在還天然需要一種“寓教于樂”的教育形式,故在宋、元、明、清時期,部分民間藝術逐漸起到了“說書唱戲勸人方”的社會效應。樂教這一有組織性、目的性的藝術教化活動,開始逐漸與民間用以享樂的藝術形式相融合,最終產生出一批高度融合道德啟示與藝術享受的民間藝術作品。也就是說,雖然樂教在東漢后便逐漸消失了,但后世的一些民間藝術其實在無形中扮演了與之類似的社會角色。樂教的精神實際已經融匯到這些藝術作品中,并在我們的文化基因中刻入“寓教于樂”的特征。直至今日,我們仍自覺或不自覺地在小說、戲劇、寓言、電影等藝術形式中尋求道德啟示、生活智慧、知識技能。在今日的中國,一種純粹以娛樂為目的,而無深刻道德內涵的藝術形式及作品,往往被人視為“難登大雅之堂”,只能處于二流位置。這其實是古人對待雅樂與鄭聲態度的翻版而已。這表明,其實在今天,社會客觀存在著復興樂教的內在自覺基礎。
首先,我們需要分析導致樂教消失的原因,總結來看有三點:一,從客觀物質層面來說。以樂為教,必定需要國家組織起一定規模的音樂機構,并擁有與之配套的一批樂器、舞具等。但以古代的物質生產水平來說,這卻極難達成。所以,“王者功成作樂”的另一層意味是,只有當國家統一安定,物質生產水平得以恢復,才具備制作樂器、搭建舞臺、供養伶官樂人的能力,也才具備開展樂教的客觀條件。但是,自東漢末年起,國家歷經“黃巾之亂”“董卓專權”“三國鼎立”“八王之亂”“南北戰亂”等災禍,至隋文帝再次一統天下的這三百余年中,國家僅在西晉實現了二十多年的短暫統一。歷經多年戰亂,物質生產能力其實一直未能完全恢復。魏晉南北朝時期,各個地方政權實力有限,無法完全復現前代雅樂制度,只能目睹其逐漸消亡,這是樂教滅亡的客觀原因。二,從此時期各政權的性質及文化來看。位于北方的政權大多由當時的少數民族建立,他們對華夏傳統的禮樂制度大多并不了解,甚至無法接受,就算經歷北魏孝文帝漢化措施的影響,但從總體上看,他們與華夏族政權在文化習俗等方面仍有不少差別,不存在主動恢復樂教的內部動力,至多是恢復宮廷樂用以自娛罷了。南方政權與此相反,大多由華夏族建立,故梁國曾在沈約主持下嘗試恢復雅樂,但由于國祚時間較短、國家能力有限,其實也未根本恢復樂教。況且,在這一亂世中,子弒父、臣弒君之事可以說屢見不鮮,傳統雅樂所歌頌的圣王道德、賢臣事跡明顯與當局的行為自相矛盾,那還談何教化民眾。三,由樂教自身特點所決定。樂教需要的樂官、樂器,其特點是“易失難得”。制作樂器、培養演奏者需要大量時間與金錢,但每當國家有變,器物往往最容易受到破壞,加上樂官四散逃亡,一時難以召回,前朝樂制頃刻間便會化為烏有。況且在當時,音樂的傳授,無論演奏技藝還是曲譜舞蹈,往往是口傳心授,一旦前代樂官離開,后世再想恢復,便是難上加難。《漢書·藝文志》曾引孔子語“禮失而求諸野”,意為如果官方層面的禮儀制度已不可見,那么可以到民間尋找古禮的蹤跡。因為文化習俗的變化遠遠滯后于政權更迭,所以民間可能還保留有前代的禮節禮儀。“樂”卻很難“求諸野”,因為百姓不可能擁有成規模的樂器,更不一定能透徹地理解雅樂的精神內涵,甚至大多不會演奏樂器。前代樂官流落民間后,往往仍以音樂技藝謀生,為此,他們大多會根據百姓的娛樂需要,丟棄雅樂,演奏鄭聲。總之,樂教自身便天然具備“易失難得”的屬性,它在東漢后便逐漸消亡而難以復現了。
雖然儒家樂教的相關實踐活動在東漢后便逐漸消亡,時至今日已全然不見蹤影,但在經過前文的詳細介紹后,我們不難發現,樂教具備相當程度的合理性,可以說它至今仍然存在價值。主要表現在三方面。一,樂教所選取的雅樂,其唱詞內容是對上古圣王、賢臣道德品行的贊嘆。所以,它們能從思想內容層面,對聆聽者形成一種道德啟示,使人通過歌曲接觸歷史上的偉大人格,并在無形中受其影響。二,雅樂自身的曲調、音階、節奏能與人之情感產生聯系,雅樂“中正平和”的旋律對人情感恢復平和的天性有積極作用。相較于“繁手淫聲”的鄭聲,它們更能幫助人實現先天善性。“美善兼備”“文質彬彬”的雅樂對于提升人的審美素質也有幫助。雅樂所體現的,往往是可以于公眾場合演唱、聆聽的、帶有社會普遍性的情感種類。它們往往是全社會所共同尋求的文化認同、倫理道德在藝術上的體現。三,樂教還能傳達國家主流意識形態,有利于民眾了解古代文化、圣人事跡,并養成對國家的認可與維護。樂教的教化塑造主要表現在道德、情感、審美、政治素養等方面,可成為現代中國開展德育的有效形式。儒家樂教思想及實踐,毫無疑問是傳統文化的優秀部分,是值得我們去深入挖掘、理解和借鑒的寶庫。將儒家樂教理念與當下國家教育工作相結合,毫無疑問將是一次重大創新。儒家樂教對于“新時代”進一步開展道德、審美教育,毫無疑問具有極大的參考性與可操作性。傳統樂教應當屬于傳統文化中重要且優秀的部分,對當前我國繼承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精神力量有重大意義。
3.儒家樂教的復興
儒家樂教亟待我們將其復興,而復興途徑有三。一,樂教是以音樂作為教育方式,將價值判斷和道德精神以音樂形式進行合理表達。國家便可以利用各種藝術資源,以更加活潑的、多樣的形式來展開思想教育。例如,可以針對宣講對象的特點與興趣,具體制定教學的目的、內容,并制作相關的音樂曲目、影視劇作品,以此為形式開展教育便能調動參加者的積極性,滿足主體的情感需要和興趣需要,使其感受到接受此類教育與實現人生價值有實在意義。這要求教育者推陳出新,摒棄一些傳統的灌輸式教育,利用更加生動豐富的資源完善課堂。我們還可以將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公民道德等融入某些藝術形式中。然而,我國從很早開始,就嘗試過以音樂的形式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識形態宣傳,從最早的紅歌,到“文革”的樣板戲,再到20世紀90年代的軍樂,直到現在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傳唱等,都是把意識形態教育與音樂相結合的例子。那么,這些相關實踐和儒家的樂教有什么不同,儒家樂教的特點又在哪,現在再提借鑒儒家樂教是不是多此一舉呢?細致說來,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儒家樂教是與儒家禮教相統一的,樂教在很大程度上是從屬于禮教的一個部分。那些中正平和的雅樂是在進行一系列禮節時候的“背景音樂”,這種音樂在傳播價值、思想的同時,還起到渲染氛圍,把參加禮節儀式的人調整到同一種的心理狀態的作用。一種禮節有一系列與之對應的音樂,這些音樂有著與這個禮節相對應的情感內核。因此,今天再提借鑒儒家樂教,就不得不將其與禮教結合在一起來看。樂教在當代尋求復興的第二種途徑,便是將其與禮教結合,樂教不再簡單地把音樂藝術當作傳教工具,以歌曲、晚會、音樂會的形式來強行灌輸價值觀念,而是將音樂與具體的禮節相結合,在禮節儀式中進行音樂活動,這是與我國已經嘗試過的藝術教育形式最大的不同之處。紅歌、樣板戲等價值觀傳唱,僅將歌曲與思想價值進行結合,把歌曲當作思想價值傳播的工具。儒家樂教在這樣做的同時,還注重把這種能傳達思想價值的音樂和一些禮節進行結合。而這些禮節儀式,往往是為了紀念人民人生中的重大環節,或國家歷史上的重大事件而設立的。在那樣一個特殊的時節進行相應的禮節儀式活動,就更能夠從情感上影響參加者,從而達到影響其內在價值取向與情感模式的教育目的。因此,儒家樂教的今日復興,首先就需要國家制定出一系列針對個人、地區、全國的重大節日,并確定與之相對應的紀念禮節儀式。例如:個人的成人禮、婚禮、葬禮、祭祀禮;地方的解放紀念日、地方名人誕辰日;國家的建國紀念日、國家公祭日;等等。在這些對個人、地區、國家的關鍵時節,通過制定、施行一套完整的禮節流程,從而以一種正式的、恰當的方式陶冶人們的言行舉止。在進行具體禮節時,可以將蘊含主流意識形態內涵的音樂作品作為禮節儀式的背景音樂,通過禮節和音樂兩種形式,在無形中影響參與者的情感、思想,從而傳播國家意識形態及實現人民個人的道德、審美、情感教化,與此同時,將德育工作擴展到學校之外更加廣闊的領域。當然,這僅僅是參考儒家樂教展開德育的諸多可能性中的一種而已。三,儒家樂教的現代復興還離不開其具體承載——雅樂。正如前文所述,我國應當盡早建立起國家層面的雅樂體系,以解決當前民間藝術大多“重娛輕德”的問題。我們可以參考西漢初年叔孫通的實踐,搜尋整理清代遺留的或流傳至日本、朝鮮的前代雅樂痕跡,并結合當前的社會現實,制定出一批在國家重大場合使用的正式音樂,包括節日樂、祭祀樂、慶典樂,以及歌唱祖國、英雄等主題的音樂。同時要系統制定個人在人生重大場合上使用的禮節儀式、慶祝方式及其使用的音樂等,以現實條件為準,逐步恢復中華禮樂傳統,建立自上而下的雅樂與樂教體系。
今日,有人說“藝術無善惡”“大俗即是大雅,大雅即是大俗”,這其實皆是中國傳統雅文化式微的后果。藝術其實與人之內在情感高度相關,音樂某種意義上是主體內在情感的一種外在藝術化表征。因此,音樂的音階樣式、風格曲調,其實是主體內在情感的外部表現。作者、演奏者的情感狀態,會隨著音樂的流傳進而影響他人。可見,音樂不僅存在藝術風格之差別,更存在情感內涵、思想精神之差距。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藝術對人情感之影響有其自身規律,保證所制作之樂為正樂的“秘訣”恰恰不是“為了道德而道德”或“為了教化而教化”。那種不顧及個人情感需要、不尊重藝術自身規律的所謂教化樂,因為其已經脫離了主體的內在需要,所以實際無法取得效果。儒家樂教的情感基礎,恰恰不是要舍棄個人情感去迎合他人,也不是舍棄個體性成全社會性,而應是將個體那些具備普遍性、能引起他人情感共鳴,并成為社會道德的內在因素,以優美的藝術形式表現出來。當其流入到社會領域,便能激起他人內心中已經具備的情感狀態和道德意識,從而產生“共鳴”。這樣一來,藝術便從個人領域走向了他人乃至世界,才能夠對他人產生影響。這是“以樂為教”的前提。因此,本文還需重申,俗文化當其作為風俗、民俗來講,當然值得我們去了解乃至欣賞,但當其劣化為惡俗、庸俗、低俗、媚俗時,則萬萬不值得肯定。一種可稱之為高雅、風雅的音樂,必然同時具備崇高內涵與優美形式,它與低俗之樂,必然是水火不相容的。今日我們再提倡恢復樂教、重塑中華風雅文明時,便意味著要反思雅俗關系,必須徹底撇清低俗文化給樂舞的不良影響,重塑具備中正性情與優美形式的中國雅樂典范。樂教必須與禮教合一,凸顯德性內涵、教化意義、社會治理作用。就算儒家樂教的實踐活動、思想著作早已消失,但只要每個人仍有提升道德涵養的需要、國家仍有以德治國的愿景,禮樂教化就永遠具備值得參考的價值。復興雅樂、重構儒家禮樂教化、維護我國禮樂之邦的性格,便不會是一句空話。
引文出處及注釋:
①[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1頁.
②[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9頁.
③[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3頁.
④[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27頁.
⑤[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84頁.
⑥[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84頁.
⑦張汝倫:《說“樂”》,載《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第21頁.
——由刖者三逃季羔論儒家的仁與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