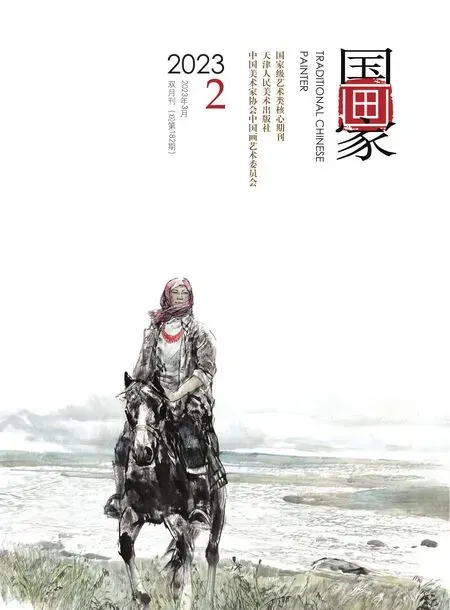水墨繪畫語言與當代教育精神的相互滲透
天津科技大學藝術學院副教授/ 韓暉
中國水墨繪畫,也稱水墨丹青,是民族文化的獨立形式和內容之一。水墨繪畫的精神追求和思想表達不斷被各個領域作為重大課題進行研究探討,因而它不單單是一種形式創作上獨具特殊語言方式的純粹藝術形態,在時代文化更迭交替的背景下,其創作內容、思想承載和精神導向也在隨之發生悄然變化。那么,如何找到一條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水墨繪畫的合適途徑,如何將傳統的藝術精髓和豐富的精神資源為藝術創作和當代教育所用,以及如何構建一個追求雅正文化的古老民族的精神生活結構,這些都將在兩個維度上進行滲透和嬗變,即精神性訴求和藝術性追求。也就是說,我們當代教育擔負著偉大的時代使命,不僅要具備吐故納新、自我完善、與時俱進的活力與能力,還要在提高學子的精神素質和藝術能力的同時,搭建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之間的橋梁,深化“文化力”即綜合國力。
一、水墨繪畫語言技法和表現形式
水墨繪畫之所以形成獨特的藝術語言,促成其發生與發展的根柢是傳統文化中的古典哲學、宗教思想的深層交融影響,它的語言起點從寬泛的一面來說,是物態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和思想文化的深層隱喻;從狹義的一面而言,則是儒、釋、道三家學說和“陰陽五行”形而上認知形態的具象表現。因此也可以理解為,水墨繪畫語言也正是通過深入觀察和身體力行中國文化所強調的“意由心生”的相關體驗,在意境和精神內涵的創造中加強對文化認知的深度性和把握的自覺性,因而又是“天人合一”自然文化的藝術呈現和思想再現。
1.水墨繪畫的語言技法
水墨繪畫的美學理論是從主導傳統文化的三家學說與陰陽五行的核心思想中演化而來。細分之,“成教化、助人倫”[1]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也是中國畫(即水墨繪畫)的重要理論,它否定了繪畫怡情悅性的單一目的性,強調的是繪畫所承擔的文化意義和道德教育意義,體現出繪畫藝術的社會功能性。道家代表人物老子認為:“‘有’為看得見的具體事物,‘無’即看不見的‘道’,為萬物的本源。”[2]也就是“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3]中“無”的哲學思想成為水墨繪畫中有關“虛”的審美,主要作用于提升藝術的境界和相關表現手段,成就了“留白”的美學理念。而釋家,即佛教中的因緣和合、業與輪回、無常與無我、解脫與涅槃這四大教義,其影響主要體現在作品的“藝術性”上,為水墨繪畫藝術的目標性與指導性明確方向。陰陽五行,其中陰陽觀對水墨繪畫藝術影響巨大,體現在構圖及畫面的主客之分,而且不注重體積,不講明暗,但卻生成陰陽對比的平面稚拙美感。以上綜合形成樸素、單純、天真、活潑的水墨繪畫藝術語言。
水墨繪畫境界中闡述出的“意象”“心性”,與中國文化認同的人格境界中強調的“自省”是相統一的。“自省”屬于“心性”的文化范疇,水墨繪畫的美學理論同樣強調自我完善,注重來源于生活中的體驗與自省,以此進入一定境界,繼而有感而發。這種順應天理、順其自然的文化體現需要渾厚的素養來支撐,并一一反映在水墨繪畫中。因此,水墨繪畫語言的本質就是反映人追尋和遵循一個信仰的過程,通過筆墨這一載體來弘揚傳統文化精神與時代人文境界,[4]所以它們又是“水映一月”的關系。
2.水墨繪畫的表現形式
南朝齊謝赫對中國畫進行了高度概括,譯成現代文意思為:“中國畫并不只是宣紙上的點染勾勒,‘氣韻’‘境界’實際上是一個系統的思想集成最終的表現。意、識、靈齊備,詩、書、畫一體,詩為畫之意,書為畫之骨。技法之熟,可呈胸臆;畫面之外,可留思想。這也是判斷中國傳統書畫作品藝術價值高下的實質所在。”[5]同時他還提出:“圖繪者,莫不明勸誡、著升沉,千載寂寥,披圖可鑒。雖畫有六法,罕能盡賅。而自古及今,各善一節。六法者何?一、氣韻生動是也;二、骨法用筆是也;三、應物象形是也;四、隨類賦彩是也;五、經營位置是也;六、傳移模寫是也。”[6]
以謝赫的品畫理論為依據,再縱觀古人的經典作品,包括近現代藝術大師作品,不難發現他們的人格和藝術是以心性與立象、立格的方式建起敦厚的藝術基礎與文化精神,其水墨繪畫表現形式總體而論都在圍繞一個主題——“天人合一”,也即道法自然。這個繪畫形式中的本體論,使后世繪畫多以“田園歸隱”為主題,更是將創作者的思維推至一個宏大的宇宙本體論的思想高度,可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萬物有成理而不說”。或者說水墨繪畫的筆法強調自然的本色,構圖也是首先通過強調意象,進而表達真、善、美的文化體驗,再將生活中的東西融入畫面中,借助藝術創作形式引申出各種不同的關于文化深層次的體驗,反映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然的生命體驗,最終以自然為上、自我為下來慰藉人作為個體存在而無法回避的心靈蒼茫與宿命孤獨。
二、當代教育精神的內在核心
在中國經濟結構和文化結構不停發生變化的當下,人們傳統的諸多經驗也顯示出與以往大不相同。當代教育在這樣一種新型社會經濟關系和文化氛圍下,必然更加關注社會與文化、現在與未來的教育切入點。也就是說,不論傳統藝術教育還是當代教育,它們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一直在面對固化的歷史范圍,因而亟須做出著眼于未來的教育精神理念的新詮釋——這種詮釋不是由教育家、社會有識人士所倡導,而是整個社會自覺地建立起與當代教育精神同步的相關思想認知,進而使教育復歸發展人之綜合潛力、挖掘人之無限豐富性的道路上。
1.當代教育的基本目的
“教育即生長,生長就是目的,在生長之外別無目的。”這句話先由盧梭提出,后由杜威做進一步闡發。西塞羅也對教育的基本目的做出了精準概括:“教育的目的是讓學生擺脫現實的奴役,而非適應現實。”這兩句話言簡意賅地道出教育之本義。學者尹艷秋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擴展認為,當代教育精神的建構應“以人性的完整性為依據,以體現人性完整性的、多元開放的、豐富流動的生活世界為根基,將教育的社會及個體的適應與超越統一在現實的教育活動中,并指向教育的超越”[7]。
以上觀點的起點和終點都將教育基本目的指向以“人”為主體的全面發展教育,以促進人的自由生長和提升人的精神世界為風向標。也如周國平所說:“人生問題和教育問題是相通的,做人和教人在根本上是一致,人生中最值得追求的東西,也是教育上最應該讓學生學到的東西。”[8]換言之,“直指事物的本質,既簡明如神諭,又樸素如常識”[9]的靈魂教育,才是當代教育精神的真正內涵。
2.當代教育精神的內在核心
王坤慶在《精神與教育:一種教育哲學視角的當代教育反思與建構》一書中認為,精神教育的根本尺度體現在人的主體性和人的自由性上。他積極倡導“在當前的教育改革中應重視人的精神世界的發展”[10],并對精神教育的內涵、性質及實施提出與之并行的觀念、目的、途徑三重定位。從某種意義而言,雖然當代教育精神至今未有語言的清晰分析界定,但仍然可以通過“本真、最高善、終極價值”等學術用語概括之。也正是通過對這三個維度的建構和追求,現實教育活動才得以不斷向新目標和新高度攀進。
教育精神本身具有極其豐富的內容,不同維度、不同層次、不同立場可以產生紛繁復雜的各種見解和千差萬別的內容。根據上一小節所論述的教育目的,可以延伸出當代教育精神內在核心,也就是基于“教育的目的是促進人的自由生長和提升人的精神世界”這一命題,從而對當代精神的廣義內涵展開具體分析得出:教育在探索中走向成熟,也必然依賴于與之相匹配的有關“人性”的教育精神實踐,這種可稱之為生命化的教育以培育人的內在精神為最終目的,同時也意味著教育精神真正內在核心所在。
三、水墨繪畫語言與當代教育精神的相互關系
基于日常生活的精神發現,展現“知行合一”的個體內心行進,兼具“天、地、人”自然哲學和審美超越,成就了水墨繪畫的經典語言。換言之,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自然文化,其哲學深度和文化積淀乃水墨繪畫藝術的生成平臺,傳統文化所強調的“知”和“行”與水墨繪畫所提倡的“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規律是血脈相通的,其作用的主體是我們認識事物、超越事物表象的認知方法,并在這一基礎上延伸出“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作為上層建筑的中國水墨繪畫藝術隨著時代與歷史的特點在前行,正所謂“筆墨當隨時代”,它所表達的藝術精神和藝術文脈中呈現的人文教化、精神內涵及哲學感染力都是當代教育極為寶貴的資源和財富。
1.水墨繪畫語言與當代教育精神的相互滲透
在對傳統文化做系統梳理時,不難發現民間的、民俗的藝術門類和藝術行當在不可逆轉的態勢下逐漸衰落,甚至消亡,但水墨繪畫卻依然產生出獨特的民族生命力和世界性感染力,其大致原因歸結為兩方面:一方面,水墨繪畫所融合的東方哲學仍然在發揮著作用和影響,思想根基不僅深厚扎實,評判標準也自成體系;另一方面,由于中華民族是善于思考的民族,也是程式化意識較強的民族,即使身處于高速發展的信息時代,仍然在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面前思考生命回歸的意識源頭,去尋找傳統文化哲學中關于本我的答案。
而在整個當代教育體系中,對人文素養的要求一直是被相當重視的,豐富的文化底蘊是當代優秀設計師和青年學子不可或缺的基本素質。青年學生作為我們民族的時代寵兒和創造者,承擔著發展科技和物質文化的重任,還要在精神追求以及藝術美育的范疇尋找自我的審美坐標。研究水墨繪畫語言,從中所體現的態度和觀念問題不是單純的、單一的,而是一個傳統的、龐大的文化和思想問題,它涉及藝術學、美學、心理學、人文、宗教、歷史等方面的研究。而我們的教育離不開對傳統文化“正本清源”精神的依賴,[11]離不開水墨繪畫語言中所呈現的精神聯系認知,這種文化的相互滲透使得藝術形式在教育的引導下不斷地發展與深化,而藝術傳承也是教育功能實現最大化、最高化的深度表現形式。
2.水墨繪畫語言與當代教育精神的相互作用
當下已經進入媒體和后媒體并行時代,各項藝術創作和各種藝術門類都在與世界對話,其專業技術、創作技巧和思想主題也在與時代接軌,基于民族文化自覺性的中國水墨繪畫的“繼承與創新”課題在此境況下備受重視。水墨繪畫的精神追求與情感表達中講意蘊、重情懷、托物言志的人文特色和審美范疇也一直是中國當代教育精神遵循的體脈。文化是需要繼承的,當代教育正可以借用水墨繪畫傳統資源和符號,幫助完成現實生活中諸如生活、人品、學養等方面的教育。
水墨繪畫在“變化中求統一,創意中融情趣”的語言方式,其主題、意識、思想、情感等東方式人文屬性完全契合當代教育精神內容,因而我們完全可以將中國水墨繪畫語言中的有意因素作用于當代教育教學中,發展并建立古為今用之善用關系;與此同時,教育的深層挖掘可以通過藝術媒介的形式闡述,中國水墨繪畫精神在這樣的基礎平面會表現出強烈的優勢。同樣,基于傳統文化的積淀,教育所生發的現象對于水墨繪畫也會產生深刻影響,對水墨繪畫精神的發展產生新的沖擊,帶來新的詮釋。這樣一個立體化發展的文化架構,藝術精神和教育責任同時兼備的傳承意識,其相互作用形成一個良性循環系統,必然成為解決當下諸多教育中現實問題的某一途徑。
結論
從人性視角探討當代教育精神的本質內涵和內在特質及生成路徑,為真正實現教育成“人”提供教育應有的精神特質的哲學層面思考,這是一個意義深刻的劃時代課題。當代教育精神在繼承水墨丹青藝術的同時,既弘揚了博大的傳統人文精神,也提升了學子的內在素質,提高了他們的審美情操,而水墨繪畫語言則為當代教育的教育功能和現實意義提供了文化主旨和精神引領。
注釋
[1][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1年。
[2][3]“全民德育經典讀本”編委會,《道德經精讀本》,中華書局,2012年。
[4]張國生,《當代水墨藝術的現代性》,《藝術評鑒》,2022年第14期。
[5][6][南朝齊]謝赫,《人美文庫:古畫品錄 續畫品錄(標點注譯)》,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年。
[7]尹艷秋,《必要的烏托邦:教育理想的歷史考察與建構》,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
[8][9]周國平,《周國平論教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
[10]王坤慶,《精神與教育:一種教育哲學視角的當代教育反思與建構》,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
[11]霍楷、魏歆彤,《傳統文化融入美育教育改革的策略研究》,《文化創新比較研究》,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