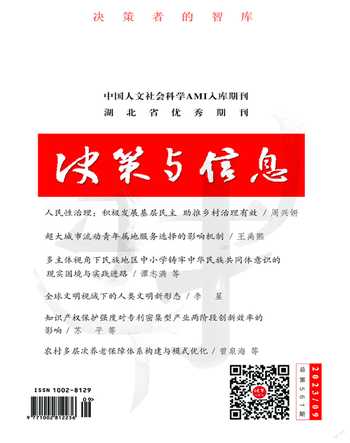全球文明視域下的人類文明新形態
李星
[摘? ? 要] 文明概念是歷史性生成的,是一個綜合和動態的概念。最初的文明是一個中性概念,凸顯自我與他者的邊界。在進一步發展和演進過程中,文明發生了異化,成為具有排他性的意識形態,用以確定文明等級和推行殖民主義。全球化時代,自我與他者的界限消失,傳統文明概念面臨著消解的危險,文明面臨著何去何從的重大抉擇。全球文明是區別于普世文明,與全球化時代相匹配的文明類型,文明對話、網絡科技、全球意識等是其生成的支撐條件。人類文明新形態本質上屬于全球文明,它是包含地方文明特殊性基礎上的普遍性文明,強調平等、多元、對話、包容和共享。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提出賦予文明概念以新生,以實現人類和美幸福的價值旨歸。貴和尚中的中華文明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文化厚植,人類文明新形態推進中華文明現代化,拓寬人類文明前進道路。
[關鍵詞] 全球文明;人類文明新形態;人類命運共同體;文明沖突;文明互鑒;貴和尚中;文明對話
[中圖分類號] D6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8129(2023)09-0037-09
文明是獨屬于人類的。文明這一古老的概念在人類歷史中生發和流變。西方資本文明塑造了人類全面和深度異化的存在方式,導致人類的總體性危機頻發,進而將文明這一概念引向了晦暗。人類與人類文明將何去何從?“在各國前途命運緊密相連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鑒,在推動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繁榮世界文明百花園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愿提出全球文明倡議”[1]。全球文明倡議秉持共建共享共贏原則,倡導全世界深入推進文明交流對話,在多種文明包容互鑒中促進全人類文明進步,彰顯全人類關懷。人類文明新形態尊重各民族國家和地區豐富多樣并且源遠流長的文明傳承,在包容各民族國家和地區文明多樣性的基礎上表征人類文明的普遍性,其本質為一種全球文明。人類文明新形態超越了文明沖突論,昭示著文明概念的新生。人類文明新形態關注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以全人類幸福為價值旨歸,將為人類開創和美幸福的生存方式。
現代文明概念不同于傳統文明概念。文明的身影常見于中國古籍,如《易傳》中的“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尚書》中的“浚哲文明,溫恭允塞”。在《說文解字》中,“文”與“明”分別側重于外在表現與內在修為。其中,“文”的本義是指表面各色交錯的紋理,又延伸為文采、文雅、禮儀等,在本義基礎上進一步引申為美、善、德行之義;“明”由自然界的光明而引申為內在澄明。然而,這些用法的指向,并非現代意義上文明概念的內涵,現代意義上的文明一詞自誕生起,就獲得了屬于自身的獨特生命形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便具有不同的內涵,這些相異的內涵其實屬于人類的不同文明觀之間的對話(dialogue of ideas)。要將人類文明演進置于全球化背景下,從全球性與地方性的關系來理解現代文明概念的演變和全球文明的建構1,進而,證明人類文明新形態本質上屬于一種全球文明。
一、“文明”概念之生發
現代意義上的文明(Civilization,源于拉丁文“Civis”)一詞出現于18世紀下半葉的歐洲,從19世紀至今一直在許多語言中廣泛使用。米拉波(Honore-Gabriel Mirabeau)通過《人類之友》這一著作為人類創造了文明這一獨特而重要的概念2。在現代語境中,文明是一個歷史現象,而非一種抽象形態,文明概念是歷史性生成的,是一個綜合性、動態的以及可比較的概念。文明是這樣一種歷史現象——人類反思自己以及自身成就的歷史。歷史學家布魯斯·馬茲利什(Bruce Mazlish)揭示,文明是一種世界視野與歷史延伸交匯而形成的結合點,又或者說文明是現存物質條件和主體意義之間的對應關系。文明形成了關于生命意義和目的的豐富多樣的觀點,促使人類自由地發揮其聰明才智。文明具有一定的物質特征,并且該文明語境中的人以特定的思想方式來行動和思考。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明和文化。文明又是一個可以相互比較的概念,一個人的文明也可能是另一個人的野蠻。
最初的文明屬于一個中性概念,發揮著區分的功能,以凸顯自我與他者的邊界。現代文明的產生源于人們對現代秩序的需要,表征一種秩序井然的制度。最初的文明內涵包括一種特定的社會交往形式,推崇不斷增長的人口、自由和公正。現代意義上的文明是一個社會科學概念,并不具有本質的或天然的特性,而是通過社會建構的方式獲得的——一方面它努力理解新的社會關系,另一方面又在建構新的社會關系。文明概念具有綜合性和過程性,它并非靜止不變,而是動態生成的,有其生老病死的過程,即個人、國家和所有人類走向教化的過程,然后也指代這一過程帶來的結果。那種將文明看作固定的和封閉的有機體的觀點是不準確的。文明概念自生成后,就獲得了自身獨立的生命,后來,文明用于全面地指代一個社會中的諸多方面,是一種科學或者知識,而后,其內涵不斷擴充,用以指代一個文雅、有教養、舉止得當、具有美德的社會群體。文明就成為進步觀念的組成部分,成為人類歷史的第三個階段,即人類經歷了蒙昧、野蠻再到文明。普芬道夫(Samuel Pufendorf)將文明作為人類發展的終點。文明及其許諾的自由被作為解決社會種種問題的解決之道[2] 10-11。
文明概念與現代性概念及其內涵緊密關聯。現代性的主要面貌是由文明反映出來的,文明成為了現代性的承載者。作為名詞的文明概念興起于啟蒙運動時期,是啟蒙時代的新詞,是由啟蒙運動中主要的改革精神孕育而生的,是啟蒙運動改革精神最直接的產物。文明概念是隨著社會科學的產生而誕生的,其包含豐富的內容:舒適程度的提升、教育進步、行為舉止更加禮貌、藝術與科學的發展、工商業的增長、物質商品和奢侈品的獲得等。文明概念充當了一個將多種觀念統一起來的概念。文明就是這一現代反思心理的一部分,文明對于人類如何想象自身、如何處理自身與他者關系產生了重大影響。可以說,人類近代歷史的中心議題就是如何處理好自身文明與他者文明的關系。
文明與文化緊密相關又具有內在差異。文明偏向于開放性,可以具有普遍性和全球性;而文化在于獨特性,扎根于某一民族血液、土地及其獨特歷史中,日益地方化,越來越看重特殊因素,不斷回歸保守。相比較而言,文明比文化走得更遠。文明與文化具有內在關聯,文明是文化的結晶,不同時期的文化凝結形成不同的文明形態,同一時期因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的差異,凝結和呈現出的文明形態也有所不同。狹義的文明形態是指人類創造的精神財富的總和,包括人類文化的價值體系,是特定時期精神和符號的總體存在。廣義的文明形態則是一個總體性概念,指在特定階段內社會發展的包括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包括政治上層建筑和觀念上層建筑)的統一體[3]。
二、“文明”概念之異化
事實上,文明概念面臨陷入墮落的危險。在抽象名詞文明還未出現的2000多年時間里,希臘人、羅馬人和中世紀歐洲人用與文雅、教養有關的動詞和形容詞,將自身與野蠻人相區分。隨著文明的演進,文明概念演變為一種意識形態,而在進一步發展和演進的過程中,文明概念發生了異化,異化后的文明概念內涵與其最初含義相去甚遠,成為一種具有排他性的意識形態,用以確定文明等級和推行殖民主義。文明概念成為歐洲人代名詞,并聲稱為世界提供了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衡量尺度,此時的文明概念實質上轉變為一個自戀性概念,用以自我欣賞。歐洲式文明自詡具有普世性,進而將自身的文明模式及各種文明相關術語強加給他者文明,從本質上看,它僅僅是一種統治意識的表達——捍衛自身的文明,又要將其輸出給不同文明的他者,以此強化自身的歐洲文明社會形象。另一方面,意識形態化了的文明概念導致人群中大部分人處于被壓迫和匱乏窘困的處境,并且導致了史無前例的世界大戰和流血犧牲。
文明被用于區分優越的自我與野蠻的他者。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將文明看作范圍最大的文化實體,要通過共同的客觀因素以及主觀認同來界定它,認為文明是涵蓋范圍最大的我們(在其中我們中的所有成員會感受到文化上的自在),區別于外部所有的他們。對于試圖凸顯自身認同的民族而言,二元對立概念的存在成為必要。排斥和詆毀他者作為一種基本的心理機制,借此來達到凸顯自身的目的,文明則是實現這一目的的一種方式或手段——用以區分我們與他們、文明與野蠻的觀念。文明體現一種優越感,人們通過宣稱自己是文明的或者是有教養的,將自身與他者即野蠻人相區別。到18世紀,文明一詞開始指代一種審慎的、機械的、普遍的思維方式,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將這種思維體現出來。亨廷頓提出了著名的“文明沖突論”,認為世界可以根據宗教和種族劃分為九個文明,這些文明將為爭奪全球主導權而展開斗爭[3] 3-4。此時的文明概念具有典型意識形態化傾向,用以維護特定民族國家的利益。
異化后的文明概念用以指代和區分歐洲及其殖民地社會[4]。與文化以及現代性概念相比,文明尤其體現了一種以歐洲為中心的視角,即意味著非歐洲的社會必須成為或效仿歐洲文明樣式。一方面,文明表達的是啟蒙哲學家們的思想和觀念,另一方面,它又體現為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衡量尺度,文明相對主義、比較文明及文明優劣論也隨之產生。在這種文明區分之中,也存在文明互滲(accivilization),文明區分始終與文明互滲相關,即一種文明雖然一方面自詡獨特,自視處于領先性地位,但另一方面又在借鑒“他者”文明的基本要素,這也充分說明,不同文明之間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2] 11。西方文明及其內涵在人類歷史上確實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但同時它也應承擔起相應的責任,要克服自身文明中存在的那些由來已久的深藏的悖論,要消除西方文明中的矛盾,這就需要用新的文明來消解、替代,以形成人類文明的新樣態。
三、全球化時代“文明”概念危機
什么是全球化?全球化壓縮了時間和空間,將各個地區、各個大陸連為一體。在全球化背景下,文明已經解除了固定的邊界,出現了跨邊界文明和不同文明相互碰撞的現象。全球化時代,自我與他者的界限消失,互動性越來越成為文明的構成要素,他者消失,文明的中心難以維系,直至中心消失,平等、公正的價值得到進一步彰顯,更加成為全世界的共識。隨著知識的擴展和世界歷史觀的變化,民族性與人類性之間產生了一條鴻溝。以往的文明是地方與全球的二元關系,強調二者的獨立性,文明概念的不足由此開始顯現,對外封閉,拒絕與其他文明相互借鑒或者產生聯系的封閉式文明概念日益不合時宜。在全球化進程快速推進的時代,文明概念可能會遭到摒棄,成為自行消失的想象之物。西方文明概念并未將全球性納入自身的視野,換言之,它是拒斥全球性的,西方文明概念及其內涵需要被重新審視。西方文明概念面臨著被消解的危險,文明何去何從成為人類的重大抉擇。
全球化時代凸顯西方現代文明概念的缺弱。人類已然進入了馬克思所斷言的普遍交往的世界歷史階段,人類的共同家園——地球村變得越來越小,人類成為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命運共同體,以及密不可分的生存共同體、生活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總體性的人類面臨著普遍性、整體性的危機和挑戰,突破群體本位和個體本位的人類整體成為人們認知與實踐的重要單位,即全人類成為人類歷史的敘事主體。當今人類文明呈現出并聯式的多元并存狀態,人類內部的分裂和對抗威脅著人類整體的生存和發展。西方現代文明遵循將資本作為本位的資本邏輯,以物質文明作為人類文明程度的主要衡量標準,這種文明屬于單向度的文明樣態,無法有效應對人類總體性危機。“普世文明”和“普世價值”具有意識形態性,它們用單一的文明標準衡量人類所有文明,這種文明標準中暗藏著對西方文明優越性的認可。文明屬于人類在歷史中發明的重要概念,完全拋棄文明概念的做法是不切實際的,應該采取的態度是對其內涵進行重新規定,剔除落后于時代的部分,納入積極因素。積極有效的做法是需要將倡導社會平等、重視平民和地方的作用、反思種族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批評文明等級觀等因素考慮進當今文明概念的解釋之中[5]。全球化時代的文明概念應該剔除精英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因素,將全球化和全人類納入視域中。以平等主義和文化多元主義取代文明等級制度和西方至上主義[5]。概言之,西方現代文明概念需要革新和重新規定。
四、全球文明: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本質
全球文明是與全球化時代相匹配的文明類型,彰顯了文明的普遍性特征。人類來自于自然界,但同時人類并非受環境主宰而被動地適應環境,相反,與其他物種相比,人類內部之間存在著更加深厚持久的合作關系,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人類是通過相互協作的方式得以存在與發展的存在物。人類能夠通過協作從事組織化的生產勞動,“人類文明的實質就是人類生產、生活和其他社會活動的組織方式”[6]。全球化時代的人類命運休戚相關,任何個體的存在都與世界歷史直接且緊密地聯系著,野蠻人或他者將不復存在。人類文明新形態踐行和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實現全人類的共同和根本利益[7]。
(一)全球文明代表真正的普遍性
區別于普世文明,全球文明的普遍性之中蘊含地方性和特殊性,包容地方文明的差異性和多樣性,并不必然造成與地方文明或文化的緊張關系。全球文明并非全人類文明的同質化,而是更加尊重和凸顯地方特色[8] 2,地方文明的特殊性更能夠豐富和發展全球文明的普遍性。全球文明承認每種文明和文化的自身價值,使充滿差異的地方文化之間和諧共存,相互促進。
1. 全球化突破了西方文明中心論。世界歷史的形成是人類文明產生的前提。現代性打破了世界各地彼此封閉隔絕的狀態,開啟了世界歷史帷幕,只有當人類歷史發展到世界歷史階段,具有普遍性的人類文明才得以產生。此外,人類共同體的形成是人類文明生長的土壤,人類共同體的成熟使得人類內部交往程度更高。人類文明是人類共同體中的普遍交往與活動的共同遵循,是一系列文明規則、共識或公理,也是人類對共同價值的信仰和追尋。在全球化背景下,文明對話具有了全球性,各種文明之間互動對話,形成一個無中心的世界性的人類社會。全球秩序的變化打破了歐洲(西方)文明中心論。單一中心的文明觀或者等級主義文明觀已經不合時宜。人類應突破西方文明中心論,強調全球視野及其相互聯系性,關注全球層面的事件或進程,賦予文明概念以適應全球化時代的新內涵,以全人類的文化精神走向為落腳點,傳達對全球化和人類命運的關懷。具有普遍意義的文明與全球化相結合,全球文明的構建成為可能,在全球文明的框架中,以往的各種文明轉變為地方性文化,且能夠在這個大的共同文明之下和諧共存。全球文明應以科學技術和理性為基礎,客觀且鮮有價值觀念,可以被全人類普遍接受。基于此,全球文明具有實現可能性。
2. 全球文明是人類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全球文明并非天然事物,該文明的形成需要特定的歷史條件。科技飛速發展,使時空壓縮,進而促使全球同步。隨著以往局部問題(如環境問題)的全球化,全球文明的構建具有必要性和現實意義。人類的普遍聯系和地球共同生活是全球文明產生的歷史背景。進入全球化時代,世界性甚至全球性的因素逐步增多,全球人道主義推動新的全球意識產生,全球人道是全球文明的價值追求和道德之維。一種全球意識和全球認同(人類認識到人類是一個整體并且內部存在廣泛聯系)也在逐步形成,全球意識覺醒是全球文明產生的主觀條件,全球認同是全球文明的價值基礎,全球利益的存在是全球文明產生的客觀基礎,跨國公司的存在和發展可以作為全球文明的經濟基礎。國際非政府組織也促進了全球文明的生成。全球文明的形成和發展提高了全球道德水準,超越諸多地方之間存在的差異性,全球逐漸成長為道德共同體。全球性道德和價值成為人類進步的精神引領,全球聯系成為超越社會聯系的人類新聯系。
3. 全球文明超越了文明沖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在提出全球發展和全球安全倡議之后,習近平總書記又提出全球文明倡議,形成了全球發展、安全、文明的思想體系。全球文明倡導人類不同文明之間展開平等的文明對話。倡導文明對話,一方面對外界保持開放態度,另一方面又不舍棄自身的文明和傳統。全球文明是一個有機體,不是多種文明的機械相加,更不是某種文明的全球推廣。文明對話的潛在用意是將不同文明通過交流互鑒融合在一起,同時保留自身的身份認同。文明對話不能凌駕于各種文明之上,而是要在認可各個文明的前提下,尊重每種文明,以平等的文明觀取代等級性的文明觀,民族、國家和地區并不會因經濟實力的強弱而對應到文明的優劣上。文明對話會誕生新型文明,文明對話是全球文明產生的必要途徑,全球文明既可以突破文明沖突,又包含和超越文明對話。全球文明是包含多種文明形態的共同文明,而不是多種不同文明的簡單相加。
4. 全球文明進一步推進新全球化。文明觀念和全球化都具有傳播性,全球化是一個過程或一系列過程,它不斷突破現有社會和國家的邊界,其內涵不斷拓展。通信科技的迅猛發展不斷開拓著人類生活的虛擬空間,使人類全球化聯系成為可能,跨國經濟活動成為現實,進而反過來促使人們創造共同的文化成果。網絡化的全球時代終結了文明自我與野蠻他者之區分的觀念,開啟了新型全球化。以科技發展為基礎和手段,各種文明和文化能夠展開全球對話,全球文明與地方文化能夠實現共存共處。文明的沖突只是人類文明發展歷程中的一個階段。當今世界更需要各文明間的互動以應對全球性難題和挑戰。全球文明中將沒有霸權的存在,更加關注和尊重地方和個體的自由,竭力將全人類共同的利益納入考量。即“弘揚立己達人精神,增強現代化成果的普惠性”[1]。人類秉持團結合作、共同發展的正確理念和原則,推動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進而促進人類文明進步,全球文明的歷史性生成彰顯了人類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力。然而,全球文明也有被濫用和扭曲的可能性,被扭曲和濫用的全球文明變異為全球同一的文明模板,全球利益有被個別國家的特殊利益所操縱和利用,成為其掩蓋自己進一步攫取私利的幌子的風險,因此要警惕全球文明的異化。
(二)人類文明新形態是一種全球文明
世界已然成為一個跨文化聯系的整體,“人類是一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命運共同體”[8]。人類正生活在一個全球文明時代,其中的諸多文化同時存在。當今時代的世界和人類文明處在新的十字路口,這需要全人類做出新的抉擇。全球文明以全球化為背景和依托,倡導多種文明的對話,是對“文明沖突論”的超越。中華文明在同一片土地上延續了5000多年,至今延綿不絕,成為人類文明的光輝典范。在全球化時代,中國及其文明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可以說,全球化時代的代表就是中國和中華文明的發展。人類文明新形態超越了西方文明,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世界意義。在人類文明何去何從的重大抉擇面前,中國的作用極為關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生發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為人類現代化路徑提供了重要借鑒,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人類文明,開創了人類文明新形態,人類文明新形態本質上是一種全球文明,具有最廣泛的人類普遍性,關注并致力于變革人的普遍生存發展狀態。人類文明新形態是對人類當今現實的最緊密契合,同時是對人類未來走向的最大開拓。
1. 中國式現代化開創了人類文明新形態。“黨領導人民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9]。人類文明新形態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創,同時由中國式現代化所推動。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內涵在于:它是一種崇尚整體、全面,以及和諧的人類文明發展模式,是新型的文明觀與人類觀。人類文明新形態是一條以和平方式尋求發展的人類文明道路,它區別并超越了人類曾經經歷過以及當下存在的文明樣態。人類文明新形態是對當今世界人類所共同面臨的現實難題的有效回應,是人類積極發揮主體能動性的生動彰顯,其宗旨在于為人類及其文明發展指明前進方向。
2. 人類文明新形態崇尚多元文明和諧共生。這一新型人類文明類型是對人類文明發展潮流的緊密契合,能夠更好地滿足當今世界作為整體的人類的需求。人類文明新形態是對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的揚棄,同時也是對具有沖突性的文明觀的超越。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所開創的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比較優勢在于:該文明形態兼具現實性與前瞻性,是和平、和諧、共享、可持續的人類文明發展新道路,能夠最大程度地代表人類整體的利益,符合更多人的價值追求。人類文明新形態堅持人是人的最高本質,以人類為中心和本位,揚棄異化,使人重新擁有自己的本質,是追求人類自主的文明新樣態。人類文明新形態理念的提出和實踐建立在順應人類歷史發展方向的基礎之上[10] 68,是人類充分發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尤其是創造性,是推動人類文明飛躍的生動體現,為人類文明發展開辟了新的前景,在某種程度上開啟了全新的人類歷史。
3. 人類文明新形態與全球文明本質一致。人類文明新形態及全球文明都“重視文明傳承和創新,充分挖掘各國歷史文化的時代價值,推動各國優秀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8]。它們是建立在地方特殊性基礎上的普遍性,強調平等、多元、對話和包容。它們都代表人類文明真實的普遍性。人類文明新形態融綜合性、立體性和多維性于一體。“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堅持文明平等、互鑒、對話、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越”[8]。區別于西方普世文明的單一文明模式,人類文明新形態堅持開放性,超越單一性和平面性;倡導人類與萬物共生和諧而非人類中心主義,具有多重意蘊(生存性意義、發展性意義、文化性意義以及和平性意義)[11],人類文明新形態擺脫了西方文明的話語權力體系,是對新的人類文明狀態的呈現與展開。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主張反映新時代人類文明的新特征,開創了人類和平發展的新道路,契合當今時代人類的需求,彰顯人類文明生態的健康狀態。
4. 人類文明新形態促進文明概念新生。隨著人類歷史的不斷發展,人類文明新形態擴展、豐富與更新了文明的內涵,不同文明之間平等、包容、交流、互鑒成為人類新文明的價值追求。“人類社會創造的各種文明,都閃爍著璀璨光芒,為各國現代化積蓄了厚重底蘊、賦予了鮮明特質,并跨越時空、超越國界,共同為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作出了重要貢獻。中國式現代化作為人類文明新形態,與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鑒,必將極大豐富世界文明百花園” [8]。在人類文明新形態之下,具有地方特色的各種文化以平等的地位,互不干涉,共榮共生,實現人類文明的普遍性與地方文化特殊性的有機統一。人類文明新形態是現實向度與未來向度的有機結合,是共享式的可持續發展的人類文明發展之路,是追求全人類共同分享世界發展成果的正義的人類文明之路。人類文明新形態既是中國的,更是全人類的,兼具中國意義和全人類意義,推動全人類不斷前進。
五、人類的和美幸福:人類文明新形態之價值旨歸
文明交流促進文明繁榮,文明對抗導致文明凋敝。全球化時代人類是密不可分的命運共同體,任何一個民族和國家都無法獨善其身。人類文明新形態是對“人類向何處去”的時代之問的智慧回答,是人類整體在文明層面的最新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理念和實踐適應全球化的時代潮流,并且能夠有效促進全球化進程。人類文明新形態與全球文明都主張世界多種文明平等包容,交流互鑒,二者價值追求一致,旨在促進全球各國人民的自由全面發展,共同推進人類解放和人類幸福。
重視和諧統一是中華文明的突出特征。貴和諧,尚中道,是中華文明的基本精神之一。“和”是中國文化的最高境界,中華文明認為宇宙為一個和諧的體系,人也應自覺地追求天地之心,擬太虛之體,達至“和”的最高境界。美肴須五味相和,美樂須五音相和,八音克諧,繪畫要“錯畫為文”,墨分五彩,又分濃淡枯濕,書法兼八種筆畫,又分長短曲直。“和”不是無矛盾、無差別的同一,而是包含諸多矛盾的相輔相成,對立統一。“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后相隨”(《老子》第二章)。陰陽五行是根據“和”的原則組織起來的。多樣性的或者相反的事物合構為一個和諧的整體。“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論語·子路》)。中華文明重和趨同,認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國語·鄭語》)。否可相濟,相濟相成。中華文明中的“和”包括多種向度,人與人的和,人與社會之和,人與自然之和,人與宇宙之和,人的身心之和,最終達到“太和”的境界(太和是至高無上的和諧,是最好的和諧狀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易傳·彖傳》),太和是道,是最高的理想追求,是最佳的整體和諧狀態。這種和諧不是排除矛盾,消弭差異,而是動態的和諧,蘊涵著浮沉、動靜、升降等對立面相互作用、相互消長、相互轉化的過程性的和諧。和諧原則和智慧能夠用以處理人類不同文明之間關系,“協和萬邦”“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12] 293-294,“和”的內涵不僅是和諧,而且還包含和善、和美之義。同理,在全球化時代的文明問題上,中國文明倡導人類多種文明之間的“和”——人類文明之和諧、和善與和美。
人類文明新形態根植于貴中尚和的中華文明之深厚土壤之中。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以和為貴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目標[13]。中華文明以和為美,兼容并包,有容乃大,人類文明新形態認為遐邇一體,承認任何民族國家的文明都有獨特價值。人類文明新形態是一條融貫包容的人類文明道路。人類文明新形態從鮮活的“現實的人”出發,以“全人類”為本位,以全人類共同價值為價值指引,追求人與自然、他人、社會、人類、宇宙以及人的身心的全面和諧和善與和美,是多層次、全方位的“和而不同”,這多個方面將人的多層次性、多維性恰當地扣合在一起,使得人獲得真實而全面的解放,多層次共同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最終使人回歸為完整的人、真實的人、幸福的人,鎖定人類自由全面發展這一總目標,實現馬克思所追尋的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該文明樣態持有寬廣的胸懷,海納百川的氣概,包容多種文明,促進人類整體的繁榮。“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悠遠浩博的中華文明為世界文明觀和人類文化多樣性提供了東方智慧。和衷共濟、和合共生,文化共通、民心共鳴、發展共享,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理論和實踐構建起全球文明百花園,達至“和平、和睦、和諧”的境界,推進人類文明的歷史進程。
[參考文獻]
[1]? 習近平.攜手同行現代化之路[N].人民日報,2023-03-16.
[2]? 布魯斯·馬茲利什.文明及其內涵[M].汪輝,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
[3]? 王文東.人類文明新形態: 生成邏輯與坐標體系[J].江海學刊,2021.
[4]? 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7.
[5]? 帕特里克·曼寧,劉文明.1756年以來的“文明”概念:世界歷史框架下的反思[J].全球史評論,2021,(2).
[6]? 韓震.如何理解我們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N].光明日報,2022-01-10.
[7]? 張鷟.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挑戰與實踐徑路[J].決策與信息, 2023,(8).
[8]? Bruce Mazlish.A Tour of Globalization[J].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Vol. 7,No. 1,1999.
[9]? 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N].人民日報,2021-11-17.
[10]? 曹典順.自由的塵世根基: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11]? 韓慶祥.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基礎性問題[J].中國社會科學,2022,(4).
[12]? 張岱年,方克立,等.中國文化概論[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13]? 張立文.儒家“和為貴”精神的當代價值[J].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23,(2).
[責任編輯:李利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