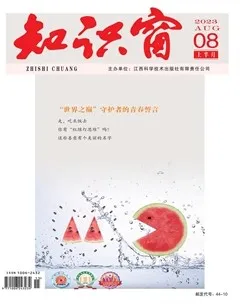那年夏天的炎熱
張君燕

父親在太行山腳下承包了幾畝地,種上了姜。豫西北地區(qū)的土質和氣候很適合種植姜,長出來的姜塊大、絲細,香辣宜口,還有極高的藥用價值,“懷姜”的名號在當?shù)啬酥寥珖己苡忻麣狻?/p>
比起其他農(nóng)作物,姜的收益明顯更多,但人們付出的辛勞也多很多。從選種、定植,到施肥、遮陰,再到收獲、儲藏,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需要人們花費大量的精力和心血,尤其是“封姜”的時候。所謂“封姜”,就是給姜塊培土。正值酷暑,頂著大日頭,人們在田里一站就是幾個小時。
在生長過程中,姜逐漸變大,原本埋在土壤里的姜塊可能會露出土來,一旦裸露出土,姜就會停止生長。培上土后,既避免了暴曬,又能很好地保濕,防止水分流失。在種植姜之前,要對土地進行深翻,筑起高壟,姜壟與姜壟之間形成一條條“姜溝”,人們在這條小溝里澆水、施肥,便于姜慢慢吸收水分和營養(yǎng),以免吸水太多,泡爛了根,或者肥料濃度太高而出現(xiàn)“燒根”的現(xiàn)象。
盛夏時節(jié),父親每天都要去田里“封姜”,疏通“姜溝”。早上五六點出發(fā),十點左右回來,下午三四點以后再去,干到傍晚收工。上午還好一點,太陽沒有那么毒辣,但是下午,即便到了三四點,日光依舊強烈。姜田兩邊都是玉米地,玉米已經(jīng)抽穗揚花,足有一人多高,形成一道密不透風的墻。如此,姜田變成一個巨大的蒸籠,太陽潑下來的炙熱,加上土壤里蒸騰起來的濕熱氣,哪怕靜立其間,一動不動,也會汗流不止。
父親卻要不停地揮動鋤頭,將松好的土一鏟鏟地培在姜根上。在縱線分明的姜田里,父親一步步倒退著,隆起來的土堆則一步步向前,追著父親走過一壟壟姜田,仿佛五線譜上跳動的音符,在天地之間響起勞動的旋律。
那天的天氣異常炎熱,母親叫我去田里給父親送水。她說父親走得匆忙,忘了帶水,這么熱的天不喝水,人怎么受得了!水是母親煮的綠豆水,被裝在透明的大水瓶里,里面加了冰糖,甜絲絲的。母親在午飯后就煮好了綠豆水,放置了幾個小時,它仍是溫暾的,喝起來遠不如冰水爽快,但讓人很舒服。綠豆水流過喉嚨,進入腸胃,悠悠閑閑地在身體里轉了一圈,像一雙柔軟的大手,撫慰著身體的每一個器官,最后從容地從毛孔里鉆出來,帶走燥熱,也緩解了身體的焦渴。
我走在路上,熱氣如巨浪般一波波襲來。之前,我長時間待在空調房里,毛孔是閉合的,身體察覺到了熱,卻發(fā)不出汗來,于是更覺悶熱無比。走到地頭,父親正埋首揮鋤,他的身體一點點地彎下去,再彎下去,好像與田野融為一體。或者說,父親本就是廣袤田野里的一部分。
父親接過綠豆水,咕咚咕咚喝下小半瓶。這時,我才感覺身體的毛孔逐漸打開,汗水開始不住地往外冒。我忍不住嘟囔:“天真熱啊!”“是呀,真熱。”父親點頭附和著,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抹了一把汗。毛巾滴答著往下滴水,父親身上的薄衫也早已濕透。
我突然覺得,我和父親說的熱并不是同一種熱。我說的熱是一瞬間的感受,而父親說的熱則是滴在姜田土壤里的每一滴汗水,是用雙腳在姜田里丈量過的每一步,如同千千萬萬在堅實的土地上耕耘與勞作的農(nóng)民。父親不會記得那年的熱,因為在他的生命中,那份炎熱與往年并無任何不同,但它銘刻在了我的心底,永遠不會忘記,也從來不敢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