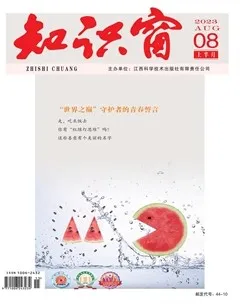饒是金絲變銀發(fā)
蕭良琛

一場煙雨過后,江南的美走出了水墨丹青畫。在散落的雨滴中,水汽氤氳,霧靄朦朧。
小雨綿綿,時而緩,時而停,時而攜著風在空中翩舞,時而和著樹葉高歌一曲,時而含蓄地親吻湖面,泛起層層漣漪,時而調(diào)皮地挑逗枝芽兒,使它探出綠色的腦袋。我總愛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推開二樓的小窗,泡上一壺茶,拿上一袋馓子,遠眺青山,細品佳肴。
在我們老家,馓子被人稱作“金絲”,可在我看來,它更像母親盤起的發(fā)髻。記憶中,母親總是留著一頭烏黑的秀發(fā),每次坐在母親的身后,我總愛撥起她的一綹頭發(fā),陶醉在芳香中。母親時常梳著長長的麻花辮,可是做飯的時候,辮子總是會沾染油煙,于是母親索性用筷子將頭發(fā)輕輕挽起,像極了古代仕女的發(fā)髻。母親要是能將頭發(fā)染成金色的,那真是和馓子一模一樣了。
若將母親的秀發(fā)比喻成一道美食,那應(yīng)該就是馓子。有人說馓子越細越好,我則不以為然,要是細到面條一般的,就失去了嚼頭,牙齒會在觸碰馓子的時刻百無聊賴,所以我認為馓子要有筷子那般粗細才是最好的。捏一把約莫十根八根,輕輕咬下,會發(fā)出清脆爽朗的回響,舌尖感受到酥脆的觸感,油香味鋪滿整個口腔,細嚼過后混著香味囫圇地咽下,整個人都變得精神了。馓子易斷,故而袋中總會留有一些殘渣,獨有的香味,讓它們成為我童年時期最好的零嘴兒。
母親是做馓子的能手,她的手藝傳承自外婆,在工具創(chuàng)新的年代又保留著傳統(tǒng)的美好。母親先將面和鹽和好,然后將它們搓成手指粗細的長條,從大盆的中心開始一圈一圈地盤繞,一邊繞一邊抹油,我們當?shù)匕堰@個步驟叫作“盤條”,當最后一層油抹好后,接下來就交給時間了。經(jīng)過一晚的浸泡,長條非常柔韌。母親的手纖長靈動,長條在母親手中被拉得又細又長,拉長的馓子擱置在長筷搭起的支架上,幾經(jīng)纏繞后便形成了線圈的模樣,待到油鍋熱起,便可下鍋炸至金黃色。
每次做馓子的時候,母親都不允許我進入廚房,一來是怕我偷吃,被剛撈上的馓子燙傷;二來則是怕我口不擇言,犯了忌諱。
有一次,我未能抵御香味的誘惑,偷偷跑到母親身后,隨即說了一句“我餓了”,伸手就想拿剛出鍋的馓子,卻被母親打得縮了回去。外婆告訴我,炸馓子的時候不能說“餓了,渴了”之類的話,這樣馓子會把鍋里的油全部喝掉。那個時候,我還太小,對外婆的話深信不疑,看著母親勞作的身影,不免對隨意脫口而出的話深感自責。
畢業(yè)之后,我遠去西北工作,大抵是水土不服的原因,剛進入西北大地的第三天就高燒不退,吃什么吐什么。在視頻通話時,母親見我消瘦許多,甚是憐惜。路途遙遠,母親隨身攜帶了一些衣服和一袋馓子來看我。說來也是神奇,一碗紅糖水泡的馓子意外地激活了我久違的味蕾,不多時,碗里便空空如也。自那一碗馓子之后,我燒也退了,飯也能吃了。至此,母親才收拾好行囊回家,許是又做馓子去了。
每逢春節(jié)前后,母親都會再次支起鍋灶,而我則是默默坐在灶臺邊烤火。灶臺時而煙熏火燎,時而毫無動靜,母親總是嚴厲地將我趕走,可每次炸馓子的時候,我總愛坐回去,一邊看,一邊和母親聊著過往的時光。時光將她的臉頰刻上了歲月的皺紋,油煙將她盤起的秀發(fā)蒙上了一層銀色的滄桑,我已經(jīng)長大,可還是那個讓母親擔憂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