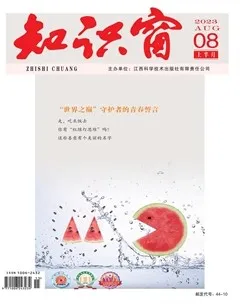你好,媽媽
孫克艷

說出來你可能不信,小時候看電視,每次看到年幼的孩子親切地呼喚“媽媽”的時候,我總是羨慕不已。“媽——媽——”多么親昵的稱呼,孩子只需上下嘴唇輕輕地觸碰兩下,猶如召喚魔法的密語似的,就能得到母親柔情的回眸,就能得到母親熱忱的回應,就能得到母親體貼的照顧……它可真是個神奇的稱呼呀!試問有哪個母親,會拒絕如此親密的稱呼呢?
可惜,我和許多兒時的玩伴從未如此稱呼過母親。故鄉的人兒,就像他們祖祖輩輩耕耘著的土地一樣,深沉、渾厚、粗糲,與細膩、溫柔絕緣。就連教導牙牙學語的嬰孩時,他們也甚少用到疊詞,諸如“媽媽”“爸爸”等很多嬰孩最先學到的稱呼,通常只取一個字來啟蒙嬰孩。母親溫和地看著可愛的嬰孩,期待地說:“喊個‘媽——”你聽,少了個疊字的稱呼,雖簡潔有力,但情感上與“媽媽”實在相距甚遠。
所以,當我在電視上聽到孩子喚母親為“媽媽”時,便大為震驚。我第一次驚詫于語言的魔力:不就是加了一個疊字嘛,為何那樣喚出來的稱謂就變得更柔軟了,甚至連母子間的關系都因此而變得更親密了呢?此后,我曾數次想嘗試改變對母親的稱呼,由“媽”改為“媽媽”。可惜,每次開口后,“媽媽”后面那個發音略為輕微的音節總是被我吞掉。特別是當母親對我不滿時,或者當我有求于母親時,我就特別想喚母親為“媽媽”。我狡黠地以為,那個稱呼瞬間就能改變母親對我的態度。然而,遺憾得很,那個已經排練了多次的呼喚就是難以說出口,無形中好像有一只手,把我只吐了一半音的舌頭截斷了。為此,我總要難過好久,我不知道一個小小的稱呼,為何會成為橫亙在我和母親之間的溝壑。是因為母親不夠慈愛,還是因為我的舌頭不夠靈敏?我懷著這個無人知曉的疑惑,期待有一天問題可以迎刃而解。
然而,在成長的過程中,我與母親漸行漸遠。我像一只羽翼漸豐的鳥兒,飛向了更廣闊的天地。距離的遙遠和思想的隔閡,讓我與母親變得更加疏離。我對“媽媽”這個稱呼的執念早已擱置在歲月的角落,并落滿了塵埃。只要一想到它曾帶給我的情感波動,便深覺遺憾。
多年后,我也為人母了,我總是回想起自己和母親之間的酸甜苦辣,并時常告誡自己一定要做個讓孩子歡喜的好母親,以彌補我的缺憾。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個稱職的母親,但我真的很享受孩子叫我“媽媽”。它是一個有魔法的稱呼,只要聽到女兒這樣叫我,再復雜的心緒都能被撫平。只是有時心潮澎湃間,我會問自己:“什么時候,我也能像女兒那樣,對著母親撒嬌地喚她一聲‘媽媽呢?”而更多的時候,和女兒的摩擦與沖突會讓我意識到,盡管自己是個有文化的、有思想的新女性,但在與孩子的相處中,仍有很多不足之處。有時,我并不如母親包容和有智慧。這個發現讓我感到羞愧,也讓我反思“媽”和“媽媽”對孩子教育的不同。其間,我洞悉了母親的不易,也理解了她的為難,并為自己的不懂事深感愧疚。于是,再與母親相處時,已為人母的我反而與母親更親近了,我仿佛逆著歲月的河流變成了小孩兒,而母親似乎也很受用,真的把我當成孩童來寵溺。
誰知,就在我還沒有成長為一個智慧的母親時,忽然有一天,孩子對我的稱呼變了,她一改多年的習慣,叫我“媽”。我很是詫異,瞬間覺得孩子和我生疏了,一時難以接受,便追問孩子緣由。孩子直言,她已經長大了,“媽媽”這個稱呼有些幼稚,與她的年齡不符。我雖理解,卻到底意難平。一個稱呼的改變看似微不足道,其間涌動的情感卻可能宛如滔滔浪潮。看著與我身高相近的孩子自覺地伏在書桌前學習,我不由得感慨,孩子真的長大了,總有一天她是要飛出去的。
直到此時,我才明白,世上所有的愛都是為了相聚,而只有一種愛是為了分離,那就是母親對子女的愛。我曾在母親的目光里飛出故鄉,如今,我也要做好守望的心理準備。想到這里,我猛然覺悟,我在嘴里喊不出的“媽媽”,母親未必不曾聽到。也許在某個剎那,她不但聽到了,還用心回應了我。
想到這里,我便釋然了。不過,我還是決定任性一下,我要給母親打通電話,開頭便說“你好,媽——媽——”,或者給母親送束鮮花,上面寫著“你好,媽——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