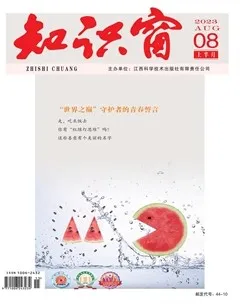青春速寫本
孫元熊

作為一個抽象而固定的詞語,青春在眾多文學作品中有不同的描述,它是肆意的狂歡,是堅定的意志,也是轉瞬即逝的風景,更是人的生命力蓬勃興盛的階段。歲月賦予它春華秋實的過程,也剝離它原有的體魄和活力,唯一不變的是那顆不甘于屈服的、跳動的心。
回顧人生中已經走過的二十個春秋,歲月的猝不及防真實得讓我誤認為這是一場夢。小時候,我總喜歡與小伙伴徜徉在大自然的懷抱里樂此不疲,從田野到山間,從村頭到村尾,都留存著我們“奮戰”的足跡。那些年,我們的娛樂方式是天真與野性并存的,爬樹上找鳥蛋、捉小鳥,在玉米地里與小伙伴開展割豬草比賽,饑餓時刨山芋、摘蠶豆來充饑,無聊時用嫩草逗羊群。待到夕陽下山,紅艷似火的晚霞渲染整個天際,父母的呼喚聲陣陣傳來,我們才返回家中。經過一天的體力消耗,回到家中的我早已饑腸轆轆,趕忙跟在母親身后尋找食物,雖是簡單的粗茶淡飯,但吃得津津有味。夜幕降臨,稻田里各種聲音相互交織,形成天然的搖籃曲,伴我入眠。那時候,青春是游走于童夢的幸福,純真而善良。
青春借光生長,好比春天里的第一抹綠,把大地戳了一個小小的窟窿,時間以它特有的方式靜待花開。轉眼就要上小學了,在父母的目送下,我第一次背著印有卡通圖案的書包踏進校園,課本上印刷體的文字和五彩斑斕的插畫勾起我的求知欲,我對一切未知事物感到好奇,渴望感受知識的力量。課后,我喜歡趴在窗子邊守望天空,那清雅的白、沉靜的藍和一切美好的事物,像極了夢幻般的童話世界,洗滌著我的心靈。我看過很多寓言故事,常常幻想自己與時間賽跑,企圖超越時間,控制萬物。我就這樣想著,傻傻地想著,在“十萬個為什么”的疑問中思索人生,幻想未來。那時候,青春是沉浸在思緒中的灑脫,純粹而自由。
噴薄而出的朝陽日復一日,就像急欲起飛的風箏,掙脫游人的雙手飛向藍天。小升初考試結束,我正式向承載著我六年歡聲笑語的校園揮手告別,帶著父母殷切的期望,步入初中的校門。初中科目的繁多、功課的繁重,使我背起了更沉重的書包,我開始厭倦學習,熱衷于在煙霧繚繞、觥籌交錯的環境下與“社會青年”稱兄道弟。由于長期荒廢學業,我的學習成績一落千丈,老師的訓斥、同學的嘲笑、父母的數落讓我心煩氣躁,只能獨自在黑夜默默流淚。終是綠意濃濃、稚氣頓失之時,我不用再刻意追趕時間的腳步,身體散發出青春的氣息,形體樣貌、思維方式的改變使內心獲得極大的安慰,我認為青春無限,可抵歲月漫長。那時候,青春是只能看的、不能摸的標本,空虛而渺茫。
電影《偉大的辯論家》里有這樣一句臺詞:“當我還是孩子的時候,我像個孩子一樣說話、理解和思考,但當我長大成人后,我就把所有孩子氣的東西拋諸腦后了。”的確如此,成人的意識總是悄無聲息地注入腦海,我漸漸告別了年少執拗的狂歡,試圖逆轉未來,審視生活。
走進秋高氣爽的九月,懷揣著憧憬與忐忑,我步入壓力很大的高中校門。每當晨鐘響起,夢想照進現實時,我便不再為睡與起的問題而糾結,開始規律作息,直面學習,因為我不敢縱容被貼上“差生”標簽的自己。文科學習總是千篇一律的,我像是陷入充滿漩渦的暗流,在瘋狂刷題中尋找方向,那刺眼的分數排名也在不斷指引我自我調節、自我反思。六月,細雨飄飄,如同考生離別的眼淚,一陣又一陣。高考如期而至,校門前拉起的警戒線也似在雨中抽泣,微擺著身體,柏油路上的坑洼處,倒映著少年的身影。帶著身后期盼的目光,我走進了考場。教室靜靜的,只聽見墻角的鐘表嘀嗒嘀嗒地響,我努力調整心態,隨著筆尖劃過試卷,理想島嶼的輪廓清晰可見,我毅然撥開了重重迷霧,殺出重圍。那時候,青春是梔子花開的芬芳,苦澀而憂傷。
七月的風,為我高中生活畫上了休止符,難以抑制的躁動與興奮交匯于大學校園。我開始認真地規劃往后的生活,不再因誘惑的呼喚而放松學習,學會在合理的時間歷練自己,掌控自己獨立而內省的靈魂。每當夜深人靜,他人熟睡時,我便不由自主地想起那段青蔥歲月,細細品味其中蘊含的智慧法則,發現青春似乎是一個不斷發展的動態過程,它屬于世界上每一個單獨的個體——人,它如影隨形,折射出糧食的四季變化:春種、夏耘、秋收、冬藏,在不同階段呈現不同形態。現實不斷牽引我們學會接受、改變、離別,然后在某一天帶著自己內在形成的淡定和從容,瞬間長大,真正像個大人一樣去面對社會的挑戰。
所謂青春不朽,就是春華和秋實都散落在歲月的洪流中奔馳相忘,你卻毫無察覺。待到芳華逝去,我們依椅長靠,在四季更迭中窺探萬物生長的奧妙,躁動與滄桑交織,唯有那份潛藏于心底的記憶才能抹平內心泛起的波瀾,心不再悲戚。歲月無痕,溫暖的記憶悄悄走進我們的心房,這正是青春不朽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