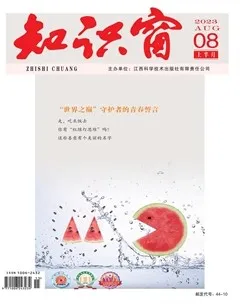蟄伏在小城的人
馬德

我們和六哥是在吃羊蝎子的時候認識的。
六哥說,他這個名字啊,好記,就是“一點一橫兩眼一瞪”。他極認真地為我們比畫這個字,仿佛空氣中有塊黑板。然后,他的指尖下便流動出飄逸的一個字:六。程不二一下子沒搞明白,定格的眼睛、微張的嘴都凝固在空氣里。
我哈哈大笑,算是認識了六哥。六哥比我們大了二十多歲,那一年,我們二十多歲,他四十多歲。他說:“叫哥吧。”程不二一抱拳,說:“六哥在上,請受小弟一拜。”那一刻,六哥喝得微醺,笑得兩眼瞇成一條線。他說,他在北京某所有名的大學讀過書,沒讀完,肄業被下放到小縣城來教書。程不二說:“那你一定學富五車。”六哥的眼睛很快又瞇成了一條線,極謙虛地說了句:“哪里比得上你們年輕人。”
我們真的跟六哥關系親密起來,是他給我們講過一個故事。說有一年,潴瀧河發大水,從上游漂下來一個溺水的人,生死未知,他一個猛子扎下去,竟在漩渦里把那個人拉了上來。六哥會水,但那次也差點溺水了。六哥說:“那是個人啊,我怎么也得把他救出來。”遺憾的是,溺水者最終還是死了。為此,六哥得了個“浪里白條”的稱號。他說,他哪里是“浪里白條”,最多算“浪里‘六條”——涉及生死的事,他也不忘幽默自己一把。
在學校,六哥教的是歷史,但他文史皆通。六哥退休之后,常吟誦一句話:“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我心想,《詩經》里不是說“優哉游哉,亦是戾矣”嘛,便疑心他胡謅。有一次喝酒,我當面質疑他。六哥說:“這句子啊,取自《左傳》。”我回去翻書,果然有,是一個叫叔向的人說的。我心底慚愧至極,六哥真高人也。
六哥有一個學生發展得很好,逢年過節必來看六哥,多少年,從未缺席。初始,我以為只是六哥書教得好,贏得了這個學生的心。后來才知道,這個學生上高中的時候因為打架,學校要開除他。當時,學生很激動,揚言要跳樓。六哥把學生攔腰抱住,然后拉進自己的宿舍。六哥了解他的學生,知道他是個好孩子,可能出于一時激憤才打架。那一晚,六哥沒有回家,陪了學生一夜,勸慰他,怕他想不開。第二天,六哥在校長那里給了一個保證:保證這個學生不會再出問題,否則他就離職。結果,學生也爭氣,高考時考了全校第三名,上了一所非常好的經濟類大學。
六哥善飲,也能豪飲。年輕的時候,有幾個人不服他的酒量,在酒桌上曾經和他比拼過一次。那一次究竟喝了多少,大家都不知道,但不服的人都被六哥撂倒在酒桌下,而六哥則自行回家。每每談起這段蕩氣回腸的往事,我們夸贊六哥的豪情,六哥卻向我們擺手,說:“沒意思,沒意思,別多喝,喝多了對誰也不好。”六哥會吹笛子,也會拉二胡、京胡,還會唱京劇,他的拿手曲目是《武家坡》的那段西皮流水。
程不二會寫幾筆書法,那都是和六哥學的。六哥臨摹過文徴明的名帖,后來又臨摹過于右任的名帖。六哥只是寫,從來不想加入書法協會,也不想參加什么書法展覽。來向六哥求字的人不少,六哥來者不拒。程不二說:“六哥,你多少要個潤筆費啊。”六哥說:“人家向咱求字,就是看得起咱,干嗎把錢盯得那么清。”
對了,六哥留著長發,已經七十好幾的年紀,依然長發飄飄。那氣質,看起來一點也不像蟄伏在這座小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