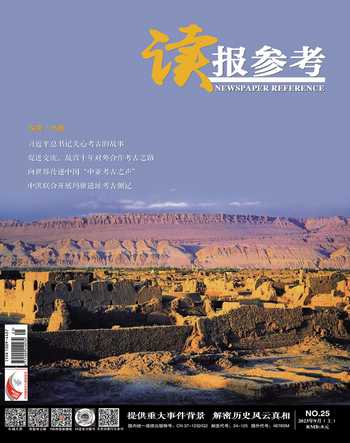李鳳玉與中國農(nóng)機(jī)“黃金十年”
在歷史的長河中,個(gè)人的奮斗史往往是一個(gè)時(shí)代的縮影。今年67歲的李鳳玉,出生在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克山縣。畢生都在與土地打交道的李鳳玉,懷揣著“如何多打糧食、如何讓農(nóng)民腰包鼓起來”的樸素想法,誤打誤撞跟上了一往無前的歷史進(jìn)程,親歷中國農(nóng)機(jī)工業(yè)“黃金十年”。
農(nóng)機(jī)夢想
生長于東北農(nóng)村的李鳳玉,一生與克山縣河南鄉(xiāng)的三個(gè)村子密不可分——學(xué)習(xí)村是他嶄露頭角的起始點(diǎn),仁發(fā)村是他大放異彩的關(guān)鍵點(diǎn),齊心村是他厚積薄發(fā)的落腳點(diǎn)。
河南鄉(xiāng)因?yàn)槲挥跒踉柡拥哪习抖妹T诶铠P玉出生那年,也就是1956年,當(dāng)?shù)爻穮^(qū)劃鄉(xiāng),設(shè)置河南鄉(xiāng);兩年后實(shí)行人民公社體制,改稱河南人民公社;1984年,政社分開,又改回河南鄉(xiāng)。
受“農(nóng)業(yè)的根本出路在于機(jī)械化”這一論斷的耳濡目染,年輕時(shí)的李鳳玉就萌生了“農(nóng)機(jī)夢想”。由于頭腦機(jī)靈,成年后,他如愿以償當(dāng)上了河南公社機(jī)耕隊(duì)農(nóng)機(jī)駕駛員,而這也正是他嶄露頭角的起點(diǎn)。“我們一個(gè)村,2000多人,就選了三四個(gè)人去開拖拉機(jī)。”
靠著多年的農(nóng)機(jī)駕駛員經(jīng)歷,李鳳玉在學(xué)習(xí)村頗有人緣,再加上敢想敢干、勇于任職的作風(fēng),他被推選為村委會主任。當(dāng)時(shí)間的指針指向2006年,李鳳玉又被選為仁發(fā)村黨支部書記。而誰也想不到,這個(gè)不知名的東北農(nóng)村會在不久的將來一躍成為全國知名合作社所在地。
2006年1月,我國全面取消農(nóng)業(yè)稅,終結(jié)了延續(xù)2600年的古老稅種,這一重大變革具有劃時(shí)代意義。同年10月,《農(nóng)民專業(yè)合作社法》審議通過,并自2007年7月1日起施行。從宏觀層面來看,2006年前的“十五”時(shí)期(2001-2005年),我國啟動了農(nóng)村稅費(fèi)改革;2001年底,我國正式加入世界貿(mào)易組織,農(nóng)業(yè)也不得不直面來自全世界的競爭。
與此同時(shí),2004年成為我國農(nóng)機(jī)工業(yè)“黃金十年”的起始年。這一年,農(nóng)機(jī)領(lǐng)域發(fā)生了兩件大事,極大地調(diào)動了農(nóng)民發(fā)展農(nóng)業(yè)機(jī)械化的積極性。一是“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對購置和更新大型農(nóng)機(jī)具給予一定補(bǔ)貼”;二是《農(nóng)業(yè)機(jī)械化促進(jìn)法》頒布實(shí)施,再次要求央地財(cái)政安排專項(xiàng)資金,對農(nóng)機(jī)購置給予補(bǔ)貼。
敢為人先探索“仁發(fā)模式”
“有哪個(gè)村愿意創(chuàng)辦農(nóng)機(jī)合作社?”2008年,黑龍江省出臺了“財(cái)政補(bǔ)貼60%、個(gè)人自籌40%,且個(gè)人出資部分由政府協(xié)調(diào)貸款并貼息,加快推進(jìn)千萬元以上農(nóng)機(jī)合作社建設(shè)”的支持政策。隨后,河南鄉(xiāng)領(lǐng)導(dǎo)召集全鄉(xiāng)19個(gè)村支部書記開會稱,全鄉(xiāng)只有一個(gè)成立農(nóng)機(jī)合作社的名額,并提出了這一問題。
在此之前,李鳳玉就找人咨詢過2007年7月施行的《農(nóng)民專業(yè)合作社法》,認(rèn)定干合作社是件大好事,農(nóng)機(jī)駕駛員的工作經(jīng)歷也使其打心眼里認(rèn)定,在東北要想提高糧食產(chǎn)量,就必須將農(nóng)業(yè)機(jī)械化搞起來。
“當(dāng)時(shí),其他村支部書記都不吱聲。我就在心里盤算,現(xiàn)在農(nóng)村一家一戶都是用‘小四輪作業(yè),要是有大農(nóng)機(jī)打破犁底層的話,一畝地最低能多打300斤糧食,效益可觀。于是,我就自告奮勇,主動站出來說,我們?nèi)拾l(fā)村愿意試一試。”李鳳玉回憶稱。
由于合作社是新生事物,仁發(fā)村農(nóng)戶雖然在動員會上情緒高漲,卻應(yīng)者寥寥。直到2009年10月,李鳳玉等7人籌資850萬元,再匹配上省財(cái)政農(nóng)機(jī)具購置補(bǔ)貼資金1234萬元,才組建了“克山縣仁發(fā)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農(nóng)機(jī)專業(yè)合作社”(下稱“仁發(fā)合作社”),農(nóng)機(jī)具由省級農(nóng)機(jī)主管部門選配,主要特征是“動力機(jī)車進(jìn)口、配套機(jī)具國產(chǎn)”。
大型農(nóng)機(jī)具就位后,大伙準(zhǔn)備大干一場,卻不曾想“敗走麥城”。2010年3月,仁發(fā)村開始嘗試“租地自營+代耕服務(wù)”的規(guī)模化農(nóng)地經(jīng)營模式。當(dāng)時(shí),仁發(fā)合作社以240元/畝的價(jià)格,流轉(zhuǎn)了本村1100畝耕地種植大豆。由于流轉(zhuǎn)土地不連片,大型機(jī)械根本派不上用場,還得花錢雇“小四輪”耕種;再加上租地經(jīng)營需要預(yù)付地租,承擔(dān)利息成本,以及當(dāng)年大豆價(jià)格下跌,致使“租地自營”板塊勉強(qiáng)實(shí)現(xiàn)收支平衡。合伙人原本指望將“代耕服務(wù)”板塊作為合作社的主要業(yè)務(wù),但當(dāng)時(shí)克山縣農(nóng)戶習(xí)慣使用自有小農(nóng)機(jī)耕種土地,造成代耕市場較小、服務(wù)費(fèi)用不高;而到蒙東呼倫貝爾地區(qū)開展跨區(qū)耕作服務(wù),由于遇到作業(yè)面積少算等一系列問題,也基本沒有盈利。
李鳳玉總結(jié)說,在家,土地沒有實(shí)現(xiàn)規(guī)模化,無法作業(yè);在外,不好要錢。結(jié)果合作社一算賬,只盈利13萬元,如果按規(guī)定計(jì)提折舊的話,反倒虧損187萬元。“剛起步就陷入困境,有合伙人要求撤股、退社。那時(shí)候,我感到特別難熬。”
經(jīng)過一番思考研究,2011年春,仁發(fā)合作社公布了“帶地入社、保底分紅”為核心的“七條承諾”。前三條涉及盈利分配,包括農(nóng)戶“帶地入社”,保底收益350元/畝;入社土地折資入股,在支付保底收益后,合作社盈余二次分紅;將1234萬元國家補(bǔ)貼資金產(chǎn)生的盈余,再平均分配給社員。后四條涉及社員管理,包括有困難的社員可付息全額借回土地保底金;入社成員仍享受國家發(fā)放的糧食綜合補(bǔ)貼;重大決策事項(xiàng)表決實(shí)行一人一票,不按投資額;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免除農(nóng)民后顧之憂。
這構(gòu)成了“仁發(fā)模式”的主要運(yùn)作機(jī)制。
農(nóng)戶從不愿入社到不愿退社
雖然“七條承諾”很誘人,但農(nóng)戶也很現(xiàn)實(shí),一開始并不相信。質(zhì)疑有兩點(diǎn):一是保底收益,二是退社自由。當(dāng)時(shí)土地轉(zhuǎn)包為240元/畝,憑啥合作社能承諾350元/畝?如果退社自由,農(nóng)民真要退地的話,還怎么做到規(guī)模連片?李鳳玉為農(nóng)戶釋疑,土地流轉(zhuǎn)給合作社后,合作社能帶領(lǐng)社員降本增效。
由于體量足夠大,合作社有議價(jià)能力,不論是買農(nóng)資,還是賣農(nóng)產(chǎn)品,都有規(guī)模優(yōu)勢,確保農(nóng)戶保底收益。而且,大型農(nóng)業(yè)機(jī)械在合作社內(nèi)部連成片的土地上也有了用武之地,能為周邊農(nóng)戶提供代耕服務(wù),確保二次、三次分紅。
更重要的是,入社農(nóng)戶沒有后顧之憂,“離鄉(xiāng)不丟地,不種有收益”。不但保底收益比自己種地收益還要高出一大截,而且解放勞動力后,還可以再打一份工。由過去種地掙一份錢,到現(xiàn)在“入社+打工”掙兩份錢。時(shí)任仁發(fā)村村委會主任張德軍是“七個(gè)合伙人”之一。他解釋稱,350元/畝是臨界點(diǎn),既不能過低,也不能過高。若只比市場價(jià)格(240元/畝)高一點(diǎn),不具有吸引力;若突破承受能力,合作社將面臨風(fēng)險(xiǎn),“最差打算是合作社不至于賠錢”。至于退社自由,如果退地的話,肯定不是農(nóng)戶原先位置的土地,而且會讓其優(yōu)先選一等地,前提是不能影響合作社規(guī)模化作業(yè)。
生產(chǎn)經(jīng)營模式的創(chuàng)新,再趕上大豆?jié)q價(jià),2011年,合作社一舉扭虧為盈,凈盈利1342.2萬元,每畝入社土地平均分紅710元。真金白銀的分紅,吸引著全河南鄉(xiāng)農(nóng)戶的關(guān)注。既保底又分紅,農(nóng)戶哪見過這種好事?于是,加入合作社的熱情格外高漲。
盡管后來“仁發(fā)模式”遇到一些新挑戰(zhàn),合作社主動取消土地保底收益,實(shí)行“盈余共沾,風(fēng)險(xiǎn)共擔(dān)”的分配方式,但也幾乎沒有退社的。“以前是農(nóng)戶不愿意入社,如今是農(nóng)戶不愿意退社。”張德軍稱,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受自然災(zāi)害影響很大,農(nóng)戶訴求其實(shí)很簡單,就是找個(gè)靠譜的經(jīng)營主體,確保土地收益。經(jīng)過多年合作,農(nóng)戶已與仁發(fā)合作社建立了信任關(guān)系。
2015年,仁發(fā)合作社發(fā)起成立合作社聯(lián)合體——黑龍江龍聯(lián)農(nóng)民專業(yè)合作社聯(lián)社,聯(lián)合全省的合作社,抱團(tuán)取暖;領(lǐng)辦深加工企業(yè)——黑龍江仁發(fā)農(nóng)業(yè)發(fā)展有限公司。折服于“老李”的個(gè)人能力和人格魅力,孟德利是最早一批加入龍聯(lián)聯(lián)社的社員。他說:“我跟老李有共同想法,就是農(nóng)業(yè)必須干成‘大農(nóng)業(yè),才有發(fā)展空間。”
(摘自《第一財(cái)經(jīng)日報(bào)》邵海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