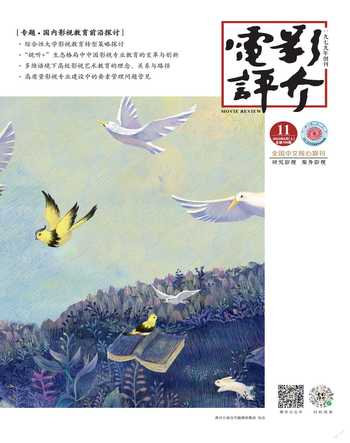刑偵劇《狂飆》:極致的寫實(shí)主義與細(xì)膩的審美形構(gòu)
刑偵涉案劇《狂飆》以39集的篇幅,講述了一個跨越整整20年的精彩故事,劇中令人拍案叫絕的細(xì)節(jié)眾多,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敘事與縝密的推理線索也符合刑偵劇的“燒腦”設(shè)定。但劇作真正出彩之處在于表現(xiàn)了理想主義與現(xiàn)實(shí)主義的交鋒,并在其中建構(gòu)了一個雙線并行的完美邏輯閉環(huán),通過劇中兩大主要人物——安欣和高啟強(qiáng)命運(yùn)起落的牽引,最終引出電視劇對權(quán)力、人性與時(shí)代變遷的深層探討。《狂飆》中既有對社會生態(tài)的真實(shí)描摹,也有刑偵劇框架下充滿戲劇沖突的勢力碰撞,在消費(fèi)主義深度介入文化市場的大背景下,該劇做到了在變革中堅(jiān)守,通過對題材類型的整編與突破,完成了一個時(shí)代巨幅下微觀命題的摹畫,將游走于理想與現(xiàn)實(shí)之間的新寫實(shí)主義發(fā)揮到極致。
一、纖毫畢現(xiàn):寫實(shí)主義主導(dǎo)下的真實(shí)細(xì)節(jié)書寫
《狂飆》將寫實(shí)主義與刑偵劇的基本框架相結(jié)合,實(shí)現(xiàn)了警匪對抗、黑幫斗爭、官場博弈等主題的祛魅,并融入了更多屬于大眾視野范疇的新鮮因素,如市井生活、黑色幽默和對小人物心路歷程的揭示等。同時(shí),無論是正派人物還是反派人物,《狂飆》都沒有一筆帶過,而是對其進(jìn)行了從外表到內(nèi)心的細(xì)節(jié)化處理,使其形象進(jìn)一步立體化,并運(yùn)用大量鏡頭語言表現(xiàn)了黑白之間的灰色地帶,比起立場鮮明的正邪對抗,這樣的處理方式更符合真實(shí)的人物心理和思維邏輯,更能給觀眾帶來耳目一新的觀感。
《狂飆》的寫實(shí)主義首先體現(xiàn)在對時(shí)代背景的真實(shí)還原上,由于劇作具備長達(dá)20年的時(shí)間跨度,對三個時(shí)間節(jié)點(diǎn)的精確還原具有相當(dāng)大的難度。在千禧年的幾集劇情中,盡管人物服裝、造型上的年代感還原不夠到位,但極具電影質(zhì)感的畫面風(fēng)格成功彌補(bǔ)了時(shí)空裂隙,對時(shí)代特征的精準(zhǔn)再現(xiàn)更是從開篇便切入了主題,京海市官場的“保護(hù)傘”、利益鏈,混亂無序的舊廠街,“龍兄虎弟”為首的地痞向商販索要好處費(fèi)、夜總會暗中進(jìn)行不法交易等,這些盤根錯節(jié)的利益勾結(jié),是掃黑除惡行動開展之前社會長期積累的痼疾。高啟強(qiáng)所生長的舊廠街就是底層黑暗滋長的一個縮影,而曾經(jīng)的京海市,更是一個金錢、美色、官職、生意……種種利益關(guān)系往來不斷的名利場,權(quán)力的碾壓令人只能為生存奔波而毫無尊嚴(yán)可言。
相應(yīng)地,《狂飆》對2021年片段的呈現(xiàn)也集中在社會背景的復(fù)原上,采用對比反襯來突顯20年間社會風(fēng)氣的根本變化。20年后的京海市可謂天翻地覆,隨著調(diào)查組的雷霆出擊,一樁樁、一件件令人生畏的陰暗交易被暴露在天日之下,掃黑除惡常態(tài)化和政法隊(duì)伍教育整頓的颶風(fēng),讓京海市大案要案倒查20年年成為可能。電視劇將深埋的罪惡公之于眾,直接點(diǎn)明輿論熱點(diǎn)與治理難點(diǎn),更用今昔對比的方式加大了善惡的反差,讓時(shí)空變幻、斗轉(zhuǎn)星移在鏡頭中變得更加真實(shí)可感,例如安欣滿頭的白發(fā)、高啟強(qiáng)逐漸失焦的眼神,它們已經(jīng)升格為電視劇的情感符號,卻又不完全等同于生活中的實(shí)物。“唯有攝像機(jī)鏡頭拍下的客觀影像能夠滿足我們潛意識提出的再現(xiàn)原物的需要。它比幾可亂真的仿印更真切,因?yàn)樗褪沁@件事物的原型,但已擺脫了時(shí)間流逝的影響。”[1]這些具有象征意義的符號一定程度上脫離了它們所處的現(xiàn)實(shí)層面,而成為戳中觀眾情感痛處的一把利刃。
劇作的寫實(shí)主義不僅體現(xiàn)在對社會背景的把握上,更于細(xì)微之處發(fā)力,將微觀視角下人物的一舉一動悉數(shù)捕捉,從而積蓄了強(qiáng)大的情感爆發(fā)力,為刑偵劇矛盾沖突走向巔峰做了層層鋪墊。劇中具有深意的細(xì)節(jié)隨處可見,從開篇調(diào)查組進(jìn)駐京海市開始,人物的對話就已暗藏玄機(jī),安長林感嘆道:“看來是要下場大暴雨了!”市長趙立冬卻輕描淡寫地說:“雨未必下得下來,頂多一陣風(fēng)。”這句看似不經(jīng)意的臺詞,實(shí)際上卻草蛇灰線、伏線千里,趙立冬話中的輕蔑與自傲,反映了他常年充當(dāng)“黑惡保護(hù)傘”的目中無人。陳書婷車禍遇難的結(jié)局在臺詞中也早有暗示,當(dāng)她第一次回京海時(shí),電視劇毫不突兀地安排保姆提醒陳書婷全程系好安全帶,這一處幾乎無人注意的細(xì)節(jié),卻在多年后陳書婷真的遭遇車禍時(shí)在觀眾腦海中瞬間閃現(xiàn),觀眾在回味之余才意識到陳書婷的悲劇命運(yùn)早已注定。細(xì)節(jié)的前后呼應(yīng)讓《狂飆》的劇情邏輯更加嚴(yán)密,但卻沒有刻意安排的巧合,避免了刑偵劇內(nèi)容的懸浮空洞,講述者對觀眾一而再的明示與暗示,更勾連起了跌宕起伏的情節(jié)。
劇中光影明暗的運(yùn)用有時(shí)也交代后續(xù)的情節(jié)走向,當(dāng)高啟強(qiáng)認(rèn)泰叔做干爹并成功接手夜總會、開始在黑道叱咤風(fēng)云時(shí),他與一幫簇?fù)碓谏砼缘氖窒抡袚u過市。而同一時(shí)刻,安欣卻因伸張正義威脅到一系列案件的幕后黑手而直接被調(diào)到交通指揮崗位,此時(shí)他也學(xué)會了以沉默的方式韜光養(yǎng)晦。在這一幕中,鏡頭將畫面完美分隔為兩半,以一半陽光、一半陰影的對稱格局,恰好象征二人的分道揚(yáng)鑣,一人從此青云直上,一人則蟄伏于地下數(shù)年之久。陰陽割昏曉的街角,從此成為安欣和高啟強(qiáng)的命運(yùn)拐點(diǎn),劇中用明暗的交替來表現(xiàn)二人從此殊途異道,這樣的細(xì)節(jié)能夠令觀眾自行體會劇情深意,比起平鋪直敘而言,充盈的細(xì)節(jié)延伸了故事的內(nèi)涵,讓觀眾情感不止停留在情節(jié)本身,而是深入到人物內(nèi)心的成長史,從而體悟到人物性格轉(zhuǎn)變的內(nèi)在動機(jī)。
二、正邪對照:雙男主人物設(shè)定下的內(nèi)在人文觀照
《狂飆》從改編立項(xiàng)到最終播映,貫穿其始終的是安欣、高啟強(qiáng)兩大主線視角。早在宣發(fā)階段,該劇的海報(bào)就凸顯了二者間的羈絆與糾葛,而后來的劇集中,一直采用的是“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雙線敘事,分別通過兩人的角度來展現(xiàn)20年間中國社會天翻地覆的變遷。警匪、正邪、黑白間的對抗是刑偵題材的核心要素,懲惡揚(yáng)善、還人間以浩然正氣,更是刑偵劇一直以來弘揚(yáng)的中心題旨和時(shí)代價(jià)值。但比起部分劇作弱化甚至丑化反面角色來凸顯正派英雄的神勇機(jī)智,《狂飆》所采用的人物塑造策略顯然更貼近真實(shí)。劇中以高啟強(qiáng)為首的反派人物絕不是天生就邪惡狠辣,而是一念之差鑄成大錯,從而走上人生的不歸路。而正派人物也并非完美無瑕,他們的身上也清晰可見人性的弱點(diǎn)與缺點(diǎn)。將每個角色詮釋得更為圓形化,避免扁平而不合乎邏輯的人物塑造,《狂飆》不僅利用這樣的策略成功塑造一群各個立場上的人物群像,而且深刻剖析了不同階層的個性與共性,使其深入人性與靈魂深處,更增添了劇中正邪博弈的復(fù)雜程度和可看性。
對于刑偵劇來說,《狂飆》正反派雙男主的設(shè)置是一場鋌而走險(xiǎn)的挑戰(zhàn),這決定了劇作不僅要表現(xiàn)二人之間的對抗性,還要深掘其共性與互補(bǔ)性。安欣和高啟強(qiáng)仿佛一張鏡子的正反面,二人同樣在十二三歲的年紀(jì)失去雙親,他們渴望實(shí)現(xiàn)理想、渴望被理解被認(rèn)同。但大相徑庭的是,安欣從小被亦師亦父的孟德海、安長林收養(yǎng),形成了正氣凜然、崇尚公道的價(jià)值認(rèn)同;而在社會底層摸爬滾打的高啟強(qiáng)遠(yuǎn)沒有這么幸運(yùn),他為了撫養(yǎng)弟妹不得不委曲求全。比起罕有的“善”來說,高啟強(qiáng)司空見慣的是各式各樣的“惡”,因此他才會將千禧年除夕夜的那盒餃子記在心頭,安欣偶然流露出的一絲善意,無形中改變了兩人一生的命運(yùn),高啟強(qiáng)青云直上,安欣卻急轉(zhuǎn)直下,二人境遇間的云泥之別無疑是對社會生態(tài)的映射,也表達(dá)了電視劇對真善美持之以恒的追求。
從正面人物塑造的角度來說,“在消費(fèi)主義和大眾傳媒時(shí)代,公眾往往并不要求名人或者他的偶像完美無缺,反而表現(xiàn)出對他們?nèi)诵匀觞c(diǎn)相當(dāng)?shù)恼J(rèn)可。”[2]安欣、李響、安長林等人物雖是劇中公平正義的化身,但卻并不是高高立于神壇之上的個人英雄,20年前的安欣意氣風(fēng)發(fā),認(rèn)準(zhǔn)公道正義一個標(biāo)準(zhǔn),難免給人以不近人情和張揚(yáng)桀驁之感。他堅(jiān)信李響對自己有所隱瞞,絲毫不顧及眾人的感受大鬧曹闖的葬禮,逼迫李響說出徐江與趙立冬勾結(jié)的真相,不解人情世故的他,由于屢次這樣刨根問底險(xiǎn)些落得身敗名裂的下場,更是直接被踢出權(quán)力中心,讓自己的前途和真相一起折戟沉沙。認(rèn)死理、問到底是安欣在為人處世上的缺陷,卻也是觀眾喜愛這一人物的較大原因,比起靠著養(yǎng)父的關(guān)系平步青云,他遭遇種種不公正的待遇更能引起大眾的悲憫與共情。
對反面人物的刻畫也是刑偵劇實(shí)現(xiàn)題材突破的關(guān)鍵,正如德國美學(xué)家黑格爾所言,“美只有一種典型,丑卻在千變?nèi)f化。”[3]刑偵劇中的反面人物因其多變性與真實(shí)性更容易出彩,就如《狂飆》中的高啟強(qiáng),電視劇完整表現(xiàn)了他地位與性情轉(zhuǎn)變的三個階段。從最初的唯唯諾諾、退避求安,到初嘗權(quán)力滋味、盡顯貪婪野心,再到覆水難收、垂死掙扎。安欣曾讓高啟強(qiáng)鉆研《孫子兵法》,可令人始料未及的是,高啟強(qiáng)從中悟出的是人情社會的權(quán)謀算計(jì),他開始學(xué)著投其所好、籠絡(luò)人心,向愛面子的黃老送上“人民公仆”的墨寶,將小龍小虎兄弟與自己的利益牢牢捆綁,向泰叔下跪,如履薄冰卻又聲嘶力竭地大喊爸爸,權(quán)力欲望的無限膨脹,注定了高啟強(qiáng)終將落入泥沼。劇作集齊了高啟強(qiáng)人生不同階段的鮮活面孔,真實(shí)再現(xiàn)了一個小人物向上攀爬時(shí)的掙扎困頓。比起徹頭徹尾的惡,高啟強(qiáng)的沉淪與轉(zhuǎn)變更具刺痛人心的情感份量,正邪的鏡像對照,深度展現(xiàn)了人性的共性與善惡抉擇的重要性。
三、迭代翻新:現(xiàn)代性審美特征下的題材創(chuàng)新突破
全媒體環(huán)境下的影視市場,大眾文化風(fēng)頭正勁,其正在強(qiáng)勢進(jìn)攻公共話語空間并大有主宰之勢,我國電視劇的表現(xiàn)對象也逐步轉(zhuǎn)移到普羅大眾身上。“影視劇成了一種由文化產(chǎn)業(yè)生產(chǎn)的商品,在文本表達(dá)上形成了一種無深度的平面文化,在傳播方式上,成了一種全民性的泛大眾文化。”[4]當(dāng)下,通俗易懂成為衡量影視劇是否成功的重要標(biāo)志,但這并不意味著審美標(biāo)準(zhǔn)無底線的退讓,庸俗粗鄙或是毫無內(nèi)涵的表達(dá),即使能夠憑借噱頭走紅一時(shí),也會被審美的歷時(shí)性與社會價(jià)值判斷所沖垮。因此,當(dāng)下大眾需要的是真正具有人文關(guān)懷的作品,對人性、時(shí)代、平民階層鞭辟入里的剖析與細(xì)致深刻的解讀,無論這樣的作品套接在何種類型題材中,或是以何種表達(dá)方式呈現(xiàn),都是大眾所期待看到并能夠接受的。《狂飆》的廣受追捧,正是建立在這一文化背景之上。底層視角與對市井平民的關(guān)注,讓劇作得以突破刑偵劇的類型框架,成功撕下人物身上的臉譜化標(biāo)簽。劇中主人公成長與沉淪的軌跡令人唏噓,而許多出人意料的情節(jié)和綿密的細(xì)節(jié)鋪墊,也讓觀眾幾乎無暇停滯思緒,反而以高速旋轉(zhuǎn)的思維緊跟劇情發(fā)展,從而產(chǎn)生強(qiáng)烈的代入感與心靈共鳴。
審美的現(xiàn)代性在當(dāng)下主要表現(xiàn)為“世俗的‘救贖、拒絕平庸、回歸感性、對歧義的寬容和審美的反思性”[5]。觀眾在面對電視劇的信息輸出時(shí),其自我意識與互動期待愈來愈強(qiáng),對于庸常瑣碎的生活,人們更愿意電視劇與其保持一種若即若離的距離,期待看到人物的情感爆發(fā)和多元性格特征,以及人物彼此之間的或是對自我的情感救贖。這些審美現(xiàn)代性的元素都是《狂飆》所能夠滿足觀眾的。劇中的時(shí)空構(gòu)建,有意地與觀眾拉開距離,卻又絲毫沒有浮夸懸置之感,尤其是幾場槍戰(zhàn)場面,觀眾的感官被牢牢牽引,但不同于傳統(tǒng)刑偵劇警匪對抗的緊張刺激,《狂飆》中撲面而來的是宿命悲劇感,能夠?qū)⑺腥司砣肫渲校恋沓鰧β氊?zé)、正義、生命價(jià)值的思考。似乎一切都架構(gòu)于活生生的現(xiàn)實(shí)之上,劇中人的行為邏輯都有真實(shí)的生活經(jīng)驗(yàn)作支撐,那些或諂媚、或失意、或狂妄的情感爆發(fā),似乎就隱藏在每個個體的心底,因而觀眾能夠全身心地接受這場情緒的狂飆,更能隨時(shí)隨地代入角色的視角審視生活。劇中血淋淋的黑幫斗爭和游走于生死線的刑警生涯,離平凡人的生活很遠(yuǎn),這一層懸疑刑偵的外殼賦予全劇更強(qiáng)的矛盾沖擊力,既警示著權(quán)力欲望的貪婪可怖,又能使觀眾不至于混淆現(xiàn)實(shí)的邊界。
除了對庸常的消解外,《狂飆》更是一部有著多元價(jià)值和平視視角的作品,其沒有對處于低位的人物加以貶低,更沒有將象征正義的主人公抬到神壇上一味吹捧,而是做到了從人物的生平遭際出發(fā)進(jìn)行描寫,讓人物能夠“接地氣”而不流俗。無論是劇中的兩大靈魂人物——安欣、高啟強(qiáng),還是重要反面角色徐江、高啟盛、趙立冬等人,創(chuàng)作者大筆墨來進(jìn)行表現(xiàn)。許多角色盡管出場時(shí)長較短,但《狂飆》依舊用寥寥幾筆將其寫得精辟傳神,毫無千篇一律的重復(fù)感。例如引發(fā)徐江等人斗爭的核心人物徐雷,家境優(yōu)渥卻整日豪賭無賴,他的賭債是激發(fā)父輩間仇殺的導(dǎo)火索,而他因貪小便宜電魚致死的結(jié)局更是相當(dāng)諷刺。一心想要為女兒洗心革面的老默,炒得一手好菜卻因有前科而屢次求職被拒,最終淪落為高啟強(qiáng)的一枚棄子,陰險(xiǎn)狠辣的外表下,他的命運(yùn)遭際以及被世俗的排斥也令人唏噓不已。
為勒索錢財(cái)而喪命的失足女黃翠翠、喜獲砌磚工作卻墜樓而亡的老李、因殘疾成為村干部借刀殺人的李青、狐假虎威官腔十足的王秘書等這些劇中戲份并不多的配角,出彩程度甚至不亞于主角,他們每個人都是社會萬花筒中的一面,折射出平凡人的辛酸喜樂、悲歡憂愁,甚至與高啟強(qiáng)同在舊廠街檔口經(jīng)營的商販們,他們在高啟強(qiáng)身份轉(zhuǎn)換前后的兩張面孔,都是構(gòu)成眾生百相的其中一環(huán)。他們無限接近于真實(shí),而攝像機(jī)的存在又放大了現(xiàn)實(shí)中的人性美好與丑惡,讓觀眾如隔簾望月般領(lǐng)略到小人物的生存智慧,以及他們在社會叢林中廝殺競爭的行事邏輯。《狂飆》用具有反差性與高辨識度的角色群像,滿足了當(dāng)下觀眾的多元審美需要,并消解了非黑即白的二元價(jià)值觀,讓感性與理性在熒幕空間中恣意交融,建構(gòu)更加具有現(xiàn)代性和大眾性的審美特征,并將其作為劇集價(jià)值傳達(dá)的關(guān)鍵,拓展了刑偵劇題材的內(nèi)容、內(nèi)涵、內(nèi)在。
結(jié)語
近年來,我國現(xiàn)代化建設(shè)發(fā)展飛速,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上的變動深刻影響了社會的文化風(fēng)向,多種文化因子的高速遷流與碰撞,鑄就了歷史車輪下滾滾向前的當(dāng)今時(shí)代。從社會背景的宏觀角度看,《狂飆》劇中與劇外的兩個世界實(shí)際上是同頻共振的,劇中的安欣、高啟強(qiáng)等人是時(shí)代洪流中不甘平庸的小人物,他們在為理想、為生活“折騰”的過程中起落沉浮;而劇外的大千世界,更是二十年間上演過無數(shù)次正邪黑白間的對抗,時(shí)代的變化促成了當(dāng)下審美的多元性。電視劇內(nèi)外空間的深刻交融,方是寫實(shí)主義之于中國當(dāng)下社會的真義,觀眾能夠透過人物命運(yùn)感悟個體與大時(shí)代的價(jià)值,從而產(chǎn)生具有真正現(xiàn)實(shí)意義的思考體悟。《狂飆》成功拓展了刑偵劇的內(nèi)涵與外延,對我國電視劇探索現(xiàn)實(shí)與時(shí)代接軌做了有益的探索。
參考文獻(xiàn):
[1][法]安德烈·巴贊.電影是什么[M].崔君衍,譯.北京: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2008:10.
[2]夏荔.中國涉案電視劇敘事審美研究[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9:24.
[3]伍蠡甫.西方文論選·下卷[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187.
[4]徐蕾,相錫桓.如何克服電視的商業(yè)化和庸俗化[ J ].聲屏世界,2003(01):23-24.
[5]周憲.審美現(xiàn)代性的四個層面[ J ].文學(xué)評論,2002(05):45-54.
【作者簡介】? 金冰冰,女,河南開封人,河南大學(xué)新聞與傳播學(xué)院講師,博士,主要從事文藝?yán)碚撆c文藝美學(xué)研究。
【基金項(xiàng)目】? 本文系河南省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規(guī)劃項(xiàng)目“文旅文創(chuàng)戰(zhàn)略下中原文化的創(chuàng)新表達(dá)與傳播路徑研究”(編號:2022BXW008)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