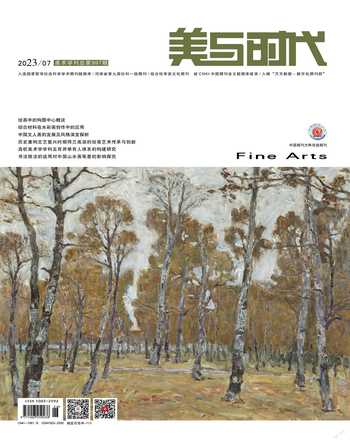符號學(xué)視角下賈滌非油畫藝術(shù)語言探究
耿琨博 胡玉森
摘 要:賈滌非的油畫藝術(shù)語言,將內(nèi)在精神世界的訴求,凝結(jié)為外在符號形式的表達(dá),構(gòu)成屬于自身油畫藝術(shù)語言系統(tǒng)的視覺特質(zhì)。通過對社會、歷史、文化等的深度自醒以及對個(gè)體生命圖景的立體感悟,實(shí)現(xiàn)了個(gè)人藝術(shù)格調(diào)與民族傳統(tǒng)內(nèi)涵的高度契合,走出了一條飽含生命情感與時(shí)代鋒芒的油畫藝術(shù)語言道路。通過符號學(xué)的視角,切入賈滌非階段性代表作品,揭示其油畫藝術(shù)語言中的符號特征及所含層次關(guān)系,從而探究賈滌非油畫藝術(shù)語言的符號張力與時(shí)代精神。
關(guān)鍵詞:油畫;藝術(shù)語言;符號學(xué);賈滌非
基金項(xiàng)目:本文系黑龍江省省屬高等學(xué)校基本科研業(yè)務(wù)費(fèi)科研項(xiàng)目(145209158)研究成果。
20世紀(jì)以來,符號學(xué)研究已經(jīng)成為一種國際性熱潮,并在21世紀(jì)與以視覺分析為研究對象的圖像學(xué)相結(jié)合,煥發(fā)出新的活力。德國哲學(xué)家恩斯特·卡西爾在《符號形式哲學(xué)》一書中指出,人在一切精神領(lǐng)域中的知識都是符號作用的結(jié)果。語言、神話、藝術(shù)、宗教同科學(xué)一樣,都是以符號來表示的不同類型的經(jīng)驗(yàn)活動。因此,在研究藝術(shù)問題時(shí),尤其在研究油畫藝術(shù)語言時(shí),符號學(xué)視角是始終繞不開的議題。
在我國20世紀(jì)80年代前后興起的一批新生代油畫家中,賈滌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似乎并不急于追趕當(dāng)時(shí)所謂的“藝術(shù)潮流”,而是一直堅(jiān)定地摸索屬于自己的理想化的藝術(shù)道路。其著重強(qiáng)調(diào)藝術(shù)語言自身的形式內(nèi)涵,并以凝固于瞬間時(shí)空的畫面結(jié)構(gòu)、充滿表現(xiàn)意味的色彩基調(diào)和感性使然的筆觸動態(tài)為依托,來表達(dá)自己對現(xiàn)實(shí)生活的深刻感悟與生命本體最真誠的熱愛。
一、“符號”與“符號學(xué)”
“符號”是符號學(xué)的核心概念。中國符號學(xué)家趙毅衡指出,“符號被認(rèn)為是攜帶意義的感知”。其用途是表達(dá)意義,因?yàn)橐饬x必須用符號才能表達(dá)。也就是說,只要一個(gè)事物存在意義,那么它就會成為潛在的符號,并且存在著被感知的可能。法國哲學(xué)家雅克·德里達(dá)曾直言:“不可能有無意義的符號,也不可能有無所指的能指。”譬如,當(dāng)我們提到“紅色”時(shí),首先想到的是熾熱的火焰;如果與國家聯(lián)系起來,那么,首先想到的國家就是中國,因?yàn)椤爸袊t”這一符號概念已經(jīng)通過各種方式深入人心。當(dāng)我們感知到語言“能指”(即語音層面)的同時(shí),就會自然而然地指向與其相對應(yīng)的“所指”(即語義層面)。
“符號學(xué)”一詞最早是由結(jié)構(gòu)主義創(chuàng)始人瑞士語言學(xué)家弗迪南·德·索緒爾在20世紀(jì)初提出,他預(yù)言將有一門專門研究“符號系統(tǒng)”的學(xué)科出現(xiàn),并為其做了初始的理論準(zhǔn)備,創(chuàng)造了語言符號學(xué)模式,提出“二元對立”的符號學(xué)理論。恩斯特·卡西爾率先提出了符號美學(xué)理論。他認(rèn)為,藝術(shù)與其他符號語言一樣,都是人用來把握世界和探究生命存在的一種方式,每一件藝術(shù)品都具有自己獨(dú)特的生命與符號。作為符號美學(xué)代表人物之一,德裔美國哲學(xué)家蘇珊·朗格則將卡西爾的理論進(jìn)一步系統(tǒng)化、具體化,并且將“藝術(shù)是具有表象形式的獨(dú)立符號,即表現(xiàn)情感意義的符號”的論斷作為其整個(gè)藝術(shù)理論的基礎(chǔ)。
二、賈滌非及其符號性油畫藝術(shù)語言的特征
自20世紀(jì)80年代起,賈滌非的油畫藝術(shù)語言便富有符號性特征。在其作品中,出現(xiàn)了大量的“像似符”(icon)、“指示符”(index)和“規(guī)約符”(symbol)。這使其逐漸突破了敘事性的思維邊界,跨越了同質(zhì)化的語言范疇,基于對藝術(shù)本體符號的深刻體悟,創(chuàng)作出一系列富有意象表現(xiàn)與生命意蘊(yùn)的藝術(shù)作品,如《貓冬》《收獲季節(jié)》《陽光·溫泉》《尷尬圖—戲人》《桑拿圖》等,對其后來個(gè)人油畫藝術(shù)語言的形成起到了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
賈滌非符號性油畫藝術(shù)語言的形成,與他對西方現(xiàn)代繪畫藝術(shù)產(chǎn)生的濃厚興趣密切相關(guān)。20世紀(jì)80年代初期,賈滌非在北京第一次看到西方表現(xiàn)主義繪畫時(shí),被那些變幻多端、充滿激情的作品深深震撼。他認(rèn)真地鉆研和探究西方現(xiàn)代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繪畫,并進(jìn)行了大量的創(chuàng)作。這段經(jīng)歷不但成為其日后自我成長的不竭動力,更使其對個(gè)人在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主體的選擇與表達(dá)方式的轉(zhuǎn)變上有了全新的自我認(rèn)知。
賈滌非自覺于符號性油畫藝術(shù)語言的視覺挖掘,通過對表現(xiàn)性符號與象征性符號的深入探索,創(chuàng)造出新的符號形式,擴(kuò)展油畫藝術(shù)語言的空間維度,形成緊湊而開放的語言結(jié)構(gòu)和包容性語言規(guī)范,達(dá)到了意與境渾的藝術(shù)境界,進(jìn)入其個(gè)人油畫藝術(shù)語言系統(tǒng)的新的臨界狀態(tài)。
(一)表現(xiàn)性符號特征
賈滌非在其個(gè)人油畫藝術(shù)語言探索的初期,便表現(xiàn)出強(qiáng)烈的表現(xiàn)主義繪畫傾向,這是他形成表現(xiàn)性符號語言的重要原因。在創(chuàng)作中,他使線條與色彩相互交融,并賦予語言符號形式以一定的表現(xiàn)性特征。同時(shí),隨著其創(chuàng)作成熟期的到來,更加多樣化的符號形式逐漸顯現(xiàn)在他的藝術(shù)語言中。這得益于其對自身藝術(shù)語言系統(tǒng)的深層次挖掘和多維度探索,在不斷豐富精神生活與外部世界聯(lián)系的同時(shí),逐步走向多元系統(tǒng)與自我開放的新形態(tài)。他曾在一次訪談中說道:“畫只是生活的一道痕跡,人性在成長中,會面對現(xiàn)實(shí)的選擇、生態(tài)的選擇,充滿了矛盾和誘惑、挑戰(zhàn)性和極端個(gè)人化的神秘。這些會讓每個(gè)人興奮和迷失。不同時(shí)代、不同的人都在不同斑馬線的交道口上,充分展現(xiàn)千姿百態(tài)的神采。”由此可見,賈滌非一直在藝術(shù)與生命、虛妄與本真、自由與約束、混沌與清靈之間捕捉自身藝術(shù)語言新的增長點(diǎn),不斷創(chuàng)造出契合于自身藝術(shù)語言系統(tǒng)的符號形式,從而獲得富有鮮活生命能量和獨(dú)特精神韻味的藝術(shù)作品。
蘇珊·朗格認(rèn)為,藝術(shù)是一種“表現(xiàn)性形式”,也是一種“情感的‘圖式符號”,能夠讓畫家的語言、精神、情感,跨越時(shí)間與空間的長河與觀者之間產(chǎn)生共鳴,而不必依靠傳統(tǒng)邏輯推理與指示稱謂。賈滌非在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對符號形式的表達(dá)很好地印證了這一點(diǎn)。1986年的《收獲季節(jié)》作為“葡萄園”系列的早期代表作品,全方位地展現(xiàn)出人類情感的復(fù)雜交織,以感性的視覺想象與自發(fā)的情感表達(dá)來詮釋符號在藝術(shù)語言中的表現(xiàn)力。在畫面內(nèi)容上,通過看似無序的筆觸與色塊,將人體結(jié)構(gòu)的力量感與厚重感充分釋放。無論是野蠻生長的葡萄藤,還是兩個(gè)在葡萄藤中辛勤勞作的人,都在不停地向觀眾詮釋著“生命”這一永恒不變的主題,彰顯出一種契合于當(dāng)下時(shí)代的原始生命力。在色彩表達(dá)上,大面積的暖色調(diào)烘托著秋季的熱辣與火氣,少量冷色的點(diǎn)綴使這種炙熱變得可控。賈滌非從不吝惜對純色的應(yīng)用,無論是冷色還是暖色,使色彩充滿表現(xiàn)力的同時(shí)又暗藏著勃勃生機(jī)。
賈滌非十分擅長通過具有表現(xiàn)性的藝術(shù)語言來表達(dá)對外在世界的主觀感受和心靈體驗(yàn)。這種表達(dá)方式使其個(gè)人藝術(shù)語言在符號形式上與創(chuàng)作邏輯緊密結(jié)合,暢快淋漓地表達(dá)個(gè)人內(nèi)在經(jīng)驗(yàn)的矛盾心理與思想情感的變化無常。通過符號將腦海中的精神圖景投射于畫面結(jié)構(gòu)之中,來訴諸一種人類共同情感的直覺意象,并蘊(yùn)含有內(nèi)在生命特質(zhì)的遺傳信息,由此進(jìn)入表現(xiàn)性符號層次結(jié)構(gòu)的心靈世界。1999年創(chuàng)作的《桑拿圖——兩個(gè)男人·B》中運(yùn)用了大量的橘色與紫色,讓觀者承受強(qiáng)大視覺沖擊的同時(shí),又將空間情景置身于“潮濕”“火熱”的色彩限定中,這在以往的作品中是從未出現(xiàn)過的。撲面而來的蒸騰感似乎在灼燒著每一個(gè)靈魂,兩個(gè)皮膚已經(jīng)呈現(xiàn)出紫紅色的裸體男人,雙手扶膝,端坐在因木炭炙烤而不斷升溫的長凳上。此時(shí),仿佛汗液在皮膚的每一個(gè)毛孔處凝結(jié)、滴落,蘊(yùn)含在人體內(nèi)蓬勃的生命能量也在一刻不停地涌動著,色彩的強(qiáng)烈表現(xiàn)力在此刻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畫面中所承載的空間已經(jīng)被赤黃色的光暈所籠罩,使得觀者的視線無法逃離這令人窒息的空間,沉浸于這一充斥著情感風(fēng)暴的畫面視覺效果之中。
德國哲學(xué)家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在《美學(xué)》一書中說道:“遇到一件藝術(shù)作品,我們首先見到的是它直接呈現(xiàn)給我們的東西,然后再追究它的意蘊(yùn)或內(nèi)容。前一個(gè)因素——即外在的因素——對于我們之所以有價(jià)值,并非由于它所直接呈現(xiàn)的;我們假定它里面還有一種內(nèi)在的東西,即一種意蘊(yùn),一種灌注生氣于外在形狀的意蘊(yùn)。”賈滌非在創(chuàng)作中對畫面整體氛圍的營造、對繁復(fù)細(xì)節(jié)的把控、對符號形式的運(yùn)用,均體現(xiàn)出蓬勃的生命意蘊(yùn)。他將符號作為精神內(nèi)涵的載體,將視覺經(jīng)驗(yàn)、社會文化與審美素養(yǎng)轉(zhuǎn)化為可視可感的客觀的外在符號形式,最終構(gòu)成一種有機(jī)的表現(xiàn)性情感生命體。
(二)象征性符號特征
所謂象征性符號,即強(qiáng)調(diào)畫面主觀存在的內(nèi)在情感,將畫家引向多層次的精神空間、抽象的形式風(fēng)格、強(qiáng)烈的主觀色彩及神秘的意境表達(dá),具有明確性或是含蓄性,并有其獨(dú)特的審美標(biāo)準(zhǔn)與價(jià)值體系,是畫家與觀眾情感交流的中介。趙毅衡教授認(rèn)為,“藝術(shù)家有意讓一個(gè)形象多次出現(xiàn),重復(fù)著力表達(dá),也可能獲得意義更深遠(yuǎn)的象征意義。這實(shí)際上是藝術(shù)家自己進(jìn)行重復(fù)”,從而賦予符號以特殊的象征性內(nèi)涵。
賈滌非藝術(shù)語言的層次結(jié)構(gòu)的重要構(gòu)成元素是象征性符號化語言結(jié)構(gòu)。他的油畫語言超脫于物性語言之外,在理性與情感的碰撞中實(shí)現(xiàn)對事物隱喻意義的表達(dá)。他將記憶中厚重的文化精神凝結(jié)為具有象征性的符號形式,并且讓每一個(gè)象征符號(果實(shí)、舞臺、人體等)在藝術(shù)語言中有效地發(fā)揮作用,從而達(dá)到對深層次意義內(nèi)涵(警告、界限、欲望等)的完整表達(dá)。在傳遞畫家自我感受的同時(shí),也為觀眾留下了思考與困惑、執(zhí)著與迷離、自由與羈絆等一種具有多義性的、荒誕的自由聯(lián)想空間。當(dāng)我們探索畫面中符號象征意義的同時(shí),能夠感受到畫面整體具有一種別樣的協(xié)調(diào)感與舒適感,這種感覺來源于其將自身精神領(lǐng)域的構(gòu)想轉(zhuǎn)化為具有象征性精神內(nèi)核的符號語言形式。
從語言表現(xiàn)上看,賈滌非巧妙地從西方現(xiàn)代藝術(shù)中吸納養(yǎng)分,并與本民族文化藝術(shù)傳統(tǒng)精華相連接,關(guān)注人在當(dāng)下歷史與社會背景下的生存環(huán)境與精神狀態(tài),在秩序與非秩序的動態(tài)之間找到自身的平衡點(diǎn)。2010年的《尷尬圖—鸜》,畫面分為左右兩部分。其中,左半部分是一位身材魁梧的戲曲人物,右半部分則是一位裸體的妙齡女子,中間是一只紅色的狐貍,并且在圖像的各處分別寫有不同的文字。這幅作品中的人物、靈怪、花朵等圖像與“藍(lán)”“疑”“鬢”等文字的象征性意義內(nèi)涵,已然成為互為關(guān)聯(lián)的補(bǔ)充要素與解釋屏障,共同反映出當(dāng)下人們在自我的世界和自身的性情中捕捉內(nèi)在生命的變化。
賈滌非一直以一種極具表現(xiàn)意味的主觀化藝術(shù)語言,將畫面中符號形式的象征涵義加以縱向延伸。采用一種近似于涂鴉式的繪畫手法,將繁復(fù)龐雜的線條與色彩融入畫面中,再將其想要表達(dá)的重點(diǎn)加以強(qiáng)調(diào),這使其油畫語言的層次結(jié)構(gòu)更為精煉,同時(shí),象征性符號形式的內(nèi)涵與外延也得到進(jìn)一步拓展與豐富。雖然“鸜”作為這幅作品的名字,也是主要象征符號之一,但在畫面中所占據(jù)的比例并不多,而是作為視覺要素隱含在整體的符號形式中,與其他象征符號互為主體,共同架構(gòu)起整體的空間意識及表現(xiàn)形態(tài)。畫面中線條的長短、粗細(xì)、虛實(shí),都在有節(jié)奏地變化起伏著,猶如萬物在生長中凝結(jié)而出的生命律動,其中暗含著以生命為整體的大宇宙生命觀,使人自身具有了更為純粹的生命意蘊(yùn)。賈滌非通過象征性符號自覺地將觀者對符號形式的解讀引申到其背后所蘊(yùn)含的人類文化世界的上下文之中。他將視角聚焦于生命及其價(jià)值之上,通過借有形寓無形、借有限寓無限、借一時(shí)寓永恒的藝術(shù)語言表達(dá),傳遞出一種精神性的超脫感與歸屬感。
三、結(jié)語
賈滌非以其獨(dú)特的視覺經(jīng)驗(yàn)、審美意識和直覺能力,將“人”和“物”分別作為其藝術(shù)語言中符號形式的兩大結(jié)構(gòu)支撐點(diǎn),這使得個(gè)人主觀情感“投射”于符號之上,傳遞出對心靈本真與生命自性的回歸與熱愛,呈現(xiàn)一種與主體精神相契合的獨(dú)特視覺韻味。在藝術(shù)語言的表達(dá)上,充分地實(shí)現(xiàn)了其個(gè)人審美趣味在特定的語言結(jié)構(gòu)中對符號形式的組織與運(yùn)用。他從早期對西方表現(xiàn)主義和抽象主義繪畫手法的借鑒中開辟創(chuàng)作路徑,到后期從東方傳統(tǒng)藝術(shù)文化內(nèi)涵的體悟中認(rèn)定表意方向,將自身藝術(shù)語言中符號形式的表達(dá)上升到人類共同的情感維度,呈現(xiàn)出應(yīng)有的內(nèi)在精神訴求與生命特質(zhì)。賈滌非借助與符號形式緊密結(jié)合的藝術(shù)語言(這種藝術(shù)語言的產(chǎn)生不是由簡單的中西結(jié)合所得來的),表達(dá)出對眾多異質(zhì)性文化的包容與取舍,以及對人類共同生命情感自發(fā)性的理解與頓悟。通過對生活中的點(diǎn)滴及周遭事物的感性體驗(yàn)和長期的沉淀,他的語言意識得到了充分覺醒。這種覺醒是深層次的,是在直覺與邏輯、理性與情感、歷史與現(xiàn)實(shí)的臨界中達(dá)到微妙平衡的。即便當(dāng)代藝術(shù)百舸爭流,賈滌非始終堅(jiān)守自己的藝術(shù)理想,不斷追求更高的藝術(shù)境界,并試圖以一種更加接近于人類生命本質(zhì)的藝術(shù)語言在畫面中呈現(xiàn)。這些特質(zhì)匯集于他不斷成長的藝術(shù)語言之中,顯得龐雜而又精純。
參考文獻(xiàn):
[1]趙毅衡.符號與物:“人的世界”是如何構(gòu)成的[J].南京社會科學(xué),2011(2):35-42.
[2]德里達(dá).聲音與現(xiàn)象[M].杜小真,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99.
[3]朗格.藝術(shù)問題[M].滕守堯,朱疆源,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83.
[4]孫欣.真意無語:“行進(jìn)中的繪畫”展訪談錄之賈滌非[J].中國油畫,2009(2):7-12.
[5]黑格爾.美學(xué)[M].朱光潛,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79.
[6]趙毅衡.符號、象征、象征符號,以及品牌的象征化[J].貴州社會科學(xué),2010(9):4-10.
作者簡介:
耿琨博,齊齊哈爾大學(xué)美術(shù)與藝術(shù)設(shè)計(jì)學(xué)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繪畫藝術(shù)。
胡玉森,碩士,齊齊哈爾大學(xué)美術(shù)與藝術(shù)設(shè)計(jì)學(xué)院教授。研究方向:意象油畫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