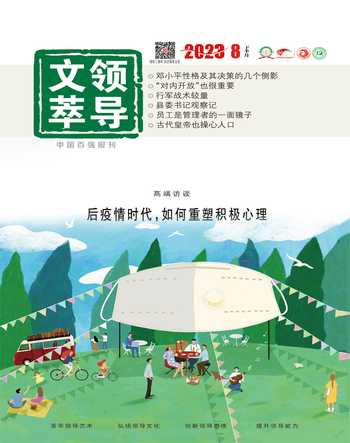“均勢”操盤手
田亮 隋坤
1968年,基辛格幫助共和黨人、洛克菲勒家族的二公子納爾遜·洛克菲勒競選美國總統。盡管洛克菲勒輸掉了黨內初選,但基辛格的外交才華以及多年來積攢下的外交人脈,被最終贏得大選的共和黨新總統尼克松看在了眼里。尼克松決定,讓基辛格出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為談判桌的形狀吵了3個月
1961年,冷戰達到新的高潮,柏林墻開建,美國與古巴斷交,肯尼迪派特種部隊進入越南,蘇聯也向越南提供軍事援助。打不下去怎么辦?1969年上任之初,基辛格就以名校教授的氣派拿出了解決越南問題的5種可能方案,國防部長萊爾德支持加快撤軍,同時裝備和訓練南越人,讓他們自己去打仗,即“越南化”。國務卿羅杰斯覺得搞“越南化”太浪費時間,通過談判迅速脫困才是正道。基辛格的意見與羅杰斯大體一致,他對南越的軍事能力和政治上的穩定性沒有信心,覺得外交途徑才是唯一可行的出路。
外交正是基辛格的老本行。他認為可以說服蘇聯領導人幫助結束戰爭,因為他得到消息,蘇聯領導人希望戰爭和平解決。他還察覺到北越對談判也抱有積極態度。
他與北越代表在巴黎的和談從1969年開始,卻遲遲不見成果。一個例子可以說明談判的難度:僅對談判桌的形狀應該是四邊形還是圓形,就進行了長達3個月的爭吵。不過,雙方都想早點結束戰爭,不管吵得多兇,總能回到談判桌。在斷斷續續的談判中,雙方逐字逐句商定協議文本,付出了很大精力。
基辛格的外交方案不只有一張談判桌。“沒有平衡,就沒有和平;沒有節制,就沒有公正。”這是他終身信奉的均勢理論。而平衡和節制的力量,在越南戰場之外——美國必須先跟中國、蘇聯達成和解。
1972年2月,在基辛格的鋪墊下,尼克松成功訪華,開啟中美關系破冰之旅。3個月后,同樣是在基辛格先行做好訪問的鋪墊下,尼克松訪問了蘇聯。美蘇關系實現緩和,越南問題就更好談了。
1972年10月9日,雙方談了16個小時,第二天又談了16個小時。經過兩次密集會談,很多分歧得到解決。第三天,雙方繼續談,并就一些具體問題討價還價。
就這樣,基辛格和對方反反復復談了近4年,直到1973年1月23日,經過數十次談判之后,雙方簽署了《關于在越南結束戰爭、恢復和平的協定》。兩年后,戰火徹底熄滅。
越南戰爭是美蘇冷戰中為數不多的一次“熱戰”。這是美國在冷戰期間一次很大的戰略敗筆,基辛格在幫助美國撤出越南的戰略決策和外交執行中都起了比較關鍵的作用。
“國務卿”變成“世務卿”
1973年10月6日,基辛格兼任國務卿之職才兩周,埃及和敘利亞同時向以色列發起進攻,分別攻擊6年前被以色列占領的西奈半島和戈蘭高地,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戰爭初期,埃及和敘利亞軍隊重創以軍,粉碎了以色列“不可戰勝”的神話。
沙特阿拉伯等石油國家為支持阿拉伯兄弟,以石油為武器加入斗爭,提價、減產,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石油價格由每桶3美元上升到1973年底的每桶11.6美元。
接著,產油國又對一味支持以色列的美國實行全面石油禁運,導致其國內生產總值出現萎縮,美元的地位也受到極大沖擊。石油危機又進一步引發了戰后西方世界的經濟危機。
此前的3次中東戰爭,均以以色列取勝告終。美國決策者們一度認為,只要在中東保持以色列的軍事優勢,就能遏制支持阿拉伯國家的蘇聯在中東擴張,保持中東穩定。這種判斷顯然失靈了。基辛格意識到,如果不迅速調整美國的中東政策,“阿拉伯國家就會被趕回到蘇聯人的懷抱,石油就會喪失掉,全世界都會反對我們,在聯合國將沒有一個國家投票贊成我們”。
石油很重要,而穩定獲得石油的方式就是保持中東的均勢。尼克松和基辛格重新制定了中東政策:美國將推進阿以沖突和平解決,放棄全面偏袒以色列的立場,促使以色列在領土上作出讓步,發展與阿拉伯國家關系,從而使美國在中東起支配作用。
任務很明確,基辛格一方面要撮合阿拉伯人和猶太人達成協議;一方面又要勸說沙特阿拉伯及其他石油國解除對美石油禁運。他打算各個擊破。隨著一次次穿梭外交的開展,美國在阿拉伯國家的影響力迅速擴大,石油禁運也得以解除。
在基辛格的斡旋下,這次和解成了中東現代史、阿以沖突和美以特殊關系的重大轉折點,美蘇在中東的實力對比發生顯著變化。有些美國人說,基辛格已然不是“國務卿”,而是“世務卿”了。
“露骨的威脅”
冷戰期間,美蘇力量處在此消彼長的變化中,一旦有外力幫助一方,這臺微妙的天平就會傾斜。
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后,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坐不住了。他感到,應該盡快行動,緩和與美國關系,否則就被中國占了先機。
打前站的任務又落到基辛格頭上。對于這份差使,基辛格很樂意接受。尼克松剛剛當選時,基辛格就向他闡述了與蘇聯“緩和”的主張,以期在一個美國、歐洲、蘇聯、中國和日本五大力量中心相互制衡的世界中,約束蘇聯行為。
待抵達莫斯科后,一個快得嚇人的車隊幾乎是以100英里的時速把基辛格一行送到賓館。第二天上午,不用基辛格動身,勃列日涅夫親自來拜會基辛格。
基辛格感到,勃列日涅夫似乎有點緊張,把手表轉來轉去,這可能是因為他初次同美國高級官員打交道。勃列日涅夫給基辛格講了一個故事作為開場白:從前有一個旅行者想從一個村莊去另一個村莊,但不知道距離有多遠,就問路旁一名樵夫,到達目的地需要多久。樵夫說,不知道。旅行者無奈,只好繼續沿路前行。可當他走了幾步后,樵夫大聲喊道:“你大約需要走15分鐘。”
“你為什么剛才不告訴我呢?”旅行者問道。
“因為我當時不知道你一步有多大。”樵夫說。
基辛格明白了,勃列日涅夫講這個故事,意思是說在談判中要跨大步。基辛格說:“我們同樣希望兩國關系能取得重大進展,但這取決于雙方的努力。”勃列日涅夫急切盼望即將到來的美蘇峰會成功舉辦,說道:“我們一定會達成幾個協議的,我很有信心。”
顯然,基辛格在這次對話中占了上風,順勢把越南牌打了出來。基辛格說:“北越的攻勢威脅到了即將舉行的最高級會談,因此防止北越的勝利同樣符合蘇聯的利益。如果我們吃了敗仗,我對尼克松總統還能到莫斯科來表示懷疑。即使到時候戰爭還未分出勝負,美國人民也知道是蘇聯的武器才使北越得以發動攻勢,總統的活動余地可就有限了。”
在基辛格印象中,對于這“比較露骨的威脅”,勃列日涅夫沒有爭辯,避開了這個話題,可見他是多么想開成這次最高級會談。
5月22日,美國總統尼克松的專機抵達莫斯科。基辛格對尼克松興奮地說:“這應該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一次外交成就。”
“二戰后美國最有影響的戰略家之一”
早在1957年,年僅34歲的哈佛大學講師基辛格就出版了人生第一本書《核武器與對外政策》,敏銳地寫道,憑借戰略核力量對敵人大規模報復的戰略,由于對方也擁有核報復能力而行不通了,必須以有限戰爭作為全面核戰爭之外的選擇。這本書一經出版,迅速成為暢銷書。1972年這次訪蘇,正是他把理念付諸實踐的絕佳時機。
1972年5月26日,經過拉鋸式談判,兩國領導人簽署了《反彈道導彈條約》和《凍結進攻性核武器臨時協定》。《反彈道導彈條約》被視為全球戰略穩定的基石,在冷戰期間發揮了重要作用。直到2001年,美國總統小布什宣布退出該條約。
基辛格一生中發揮作用最大的是在冷戰時期,一是促使美國和中國和解,二是緩和美蘇關系,這有利于世界的穩定、和平與發展。他就像一位操盤手一樣,影響著世界局勢的走向。
(摘自《環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