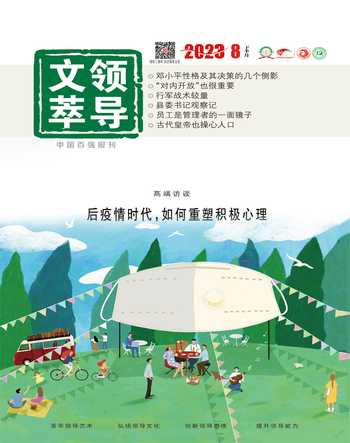師友到主奴:中國古代的君臣關系
李競恒
在清皇帝看來,士大夫與天子共治的聚議不過是“庸主”所為,只有乾綱獨斷的皇權才是正道。但它并不是中國歷史的常態。
夏商周的貴族制時代,君臣多為一個家族的成員,如商代甲骨子組卜辭、午組卜辭的主人就是商王的兄弟或堂兄弟。周代宗法制下,嫡長子為君,庶子為臣,君臣即兄弟。殷周時期的君臣關系,籠罩在親人血緣溫情脈脈的氛圍之中,并無后世“尊君卑臣”的現象。當時君臣之間是一種相對概念,臣在自己領地上也是君,所以“一個國家內存在著不同層次的眾多君主”。貴族政治下的君臣共治,“堪與羅馬帝國以前的共和時代媲美”。
春秋時代禮崩樂壞,傳統以血緣凝聚的小共同體社會瓦解,人員流動加速,陌生人之間互相選擇成為君臣。郭店楚簡《語叢》就提到“君臣、朋友,其擇者也”,《父無惡》:“友,君臣之道也”,將君臣和朋友視為一倫。“朋友”一詞在西周金文中指有血緣關系的兄弟或堂兄弟,商周時代朋友(血緣親人)就是君臣,東周陌生人社會,“朋友”成為非血緣的友誼,君臣之間像建立朋友關系一樣互相選擇。除了朋友一倫外,戰國時代的君主也會將士人尊為老師或賓客,《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記載魏惠王以“賓主之禮”待鄒衍,燕昭王待之以老師之禮,自居弟子行列。
法家及道法家主張尊君卑臣,以實現耕戰機器的最高效率。韓非子最早提出“三綱”,所謂“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管子·明法》《鹖冠子·天則》中也都提出“尊君卑臣”之說。以法家立國的秦始皇自稱“大圣”,朱熹就談道:“至秦欲尊君,便至不可仰望。抑臣,便至十分卑屈”。漢承秦制,行尊君卑臣之法,叔孫通制朝儀令群臣震恐,朱熹就看破了這繼承的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
漢雖繼秦制,但董仲舒提出“屈君而伸天”之說,以天命災異抑制非理性的君權,而漢代公羊學也有“貶天子”“君臣朋友”之說,《韓詩》亦提倡天子以士人為師、友。隨著漢代復古更化的進程,君臣關系出現了某些向先秦的回歸,如《漢書·禮樂制》記載漢明帝“養三老五更于辟雍”,顏師古解釋這是天子以尊父親的禮敬養三老,以尊兄長的禮侍奉五更。其后三國至南北朝,亦有天子尊養三老五更大臣之禮。
漢晉之際,并非皇帝一人才是君,郡守長吏與其屬下之間也屬于君臣關系。趙翼談到,三公、刺史、二千石的大臣可以自己招募屬下,所以他們之間有君臣的關系,“雖帝王不禁也”,錢穆認為郡太守也稱君的習慣,屬于“古者諸侯封國自專之遺意”。不但郡守可以稱君,縣令也稱君,如《華陽國志》卷十記載嚴道縣的主簿就將縣令稱為“我君”。整個漢晉之際部分重建了先秦封建遺意的君臣關系,并非皇帝一人才是君,君臣關系具有相對性。
晉朝以后至唐,君主大多情況下不稱呼大臣之名,而是稱呼平等身份的“字”,以示尊重,顧炎武曾列舉南北朝、隋唐時期多個例子,認為“其時堂陛之間未甚闊絕,君臣而有朋友之義,后世所不能及矣”。
宋代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君主與士大夫之間多處于賓客、師友之間,如葉適描述孝宗與宰相史浩之間的關系是“以師以友”;王安石則認為大臣應當與天子“迭為賓主”,神宗則將其尊為“師臣”;馬永卿記劉安世《元城語錄》中也說王安石“與人主若朋友”;梅堯臣《太師杜公挽詞》:“國佐三公進,師臣一品歸”,也是以“師臣”描述大臣太師;至南宋末期度宗亦尊賈似道為“師臣”。
遼金元的部族傳統重視主奴關系,將大臣視為私屬奴婢,多有鞭笞臣下之事,元朝大臣上奏亦多見自稱“奴婢”的現象。明朝在此基礎之上創制廷杖,并廢除宰相中書,皇權獨大,但終以士大夫文官集團與皇帝的僵持對抗而漸至消磨。清皇權高熾,“惟以一人治天下”,以君師合一自詡,決不允許出現“師臣”“賓友”之類大臣,并輔以密折制度使諸臣相互告發。乾隆仇視宋明體制下的君臣聚議:“設不斷以乾綱,如宋明庸主,遇事輒令廷臣聚議,眾論紛紛,迄無定見,征調紛繁,緩不濟急”,在清皇帝看來,士大夫與天子共治的聚議不過是“庸主”所為,只有乾綱獨斷的皇權才是正道。這個畫面,也就是我們熟悉的清宮劇了,但它并不是中國歷史的常態。
(摘自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