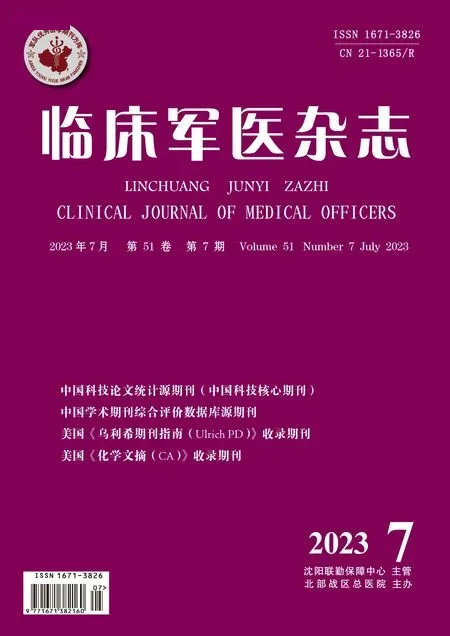圍術期急性腎損傷評估預警研究進展
羅紫月, 周瑞豪, 郝學超, 陳 果, 朱 濤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 麻醉手術中心,四川 成都 610000
圍術期急性腎損傷(acute kidney injury,AKI)與短期發病率、病死率及包括慢性腎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發展在內的長期不良結局相關。在術后器官功能障礙方面,以AKI尤為突出,占高危患者的20%~40%。有研究表明,即使腎功能輕微下降,也會導致死亡增加及住院時間延長[1]。AKI的持續時間及相關合并癥對預后具有重要意義。有研究表明,患有術后AKI的高血壓患者在擇期行非心臟手術5年后,發生致命性中風、心肌梗死及猝死的風險均顯著增加[2]。風險預測模型、新型生物標志物等方面的研究為圍術期AKI的評估預警提供了新的思路[3]。本文圍繞圍術期AKI的定義、診斷標準、危險因素、預測預警進行綜述,以期提高臨床醫師對圍術期AKI的認識,早期識別高風險患者,最大限度地改善手術患者的結局。
1 圍術期AKI定義及診斷標準
圍術期AKI是指在手術期間或手術后發生的以急性腎小球濾過率減少為主要特征的臨床綜合征。目前,AKI的診斷和分期主要依據血清肌酐升高值和尿量減少量。常用的AKI診斷標準包括急性透析質量倡議(risk,injury,failure,loss,end-stage renal disease,RIFLE)標準、急性腎損傷網絡(acute kidney injury network,AKIN)專家組的診斷指南,以及改善全球腎病預后組織(kidney disease:improving global outcomes,KDIGO)的診斷指南[4]。RIFLE標準于2004年發布,取消了“急性腎衰竭”一詞,引入了“急性腎損傷”以表示急性情況的可逆性。RIFLE 標準根據血清肌酐相對于基線的變化和尿量進行分級,同時區分了嚴重程度和結局類別。但是,RIFLE分類存在局限性,低估了小幅度肌酐變化對病死率的影響。為了提高敏感性,AKIN專家組在2007年對RIFLE標準進行了修改,降低了AKI的診斷門檻。2012年,KDIGO任務組整合了RIFLE標準、AKIN標準和兒科RIFLE標準,提供了一個統一的定義,根據血清肌酐的急性增加或尿排出量分為不同階段[2]。基于目前診斷方法的局限性,近年來,許多研究致力于尋找與AKI潛在病理生理過程相關的新型生物標志物,幫助早期識別并診斷AKI[5]。但是,預防和逆轉AKI仍缺乏可靠的方法。
2 圍術期AKI評估預警
2.1 術前危險因素識別
2.1.1 患者基本特征 患者的基本特征中存在多個與圍術期AKI風險增加相關的因素,包括性別、高齡、肥胖、術前高血壓、術前貧血、術前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活動性充血性心力衰竭、已知的腎功能障礙、肺部疾病、胰島素依賴型糖尿病、周圍血管疾病等[6]。其中,術前肌酐水平升高(超過1.2 mg/dl)是心臟和非心臟手術患者術后AKI的顯著預測因子[7]。肥胖患者手術中AKI的發病率約為6%~8%,主要原因為肥胖造成機體的氧化應激、促炎性細胞因子和內皮功能障礙,從而導致AKI發生[8]。
2.1.2 術前藥物使用 圍術期患者常使用具有潛在腎毒性的藥物及靜脈造影劑,因此存在間質性腎炎和急性腎小管損傷的風險。抗高血壓藥物,特別是血管緊張素轉化酶抑制劑(ace inhibitors,ACEI)和血管緊張素Ⅱ受體拮抗劑(angiotensin Ⅱ receptor blockers,ARBs),在手術前24 h通常會停用,因為其持續使用與術中低血壓風險較高相關[9]。但最近的研究認為,在普通外科患者中停用ACEI或ARBs,未顯示出對術后AKI的保護作用[10]。鑒于許多患者使用ACEI或ARBs既具有心臟保護作用又具有腎保護作用,臨床醫師應該根據個體情況分析圍術期持續使用這些藥物的風險與益處,且術后是否重新開始使用也應進行個體化決策。
2.2 術中危險因素識別
2.2.1 手術因素 手術中存在有效血容量減少或機械性阻塞的風險,可能導致腎受損。急診手術、大血管手術(尤其是心臟手術)、腹腔內手術和特殊類型手術(如移植手術)與AKI的風險密切相關。心臟手術相關的AKI機制多樣,體外循環是重要的危險因素之一,持續時間越長,風險越高。AKI在心臟手術中發生率為10%~30%,在體外循環手術中高達50%[11]。而接受腹腔內手術的患者,特別是剖腹探查和小腸切除的患者,更容易發生AKI[12]。肝移植術后AKI發生率為17%~95%,其中肝硬化、免疫抑制藥物的腎毒性及手術自身風險均是造成AKI高發的危險因素[13]。肺移植術后AKI發生率為54%,雙肺移植AKI發生率更高,術中缺氧是其影響因素之一[14]。
2.2.2 麻醉因素 麻醉方法對術后AKI的發生率具有影響。維持血容量和術中血流動力學穩定是減少術后AKI發生的關鍵。術中低血壓可能與全身麻醉和局部麻醉技術的血管擴張、靜脈擴張效應有關,以及與術前禁食導致的相對血容量減少有關。目前,尚缺乏共識認為哪種麻醉方法能顯著降低術后AKI的發生率。無論是局部麻醉還是全身麻醉,聯合麻醉還是單獨使用靜脈或吸入麻醉,所有方法均與相對靜脈擴張和術中低血壓相關[15]。有研究發現,在心臟手術中聯合使用硬膜外麻醉和全身麻醉可以減少AKI的發生[11]。吸入麻醉劑和異丙酚在實驗研究中可能對AKI具有一定的保護作用,但在人體研究中尚未得到證實。而一些鹵代麻醉藥物(如甲氧氟烷),被認為具有腎毒性,已不再常規使用[16]。
3 基于預測模型的評估預警
風險預測模型通常采用獨立預測因子,如基線特征(年齡、估計腎小球濾過率、血清肌酐、是否患糖尿病等)的組合,并為這些因子分配相對權重,以預測臨床結局。目前,雖然臨床已開發了多個風險預測模型,但許多模型使用的是較舊的AKI定義,或僅在特定外科亞專業中驗證[17]。許多模型在臨床上未得到廣泛應用,且通常難以區分不同程度的AKI。因此,為了增加預測的準確性,往往需要在模型中考慮術中或術后因素,但這可能導致預測結果在患者治療過程的較晚階段才能得出,而此時實施保護性策略的機會較少[18]。該領域的研究仍在不斷發展中,在基于傳統臨床評分的情況下,新的評分系統已經應用了多種方法來提高預測性能。這些方法包括添加新的生物標志物、基于實驗室測試和利用機器學習技術構建預測模型,這些評分系統的診斷準確性在70%~85%[4]。
由于AKI在重癥患者中的發病率較高,預測AKI的風險也在重癥監護環境(包括ICU住院)中進行了廣泛的研究。Malhotra等[19]報道了ICU中AKI風險預測模型,并使用10個臨床變量進行了外部驗證。Kashani等[20]對ICU患者進行研究,測試了新型尿液生物標志物組織抑制劑金屬蛋白酶2(tissue inhibitor of metalloproteinases 2,TIMP-2)和胰島素樣生長因子結合蛋白7(IGF-binding protein 7,IGFBP7)對AKI的預測價值,并提出了一種預測AKI風險的臨床模型,結果表明,新的生物標志物可以提高早期重癥監護預測模型的穩健性。曾智賀等[21]利用機器學習模型,通過隨機森林集成學習算法等建立了關于非心肺轉流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相關的急性腎損傷(OPCABG-AKI)預測模型,結果顯示,術中尿量等指標與OPCABG-AKI關系十分密切。但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數據多來自回顧性研究,仍需要進行更大規模、多中心和前瞻性的研究,以進一步探索這些評分系統在不同臨床場景和情況下的有效性。這樣的研究將有助于提高AKI風險預測模型的可靠性和適用性,為臨床醫師提供更準確的預測工具。
4 基于生物標志物的預測預警
血肌酐和尿量是在AKI過程中較晚發生變化的指標。鑒于尿量和血清肌酐在術后AKI識別方面的局限性,許多研究致力于尋找與AKI潛在病理生理過程相關的新型生物標志物,早期識別AKI高風險患者,避免對無腎實質損傷的患者進行不必要的干預。中性粒細胞膠原酶相關脂聯素(neutrophil gelatinase-associated lipocalin,NGAL)是最初有希望的生物標志物之一。但后續數據顯示,NGAL水平不僅在AKI發展中升高,還在其他慢性和急性炎癥情況下升高[22]。因此,有學者建議,在針對腎特異性的NGAL測定方法可用之前,不應使用NGAL[23]。除NGAL外,與腎小管G1細胞周期阻滯相關的生物標志物,如TIMP-2和IGFBP7已被證明是AKI的獨立預測因子[24]。免疫測定方法“NephroCheck”用于測量尿液中這些生物標志物的濃度,已獲得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的批準,并在多項研究中得到應用[1]。
多項研究探索了多種生物標志物的組合應用。有研究同時采用NGAL和腎損傷分子-1預測AKI,結果顯示,預測效果良好(P<0.002)[20],但仍需要進行更大規模的研究來驗證結果。此外,有研究在接受心臟手術的患者中探索與慢性腎小管應激和CKD進展相關的尿液Dickkopf-3(DKK3)標志物,發現術前尿液中DKK3/肌酐比值升高的患者術后AKI風險顯著增加,且與出院時及隨訪820 d后的腎功能下降密切相關[25]。此外,可溶性尿激酶型纖溶酶原激活物受體(soluble urokinase plasminogen activator receptor,suPAR)水平與AKI的風險呈正相關。動物模型研究顯示,suPAR可能通過調節細胞生物能量和增加氧化應激,直接參與AKI的發病機制[26]。此外,N末端腦鈉肽前體在術前風險分層中也顯示出潛力[5]。這些新型生物標志物的發現對于臨床試驗的設計具有重要意義,有助于評估新型治療方法的療效。但將生物標志物納入常規實踐之前,仍存在許多障礙需要克服。
5 小結
早期診斷AKI對手術患者的康復和預后具有重要意義。目前,臨床常用尿量減少和血清肌酐增加作為AKI的診斷指標,但仍需尋找更早期和更準確的生物標志物來提高診斷的準確性。預防和治療AKI的策略需要綜合多種方法。風險評估是關鍵步驟,可通過評估年齡、性別、基礎腎功能、合并癥和手術類型等因素來識別高危患者。術中麻醉和手術共同影響腎功能,需要特別注意手術過程中的液體管理和血流動力學監測等。同時,避免腎損傷的因素也應得到關注,如減少使用腎毒性藥物并控制血壓等。未來的研究應進一步完善風險評估系統,如基于一致的數據采集、結合人工智能技術,利用新的生物標志物,并考慮臨床實際情況,實現有效的AKI風險預測模型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