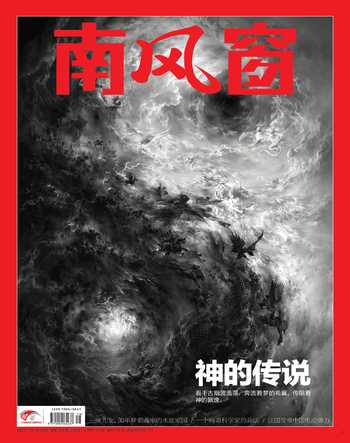互聯網人類觀察愛好者指南
祖曉謙

董晨宇在所有社交媒體的簽名檔,都是“互聯網人類觀察愛好者”。
作為一名研究社交媒體和數碼人類學的學者,董晨宇本著“傳播學不傳播自己是個奇怪的悖論”的想法,躬身入局,2006年注冊豆瓣賬號“mlln”同7萬多位友鄰交往,2019年開始在微博分享研究日常,今年4月底開箱B站10萬粉絲獎牌,親自成為了一名跨平臺的“網紅”老師。
平臺社會是董晨宇關注的重要議題。當下越來越多的互聯網服務以平臺的形式出現,人際交往、內容創作、外賣、網約車……數字技術從線上滲透到線下,平臺成為了日常生活的基礎設施,逐漸改變著社交方式、勞動關系乃至社會結構。技術發展會帶來“破壞性的創新”,也會帶來“創新性的破壞”,我們身處其中,時常是技術的受益者,也時常是創新的代價。
2023年7月初,我在一個人類學圓桌論壇上見到了董晨宇,他剛剛結束自2020年3月開始的秀場主播田野調查,在5位女主播的直播間內做了一年房管,并正在與合作者籌備《做主播》一書的出版;他同時也合作進行了對外賣小哥與網約車司機的研究,試圖理解職業被平臺化之后的個體命運。新的學術譯作《平臺與文化生產》也于日前交稿。
他在微博記錄了自己走入田野的想法:“去進入這個社會的巨輪內部,尋找因摩擦而疼痛的一顆顆齒輪。研究者應該與宏大的贊嘆保持距離,去觸摸堅硬、感受冰冷、傾聽疼痛,讓理所當然的被重新質詢,讓消失不見的被重新看見。”
以下是南風窗與董晨宇的對話。
直播界的耶路撒冷
南風窗:我們先從你與團隊的田野調查說起,在調查中,你有哪些有趣的見聞和洞察?平臺怎樣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董晨宇:我想先分享一個對網約車司機的觀察。我跟司機聊天,問他們有什么變化,他們說以前年紀越大掙得可能越多,因為知道每個時間段哪兒的活兒多,就去哪兒趴活兒。但是平臺到來之后這些經驗大多沒有用了,因為去哪兒不是他們選,而是平臺派單決定,算法驅動了相遇。這種去技能化,讓這個行當最終變成拼體力,越年輕的反而干得越好。
10年前我在街上打車用的是招手的方式,北京的出租車司機都有一個“特異功能”,他們可以邊安全駕駛邊用余光瞟向路邊看誰需要服務,甚至你都還沒招手,他都能從你的眼神中判斷出你要打車。但現在這個能力并不重要了,平臺崛起讓我們和司機連接在一起,但同時平臺也在拒絕從前那種招手的非中介化的連接。平臺宣稱的連接是高度偏向的,讓人們的相遇越來越依賴于技術中介。
再說外賣小哥,外賣小哥跟網約車司機一樣,也是連接了服務的提供者和需求者。我們之前一直將網絡看作另一個世界,但像外賣這種數字產業正以物質性的方式改變我們現實生活中的交通狀況,比如外賣小哥的電動車,在平臺對送餐時間的控制之下,幾乎所有的外賣員都會進行改裝,讓電動車提速超過每小時25公里的國標,或是更換續航能力更強的超標電池,檔口等待的外賣員、路上飛馳的電動車,徹底改變了我們街區的景觀。
南風窗:說到現實的景觀,我想起你今年去長沙的“直播界的耶路撒冷”朝圣,還試著在那兒開直播。
董晨宇:是長沙的黃興廣場,很魔幻現實主義的地方,我走在那里,簡直像愛麗絲夢游仙境。你會發現,這邊三個小姐姐突然跳著舞過來,那邊一個大叔舉著自拍桿對著手機喊“最后30秒家人們眾籌我們一起打他”,他們是在PK。再往深處走有一個麥當勞,從晚上11時開始,就會有男女主播聚集在一起,直播到早上5時。為什么選中了這個偏僻的麥當勞?當地人告訴我,是因為那個大大的M燈牌很適合為主播打光。
他們的互動方式是一場接一場的PK,其實就是以羞辱和自我羞辱作為最主要的獲取打賞的方式。那天在下雨,我看到一個女孩突然沖進雨里開始轉圈,還沒轉完,另一邊一個女主播抄起拖鞋追著另外一個男主播,在雨中打他的屁股。那聲音震天響,這些都是PK輸了的懲罰。
我從來不認為數字技術僅僅改變了線上世界,我的合作者王怡霖博士給我介紹了一個網紅景觀聚集地:成都三圣鄉。你可以假裝在摩洛哥、京都、洛杉磯、普吉島……這些地點之間可能距離不足20米,一個個由漂亮女孩、打光板、相機三要素構成的小隊伍在其中行進。他們可能會在“摩洛哥”待一個下午,等待光線到了某一個角度拍出最完美的照片。
他們的互動方式是一場接一場的PK,其實就是以羞辱和自我羞辱作為最主要的獲取打賞的方式。
我們經常說互聯網賦予人移動的能力,比如有個直播平臺的定位就是“在這里,遇到你的鄰家女孩”,對女主播而言,她的愿望也是被人遇到。平臺的運營,也叫“星探”,招募主播的時候就會說“你在我們這兒會遇到你在現實中這輩子都不會遇到的有錢人”。
但這些女主播并不是大家想象中那種很光鮮亮麗的一群人,我們跑了很多地方,見到大多數的女主播來自高度性別化的產業,比如幼師、空姐、模特、公司前臺,還有一部分是向上流動非常困難的階層,比如富士康倒掉后紛紛轉投直播的廠妹。
他們可能沒有或者看不到明朗的職業發展前景,當自我羞辱成為一種有利可圖的工作技能,這份工作的門檻又很低,成為主播就帶來一種愿景(expectation),吸引相當多人進入這個行業。
我們在田野中掉了很多次眼淚,比如有一位單身媽媽,孩子只有一兩歲,她沒有辦法全職工作。有一次她跟我講,孩子睡著之后,她把臥室門關上,然后在客廳里打開手機,開始跳舞,跟大哥調情,拿了打賞,孩子醒了她再暫停直播把門打開。
他們并非刻板印象中那種有道德污點的人,道德判斷有時候會特別傲慢和精英主義,我們有很好的職業和較高的社會地位,不需要這樣也可以過上不錯的生活,但如果我們身處他們的位置,我們可能會做出一樣的選擇。社會學的意義并不是指責一個群體,而是問“何以至此”,也就是事情為什么會到這一步?
平臺帶來的相遇和移動性其實還有一個有趣的反面,王怡霖和我分享過一個故事,有位主播在遼寧一個小邊陲直播,但她將IP定位改到了上海,因為她所在小鎮上的大哥沒多少消費能力。這意味著她必須讓所有人以為她真在上海,所以她要了解上海哪里人多好玩,每次上播前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上海的天氣,才有話可聊。于是她每一天都在想象中描摹一個上海,后來王怡霖問她“你有什么愿望”,這個女孩沉默良久,說“我想以后有機會,去一趟上海”。
平臺社會賦予我們消滅空間的移動性的能力,但卻帶來一個不必移動的非移動性結果。直播讓人相遇,但主播其實更孤獨。
平臺,嵌入日常的基礎設施
南風窗:互聯網技術承諾給我們去中心化的愿景,但通過剛才的觀察,平臺統治了人與人之間的相遇,甚至改變了現實中街區的景觀,我會感覺在生活里,平臺反而是在中心化,權力邊界在不斷擴張。你作為社交媒體的重度使用者,有沒有發現平臺在發展過程中的規律或者說共性?
董晨宇:平臺的發展趨勢是一個壟斷性趨勢,早期校內網、開心網、豆瓣這些平臺媒體的雛形,依然在它的細分領域扎根,甚至抖音最初也只是一個在BGM中唱歌跳舞的社交媒體,但我們現在看到的平臺,已經不僅僅是唱歌、跳舞、分享書影音這種細分領域的載體了。
一個鮮明的例子是微信,我們可以在微信上繳水電費、購物、訂機票和酒店,甚至進行小額貸款,不是我們在用微信,而是微信已經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不管是中國還是美國,幾個巨型公司幾乎已經包辦了所有人的衣食住行。平臺現在是嵌入我們日常生活的基礎設施,這是我認為它發展過程中最大的變化。
南風窗:舉個例子,你在5月底也擁有了小紅書賬號,我們最近也都很關心小紅書,很驚訝地思索,它是怎么在近一兩年從美妝海淘的垂直平臺發展成了一個包羅萬象的國民平臺?
董晨宇:小紅書非常有趣的轉變就是它的“搜索引擎化”,比如我孩子發燒的時候,我太太的第一反應是在小紅書上搜索一下,有沒有跟他一樣癥狀的人。平臺要做大,它往往會從一個細分領域轉變成為我們生活中的工具,這仍然是平臺“基礎設施化”的概念。

抖音也是類似的,比如它最近推出的本地生活板塊,包括探店分享、優惠券,跟本地的衣食住行嫁接在了一起。以往我們外出就餐消費習慣用大眾點評這類非常細分的App,現在抖音其實對大眾點評造成了很大沖擊。
平臺成為基礎設施有兩條路徑,一是像微信、抖音這樣,成長為無所不包的巨型平臺,還有一條出路就是通過不斷的兼并收購,把眾多細分平臺納入麾下,比如我們可以在高德這樣的導航應用上叫車、探店,因為它的背后是阿里,能夠連接阿里系平臺龐大的受眾群體。
這是資本的必然邏輯,很多研究稱其為“集中化”(centralization)。集中化一定是有好處的,比如更高效、決策的影響力會更大、轉變會更快,但它也有可能走向一種危險的壟斷,帶來的不僅僅是經濟后果,還有可能有政治和文化的后果。
小紅書非常有趣的轉變就是它的“搜索引擎化”,平臺要做大,它往往會從一個細分領域轉變成為我們生活中的工具,這仍然是平臺“基礎設施化”的概念。
南風窗:照這個趨勢發展下去會帶來怎樣的效應?平臺權力的邊界在哪里呢?
董晨宇:我們剛才談到人與人之間的相遇是由平臺規定的,這是深度媒介化的現象。人與人的關系越來越受制于一種非面對面的中介化關系,這種關系既包括我們和親朋好友,也涵蓋了我們作為需求方所期望得到的服務。而這一切并不是在自然條件下發生的,而是在平臺設定的框架或者說基礎配置之下。技術中介絕對不是中立的,算法一直在調節我們的相遇,這種調節我們往往無法清醒地認識到。
如果我們把平臺當成一種生意,從經濟角度來講,平臺跟從前的大眾媒體或者社交媒體的區別在于,它是一個多邊市場。大眾媒體負責生產內容,讀者購買雜志,把自己跟用戶相連,社交媒體是讓用戶和用戶自行相連,這些還都是雙邊市場下比較線性的商業模式。而平臺的機制是讓用戶之外的大量輔助者參與這個市場,比如微信上的小程序,或者直播行業主播和觀眾之外的MCN公會、法務公司、直播設備供應商等等,這是一個更加網絡化的商業模式。
平臺的權力已經不僅僅是連接人與人了,而是擁抱社會的方方面面;走向集中化是必然的趨勢,最終一定是少數幾個公司進行競爭。
賽博空間,沒有鐵飯碗
南風窗:說到這里,我記起我上個月打車從機場坐到市區,那位司機告訴我一個統計結果,近幾年內他載的乘客超過50%都在從事由抖音衍生出來的職業,比如網紅、剪輯、編導。他很不解:怎么能有這么多人依附于這個誕生還沒有10年的平臺工作?
董晨宇:這是個“平臺依賴”的問題。各個行業的人進入這個多邊市場,借助媒介的相遇打破了空間和時間的距離。我們會發現,平臺最初一定是為新入場者賦權,燒錢讓利、流量扶持,一個平臺做大以后,它之上的內容生產者和輔助者的議價權會越來越小。比如說你想去做直播帶貨,但對主流的淘寶、京東、抖音、快手等幾個平臺都不滿意,就會發現無處可去,沒有什么討價還價的空間。
另外就是平臺區隔帶來的分眾化,一個人在抖音上出名,但離開了抖音去其他平臺,幾乎要從零開始。名聲往往局限在特定平臺之內,這造成了巨大的權利不對等。過去我們常說,在抖音快手做短視頻的人是自由職業者,其實他們一點都不自由,他們對平臺的依賴甚至超出我們對傳統公司的依賴。
我們經常談論文化生產者的不穩定性,我錨定一個賽道,如果賽道因為平臺政策流量驟降,結果是致命的,比如電影解說因為版權爭議進入寒冬,這個賽道的從業者就會遭遇重創。與之類似,新聞或者游戲行業跟平臺的議價權也非常有限。
小紅書是一個很有趣的案例,你會發現,其中幾乎沒有一個所謂的“頭部網紅”盡人皆知,這緣于相當多平臺傾向采用的普惠算法。他們會選擇扶持多個有不錯變現能力但掌握不了議價權的腰部網紅,而不是讓頭部網紅統治這個平臺,成為流量主宰者后迫使平臺屈從。
當然,平臺的權力也并不是任性的,例如平臺希望用戶留存、創作者留存,創作者和用戶還是能夠跟平臺爭奪一些權力,這種算法調節之下不對等的動態協商是一種必然結果。
我們發現,大的平臺其實是擁抱管理的,真正打政策擦邊球的往往是小公司。平臺公司真正怕的,是“三天一變”的治理。
南風窗:這種權力的動態平衡,其實會打破一些將網紅作為理想職業,將來一路變現端上賽博鐵飯碗的認知。就在采訪前,我被推到一條視頻,是一位中傳碩士決定畢業后不工作而成為一名UP主的宣言。類似的故事在最近半年也是頻繁上演,不過我被推到時播放量只有40次,看來我就屬于這條視頻被平臺扶持之后的首批觀眾。
董晨宇:其實網紅夢想的魅力正在于不確定性。現實的工作對很多人來講太確定了,天花板一眼能望到,甚至可以看到退休時候的樣子。穩定是沒辦法激發人的期待的,網紅這個行當本身承諾的就是一種不穩定,過去一夜成名很稀缺,現在流量神話幾乎天天都在上演。
但做網紅也存在兩種幻覺,一是頭部網紅的比例實在太低,堪比買彩票,絕大多數底層從業者沒什么收入;二是中國網紅的職業壽命實在太短,大都“火不過三個月”,我們在田野中也常常想“他們之后能做什么”,但眼下并沒有一條成熟的發展路徑可供大多數人參照,這份工作跟鐵飯碗毫無關系。
不過,想當網紅沒什么可指責的,網紅未來很可能會成為一種司空見慣的職業選擇,相當多人都會去試一試。人們是很理性的,我們觀察到,進入這個行業的從業者,絕大部分都是兼職碰個運氣、抽張彩票,就算什么都沒抽中,也被人喜歡、自我表達過了。
南風窗:你現在對平臺秉持怎樣的態度?
董晨宇:平臺治理是這幾年非常熱門的話題,我從來不會唱衰平臺,這已經是無法逆轉的現實,沒有任何技術帶來的福祉是沒有代價的。所以我們更多在想的是,從政府職能部門的角度,如何讓平臺經濟更健康地發展;從用戶的角度,如何應對新的媒介素養挑戰。
當下呼喚的媒介素養是一種共存力,如何與算法、平臺共存,如何擁抱新的基礎設施,比如反過來訓練算法,利用它方便自己、娛樂自己,而不被它利用以致沉迷其中。
政府承擔的責任會更大,我們發現,大的平臺其實是擁抱管理的,真正打政策擦邊球的往往是小公司。實際上投機分子被治理,對大平臺有利,對行業大環境和可持續性發展也有幫助。所以平臺治理和平臺公司利益并非截然對立,平臺公司真正怕的,是“三天一變”的治理。
但“三天一變”,又是平臺治理在探索過程中必然出現的手忙腳亂。不光國內,放眼世界目前也很難有確定的治理規則。
我們不是和平臺“相遇”,而是和平臺“遭遇”,所以如今我們應對的方法常常是“出了事兒就罰款”。這是一種以事件為單位的治理方式,在短期內非常有效,但也只是一種權宜之計。隨著技術革新,我們在未來會不斷修正甚至顛覆既有的治理方式,尋求平衡平臺經濟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解決方案,即便恐怕并不存在最終的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