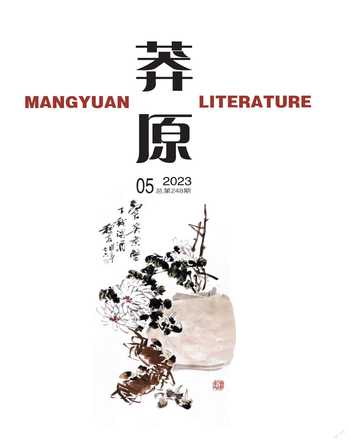話說(shuō)·說(shuō)話
張文豪
就是這座坡。
長(zhǎng)約二里余。一端依著大山,一頭系著平川。一條黃土路從山頂拋到山下,系著山里人上上下下的日子。
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北坡那眼四季不息的汩汩泉水,給匆匆的路人洗去塵垢,也滋潤(rùn)著坡上大片的柿樹(shù)林。泉眼的名字卻叫人納悶:咸水泉。于是,這坡上和坡下的村子就有了味道,叫咸水坡、咸水村。
鞭子爺說(shuō):“咸啊,都是咸的呀。眼淚也咸啊!”
男子漢竟知道淚水是咸的?
柿子謠
咸水坡的柿子卻是甜的。
道光年間,此地的官兒把咸水坡的柿餅作為貢品送到皇宮,皇帝吃了以后龍顏大悅,稱“蜜而不膩,奇果。”從此,咸水坡的柿餅便成了珍品……這是鞭子爺說(shuō)的。
村里,鞭子爺知道的事兒最多。
白云般的羊群在坡上涌動(dòng)著,專心吃著嫩草。鞭子爺攥著鞭桿兒,悠閑地背著雙臂,直著脖頸“吆喝”《柿子謠》:
咸水坡喲數(shù)三紅,
“蜜金”“羊果”“映天紅”。
定婚、娶親、走娘家,
哎呀呀,
缺了哪樣都不行……
那時(shí),鞭子爺很年輕,一口好嗓子,唱出來(lái)有調(diào)有韻而不失詼諧。這首用柿子名兒巧妙串起來(lái)的歌謠,讓人能想到很多滋味。在咸水坡,日常生活,人情往來(lái)都離不開(kāi)柿子,各色各樣的柿子寄托著希望,也蘊(yùn)涵著鄉(xiāng)村情感和民間哲理。
那年秋天,柿葉紅了,柿子摘了,“噼噼啪啪”的鞭炮聲響起,鞭子爺和一個(gè)身著大紅衣褲的俊俏女人拜了天地。紅紅的蓋頭布揭開(kāi)了,新媳婦臉上卻無(wú)喜無(wú)憂,兩只黑黑的眼珠兒呆呆的,沒(méi)有羞澀,也沒(méi)有希冀。
秋陽(yáng)輝煌,燥熱的光讓鞭子爺鼻尖滲出了汗粒。無(wú)論如何,鞭子爺心里還是充滿了興奮和期待。等月兒被云彩藏進(jìn)懷中,送走酒足飯飽的最后幾位鄉(xiāng)親,鞭子爺在新房前緊張地搓了會(huì)手,懷里像揣了兔兒一樣進(jìn)屋,閂上了門(mén)。
院子里,麻子領(lǐng)著幾個(gè)調(diào)皮蛋從墻頭溜下來(lái),躡手躡腳蹲到窗下聽(tīng)房。
新媳婦和衣而臥,臉朝里側(cè)。鞭子爺站在床前愣了一會(huì)兒神,終是嘆了口氣,和衣躺在床邊,“呼——”,吹熄了油燈。竟是一夜無(wú)話,一夜無(wú)聲。
窯外麻子他們很是失望,說(shuō):“新郎官這幾天太累了,我們明晚再來(lái)吧。”
第二天晚上,新媳婦仍然和衣而睡。鞭子爺窸窸窣窣脫了衣服,“呼——”,吹熄了油燈。
窗外,都屏住了呼吸。
屋里一團(tuán)黑,卻有了急急的粗粗的喘氣聲,還有掙扎和抗拒的聲音。鞭子爺硬是沒(méi)把媳婦的褲子脫掉,便氣惱地問(wèn):“為啥?”
新媳婦只凄凄地飲泣。
鞭子爺便泄了氣。
窗外的人又沒(méi)看成好戲,都輕輕嘆息。“還是沒(méi)戲,”麻子說(shuō),“鞭子真不治事。嗨,我白白替他放了一天羊……”
羊圈在咸水坡下的窯洞里。早上麻子又去替鞭子爺放羊,見(jiàn)圈門(mén)開(kāi)著,清點(diǎn)數(shù)目,發(fā)現(xiàn)少了兩只羊,去跟鞭子爺說(shuō)了,猜測(cè)是夜里被狼叼走了。這天晚上,鞭子爺便從新房扛了鋪蓋,住進(jìn)了羊圈旁的小窯洞。
如此過(guò)了小半年光景,新媳婦卻生下了一個(gè)胖小子。村里人一片嘩然,說(shuō)三道四,猜測(cè)那孩子不是鞭子爺?shù)姆N。鞭子爺卻激動(dòng)得臉膛紅亮,抱著娃兒親了又親,嘴里“心肝肝,肉蛋蛋,寶乖乖……”叫個(gè)不停。媳婦聽(tīng)著,兩眼閃爍起亮光。人們納悶:日子不對(duì)啊?可小兩口卻不管這些,他們給娃兒起名叫拴拴。
之后,鞭子爺依舊住在小窯洞。
柿葉青了又黃,拴拴一點(diǎn)一點(diǎn)長(zhǎng)大了,會(huì)坐了,會(huì)爬了,會(huì)咿咿呀呀學(xué)話了,人們好像都忘了曾經(jīng)的猜測(cè)。
一天傍晚。鞭子爺圈好羊回家吃飯,灶冷著,鍋空著,屋里院里卻不見(jiàn)了拴拴和媳婦,唯有案板上擱了一撂柿子和秫秫面的餅子饃。紅紅的,黃黃的,散發(fā)著甜絲絲的香氣。鞭子爺從家里找到街上,又從村里找到村外,終是沒(méi)找到這娘兒倆。鞭子爺一口餅子也沒(méi)有吃,默默地流淚。
日子一天天過(guò)去,鞭子爺硬板板的腰駝了,亮光光的臉上布滿了皺紋。小伙伴們一道光著屁股驚喜地尖叫著,跟著鞭子爺在咸水坡放羊,吃著鞭子爺給摘的酸棗兒,聽(tīng)鞭子爺講又可怕又有趣的故事,但心里總想起鞭子奶和拴拴。
有時(shí)候?qū)嵲谌滩蛔×耍蛦?wèn):“鞭子爺,你想不想鞭子奶跟拴拴啊?”
鞭子爺嘆口氣,說(shuō):“想啊,能不想嗎?”
“叭叭”,鞭子在他手中揮動(dòng),兩只離群的羊兒嚇得扭頭跑進(jìn)羊群里。
“人心啊……”鞭子爺渾濁的雙眼遙望遠(yuǎn)處的青山。
有一年秋天,幾個(gè)解放軍押著兩個(gè)人來(lái)到咸水村,卻是鞭子奶和她的兒子拴拴。鞭子奶穿著像個(gè)貴婦人,只是憔悴不堪;拴拴已經(jīng)長(zhǎng)成半大小伙兒了,穿著打扮像城里人,卻愁云滿面,好像有滿懷心事。
人們奔走相告——部隊(duì)把鞭子爺?shù)南眿D、兒子送回來(lái)啦!
咸水坡的人習(xí)慣用組織稱呼組織里的人。比如他們把當(dāng)兵的叫部隊(duì),把警察叫公安局,把當(dāng)官的叫政府。
解放軍在村頭那棵老柿樹(shù)下召開(kāi)了全村大會(huì)。柿葉已是稀疏,柿子卻紅亮如串串燈籠。黑壓壓的村民都有些興奮。孩子們歡天喜地在會(huì)場(chǎng)瘋跑,女人們有的納鞋底,有的敞著懷用或肥碩或干癟的奶頭喂娃兒,男人們則吧嗒著煙袋,猜測(cè)著鞭子奶和拴拴被掐去了一截的故事。
鞭子爺直倔倔地坐在柿子樹(shù)下的燈影里,誰(shuí)也不看,就看著天上的星星,樹(shù)上的柿子。
隊(duì)長(zhǎng)麻子說(shuō):“部隊(duì)同志說(shuō)了,拴拴他爹是個(gè)大壞蛋,歷史反革命,已經(jīng)抓來(lái)了。”又對(duì)鞭子爺說(shuō),“鞭子爺,那壞蛋欺你妻兒,你苦大仇深,軍隊(duì)叫你控訴哩。”
鞭子爺正襟危坐,嘴里插著旱煙袋,一言不發(fā)。
“大爺,你不要有顧慮,有冤申冤,有苦訴苦,我們給你作主。”一個(gè)拿筆記本的解放軍說(shuō),同時(shí),目光凌厲地掃了鞭子奶和拴拴一眼。
鞭子奶和拴拴的身子本來(lái)就縮成一團(tuán),這被解放軍的目光一掃,馬上又縮小了許多。
鞭子爺呼地起身,在鞋底上狠狠磕了磕煙袋,說(shuō):“部隊(duì)同志,咱做人可得憑良心,要說(shuō)欺,是我欺了人家妻兒……”
人們對(duì)當(dāng)初的事一直不甚了了,鞭子爺?shù)脑挶阋诲N定音了。
部隊(duì)的同志很奇怪,問(wèn)鞭子爺?shù)降资窃趺椿厥拢拮訝攨s死活不肯說(shuō),只口口聲聲說(shuō)是自己糊涂,做了對(duì)不起人的事。再問(wèn),還是這車轱轆話。部隊(duì)的同志終是無(wú)奈,扔下一句話:那就讓他們?cè)谙趟甯脑欤∽吡恕?/p>
麻子大叫:“鞭子爺,咸水坡人的臉面都叫你丟清啦!”
鞭子爺噙著煙袋說(shuō):“麻子,你懂個(gè)屁。”
于是,拴拴和他娘便又成了鞭子爺?shù)娜恕1拮訝斠幌伦酉衲贻p了二十歲,整天臉上掛著喜氣。可喜歸喜,樂(lè)歸樂(lè),他依然住羊圈的窯洞里,也吃拴拴娘做的飯,也穿拴拴娘做的衣,只是不肯跟拴拴娘同房。麻子急得直跺腳,咸水坡男人也惋惜得唉聲嘆氣。
歲月如逝水,又是數(shù)年過(guò)去了。
鞭子奶被改造得臉色紅潤(rùn),身體健壯,家里地里,細(xì)活粗活,樣樣拿得起放得下,且為人和善,處事厚道,極受咸水坡人的愛(ài)戴。拴拴也是一表人才,加上識(shí)文斷字,就在村小學(xué)當(dāng)了老師,招引得三里五村的大閨女們眼波蕩漾。鞭子爺便托媒婆鳳仙給拴拴說(shuō)媳婦兒。鳳仙果然不負(fù)眾望,從后山給拴拴選了一個(gè)天仙般的女子。三聘五禮下過(guò),就到了談婚論嫁的關(guān)口。
忽一日,兩輛烏黑賊亮的小臥車開(kāi)進(jìn)了咸水村,地區(qū)、縣里、公社都陪著來(lái)了人。他們是來(lái)接拴拴跟他娘的。拴拴在村學(xué)校上課,鞭子奶去鎮(zhèn)上趕集了,正好都不在家。
隊(duì)長(zhǎng)麻子把他們接到大隊(duì)部,沏茶倒水,先穩(wěn)住了他們,然后去找鞭子爺。他在咸水坡上找了半天,才找到鞭子爺。
“那家伙又官?gòu)?fù)原職啦,來(lái)接人哩!”麻子說(shuō)。
當(dāng)時(shí),鞭子爺正在趕一只羊,他手里的鞭子驟然僵在空中。
“咋辦?”麻子說(shuō),“兩個(gè)大活人,也藏不住啊,也不知道拴拴娘倆是啥心思……”
“唉——”鞭子爺重重吐出一口氣,“不是咱咸水村的人,留不住的,隨他們?nèi)グ伞!?/p>
“那……這恁些年,你就白養(yǎng)活她娘兒倆啦?”麻子有些不甘心。
“緣分呀,該他們娘倆喝咱咸水水。”鞭子爺咕噥著,神色有些黯然又有些欣喜,“再說(shuō)了,這也是好事,她娘兒倆總算熬出頭啦!”
鞭子爺力排眾議,硬是把鞭子奶和拴拴送上了小臥車。
鞭子奶和拴拴哭得鼻子一把淚一把,遲遲不肯上車,最后,撲通一聲跪在地上,給鞭子爺磕了三個(gè)響頭。
后來(lái),麻子說(shuō),拴拴他爸在黨,要不,別看他那么大的官,照樣也得給鞭子爺下跪哩。 對(duì)麻子的這種說(shuō)法,咸水村無(wú)人質(zhì)疑。
有那么一陣兒,化肥緊張,麻子不知怎么就想到了拴拴他爸。于是,就拉上鞭子爺,扛了幾袋子上好的柿餅、柿瓣兒、柿皮兒,曉行夜宿,進(jìn)了省城去找拴拴他爸。然而,幾天以后,鞭子爺和麻子垂頭喪氣地回來(lái)了,兩手空空。人們懷疑他們沒(méi)有找到拴拴他爸,可他們那些袋子都不見(jiàn)了;莫非是人家不肯幫忙?但兩個(gè)人對(duì)那趟省城之行的具體情節(jié)都諱莫如深。被人們問(wèn)急了,鞭子爺就幽幽地嘆息;麻子呢,就猛然迸出一句話:“咸水村的人都瞎了眼!”
他不罵城里人瞎了心,只罵咸水村的人瞎了眼,人們也都能猜出個(gè)大概了。
鞭子爺站在崖畔那兒,對(duì)著咸水坡吼起了《柿子謠》:
蜜金對(duì)不上牛心柿,
羊果對(duì)不上鬼臉青,
哎喲喲,缺了哪樣都不中……
此后,鞭子爺傍晚收了圈,又回家里住了。只是家里冷鍋涼灶的,再?zèng)]人給他做飯了。
一個(gè)夏夜,電閃雷鳴,暴雨如注,山水順坡而瀉。圈羊的窯洞頂裂開(kāi)了好幾道大口子,渾濁的雨水灌了進(jìn)去。羊們?cè)诳謶种羞氵銇y叫。
鞭子爺從家里趕來(lái),打開(kāi)羊圈,揮著鞭子將羊群往外趕。羊們害怕外邊的電閃雷鳴,都死活不肯出去。鞭子爺就一只一只往外牽。可前腳牽出去,后腳那羊又跑進(jìn)來(lái)了。沒(méi)辦法,鞭子爺就一只一只把它們拴到坡上的柿樹(shù)上。這樣就耽誤了時(shí)間,等他最后抱起一只小羊羔時(shí),轟然一聲,窯突然塌了,鞭子爺沒(méi)來(lái)得及出來(lái)。
麻子領(lǐng)著人們扒了半天,才將鞭子爺和他懷里抱著的羊羔扒出來(lái)。隊(duì)里派人買(mǎi)了一口柏木棺材,村里女人給鞭子爺做了衾衣衾被,統(tǒng)統(tǒng)緞子的,鞭子爺看著很富貴,他被葬在了咸水坡上。
殯埋了鞭子爺,隊(duì)長(zhǎng)麻子才說(shuō)起了鞭子爺和拴拴娘的事——
拴拴娘家在后山,年輕時(shí)有個(gè)相好,就是拴拴他爸。拴拴他爸不知犯了什么事,在老家混不下,就跑到山外闖世界去了。那時(shí)候,拴拴娘肚子里已經(jīng)有了拴拴,大閨女懷孕,這在山里是很丟人的事,眼看著瞞不下去了,家里就四處給她找男人;近處都知道她的丑事,沒(méi)人要,就往遠(yuǎn)處找。鞭子爺那年在坡上放羊,偶然遇到了拴拴的外爺,兩人一拍即合,當(dāng)下就把親事定了。拴拴的外爺隱瞞了實(shí)情,只說(shuō)家里窮,還有兩個(gè)兒子都沒(méi)說(shuō)下媳婦,鞭子爺用了全部積蓄,才娶了拴拴娘。所以,過(guò)門(mén)才小半年,就生了拴拴。
新中國(guó)成立以后,拴拴他爸衣錦還鄉(xiāng),才知道拴拴娘已另嫁他人,而且還有了孩子。拴拴他爸放不下心愛(ài)的女人,更放不下兒子,就偷偷來(lái)到了咸水坡找人。可能拴拴娘怕鞭子爺不放她娘兒走,就趁著鞭子爺上坡放羊的時(shí)候,抱著孩子跟拴拴他爸跑了。原以為從此可以在城里過(guò)人上人的日子,可趕上了運(yùn)動(dòng),查出拴拴他爸給國(guó)民黨當(dāng)過(guò)兵,扣上個(gè)歷史反革命的帽子,整天批斗游街,娘倆的生活沒(méi)了著落,只好又回了咸水村。鞭子爺?shù)挂膊挥?jì)前嫌,重又接納了他們。
還真是世事無(wú)常,過(guò)了些年,拴拴他爸的歷史問(wèn)題查清了,說(shuō)他雖然給國(guó)民黨做過(guò)事,可也給共產(chǎn)黨立過(guò)功,將功補(bǔ)過(guò),恢復(fù)了公職,還一步一步當(dāng)了大官。人當(dāng)了官,就想起了妻兒,這回不再偷偷地干活了,開(kāi)著小臥車,接拴拴娘兒倆進(jìn)城團(tuán)圓了。
至于買(mǎi)化肥那件事,麻子死活不肯說(shuō)。他不肯說(shuō),鞭子爺也已經(jīng)歿了,就成為咸水村一個(gè)謎,只能憑人們猜測(cè)了。謎就謎吧,猜就猜吧,哪個(gè)地沒(méi)幾個(gè)謎呢?
兩面臉
農(nóng)忙五月天,頭夜剛落過(guò)一場(chǎng)雷陣雨,早晨西邊天際就掛起一弧彩虹。那場(chǎng)雨雖然下得不大,但來(lái)得很急,很多人家場(chǎng)里的麥子都淋了雨,唯獨(dú)金連山家的麥子躲過(guò)了。金連山家長(zhǎng)工多,麥子早就打好揚(yáng)凈,收進(jìn)了場(chǎng)房屋,等著曬干收倉(cāng)了。
正所謂福禍相連,正因?yàn)榇蠹业柠溩舆€攤在場(chǎng)里,而金連山家的麥子已經(jīng)打好裝袋,這就方便了后山王豁子那桿土匪。趁著夜里電閃雷鳴,土匪們下了山,把看場(chǎng)的家丁捆了個(gè)老漢吃瓜,幾十袋新麥被搶了個(gè)精光。金連山一氣之下,病倒了。他躺在床上,想想大長(zhǎng)一年的收獲,又是心疼,又是氣憤,連著三天水米沒(méi)打牙。
兒媳婦柿花把荷包蛋端到他床前,說(shuō):“爹,錢(qián)財(cái)是身外之物,您老的身體要緊,吃口飯吧。”
看到俊俏的兒媳婦,金連山又想起他那個(gè)傻兒子。這結(jié)婚都兩三年了,兒媳婦的肚子還沒(méi)有動(dòng)靜,這萬(wàn)貫家產(chǎn),可交給誰(shuí)啊!
勉強(qiáng)吃兩個(gè)荷包蛋,金連山就起床了。他叫人請(qǐng)來(lái)了風(fēng)水先生“十只眼”。
“十只眼”繞著宅子里里外外看了一遍,沒(méi)毛病;又去看了金家的祖墳,說(shuō)問(wèn)題出在金家祖墳,這祖墳氣數(shù)已盡,得遷墳。挪則枯木逢春,后繼有人;不挪家財(cái)散盡,斷子絕孫。金連山陪著“十只眼”在咸水坡轉(zhuǎn)了一圈,末了,“十只眼”指著半坡一塊玉米地,說(shuō):“這是一塊風(fēng)水寶地!”
金連山愣了愣,說(shuō):“換一處吧。”
“十只眼”閉目不語(yǔ),將頭搖得像個(gè)撥浪鼓。
金連山捋捋山羊胡子,使勁咬了咬牙根。
這是林棵子家那二畝多地。
要是論起來(lái),林棵子是金連山的遠(yuǎn)門(mén)表侄。林棵子祖上曾經(jīng)也是咸水村的富戶,論家產(chǎn)莊園,一點(diǎn)都不落金連山祖上的下風(fēng)。只是到了林棵子他爺,整天游手好閑,跟著金連山他老爺進(jìn)城吸大煙、賭博、逛窯子,把個(gè)萬(wàn)貫家產(chǎn)糟蹋殆盡,家產(chǎn)莊園都?xì)w了金家名下,僅剩咸水坡那二畝多好地。這真是塊風(fēng)水寶地,因?yàn)樵谄律希略俅蟮挠辏乩镆膊淮嬉煌羲?又因?yàn)榘趟瑒e處一片焦土,這塊地卻不缺一點(diǎn)墑情。所以,哪怕普天下都絕收了,偏偏這塊地旱澇保收,五谷豐登。因了這地,林棵子家才勉強(qiáng)果腹遮體,因而也從未理會(huì)過(guò)首富金連山的臉色。
沒(méi)想到“十只眼”偏偏相中了這塊地。金連山知道林棵子不會(huì)舍得,可為了子嗣香火,還是硬著頭皮去找了林棵子。果然,沒(méi)等金連山把話說(shuō)完,林棵子就跳了起來(lái):“咋么,林家的莊園田地都姓金了,你還不知足?休想!”
金連山知道是休想,可休想也得想,想著想著,就落下了心病。
每年六月十六,遠(yuǎn)遠(yuǎn)近近的鄉(xiāng)民都會(huì)涌向靈山寺,燒香許愿,也趁著趕靈山寺廟會(huì)。廟門(mén)前偌大的空地上,做生意的,耍把戲的,人頭攢動(dòng),熱鬧得像一口翻滾冒泡的開(kāi)水鍋。
這是林棵子最露臉的一天。
在玩耍上,林棵子遺傳了他爺爺?shù)钠⑿裕皇菆D個(gè)熱鬧,二是為了掙倆小錢(qián)貼補(bǔ)家用,他不聽(tīng)老父勸阻,十幾歲便拜師進(jìn)了“響十里”鼓樂(lè)班,干起這下九流的行當(dāng)。嗩吶竹笙鑼鼓家什他一概不會(huì),但他有一個(gè)絕活兒,就是柳木棍兒上耍“兩面臉”。他腦袋瓜子刮得青光溜亮,坐于廟前一根青石條上,“響十里”鼓樂(lè)班班主用油彩給他描鼻子畫(huà)臉,前面是一個(gè)白眼窩小丑,后面是一個(gè)紅臉蛋花旦。林棵子不光前面能呲牙咧嘴,后腦勺也會(huì)擠眉弄眼。那身衣裳呢,前面是跑堂小廝的短打扮,后邊是媒婆的紅襖綠褲。只要他一亮相,便會(huì)招來(lái)圍觀者鼓掌叫好,跟著,銅錢(qián)毛票就下雨般落到班主的銅鑼里。
化好了妝,班主揮揮手,琴瑟簫笙喇叭笛子鑼鼓梆子便一齊奏響,兩個(gè)膀大腰圓的棒小伙,肩上扛根茶碗粗的柳木棍。林棵子抓住柳木棍,兩臂一撐,便穩(wěn)穩(wěn)妥妥坐于柳木棍上,兩手相攏不扶,立馬贏來(lái)一片喝彩。
騎坐在柳木棍上,林棵子先是敏捷地前后左右側(cè)身轉(zhuǎn)體,叫人眼花繚亂辨不清真假前后臉;然后是雜耍,在光溜溜的柳木棍上輕巧學(xué)武大郎賣燒餅,學(xué)王婆打情罵俏勾引人,學(xué)蔣干盜書(shū)、濟(jì)公醉酒,學(xué)東施效顰……上下翻飛,身輕如燕,表情惟妙惟肖,動(dòng)作幽默風(fēng)趣。人們伸長(zhǎng)脖頸,喝彩不絕。
這手“兩面臉”騎柳棍技藝耍得出神入化,給本來(lái)就“響十里”的鼓樂(lè)班增色不少,也增收不少。
夏日天長(zhǎng),這年靈山寺廟會(huì)散了以后,西天還晚霞斑斕,林棵子走在回村的小路上,走到一片雜樹(shù)林當(dāng)中,忽然從一棵樹(shù)后閃出一個(gè)穿戴鮮艷、長(zhǎng)相俊俏的女人,嚇了林棵子一跳。定睛一瞧,心里就忽悠了一下——是金連山家傻兒子的媳婦柿花。
世上事從來(lái)不會(huì)十全十美,金連山富甲一方,可他唯一的兒子卻是個(gè)光會(huì)嘿嘿傻笑的憨子,這叫金連山傷透了腦筋。便是如此,靠著家大業(yè)大,又是村里的保長(zhǎng),上門(mén)提親的也踩折門(mén)檻。挑來(lái)挑去,就挑了這么個(gè)乖巧伶俐的媳婦。柿花嫁到金家一年有余,似乎是那傻男人不懂怎樣打發(fā)媳婦如意。媳婦肚子未鼓,笑臉也無(wú),人們都說(shuō)一朵鮮花插到了牛糞上,可惜了。只是近些日子,柿花突然有了叫人捉摸不定的笑。隨之,村里就有人私下議論,說(shuō)金連山那老不要臉的扒灰,和兒媳婦鬼混到了一塊……
當(dāng)時(shí),柿花就那么斜斜地側(cè)身?yè)跽驹谛÷飞希浑p俏杏眼流光溢彩地望著林棵子。“棵子哥,我看見(jiàn)你耍兩面臉了,贏人哩,喜歡哩。”
林棵子被看得臉熱心跳,眼光不敢跟柿花對(duì)視,別過(guò)臉說(shuō):“我那是下九流的勾當(dāng),狗肉不上桌。”
又想起這些日子,在村街遇上了,柿花總是沒(méi)事找事跟自己搭話,說(shuō)話就說(shuō)話吧,還搔首弄姿送來(lái)叫人心神不定的笑。今天又在這兒遇見(jiàn),看似碰巧,可這荒天野地里,孤男寡女,難免有瓜田李下的嫌疑,心里想著,就要繞過(guò)去走開(kāi)。
“棵子哥……”柿花軟綿綿地叫了一聲,像絆馬索一般絆住了林棵子的雙腳。
“俺去靈山寺趕會(huì)回來(lái),在這兒……等你可長(zhǎng)時(shí)辰啦。”柿花含情羞羞地說(shuō)。
“等我?”林棵子愣怔了一下,皺著眉頭扭過(guò)身來(lái),“有事嗎?”
“俺心里苦,想跟你說(shuō)說(shuō)話。”柿花可憐兮兮地說(shuō),“都怪俺爹圖金家的錢(qián)財(cái),又上了媒人的當(dāng),俺才嫁給那個(gè)傻子。他不會(huì)心疼俺,一上床就知道又咬又啃的……”
有亮亮的東西從柿花眼里淌出,淌過(guò)俊俏的臉蛋,淌過(guò)顫動(dòng)的嘴角,淌到光潤(rùn)的下巴尖處,懸著,著實(shí)梨花帶雨般楚楚可憐。只是,這剛一開(kāi)口,就說(shuō)到床上的事,聽(tīng)起來(lái)還是叫人心驚肉跳。
“他是……是有點(diǎn)不透氣,可他實(shí)在,厚道……”林棵子說(shuō)。
“棵子哥,這話你信嗎?”柿花說(shuō)。
林棵子點(diǎn)點(diǎn)頭,又搖搖頭,其實(shí),他嘴上這么說(shuō),卻連自己都知道這是假話,給不了柿花一點(diǎn)安慰。
“棵子哥,你聰明,有本事,就你耍那兩面臉,人見(jiàn)人愛(ài),俺好喜歡……你哩……”柿花說(shuō)著,就朝林棵子這邊移過(guò)來(lái)。“俺知道你是好人,俺搭眼一瞧就知道你是好人……棵子哥,你可憐可憐妹子……”
林棵子想轉(zhuǎn)身離開(kāi),卻像被施了定身法,兩只腳生根似的長(zhǎng)在地上。雜樹(shù)林里好寂靜,也好寂寞,連枝頭的風(fēng)都是寂靜的,連草叢中的蟲(chóng)叫聲都是寂寞的。柿花慢慢向他移來(lái),他聽(tīng)見(jiàn)她出氣的聲音了;柿花朝他貼過(guò)來(lái),他聞到她熱乎乎的肉味了;柿花依到他懷里了,他感到她軟軟的身子了……林棵子使勁眨眨眼,喉結(jié)猛地躥上去,攔腰抱緊了她,喉結(jié)又緩緩地移下來(lái),他使勁咽了一口唾沫,也伸手抱緊了柿花——兩個(gè)身子糾纏著,離開(kāi)小路,朝雜木叢后邊移去。
四周已經(jīng)黑了,天上有云,看不見(jiàn)一粒星星,應(yīng)該還有月亮,卻是個(gè)啞巴月亮。咸水坡的夜靜得出奇,好像整個(gè)世界都死了一樣。他們擁抱著,也一同向死亡走去。不過(guò),眼下他們還沒(méi)有死,他們還能說(shuō)話。
“棵子哥……”柿花叫了一聲。
“柿花……”林棵子也叫了一聲。
他聽(tīng)到柿花撩人的喘氣聲,也聽(tīng)到了自己的心跳聲。他覺(jué)得自己色膽包天,他已經(jīng)什么也顧不得了,一面低頭急急親吻柿花的臉蛋、眉眼、嘴唇、脖子,一面手忙腳亂地剝她的衣服。
柿花先是輕輕地呻吟,忽然“啊”了一聲。林棵子感覺(jué)到她這一聲叫得有些大,未等他從熱烈中反應(yīng)過(guò)來(lái),這叫聲像號(hào)令一般引來(lái)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聲音:
“狗日的,欺侮到老子頭上了!”
是金連山在喊。跟著是幾聲馬嘶。
隨著這人喊馬叫,柿花猛地推開(kāi)林棵子,返身向坡下跑去,很快隱在了夜幕中。
林棵子不知所措,一時(shí)還在那愣怔著。
金家七八個(gè)家丁撲過(guò)來(lái),扭住了林棵子。
“狗日的,吃了豹子膽,竟敢勾引我金連山家媳婦!”金連山嘶啞著嗓子喊,“綁了他,給我拖回去!”
“啪啪”,又是兩記狠狠的耳光。
林棵子鼻子立時(shí)酸麻發(fā)熱,他倒吸一口氣,一股咸腥味便進(jìn)了口腔。也顧不上疼了,趁家丁往他身上搭繩子的工夫,他奮力掙脫,一頭沖進(jìn)了黑暗里。
金連山和家丁們沒(méi)有追到他。
其實(shí),林棵子并沒(méi)有跑遠(yuǎn),他知道他就是跑得再快,也跑不過(guò)金家的馬蹄子,循著他的腳步聲,幾匹快馬很快就會(huì)追上他。林棵子沖出雜樹(shù)林,沖進(jìn)柿樹(shù)林,從一處斷崖上溜下去,就聽(tīng)見(jiàn)羊們的叫聲,不遠(yuǎn)處便是鞭子爺?shù)难蛉Α?/p>
“爺,救我,金連山要害我哩……”林棵子闖進(jìn)鞭子爺?shù)母G洞,結(jié)結(jié)巴巴對(duì)鞭子爺說(shuō)著他跟柿花的事。
他還沒(méi)有說(shuō)清楚,鞭子爺已經(jīng)聽(tīng)明白了,說(shuō):“怪不得傍黑時(shí)見(jiàn)金連山領(lǐng)人藏在坡上哩……”
一邊說(shuō)著一邊把林棵子推進(jìn)窯洞深處,讓他藏進(jìn)一個(gè)拐窯里,說(shuō):“你中了人家圈套了。”
林棵子腦袋嗡了一聲,反應(yīng)過(guò)來(lái)——他想起金連山要他那二畝地的事。
一陣馬蹄聲從窯頂上過(guò)去了。
過(guò)了一會(huì)兒,一陣馬蹄聲又停在窯前了。
金連山和家丁走進(jìn)窯里,問(wèn)鞭子爺:“你看沒(méi)看見(jiàn)林棵子那狗日的?”
鞭子爺吧嗒著旱煙袋,說(shuō):“這三更半夜的,我連個(gè)鬼影都沒(méi)見(jiàn)著。”
金連山狐疑地朝窯洞深處看了看,一只公羊正日急馬慌往一只母羊身上爬,母羊不愿意,屁股掉來(lái)掉去;別的羊們倒著沫,不屑一顧的樣子。
金連山?jīng)]看出蹊蹺,帶著家丁走了。
鞭子爺把林棵子叫出來(lái),嘆了口氣說(shuō):
“走吧,你咋是金連山的對(duì)手?留得青山在,不愁沒(méi)柴火。走吧,走得越遠(yuǎn)越好。”
林棵子返身又上了咸水坡。他捧起咸水泉清涼的水洗凈臉上的血污,踏著坡頂?shù)耐谅纷吡耍哌M(jìn)了無(wú)邊無(wú)際的山巒。
第二天,金連山去了林棵子家,說(shuō)林棵子強(qiáng)奸了柿花,要林棵子他爹交出林棵子,不然子罪父頂,就把林棵子他爹送官。別說(shuō)林棵子他爹交不出兒子,就是能交他也不會(huì)交的,他不相信兒子會(huì)做出那種事,可偏偏兒子又跑得無(wú)影無(wú)蹤,真是個(gè)有口難辯。老人害怕打官司坐牢,羞愧無(wú)奈,一根麻繩把自己吊死在咸水泉邊那棵鬼臉青柿樹(shù)上。兒子跑了,老子死了,金連山借機(jī)霸占了林家那二畝風(fēng)水寶地。
沒(méi)過(guò)幾天,金連山就把他祖宗幾代從老墳里挖了出來(lái),重新裝殮,大大小小十四副棺木擺在金家門(mén)前的靈棚里。鼓樂(lè)班吹吹打打,金連山一家披麻戴孝,三牲供奉,九叩跪拜,一番隆重祭祀,祖宗們被抬到新看的墳地里。正待入土下葬,突然,從柿樹(shù)林“叭叭”傳來(lái)兩聲槍響,有兩個(gè)靈牌被打倒了。鼓樂(lè)班和送葬的人驚恐不已,四散逃去。金連山命家丁去柿樹(shù)林搜尋,又是幾聲槍響,走在前邊的兩個(gè)家丁各自捂著血淋淋的耳朵,丟了槍,哭嚎著回頭逃竄。
唯有金連山和他那傻兒子原地站著動(dòng)彈不得,子彈冰雹一樣往這邊落,卻都打在他們的前后左右,尖叫著“噗噗”鉆進(jìn)土里,沒(méi)有逃路,寸步難移。柿花躲在一口棺材后邊,雙手抱頭,嚇得渾身瑟瑟發(fā)抖。
原來(lái)林棵子受了冤屈,走投無(wú)路,就跑到后山,找到土匪頭兒王豁子,向他訴說(shuō)了自己的冤情。王豁子向來(lái)喜歡林棵子的“兩面臉”,答應(yīng)替他洗清不白之冤。打聽(tīng)到金連山遷墳的日子,就帶領(lǐng)土匪下山了。
林棵子提著盒子槍從柿樹(shù)林里竄出來(lái),來(lái)到金連山跟前,將灼熱的槍口頂緊在金連山的禿腦門(mén)上。金連山立馬癱軟,連連求饒:“棵子,賢侄,饒我一條命吧……”
柿花看到林棵子,嚇得“啊”地尖叫一聲,尿了一褲襠。林棵子稍一愣神,撇下金連山,轉(zhuǎn)身挾了柿花,返身跑上北坡鉆進(jìn)了柿樹(shù)林,“撲咚”一聲,把她丟在草地上。
“棵子哥,饒命……”柿花蒼白著臉說(shuō)。
“他金家祖上設(shè)套昧了我林家的家產(chǎn),到如今你們又設(shè)局坑我,我豈能饒你!”林棵子咬牙切齒地說(shuō)。
“棵子哥,是俺公公叫俺那樣做的,俺不敢不答應(yīng)啊……”
“你公公,那豬狗不如的扒灰佬兒,你們沒(méi)一個(gè)好東西!”金棵子收了槍,“說(shuō),為什么要陷害我?”
柿花瑟縮著身子說(shuō):“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那傻子,他不會(huì)給俺娃,公公便跪下求俺,說(shuō),金家不能斷香火,只要遷了祖墳,我就能懷上孩子。俺依了公公的話,這才騙你上當(dāng)……”
“你跟金連山做那丑事當(dāng)我不知道?”林棵子鐵青個(gè)臉,“像你這種騷貨,活在世上也是禍害人,我今兒就替咸水村清除你這個(gè)害人精!”
“叭!”隨著槍響,柿花歪倒在草地上。
林棵子“哎喲”一聲,他手上淌著血,手里的盒子槍也落在地上。
土匪頭子王豁子站在一棵柿樹(shù)下,看著林棵子:“你真是個(gè)兩面臉,為啥不殺金連山卻要?dú)⒁粋€(gè)女人?”
“女人是禍根,我先殺這騷貨,再殺金連山!”林棵子說(shuō)。
“我從來(lái)不殺女人,況且,咱說(shuō)好的,這女人歸我,不然我也不會(huì)跟你蹚這趟渾水。”王豁子很不高興。
他說(shuō)著,走上前來(lái),扛起昏死過(guò)去的柿花,把她搭在馬背上,跟著飛身上馬,風(fēng)也似的卷出了柿樹(shù)林……
又過(guò)了兩年。土改時(shí),金連山和林棵子都被鎮(zhèn)壓了。
金連山是惡霸地主,欺男霸女,十惡不赦;林棵子的罪名是土匪,助紂為虐,為害鄉(xiāng)里。林棵子死時(shí),子彈把他的腦瓜蓋揭開(kāi)了,血糊糊的腦汁流出來(lái),再也分不清前臉和后臉。
大奶兒
樹(shù)枝光禿禿、麥苗綠油油的時(shí)候,沒(méi)結(jié)婚的小伙子們無(wú)聊地抄著手閑轉(zhuǎn),或起哄看狗咬架;而結(jié)過(guò)婚的男人晚上把勁兒用在了女人的肚皮上,白天則無(wú)精打采地坐在門(mén)檻上犯愣怔、打瞌睡;在街墻下曬暖兒的婆娘們,兩手忙不停地納鞋,一邊把線繩拉得呲溜呲溜響,一邊東拉西扯,扯著扯著,話題就扯到了大奶兒。
“咱哪能和人家大奶兒比。咱出嫁時(shí),頂破天坐個(gè)三套馬車就謝天謝地。人家,嘖嘖,屁股值錢(qián),坐八抬大轎娶來(lái)的,美得騰云一樣,那氣派勁,那景陣,哎喲喲,饞死人啦。”香菊把頭搖得像撥浪鼓。
大奶兒并非她的真名,也談不上多俊俏,那臉蛋兒卻很耐看,最招人的是那倆大奶子,走起路來(lái)像兩只活蹦亂跳的兔子,不彎腰看不見(jiàn)腳尖兒。人們像發(fā)現(xiàn)了奇跡,驚得無(wú)數(shù)雙眼睛放光:“媽喲,這倆大奶兒!”從此,“大奶兒”便取代了她的名字。“大奶兒”的原名叫什么,人們已經(jīng)不記得了。
點(diǎn)兒在一旁“噗噗”吐著瓜子皮,揶揄道:“人家奶子大,招男人喜歡。眼氣啦?回家叫我可勁吹,說(shuō)不定也能吹起倆豬尿脬呢。”
點(diǎn)兒是隊(duì)長(zhǎng)麻子的獨(dú)生女,嬌生慣養(yǎng),從來(lái)不用做針線,閑下來(lái)就“噗噗”地嗑瓜子。
香菊伸手打了一下點(diǎn)兒,說(shuō):“死妮子,還沒(méi)結(jié)婚就敢胡吣,也不害羞啊。”
點(diǎn)兒躲了一下,說(shuō):“俺沒(méi)吃過(guò)豬肉,還沒(méi)見(jiàn)過(guò)豬走?就那倆肉疙瘩,誰(shuí)還沒(méi)有?”
幾個(gè)女人發(fā)出放肆的笑聲,像幾只老鴰炸了窩,啥調(diào)都有。說(shuō),咱有是有,最多也就兩個(gè)茄子,人家大奶兒那可是大葫蘆,裝著迷魂湯哩,要不能把亮寶迷得神魂顛倒的?要不人家能叫大奶兒?
說(shuō)實(shí)話,亮寶能娶到大奶兒做媳婦,可真是祖宗八輩子燒了高香。
村上人誰(shuí)也沒(méi)見(jiàn)過(guò)亮寶他媽。他爹是村里的“悶子”,一年到頭趕著個(gè)驢車給礦上運(yùn)煤,要說(shuō),這在那個(gè)年代屬于投機(jī)倒把,政策是不允許的,可悶子不知走了哪個(gè)門(mén)路,從公社開(kāi)了介紹信,拉一天煤,給隊(duì)里繳五塊錢(qián),麻子也就沒(méi)話說(shuō)了。村里人說(shuō),“小毛驢一拉。十五塊到家,五塊錢(qián)交隊(duì),十塊錢(qián)自花”,日子過(guò)得跟神仙似的。只是在村人眼里,終究不算個(gè)正經(jīng)營(yíng)生,加上四處漂泊,居無(wú)定所,一直沒(méi)人給他說(shuō)親,悶子也就終身沒(méi)娶。有一年,悶子冷不丁從外面領(lǐng)回了個(gè)半大小子,叫亮寶,說(shuō)是他的兒子。村里人這才知道悶子不悶,這孩子保準(zhǔn)是他在外邊尋花問(wèn)柳結(jié)的果。悶子請(qǐng)了大隊(duì)干部的客,亮寶就有了戶口。
亮寶身子瘦弱,倆小眼整天瞇著像沒(méi)睡醒,還不停吸溜鼻涕,像漏粉條。二十大幾了,挑一擔(dān)水都累得像拉風(fēng)箱一樣直喘粗氣。這個(gè)球樣兒,村里年輕女子正眼都不看他一下。
悶子給媒婆鳳仙送去了二尺燈芯絨,請(qǐng)她給亮寶說(shuō)親,說(shuō)不管誰(shuí)家閨女,有啥要求就是傾家蕩產(chǎn)也滿足,并用大轎迎親,還保證親事定下,一定重禮酬謝媒人。都說(shuō)跑堂的腿,媒婆的嘴,鳳仙不知使了什么巧計(jì),果然給亮寶定下一門(mén)親事,新媳婦就是大奶兒。
大奶兒娶過(guò)來(lái)那天,的確風(fēng)光得讓人眼饞——轎前是“二踢腳”開(kāi)道,轎后有“響十里”鼓樂(lè)班壓陣,轎兩側(cè)是夾著紅氈的“護(hù)神”,前呼后擁,鞭炮齊鳴,鑼鼓喧天,八抬大轎下了山,走過(guò)了咸水坡那條土路,抬進(jìn)了咸水村。
大奶兒過(guò)門(mén)后,亮寶再也不四處閑逛了,整天守在家里,像媳婦的跟屁蟲(chóng)。雖然還是懶,可大奶兒能哄轉(zhuǎn)他。結(jié)婚后的第一個(gè)中秋節(jié),悶子準(zhǔn)備了兩挑子禮物,讓小兩口走娘家,亮寶哼哼嘰嘰不想挑,大奶兒就編了個(gè)順口溜哄他:“八月十五去瞧娘,叫聲亮寶你挑上。還未上路先別慌,走到路上你先嘗。吃柿子先吃羊果紅,吃梨先吃馬蹄黃。”
“挑上就挑上,路上咱先嘗。”亮寶歡喜得很,美滋滋兒挑起了擔(dān)子,“吱扭,吱扭”跟媳婦上了路。
一年后,大奶兒便給亮寶生了兒子。悶子做了爺,高興過(guò)度,喝孫子的滿月酒時(shí),有點(diǎn)放肆,結(jié)果嗚呼著命歸了黃泉。
大奶兒的奶水像坡底那個(gè)咸水泉,兒子吃不完,常常憋得她難受,就叫亮寶吃。一開(kāi)始亮寶不吃,大奶兒說(shuō),我憋得難受,你不吃我可叫別人吃了。亮寶想了想,肥水還不流外人田哩,何況這是他媳婦的奶水啊。就吃了。這一吃,就上癮了,他跟兒子一人抱著一個(gè)奶葫蘆,吃得嘖嘖有聲。兒子養(yǎng)得白胖,可亮寶仍舊精瘦精瘦的。不過(guò),在那事兒上亮寶卻有使不完的勁——兒子吃著吃著就睡著了,亮寶吃著吃著就來(lái)了精神,這樣,大奶兒不停頓連生了三男三女六張嘴兒。
這讓隊(duì)長(zhǎng)麻子很是眼饞。
麻子媳婦肚子不爭(zhēng)氣,生下點(diǎn)兒這唯一的閨女,十幾年便再?zèng)]有見(jiàn)她肚子鼓起過(guò)。人都說(shuō)她有月子病而且性冷淡,有了點(diǎn)兒以后,她跟女兒睡一個(gè)屋,從來(lái)不讓麻子沾她的身子。麻子當(dāng)著隊(duì)長(zhǎng),是個(gè)一手遮天的人物,就不免干些偷雞摸狗的勾當(dāng)。麻子的臉上盡是麻子。坑坑洼洼里像灌滿了油水,亮汪汪的;鼻子小而紅,像個(gè)剛從油鍋里炸出來(lái)的小肉丸;頭大脖子粗,腦后肉嘟嘟的叫人分不清脖子和后腦勺。要說(shuō)這相貌實(shí)在不招女人喜歡,可大集體的時(shí)候,工分兒工分兒,社員的命根兒,他手里捏著全隊(duì)的命根兒哩;何況,他腰里還有一串鑰匙,生產(chǎn)隊(duì)倉(cāng)庫(kù)里的油啊糧啊,都在他腰上別著哩。所以,他很有底氣,隊(duì)里稍有姿色的女人,幾乎都被麻子不同程度地占過(guò)便宜。唯有大奶兒,麻子眼饞已久卻無(wú)機(jī)會(huì)下手,暗里不知咽過(guò)多少口水。
村里有個(gè)復(fù)員兵叫狗旦,他剛一回村,就把一頂“的確涼”綠軍帽送給了麻子,麻子戴了那頂軍帽,村里村外招搖了一天,就任命狗旦當(dāng)了生產(chǎn)隊(duì)的記工員。
又是一季秋風(fēng)涼。摘罷坡北的柿子,人們又轉(zhuǎn)到南坡收棉花。這活兒同往常一樣,隊(duì)里的婦女除麻子老婆以外,全都會(huì)積極出工。十幾個(gè)女人穿行在碧波蕩漾的棉田里,頭上頂著各色的頭巾,腰里系著各色的包袱,靈巧的手指在棉花叢中蜻蜓點(diǎn)水一般,潔白的棉花像蝴蝶一樣,張著翅膀一朵一朵飛進(jìn)她們腰間的包袱里。
傍晚收了工,女人們陸續(xù)向地頭走來(lái)。一個(gè)下午過(guò)去,個(gè)個(gè)都像吃了化肥一樣,陡然胖了一圈,腿粗得像檁條,腰粗得像水桶,屁股肥得草篩子。她們走得小心翼翼,好像喝醉了酒的鴨子。女人們走到地頭,從腰間解下包袱,等著讓麻子過(guò)了秤,然后倒進(jìn)一個(gè)大布袋里。
麻子神色忽兒變得陰沉起來(lái)。他一一給女人們稱了斤兩,讓狗旦登記了,然后說(shuō):“狗旦,你們幾個(gè)把棉花拉回去。”
狗旦拉著車子走后,麻子照例把十幾個(gè)女人巡視了一遍,目光如刃,女人感到都被刮掉了一層皮,紛紛縮緊了身子。麻子咬咬牙說(shuō):“香菊、大奶兒你倆留下,別的人可以走了。”
女人們像得到了大赦,雖然還是很小心,卻明顯加快了腳步。麻子讓誰(shuí)走、讓誰(shuí)留,他心里是有數(shù)的,這天,輪到了香菊和大奶兒。香菊對(duì)麻子的意圖早已領(lǐng)教過(guò),一屁股坐在田埂上,死豬不怕熱水燙的樣子;大奶兒仍然站著,瞇著眼看天上的夕陽(yáng),很從容。
“香菊,褲襠里塞的花掏出來(lái)吧。”麻子說(shuō)。
“前天才掏過(guò),咋今又讓我掏?”香菊嘟囔著說(shuō)。
“什么叫前天?我心里有數(shù),七天了。”麻子說(shuō)得很肯定。
那時(shí)候,棉花屬于統(tǒng)購(gòu)統(tǒng)銷,絕大部分都得上繳國(guó)家,國(guó)家換算成布票,再發(fā)給社員,生產(chǎn)隊(duì)留下一小部分籽棉,統(tǒng)一軋成皮棉,按人頭分到每家每戶,做棉衣被褥。可實(shí)在是太少了,也只夠做棉衣被褥,要想紡花織布,就得想辦法。雖然發(fā)了布票可以買(mǎi)洋布,可那得花錢(qián)哩,誰(shuí)家有那閑錢(qián)?
麻子知道,每個(gè)女人身上都藏的有棉花,他可以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卻不能把兩只眼睛都閉上。他只有兩只眼,所以,每天只留兩個(gè)人。
香菊撇了撇嘴,極不情愿地把褲腰里、褲襠里、褲腿里的棉花都掏了出來(lái),堆到地頭,然后拍著屁股上的灰走了。她的身材一下子苗條了一圈。
待香菊轉(zhuǎn)過(guò)遠(yuǎn)處那道土堰后,麻子走到了大奶兒面前,望著她的胸脯,他喉結(jié)滾動(dòng)了一下,臉上的麻子都紅了。
大奶兒的心狂跳起來(lái),她想,今兒怕是逃不過(guò)去了。
“那里面裝的不光是倆大奶吧?”麻子色瞇瞇地看著她的胸脯說(shuō)。
大奶兒急忙用手護(hù)住胸脯,往后退避著,說(shuō):“你知道,我從來(lái)不偷花的……”
“從來(lái)不偷?你要不偷你那六個(gè)孩子八口人能過(guò)去冬天?”麻子嘴角掛著笑。
“我真的沒(méi)偷,不信你問(wèn)問(wèn)她們……”大奶兒覺(jué)得很冤枉。
大奶兒說(shuō)的是實(shí)話。她本來(lái)也想學(xué)著別人偷棉花,可自從發(fā)現(xiàn)麻子別有用心,就一次也沒(méi)偷過(guò)。這些年,家里棉衣棉被、紡花織布,都是亮寶從黑市上買(mǎi)花。她公公死了,可小毛驢留下的家底還在。
“我不問(wèn)她們,我就想親手摸摸。”他雙手向大奶兒的胸脯抓去,“嘻嘻,你別怕,叫我摸摸,這么大啊……”
“你……別、別,我自己來(lái)。”大奶兒又退了一步,一只手放到了胸口上。
“哎,這就是了,你懂事,我不會(huì)叫你吃虧的。”麻子滿意地笑了,“你身上的花,還有香菊這堆花,都拿回家,以后,我也會(huì)照顧你的。”
大奶兒的手在胸口停了一下,終于還是解開(kāi)了扣子,她把布衫往兩邊一扯,說(shuō),“你看,我真沒(méi)偷花……”
大奶兒的布衫扯開(kāi)了,麻子的眼皮也扯開(kāi)了。可他沒(méi)有看見(jiàn)大奶兒的大奶,他看見(jiàn)的是兜著兩個(gè)大奶的小背心。雖然隔著小背心,那兩個(gè)大奶還是像受驚的兔子,呼之欲出。
“嗬!”麻子叫了一聲,撲了上去,“叫我吃一口……”
“噢——”大奶兒也叫了一聲,驚慌后退,棉花棵子把她絆倒了……
夕陽(yáng)西下,四野一片寂靜,蚰子在半人高的棉花棵子地里急急地叫著,聲聲不歇。
土堰后有個(gè)人突然探了一下頭,又迅即隱去。
第二天,人們上工時(shí),聽(tīng)到這么一個(gè)消息——大奶兒手腳一貫不干凈,昨天又偷了隊(duì)里棉花,被隊(duì)長(zhǎng)發(fā)現(xiàn)。害怕追究查辦,吊死在咸水坡那棵歪脖子鬼臉青柿樹(shù)上了。證明人是生產(chǎn)隊(duì)記工員狗旦。
就在大奶兒死后不久的一個(gè)傍晚,從街上傳來(lái)亮寶的吆喝聲。滿街筒子都是人,亮寶用竹竿抖動(dòng)著一條女人的花褲衩和一條軍用褲頭,向圍觀的鄉(xiāng)親們噴著唾沫星子大聲說(shuō)著:“嘿呀,一樁風(fēng)流事呀。點(diǎn)兒和狗旦一身凈光在倉(cāng)庫(kù)棉花垛里耍哩,叫我鎖到倉(cāng)庫(kù)里啦,快去看哪!”
人們都跑去了,沒(méi)看到赤身裸體的點(diǎn)兒和狗旦,他們用兩個(gè)裝棉花的大袋子,把自己裝了起來(lái),只有腦袋露在外面。但點(diǎn)兒一點(diǎn)也不慌張,她說(shuō):“他孤著,我單著,我們自由戀愛(ài)哩,咋啦?”又說(shuō),“我愿意嫁給狗旦,咋,丟你們先人啦?”
人們覺(jué)得很沒(méi)趣。想想也是,年輕人烈火干柴的,沒(méi)忍住,這也不算多丟人。
然而,麻子不愿意點(diǎn)兒嫁給狗旦,他覺(jué)得點(diǎn)兒丟了他的人,狠狠地打了點(diǎn)兒兩耳光,當(dāng)場(chǎng)就撤了狗旦的記工員職務(wù)。
第二天,點(diǎn)兒吊死在咸水坡一棵柿樹(shù)上。就是大奶兒上吊的那棵歪脖子鬼臉青柿樹(shù),那根麻繩還在,好像專門(mén)給點(diǎn)兒預(yù)備的。
悠晃仙兒
麥子割完了,場(chǎng)光地凈,該上繳的上繳,該分的早已分到了各家各戶。蛙在鼓噪,蟬在長(zhǎng)鳴。“悠晃仙兒”胡長(zhǎng)生在街上喊:“下大
啦,麥罷啦,赤肚子娃子長(zhǎng)大啦……”
在院子里睡覺(jué)的隊(duì)長(zhǎng)麻子蒙眬中睜開(kāi)眼看天,銀河依舊橫在當(dāng)空,明晃晃的月亮懸在天上,星星也似乎一個(gè)不比昨晚少。習(xí)習(xí)涼風(fēng)吹來(lái),麻子翻了個(gè)身,又睡著了。
“下大了,麥罷啦,赤肚子娃子長(zhǎng)大啦……”聲音由強(qiáng)到弱,漸漸遠(yuǎn)去。
不大一會(huì)兒,便有豆大的雨點(diǎn)砸在麻子的臉上。他打了個(gè)激靈,睜眼再看天上,陰得黑鍋底一般,大雨已經(jīng)密了起來(lái)。曬在平房上的麥子被淋了個(gè)透濕;那些睡在平房上的人們也都趕回了屋里。
第二天早上,麻子在村口瞅見(jiàn)胡長(zhǎng)生來(lái)了,問(wèn):“昨晚又喝酒了吧?”
“那是自然。”胡長(zhǎng)生答。
“夜黑你在街上瞎雞巴吆喝,你咋不催老少爺兒們快起來(lái)收拾麥子?”麻子說(shuō)。
胡長(zhǎng)生兩眼一片茫然,說(shuō):“夜黑下雨
啦?我說(shuō)我的衣裳咋透了……”
他竟忘了昨晚的喊叫,也不知下雨了。
麻子無(wú)奈地?fù)u搖頭,咕噥道:“你呀,可真是個(gè)悠晃仙兒。”
“悠晃仙兒”是胡長(zhǎng)生的外號(hào)。他長(zhǎng)得人高馬大,嗜酒如命,量卻不大,沾酒就醉。人們知道他這么個(gè)毛病,都想戒了他的酒。可是誰(shuí)家若有了紅白事,他一樁不落都會(huì)去幫忙。勤勤快快,也極有眼色,掃地、抹桌、挑水和煤、搬凳、擇菜、刷碗、端盤(pán)……臟活累活搶著干,就是再嫌棄,也不忍心轟他走。紅白事斷不了喝酒,胡長(zhǎng)生忙完,定會(huì)在酒桌上同人喝個(gè)痛快。
但并不是每天都有紅白事,胡長(zhǎng)生的酒癮得不到滿足,就去大隊(duì)小隊(duì)干部家里悠晃。他知道大小是個(gè)官,手里就有權(quán),別人求情或感謝時(shí)就免不了送禮。禮品中酒居多,且必定是好酒。干部們知道胡長(zhǎng)生這個(gè)毛病,就把酒藏起來(lái)。但不管藏到哪里,都瞞不過(guò)胡長(zhǎng)生的鼻子,想喝,照樣能偷出來(lái)喝。喝了人家酒,無(wú)論明里暗里,只要主人家不提,胡長(zhǎng)生絕不露一個(gè)字。干部們很欣賞胡長(zhǎng)生這一點(diǎn)。
胡長(zhǎng)生喝酒卻從不發(fā)酒瘋,喝醉了,就滿世界悠晃,唱稀奇古怪的小曲兒——莊稼地、溝坎邊,窯洞里、麥秸垛、柿樹(shù)林……無(wú)處不去,仙人般行蹤不定。
大小是個(gè)村,都有偷雞摸狗的齷齪事。有時(shí)候家里不方便,相好們就會(huì)到野外偷情幽會(huì)。但胡長(zhǎng)生撞上了,從來(lái)目不斜視,甚至目中無(wú)人。時(shí)過(guò)境遷,便有心虛之人試探他,說(shuō):“悠晃仙兒,你昨黑在排灌站干水溝看見(jiàn)啥啦?”胡長(zhǎng)生做若有所思狀,少頃,又一副不可思議的神態(tài),說(shuō):“我去那兒干啥哩?有那工夫還不如喝二兩酒哩。”問(wèn)者若是還不放心,便會(huì)弄瓶酒給他喝,想以此堵住他的嘴,自己也好去塊心病。
也不全是這樣,有一次胡長(zhǎng)生仙游時(shí),還救過(guò)兩條人命——
天氣漸漸涼下來(lái),覆蓋整個(gè)咸水坡上的柿葉由青綠變淡黃、由淡黃變淺紅、由淺紅變醬紫。若有風(fēng)兒吹過(guò),整架坡的柿葉兒搖搖曳曳,閃閃爍爍,像燃燒的火焰一般。灼得咸水村的男女老少們心里直發(fā)熱。
這時(shí)候就該漤柿子了。
滿倉(cāng)媳婦腆著個(gè)大肚子,趁晌午來(lái)到咸水坡,她想摘些“鬼臉青”,漤了給她的孩子們吃。她已經(jīng)生了四個(gè)女娃兒,老大不到十歲,老四才兩歲,家里吃閑飯的多,能干活的少,糧食總是不夠,每年她都要漤很多柿子來(lái)填補(bǔ)那些轆轆饑腸。所有的柿子里,她最喜歡“鬼臉青”,這種柿了樣子不好看,皮厚,泛著青灰色,可它肉多、味甜也耐放,漤柿子能吃到秋罷,曬成柿餅拌上麩皮雜糧,蒸窩頭比玉米面饃好吃多了。再者,咸水坡還有一說(shuō),“漤了鬼臉青,一年走順風(fēng)。大鬼不來(lái)纏,小鬼無(wú)影蹤”。她就是圖個(gè)吉利,去個(gè)心病。滿倉(cāng)兩口子一直有塊心病,生了四個(gè)娃,卻都是女娃。在鄉(xiāng)下,沒(méi)個(gè)男娃兒總是頂不起門(mén)戶,所以,不生男娃兒誓不罷休。眼下,她又懷上了,她希望這次能生個(gè)男娃。
那天,滿倉(cāng)媳婦拽住一枝“鬼臉青”柿子,用力壓下來(lái),誰(shuí)知道用力過(guò)猛,手還未摘到柿子,樹(shù)枝就斷了,腳下失去平衡,身子就倒在地上,順坡打了幾個(gè)滾,幸虧有棵柿樹(shù)攔住了,才沒(méi)出大事。
當(dāng)她想要爬起來(lái)時(shí),忽覺(jué)兩腿間有熱乎乎的東西流出。感覺(jué)不妙時(shí),已生出來(lái)了一個(gè)男孩。這荒天野地的,連個(gè)人影都沒(méi)有,滿倉(cāng)媳婦一下子慌了神,絕望地喊叫起來(lái)。
趕巧,胡長(zhǎng)生又喝醉了,逛到了咸水坡,嘴里破喉嚨爛嗓門(mén)地唱:“日頭落,狼下坡,逮住男娃當(dāng)蒸饃,逮住女娃當(dāng)湯喝……”正唱著,聽(tīng)見(jiàn)女人的喊叫,扭頭一看,見(jiàn)滿倉(cāng)媳婦躺在柿樹(shù)下,褲子已退到了腳脖兒,露著白花花的大屁股。他以為滿倉(cāng)媳婦跟誰(shuí)在干見(jiàn)不得人的事,若是往常,他也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扭扭臉過(guò)去了,可轉(zhuǎn)念又想,要是干那事,肯定不會(huì)不管不顧地亂叫,就躲閃著,靠近了一些,這一看,就看見(jiàn)了大事——滿倉(cāng)媳婦佝僂著身子,手里捧著個(gè)血淋呼啦的孩子。
他酒醒了大半,幾步跑上前去,問(wèn):“嫂
子,你這是咋啦?”
“生了,快,你快點(diǎn)啊……”滿倉(cāng)媳婦叫。
胡長(zhǎng)生卻快不了。他三十大幾了還沒(méi)有媳婦,更不知道如何面對(duì)女人生孩子。情急之下,也顧不得許多了,彎下腰去,連大人帶孩子抱了起來(lái),飛快地跑回村里。
大人孩子揀了兩條命,滿倉(cāng)很感激,給胡長(zhǎng)生買(mǎi)了兩瓶好酒表示謝意,還讓胡長(zhǎng)生給孩子取名。胡長(zhǎng)生說(shuō):“該你幸運(yùn),總算得了個(gè)男娃,五個(gè)了,不敢再生了,這娃兒就叫鎖住吧。”
當(dāng)然不能叫鎖住,就叫了“鎖柱”。不過(guò),滿倉(cāng)媳婦還是去做了結(jié)扎手術(shù),她把自己徹底給鎖住了。
胡長(zhǎng)生喝醉酒,還有一個(gè)嗜好,就是用渾身力氣跟村里的石頭作對(duì)。晚上人們睡下后,胡長(zhǎng)生在村街上悠晃,身上躁得慌,就搬各家各戶門(mén)口的墊腳石玩兒——常常是把這家的墊腳石搬到那家,又把那家的搬到另外一家。有時(shí)幾家,有時(shí)十幾家,墊腳石被他差三隔五地給搬來(lái)?yè)Q去。久了,誰(shuí)也不說(shuō)啥,任他來(lái)回?fù)Q,反正過(guò)不了多久,墊腳石自然會(huì)再回到自家門(mén)前。
但白天下地干活,胡長(zhǎng)生從不耽誤,也從不惜力。有人問(wèn),悠晃仙兒,你搬了一夜石頭,也不累啊?胡長(zhǎng)生像受了冤枉,說(shuō):“我閑著沒(méi)事啦,搬什么石頭?”
說(shuō)是這么說(shuō),胡長(zhǎng)生喝醉了酒,夜里依舊搬石頭。那一次,不知有心還是無(wú)意,他可把麻子坑苦了。
村人都知道麻子跟香菊不清不楚,但人們都心照不宣。看透不說(shuō)透,還是好朋友,何況,人家男人都不說(shuō)啥,也用不著別人多嘴多舌;更何況,麻子當(dāng)著隊(duì)長(zhǎng),得罪了麻子,可沒(méi)好果子吃。
那天,香菊的男人被麻子派去縣上給隊(duì)里買(mǎi)抽水機(jī)零件,路途遠(yuǎn),當(dāng)天打不了來(lái)回,就得在城里隔一夜。當(dāng)天夜里,麻子便躡手躡腳閃進(jìn)了香菊家的院門(mén)。
麻子前腳進(jìn)了香菊家,胡長(zhǎng)生后腳就進(jìn)了麻子家。他好像進(jìn)了自己家一樣,熟門(mén)熟路地摸到存放糧食的廂房屋,從糧囤里摸出一瓶酒。其實(shí),糧囤里的酒可不止一瓶,但胡長(zhǎng)生只拿了一瓶,他是酒仙兒,又不是小偷,一瓶酒就足夠他喝了。
麻子跟香菊在炕上騰云駕霧時(shí),胡長(zhǎng)生靠在糧囤上也喝了個(gè)騰云駕霧,三個(gè)人各得其所,也各得其樂(lè)。然后,胡長(zhǎng)生從麻子家走了出來(lái),出門(mén)時(shí)他趔趄了一下,發(fā)現(xiàn)門(mén)口的墊腳石沒(méi)有了。他覺(jué)得隊(duì)長(zhǎng)家不能沒(méi)有墊腳石,寬門(mén)臉兒,高門(mén)檻兒,麻子怎么說(shuō)也是個(gè)官人,沒(méi)個(gè)墊腳石像什么樣子?于是四下脧摸,就瞅見(jiàn)斜對(duì)門(mén)香菊家門(mén)口那塊石頭。走上前去,雙手對(duì)角摳住石頭底下,沒(méi)費(fèi)多大勁,就搬了起來(lái)。他把那塊石頭搬到麻子家門(mén)口,往下一放,不大不小,剛好合適。他嘿嘿笑了,這石頭好像就是給麻子準(zhǔn)備的一樣。其實(shí)是他忘記了,幾天前正是他把這塊石頭搬到香菊家門(mén)口的。那時(shí)候他想的是,好你個(gè)麻子,你占了人家香菊的便宜,不能一點(diǎn)表示都沒(méi)有,你這塊墊腳石算是給人家香菊的報(bào)酬吧。現(xiàn)在,他又把“報(bào)酬”搬了回來(lái)。
麻子和香菊折騰了大半夜,都盡了興,麻子才從香菊家出來(lái)。他打開(kāi)院門(mén),先把頭從門(mén)縫里探出,前后左右瞧瞧,連個(gè)人影都沒(méi)有。遠(yuǎn)處傳來(lái)胡長(zhǎng)生的吼唱:“張家麥,李家籮,王家嫂子烙餅饃,送給對(duì)門(mén)的趙大哥……”麻子想,這貨又喝多了。又想,說(shuō)來(lái)長(zhǎng)生也是個(gè)可憐人,三十多了還是光棍一條,要是有個(gè)女人,誰(shuí)愿意喝那口馬尿?喝醉了大半夜四處亂逛?唉,可憐人哩,回頭有合適的,無(wú)論如何得給長(zhǎng)生說(shuō)個(gè)媳婦……
這么想著,邁腳出門(mén),卻一腳踏空,重重摔了個(gè)屁股墩。剛干完那事,腿肚子酸軟無(wú)力,那一跤跌得麻子在床上躺了半個(gè)月,卻只有咬緊牙關(guān)倒抽涼氣。他知道肯定是胡長(zhǎng)生干的,暗罵這“悠晃仙兒”沒(méi)事找事。
眼看著三十大幾啦,胡長(zhǎng)生嗜酒如命,還有這折天野地閑逛、黑天半夜搬石頭的毛病,誰(shuí)家閨女也不愿跟他。胡長(zhǎng)生便一直打著光棍,并落下了“悠晃仙兒”的外號(hào)。但胡長(zhǎng)生也有他的優(yōu)點(diǎn),他從來(lái)不會(huì)壞了別人的好事,也從來(lái)不張揚(yáng)別人的壞事。所以,他總是有酒喝,悠過(guò)來(lái),晃過(guò)去,過(guò)著神仙一樣的日子。
責(zé)任編輯 丁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