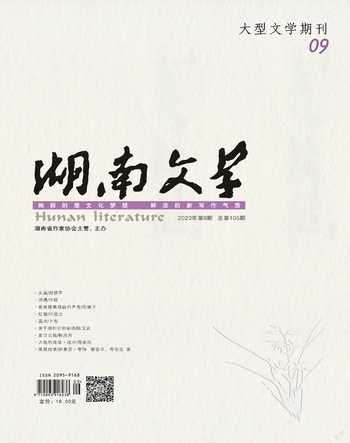存在的瞬間
楊殳
在電影行業鏈條上做齒輪十余年,主要干了兩種活兒:一種需大量開會溝通,與眾人周旋;一種需大量閱讀寫作,與文字磨合。我喜歡后者,但正如齒輪服務于鏈條,后者往往須臣服于前者。很多時候,漫長的聊天就是創作——講理論,講方法,更講即興,像是頭腦的爵士樂,但不一定美妙。
這就有了傾聽(偷聽)的樂趣。這樂趣不僅在聽故事,還在于對談話者明目張膽的窺探,看人說什么,怎么說。陳述、疑問,傾吐、遮掩,直白、婉轉,講述、重述,以及批判與嘲諷、訴求與控制——既是技巧,也是幻象。尤其當講故事變成職業的功利手段,“創作”免不了陷入世故人情之網,處處攻防,步步驚心。當疲乏和無聊來襲,人便有如靈魂出竅,看見了自己和他人的荒誕。
這種荒誕感來自人在日常中無可避免的表演,涉及到真實與虛構,或者真誠與虛偽。人與人交流是迎合,也是沖撞,一旦實對上虛,誠遇上偽,就會像堂吉訶德奮力沖向風車,會讓我感覺到一種殘酷。也許是過于敏感,我常常從“相談甚歡”或“棋逢對手”的間歇空白中覺察到尷尬和不適。記憶被擺上桌,就像身體的一部分接受會診,而極盡所能完善虛構之事,則是為他人生生植入記憶。比如醉鬼的漫長講述,中斷的句子,脫節的閃回,顛倒的黑白,肢解的情緒,煙霧中彌漫著言不及義和冷槍冷箭。可就在倏忽之間,說者或聽者冷不丁抵達了某個無可言說之境,話題冷冷地收了場,人的“存在”卻瞬間顯現,如靈光乍現。這也許類似文學上所謂“頓悟時刻”,但又不太一樣。你可能并未領悟什么,卻似乎感覺到了伍爾夫所說“Moments of Being”,即人真正體會到自我存在的瞬間。
換句話說,人的日常被密集的聊天——口談、手談或自我內心交戰——死死圍困,“存在的瞬間”長期被符號、象征與隱喻所遮蔽,我們在滔滔不絕的敘述之流中隨波起伏,卻難以觸及真實的存在物,正如我們只能漂在過去與未來的河流之上,卻無法停留在此刻。
但是呢,就像禪宗所謂“心無所住”,自我“在場”的可能恰恰在于放下去除遮蔽的執念。伍爾夫說得貼切,回憶往事中的人無法感覺到自我,只是情感的容器。那么,小說、戲劇、電影等敘事藝術對記憶的重構、演繹、調侃,乃至冒犯,可以理解為情感容器的清理過程。雖說自我依然不會因你的清理而顯形,但想必就藏匿在其中。讀和寫都是我與“我”周旋。
小說《海裂》模擬了日常生活中不同形式的敘述,最初寫作的沖動源于“聊天”以及“聊天者”的各種情態。從動筆到定稿,《海裂》改了三遍,最后重寫了一回,刪掉大半,清理掉的多是執念。上述零碎想法,都是在修改過程中產生的,而最后的重寫,則是對人物和敘述聲音的傾聽,也是自我體察的過程。也許,這篇小說就是對碌碌庸常中“存在瞬間”的徒勞捕捉。小說里的人,有意無意借虛構之名尋求對真實的表達,或在功利的敘述中解構他人的故事,或在別人的記憶里意外看見了自己的后腦勺。
這也正是寫小說的樂趣。有時杜撰烏有之地,有時假借人物之口,有時敷衍道聽途說——就是少見坦蕩的自白,可這一切迂回與遮蔽都是為了去“我執”,為了道出無可言說之物。
既然無可言說,又如何能道出?我不知道,因為這件事只能交給讀者。如果記憶是虛構的真實,那么小說就是我的表演。哪怕能有一剎那觸及到觀眾某個不可言說的念頭,我這個蹩腳演員便已知足。
責任編輯: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