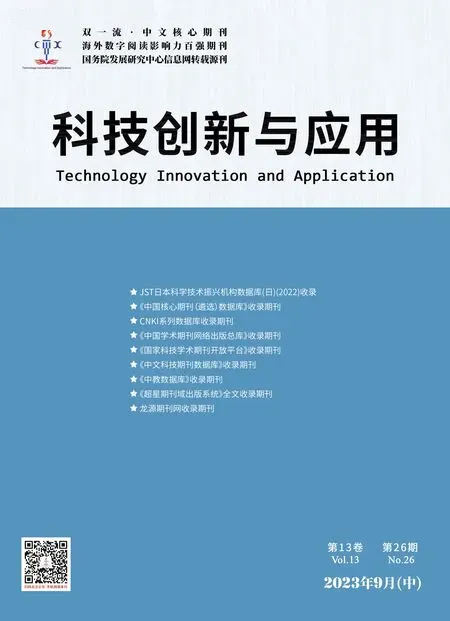某群樁套井基礎式大型跨海橋梁船撞設防標準研究及抗撞性能分析
林佳漫,張焱焜
(1.廣東汕頭海灣大橋有限公司,廣東 汕頭 515041;2.招商局重慶交通科研設計院有限公司,重慶 400067)
隨著我國經濟的蓬勃發展,航運事業也蒸蒸日上。橋梁作為跨越航道的水上建筑物,對城市的發展、區域之間的經濟聯動、居民的日常生活等方面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通航船舶密度的增加給橋梁的安全運營帶來了嚴重的安全隱患。近年來船舶撞擊橋梁的安全事故屢見不鮮,相關統計資料表明,橋梁遭受船舶撞擊是跨航道橋梁發生倒塌的重要原因之一[1]。因此,針對橋梁抗撞性能提升的研究近年來逐漸成為熱點,通過對橋區所在通航環境及抗撞性能進行分析,進而選取適宜的抗撞性能提升方案逐漸被橋梁工程設計人員所采用。黃飛龍等[2]在綜合考慮船撞角度、船撞速度等風險因素的情況下通過建立橋梁有限元模型分析了不同工況下的橋梁抗撞性能。陳巍等[3]基于“分層耗能”的優化思想,通過系列分析研究對比了防撞設施不同設計參數下的吸能效果。郭健等[4]提出了一種基于模糊數學理論的船撞橋風險概率分析方法,并以實際工程案例分析了某大橋船撞風險概率。劉偉慶等[5]同時對比了數值經驗公式以及有限元模擬仿真計算的船撞力大小,進而開展了系列橋梁防船撞系統的結構設計研究工作。方海等[6]采用數值仿真與試驗相結合的方式針對某防船撞裝置進行了性能分析。王紀鋒等[7]、王鵬等[8]利用有限元數值模擬軟件針對某大橋的抗撞性能進行了分析,同時對比分析了增設防撞設施后的船舶撞擊力。彭聰[9]通過比較國內外船撞力計算公式,進而對某斜拉橋的抗撞性能進行了分析,同時探討了不同防撞設施的防護效果。馮佳佳等[10]通過建立有限元模型探尋了不同撞擊工況下橋梁結構的最大受力部位。廖鴻鈞等[11]針對某大橋的船撞風險概率進行了分析,并詳細分析了影響橋梁碰撞概率的敏感性參數。不難發現,現有研究對于橋梁結構抗撞性能的分析已趨于成熟,但對于橋梁各涉水墩設防標準的確立卻未有統一的標準,其將直接影響橋梁結構的抗撞性能分析結果。因此,本文采用JTG/T 3360-02—2020《公路橋梁抗撞設計規范》船撞風險概率分析方法,分析了某大型跨海橋梁的船撞風險概率并確定臨界標準下的設防代表船舶。同時,通過數值仿真比較了船撞力數值大小,相關研究方法可供其他大型跨海橋梁船撞風險評估及抗撞性能提升治理提供參考。
1 工程概況
某大型跨海橋梁全長2 500 m,包括南、北兩側引橋。主橋為154 m+452 m+154 m 的三跨雙鉸預應力混凝土箱型加勁梁懸索橋。主塔采用上下游分離的群樁套井式基礎,分離的群樁套井基礎為單壁鋼殼結構,長11.0 m,寬7.0 m,高15.5~23.0 m,內設6 根直徑2.2 m鉆孔樁,樁長6~19 m,單壁套井封底混凝土厚5 m,承臺系梁高5 m。主塔為3 層門式框架結構,承臺以上塔柱高95.10 m,塔柱為D 形空心截面鋼筋混凝土結構(圖1)。

圖1 全橋總體布置圖

圖2 主塔立面圖

圖3 主通航孔有限元模型
全橋設計行車速度為80 km/h;橋位區20 m 高處百年一遇10 min 平均最大風速47.0 m/s;場地基巖地面最大水平地震系數取K=0.222 9 g。大橋主橋橫跨一級航道榕江主航道,南側為主航道,供外海客貨進出的通航凈寬不小于400 m,平均潮位以上凈高46 m,滿足5 萬噸級海輪通航要求,北側次航道按1 000 t 貨輪考慮。
2 橋梁船撞風險分析
2.1 橋梁船撞風險概率分析方法
目前,國際范圍內在對橋梁進行船撞風險評估分析過程中,應用較多的主要有3 類模型:AASHTO 模型、KUNZI 模型和歐洲規范模型。其中AASHTO 模型由于理論方法較為完善且計算方式較為簡單,使得其被多國所采納[11],然而該模型并未考慮一些強制的停船措施,使得其計算結果不能合理反映實際的船舶碰撞概率;KUNZI 模型雖考慮了人為因素在船舶碰撞橋梁過程中的影響,但未考慮通航船舶在橋區所在航道橫向分布的影響;而歐洲規范模型同時考慮了船舶橫向分布、橋區所在航道單位航程碰撞事故率等因素的影響,理論推導更為嚴謹,然而該模型缺乏定量表達式,使其并未被大范圍采用。針對上述分析模型的不足,我國于2020 年頒布的JTG/T 3360-02—2020《公路橋梁抗撞設計規范》[12]提出了三參數概率積分路徑模型,即同時考慮不同水位分布概率、通航船舶航跡橫向分布密度、船舶單位航行距離的失誤概率以及人為因素影響下的停船概率,使得分析模型更為符合實際。
2.2 船撞力計算方法
根據JTG/T 3360-02—2020《公路橋梁抗撞設計規范》6.1.4 條的規定,船舶撞擊力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F 為輪船撞擊力設計值(MN);a 為輪船撞擊力系數,取0.33;η 為幾何尺寸的修正系數,γ 為撞擊角度的修正系數;V 為船舶撞擊速度(m/s);CM為附連水質量系數;M 為滿載排水量(t);ΔH 為被撞體厚度,Hs為船艏高度,β 為統計系數取4.0;θ 為船舶軸線與碰撞面法線夾角;a0、b0參數參考JTG/T 3360-02—2020《公路橋梁抗撞設計規范》表5.1.3 取值。
2.3 橋梁抗力計算有限元模型
采用Midas Civil 建立全橋有限元模型,并采用“m法”考慮土-基礎的相互作用。抗撞性能驗算時所采用的荷載組合為:自重+二期恒載+車輛+船撞力。為確保本次分析是基于橋梁目前的結構特性,建模時采用了定期檢測報告的檢測索力。由于施加水平力的作用點位置不同,結構自身的極限船撞力也不相同。計算結構抗力時選取組合荷載作用下的最不利工況,最不利驗算截面選為:墩頂截面、墩底截面、樁基截面。
3 計算分析結果
3.1 全橋設防代表船型計算
由于設防代表船型以及設防船撞力的大小與橋梁可接受風險選取有關,因此,為得到該跨海大橋主通航孔滿足可接受風險時對應設防船撞力,計算了不同設防船撞力下的橋梁倒塌概率,并選取1.0×10-4為可接受臨界風險概率進而得到橋梁年倒塌風險隨橋墩設防船撞力變化的曲線如圖4 所示。

圖5 船舶撞擊橋墩數值仿真模型

圖6 船舶撞擊工況及船頭變形

圖7 船舶撞擊力時程曲線
圖4 中A、B、C、D、E 分別代表各涉水墩的一組抗力,單位為MN,具體取值見表1。

表1 各涉水墩抗力鄧值表MN
計算結果表明,隨著各橋墩設防船撞力不斷增大,全橋的船撞年倒塌風險呈逐步減小。當大橋各涉水橋墩設防船撞力為C 組時,全橋的年倒塌頻率可降低至可接受風險1×10-4/a。此時,主塔設防船撞力為26 MN。進一步根據設防船撞力,反算得到各涉水墩的設防代表船型以及船舶撞擊速度見表2。

表2 各涉水墩設防代表船型
3.2 船撞風險分析
在詳細收集橋區現階段通航密度、通航船舶船速、水流速度、不同水位分布密度及橋梁各涉水墩自身抗力等基礎上,適當考慮遠期通航密度的增加后計算得到該跨海大橋遠期各涉水墩的年碰撞概率以及年倒塌概率見表3。

表3 大橋各涉水墩年碰撞概率以及倒塌概率
計算結果表明,根據規范方法的計算結果,大橋在遠期通航密度下的年碰撞頻率約為0.284 次/a;年倒塌頻率為3.73×10-7,低于可接受風險1.0×10-4/a。全橋年倒塌概率的風險值主要來源于南側主塔。
4 船撞數值仿真分析
4.1 數值仿真模型的建立
基于上述研究可知,雖然該跨海大橋抗撞性能滿足現階段通航需求,但橋區所在航道航密度較大,船撞風險較高。為針對性地開展抗撞性能提升工作并確保抗撞性能分析結果偏于保守,研究團隊利用LS-DYNA軟件針對該橋橋塔遭受5 000 噸級船舶3 m/s 的撞擊工況開展了動力數值仿真分析并分析得到船舶撞擊力,以進一步探尋原橋結構的抗撞性能是否滿足抗撞性能要求。
計算結果表明,當采用數值仿真軟件針對5 000噸級船舶3 m/s 的速度撞擊橋墩時,船舶撞擊力在撞擊發生后的第0.7s 到達峰值29.93 MN,撞擊力大小略高于JTG/T 3360-02—2020《公路橋梁抗撞設計規范》公式計算的數值大小26 MN,此后撞擊力逐漸降低,直至撞擊發生后的第1.7 s 降至為0。數值仿真撞擊力略微高于規范公示數值大小原因可能是由于群樁套井式基礎剛度大抗力高所致。
4.2 結構自身抗撞性能計算
綜合比較數值仿真方法計算得到的船撞力及JTG/T 3360-02—2020《公路橋梁抗撞設計規范》計算得到船撞力數值大小之后,從偏于保守的角度選取較大者,并將其以節點力的方式加載到通過Midas Civil建立得到的橋梁有限元模型對應節點上,進而得到橋梁結構最大受力部位,并進一步針對最不利控制截面進行M-φ 曲線分析以判斷橋梁結構抗撞性能是否滿足相應要求。計算結果見表4。

表4 各工況下橋墩抗撞性能驗算結果
計算結果表明,在5 000 噸級船舶以3 m/s 的速度撞擊下,北橋塔安全系數低于南橋塔為1.37,但總體而言,原橋主塔結構抗撞性能滿足要求。
5 結論
本文針對某跨海大橋進行了抗撞性能以及船撞風險分析,并分析比較了數值仿真與規范公式計算的船撞力大小,主要結論如下。
5 000 噸級船舶3 m/s 速度撞擊工況下,數值仿真計算的船撞力略高于JTG/T 3360-02—2020《公路橋梁抗撞設計規范》規定的公式計算結果。
在遠期通航密度下,該跨海大橋年碰撞概率為0.287 次/a,全橋年倒塌概率為3.73×10-7,遠低于規范限值1×10-4/a,原橋結構抗撞性能滿足設防代表船舶的撞擊工況,但由于全橋年碰撞概率較高,建議增設柔性防撞設施避免船舶撞擊工況下混凝土表面發生損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