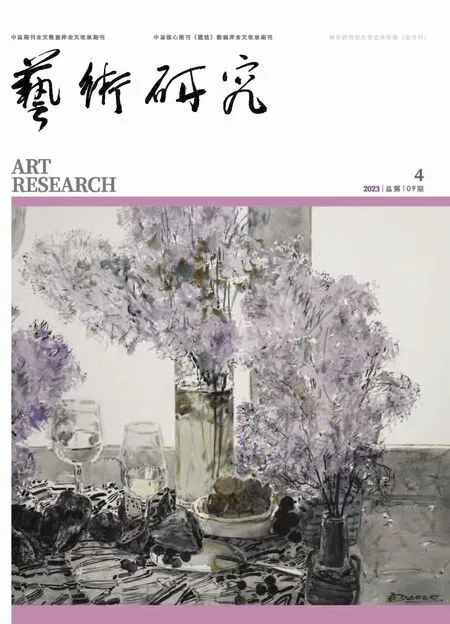論波普藝術對“靈暈”的消解與重構
云南藝術學院/楊哲卿
一、本雅明的“靈暈”觀
(一)“靈暈”的概念與內涵
“靈暈”一詞是本雅明的一個獨創概念,德語原文寫作為“Aura”,在中文譯本中,有“靈光”“靈暈”“光暈”等譯法。本文選用“靈暈”一詞,意在能更好地體現本雅明本人神秘主義與精神性的表達。“靈暈”的概念最早出自文章《攝影小史》中,并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做了進一步的闡述。
“靈暈”這一詞匯被用來歸納古典藝術的一些特征,這些特征通過機械復制藝術的產生而隨之消解。其概念可大致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其原真性,即藝術作品的“此時此地”,這也是“靈暈”最本質的特征。我們可以將其理解為古典藝術作品在創作完成后自身所具有的獨一無二性。這一概念的提出顯然受到了當時機械復制藝術快速發展的影響,本雅明意在將這兩種藝術形式進行區分,即古典藝術的“不可復制”性與消解了這一特征的現代復制藝術。
其次,是藝術作品自身與觀者之間的距離感。本雅明在書中用自然事物的比喻來形容這種距離感:“靜歇在夏日正午,沿著地平線那方山的弧線,或順著投影在觀者身上的一截樹枝——這就是在呼吸那遠山,那樹枝的靈光。”①本雅明認為,古典藝術只有在時間,空間甚至心理上保持著一定的距離,才能實現美的感受。
再次,這意味著這些藝術作品具有歷史感與時代性。本雅明提出:“談到歷史,我們就會想到藝術作品必須承受物質方面的衰退變化,也會想到其世世代代擁有者的傳承經過。要確知作品轉手易主的過程,則需要從作品創作完成之地為起點,追溯整個傳統。”②也就是說,一件藝術作品的完成必然依附于其創作時代的歷史語境,并且在其后的千百年間展現著其自身的傳承價值。同樣這些特征“對于‘復制品’而言(不管是機械復制與否)都毫無意義。”③
最后,“靈暈”還體現在藝術作品的“膜拜價值”,這與復制藝術“展示價值”是一對相對概念。“我們曉得最早的藝術作品是為了崇拜儀式而產生的,起先是用于宗教儀式。然而,藝術作品一旦不再具有任何儀式的功能便只能失去它的‘靈光’”④。早期的藝術作品大多具有膜拜的功用,它大多數時候是作為祭祀禮儀或宗教信仰的一種外在顯現。它根植于神學思想,通過特定的主題體現出其神圣性。而機械復制藝術顯然消解了這種特性。
(二)“靈暈”與“藝術救贖”
本雅明第一次在《攝影小史》中闡述“靈暈”觀點的時候,其本質上表現的是一種攝影過程中特殊存在的自然美學概念。“當人與自然的直接統一破裂之后,自然的光韻便逐漸淡出了人的視野。在一個以人為中心的現代世界中,一切存在者都被人化了,任何事物的光韻都成了人化的‘光韻’。”⑤本雅明之后闡釋的人化“靈暈”的概念,實際上是為了以此為參照,來凸顯當代藝術,尤其是電影藝術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所表現出的新的審美特征。

圖1 安迪·沃霍爾《瑪麗蓮·夢露雙聯畫》1962年

圖2 安迪·沃霍爾《200個坎貝爾湯罐》1962年
但是從嚴格意義上來講,“靈暈”概念的提出并不只是為了區分古典藝術與現代藝術,更重要的是通過古典藝術中“靈暈”的消解來探討其背后的時代變化。對于這種變化,即藝術的新特征,本雅明本人的態度是較為復雜的,他既對傳統藝術的消逝感到傷懷,又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對這種歷史必然表現出極高的熱情。作為文藝工作者,本雅明自然對“靈暈”消散抱有懷戀情節,而從另一方面講,本雅明的行文中也時刻貫穿著他本人的“藝術救贖”理論,所謂“救贖”,也就不免與其藝術政治化的訴求有所關聯。
本雅明在文末的結語中筆風一轉,開始談及政治審美以及對法西斯主義的批判,可以看出其本人對于這些概念的闡釋有其自身的政治需求。因此“靈暈”概念的產生具有復雜性,它的本質意義并不能完全作為劃分古典與現代藝術的標準。盡管如此,本雅明站在其所處時代的角度,對當代藝術的一些特征做出了具有前瞻性的解讀,即使放在今天,其一些預言性的觀點仍對我們理解當代藝術,尤其是大眾藝術,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
二、機械復制與波普藝術
(一)波普藝術與達達主義
本雅明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談及了達達主義與電影復制藝術之間的關聯。“不久前我們才看到達達藝術家自鳴得意地進行反成規反文明的表演活動。我們今天才明白他們何以會如此賣力:達達主義是想借著繪畫(或文學)來制造現今觀眾對電影所期待的同種效果。”⑥文中所提到的“同種效果”我們可以將其理解為對傳統意義的解構,即對古典藝術“靈暈”的消解。本雅明認為:電影與在當時興起的達達主義同樣都具有“消遣”的特征,因此達達主義擁護電影的喜好。
達達主義是對藝術與規則體制的挑戰,而這種理念的建立為后來波普藝術的產生提供了理論基礎與精神支柱。“從某種層面上來講,達達主義是波普藝術的‘立論者’,波普則扮演了‘普及者’的角色。”⑦波普藝術繼承發展了達達主義反本質,反理性的藝術主張。它在消解藝術作品本身意義的同時,將藝術與現代生活,消費文化相結合,更好地將現代技術運用到藝術視覺化的過程中來。
達達主義與波普藝術同樣作為先鋒派藝術,同樣都對“唯美主義”美學持有批判態度。1957 年作為波普藝術之父的漢密爾頓曾指出波普藝術應該具備的品質:“年輕的,充滿活力的,短暫,便宜,通俗,可消費性,機智詼諧的,大批量生產,性感的,大企業式的,有刺激性和冒險性的。”⑧在波普藝術看來,“文藝復興的美是獨一無二的”的論調是非常荒謬的,也就是說,波普藝術主張消解藝術品的“原真性”。本雅明曾在書中提到:大眾想要散心,藝術卻要求專心。在散心的角度上,波普藝術相比于電影則體現得更加明顯。檢驗這些藝術作品的觀眾“將藝術的崇拜儀禮價值棄置于遠景處”,而他們檢驗的方式就是“消遣”。

圖3 理查德·漢密爾頓《是什么讓如今的家庭如此不同,如此有吸引力》1956年
(二)波普藝術的復制性
“機械復制”的概念在本雅明書中大多特指的是電影藝術或者說攝影技術的復制。當然,機械復制藝術的表現形式絕不僅僅只局限于電影的層面,本雅明之所以著重論及電影藝術,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其政治宣傳作用的影響。而在幾十年后,同樣具有復制性的波普藝術運動興起了。
波普藝術采用的創作媒介與創作手法都與電影有所不同,波普藝術家們在創作時,通常會采用印刷技術,尤其是絲網印刷。這種“復制”是在創作的過程中的一種復制,這種創作方式可以消解所塑造形象的意義,最有代表性的藝術家便是安迪·沃霍爾。日本平面設計大師原研哉曾言:“從無到有,是創造,但將已知事物陌生化,更是一種創造。”安迪·沃霍爾將“復制”做到了極致,也可以說是將這種觀念融入藝術創作的第一人。他的作品與其說是復制,更準確來說是一種刻意的重復。這種視覺審美疲勞的沖擊感被安迪·沃霍爾運用到了自己的作品中,并對后來波普藝術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機械復制的消解是無意的,而波普藝術對作品意義的消解則是刻意的,并成為了他們的創作理念。
三、波普藝術中“靈暈”的消解與重構
(一)波普藝術對“靈暈”的消解
本雅明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談到了機械復制藝術作品中“靈暈”的消散。在該書寫作完成的十幾年后,波普藝術出現了,而這種藝術形式背后的理念同樣也具備書中“靈暈”消解的一些特征。英國藝術家愛德華·波立茲曾運用廣告與雜志中的一些形象進行拼貼,因此創作出《一個有錢人的玩物》,畫面中的槍支打出了“POP”的字樣,并對準了暗指瑪麗蓮·夢露的女性形象,這也是對她工具似的命運進行的暗示。波普藝術大多是這樣一些商業,世俗的作品,這些作品與古典藝術在特征上具有明顯的區別。波普藝術弱化甚至消解了過往藝術中散發出的“靈暈”。
首先,波普藝術作品的原真性變得不再重要。作為一種大眾文化,波普藝術的受眾面向的是整個社會群體,其本身有較強的宣傳性,這就使波普藝術需要具備可復制的特征。這種復制性不僅作為招貼海報的宣傳手段,還體現在藝術家本身將“復制”的創作理念融入到藝術作品之中,也從形式逐漸轉變為觀念。“靈暈”的被消解也不再是一種被動的結果,而是藝術家創作的動因。安迪·沃霍爾可以說是這一理念的代表性人物,作為一種流行文化的再闡釋,《瑪麗蓮·夢露雙聯畫》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安迪·沃霍爾藝術的主要思想。沃霍爾通過大量采用仿真和挪用手法,將瑪麗蓮·夢露的頭像進行重復排列,并故意運用粗糙的套色方法,使畫面世俗化、大眾化。作品本身的創作原型是攝影師基因·科曼的攝影作品,沃霍爾通過劣質印刷的方法將人物俗套化,這種復制手法本身便意在消解原作的原真性,而作品刻意的曝光度與大量的套色也使作品完全脫離了過往藝術發展所形成的美學體系。
其次,藝術品與觀者之間的距離感消失了。無論從表現形式還是創作題材的角度,藝術家都有意的將視野放在大眾文化上。安迪·沃霍爾喜歡將政壇、演藝界、文化界的各種知名人士作為創作對象,因此在瑪麗蓮·夢露去世后,安迪·沃霍爾便以她為中心,創作了一系列作品。家喻戶曉的明星形象被再創作成藝術作品,這無疑拉近了觀者與藝術之間的距離。在他另一幅作品《200個坎貝爾湯罐》中,畫家以一種最直白的方式將大眾消費品進行了復制。該作品第一次展出的時候共有32幅,而坎貝爾在當時正好有售有32 種罐頭品種仿佛這些罐頭真的排列擺放在貨架上一樣。安迪·沃霍爾說:“我認為藝術不是為被挑選出的少數人服務的,它應該服務于美國大眾。”在波普藝術那里,藝術不再遙不可及,用本雅明的“靈暈”比喻來說,藝術不再是那散發著光暈的“遠山”,而成為了路邊人們隨意納涼的“綠茵”。
最后,在波普藝術中,“展示價值”代替了“膜拜價值”,要談論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探討過往古典藝術中所體現的膜拜價值。本雅明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提到:“藝術的生產最早是為了以圖像來供應祭典儀式的需要。我們得承認這些圖像的‘在場’比它們被看到與否更為重要。”⑨我們就以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為例,米開朗基羅為西斯廷教堂天頂所繪的壁畫,早已成為西方藝術的典范之作,我們如今在談及其藝術價值的時候,往往會著重對米開朗基羅高超的技藝與崇高的畫面進行解讀。而實際上,這樣的藝術作品最初具有極強的功用性,它們大多為宗教服務,而欣賞的意識在當時卻被弱化。這些早期藝術品從誕生之初便像本雅明所言的那樣“靈暈”充盈,接受著人們的頂禮膜拜,它們本身具有獨一無二的神圣性,并起到洗滌人們心靈的作用。
這種神圣性在波普藝術中被完全消解了,藝術品的場地不再是教堂,博物館,其自身也不再具備崇拜的意義。本雅明在書中引用了杜哈梅在《未來生活的舞臺》中的一段話:“這是毫不費勁的演出,不會留下任何繞梁余韻,引不起任何問題,也不知探討任何嚴肅的問題,燃不起熱情,激不起由衷的感觸,興不起任何希望,不然頂多是很可笑地夢想有朝一日變成洛杉磯好萊塢的‘巨星’。”⑩而波普藝術也與電影一樣,采用一種散心,消遣式的接受狀態,它不需要你有很高的藝術鑒賞能力,也不需要一種虔誠的觀賞態度,藝術的神秘感消失了。
在波普藝術中,我們時常能見到表現偶像崇拜題材的作品。1967 年,瑞典女攝影師林西莉在玻利維亞拍下了古巴革命者切·格瓦拉的遺照。由于照片效果與耶穌受難極為相似,再加上其本人生前的影響力,這組照片迅速在世界傳播開來,其形象也被大量的制作成波普拼貼畫的形式,在美國街頭張貼。如今我們依然可以看到采用該形象創作的“安迪·沃霍爾”式的絲網印刷作品,但戲謔的是,這其實是一幅他人模仿安迪·沃霍爾手法的作品。安迪·沃霍爾其本人也遭到了“復制”。因此當復制手段成為觀念之后,其藝術本體就走向了無意義,切·格瓦拉等作為偶像崇拜背后的膜拜功用也在漸漸消失。如今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還時常可見印著格瓦拉頭像的T恤或文化衫,這些經歷過無限次再構的藝術形象,早已成為了一種符號化的圖案。
(二)波普藝術對“靈暈”的重構
我們在上文中談到了波普藝術對“靈暈”的進一步消解,從中可以看出,對于本雅明文本意義上的“靈暈”消散,波普藝術已經完成了這個過程。然而,如果我們進一步去探討這種解構的意義,就會發現,藝術品的“靈暈”其實并沒有消逝,而是以另一種形式存在。“只不過,前者旨在建構意義,而后者則是以解構的面目出現的。”?
首先,來探討“靈暈”中的原真性。之前提到,安迪·沃霍爾的“復制”藝術完成了對藝術品“靈暈”的消解。誠然,面對著眾多的“瑪麗蓮·夢露”,我們顯然無法辨別哪一張面孔才是其原真的表達,藝術品的獨一無二性被解構了。然而,在波普藝術中,“復制”并不是一種宣傳手段,而變成了一種創作方式。“從藝術作品呈現的效果看,傳統意義上的復數性并不是安迪·沃霍爾的波普藝術中的重點,因為傳統意義的版畫復數性基于作品的數量,是為了更好地傳播而進行的機械復制,只是一種數字意義上的變化,并不是構成藝術作品的必要元素。”?在安迪·沃霍爾的作品中,復制的目的是為了體現單一意象的無意義感與商業性,也就是說,復制已然成為了作品中的元素,是作品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如果只有一個“瑪麗蓮·夢露”,便沒有了這一系列偉大的作品。我們可以認為,這些坎貝爾湯罐的整齊排列是在模仿商場的貨架,“復制藝術”成為了一種寫實性的表達。這種復制使作品成為了更完整的整體,它自有其本身的“獨一無二性”,這是一種美學意義上的復制性。因此,“即使是現代復制技術所產生的藝術——復制在此不是指對產生的作品的拷貝,或許它的生命光韻的體現與傳統藝術不同——只要是真正有創意的作品,就依然富有構成原真性的生命光韻。”?
其次,過去我們一度認為,要想實現藝術自律,必須要在心理層面和創作層面上脫離現實的束縛,較好的例子是與波普藝術時期相近的抽象表現主義,而這種試圖抽離一切的創作方式卻是波普藝術所要克服的。波普藝術真正做到了立足于現實社會并完成了對現實社會的批判。例如理查德·漢密爾頓所創作的作品《是什么讓如今的家庭如此不同,如此有吸引力》,便不僅僅只是一幅現代元素的拼貼畫,它實際上隱喻了現實中豐盈的物質生活與虛無的精神狀態。而安迪·沃霍爾的《綠色的可口可樂瓶子》也不僅僅是意象的簡單堆砌,而是為了表達千篇一律的物質產品使得當今世界人們逐漸失去自我。因此,波普藝術雖下沉到了大眾社會,但它卻與普遍意義上的機械復制藝術具有明顯的不同。也就使觀者與作品之間有了一種與眾不同的距離感。
最后,我們再來討論波普藝術有關膜拜價值與展示價值的問題。波普藝術作為一種消費文化支配下的產物,其內在意義與傳統架構下的膜拜功用是背道而馳的。然而一些學者從解構主義的視角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費瑟斯通在《消費文化與后現代主義》中談到了消費文化與神圣性的問題:“雖然消費主義帶來了商品的過度膨脹,但這并不意味著神圣被遮掩覆沒了。若我們能注意到在實踐中的商品所具有的象征意義,那事情就一目了然了。”?在他看來,如果采用一種更為寬泛的文化定義,那么國家儀式,搖滾音樂會,愛人間進行的小型神圣性儀式等行為都產生了類似于宗教活動中所體現的神圣性。以此為參照,我們便可以探討波普藝術在消費社會中的價值及其神圣性問題。
按照本雅明的分類標準,高雅的藝術品需要能夠體現崇拜價值(除個人肖像外),而不具備崇拜價值我們就將其稱為通俗的藝術品。波普藝術顯然不具備前者的特征。然而問題在于,通俗的藝術就一定無法具有崇拜價值么?費瑟斯通強調“通俗的藝術在某種情況下可以擺脫原來的元素而獲得象征意義,也即具有了神圣性。”?
現在來看前文所提到的符號化的“切·格瓦拉”,它實際上是絕對價值觀和統一論被社會相對論和多元社會所代替后的產物。這種消解與解構的風潮實際上已在世界上廣為流行。齊美爾認為,“現代性的本質是心理主義,根據我們內在生活的反應來體驗和解釋世界。”?因此在這些簡單甚至粗俗的圖像背后,其反叛消解的內涵及象征本身就具有泛神圣化的意義,這種意義背后所隱含的是一個龐大的信仰團體,而其信條便是如何用此種方式去認識與對待世界。
如果我們進一步挖掘波普藝術的本質意義便會發現,無論從內涵意義還是外在表象上來講,波普藝術的“靈暈”并沒有消失。首先,由于復制成為了一種創作手法,使得其依然具有原真性,其次,在觀者的角度上,二者依然有其若即若離的距離感。不難發現,從神圣多元化的視角來看,波普藝術是用一種去神圣化的方式來表達其象征意義,而這種意義也就具有了神圣性。
四、結語
自攝影技術普及以來,藝術的發展去向成為眾多理論家爭論不休的話題,而“下沉大眾”與“上升心理”便成為了當代藝術家普遍嘗試的兩種道路,格林伯格也將這二者歸納為“媚俗藝術”與“精英藝術”。根據上面的闡述,我們可以看出這二者之間實際上是缺少一個明確的界限的。在波普藝術中,消費主義所帶來的世俗性消解了普遍意義上傳統的藝術特征,我們確實可以認為這是與高雅、神圣的藝術背道而馳的。但正如費瑟斯特所強調的藝術品的功能限度問題,我們已經無法定義一件藝術品在當今社會所承載的社會功能及其背后所蘊含的象征意義,也更無法用本雅明所說的“藝術品的韻味”來劃定區分藝術。藝術理論與藝術創作相互塑造消解,藝術的發展呈現出不可逆式的多元發展趨勢,藝術的邊界也在不斷模糊。本雅明在書中所探討的機械復制藝術,由于歷史的原因,僅僅局限于電影,乃至達達主義,而對于其后藝術的發展,縱使是本雅明,也無法看清其全貌。因此,如何看待過往藝術理論的建構意義,如何將其更好的帶入到瞬息萬變的藝術發展潮流中,才是我們學習和借鑒前人成果時最應該思考的問題。
注釋:
①【德】本雅明,許綺玲,林志明譯.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本雅明論藝術·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63.
②【德】本雅明,許綺玲,林志明譯.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本雅明論藝術·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60.
③【德】本雅明,許綺玲,林志明譯.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本雅明論藝術·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60.
④【德】本雅明,許綺玲,林志明譯.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本雅明論藝術·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64.
⑤朱寧嘉.藝術與救贖:本雅明藝術理論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64.
⑥【德】本雅明,許綺玲,林志明譯.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本雅明論藝術·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88.
⑦王欣欣.波普藝術的美學研究[M].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2008:13.
⑧王欣欣.波普藝術的美學研究[M].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2008:7.
⑨【德】本雅明,許綺玲,林志明譯.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本雅明論藝術·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65.
⑩【德】本雅明,許綺玲,林志明譯.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本雅明論藝術·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93.
?賴佳.從“神圣”到“多元”試論波普藝術對本雅明“光暈”理論的解構[J].當代文壇,2011(6):32.
?王穎.安迪·沃霍爾藝術中的復數性[J].美術教育研究,2021(9):74-75.
?朱寧嘉.藝術與救贖:本雅明藝術理論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73.
?【英】邁克·費瑟斯通,劉精明譯.消費文化與后現代主義[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177.
?【英】邁克·費瑟斯通,劉精明譯.消費文化與后現代主義[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175.
?【英】戴維·弗里斯比,盧暉臨,周怡,李林艷譯.現代性的碎片[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