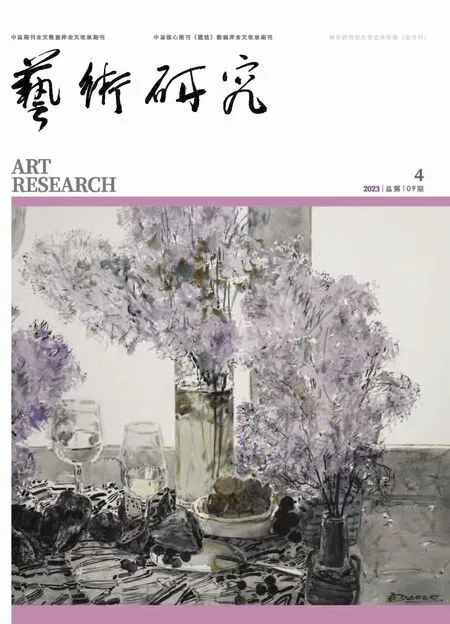河姆渡文化視域下的城市形象視覺化設計研究
——以寧波為例
江南大學設計學院/劉曉燕
城市形象作為城市有價值的無形資產和重要的綜合競爭力因素,是城市自然景觀、人文建筑、基礎設施等外在呈現和文化精神、氣質內蘊、思維觀念等內在屬性的整體概括,是公眾對城市的具體認知和總體評判,承載著城市物質與文化內核,是進行視覺化構建的主要渠道方式。城市發展日漸趨同化、單調化而競爭多樣化。利用視覺設計將城市基本要素轉化為具體的、可識別的符號,是清晰地表現城市獨特形象風貌的傳達手段。將城市本土的歷史文脈融入設計,構筑城市的獨特風采和顯著形象,可以明確傳達城市的文化內蘊特色,使民眾能夠徑直、有效地感知城市信息,強化印象。
一、寧波城市形象設計概況
寧波市地處大陸海岸線中部,長三角沖積平原東南部①,東北方向與東海和錢塘江相連,海港區位條件良好。是東南沿海著名的現代化貿易航運港口,擁有鮮明的城市風貌和豐富悠久的文明古跡。不僅是河姆渡文化的發源地,同時也是“海絲之路”的中華始發港。是全球唯一運河與海絲之路交匯的城市,被冠以記載古絲綢之路瑰寶的美譽。
20 世紀90 年代開始,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與城鎮化發展的推進,國內城市發展特色意識也逐步增強,嘗試實行城市的現代化發展轉型,在城市革新中探尋和建立與眾不同的都市特色。寧波在改革開放初期“東方大港、河姆文化、名人故里、儒商搖籃、佛教勝地”的城市宣傳,歷經嬗變,到如今體現“港口、文化”理念特色的“國際港口名城,東方文明之都”和“書藏古今,港通天下”并用的城市新形象。②
縱覽而言,寧波始終致力于挖掘自身優勢特色,努力找尋城市更新發展的突破點,在實際形象塑造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前期重點更偏向于經濟支柱的港口貿易產業特色,抓住臨海港口城市的優勢定位,本土歷史文化資源的內涵并未得到充分挖掘和活化利用,整體的城市形象缺少歷史感和文化感,與上海、杭州等城市相比,城市的個性特色和國際影響力、認可度等方面遜色不少,對外吸引力不足。
在世界貿易增長放緩的大環境下,整體貿易出口市場持續惡化,直接導致寧波當地外貿加工的制造產業遭受重大打擊。因此政府在把握并立足于現有的港口商貿、制造加工等優勢資源的基礎上,竭力尋根溯源城市文脈,精煉與深化人文精神,傾力打造海洋文明、地域歷史,大力開發旅游經濟、創意產業、服務平臺,獻力城市發展新動力。
二、河姆渡文化的藝術審美表征
河姆渡文化歸屬于史前時代原始社會中早期文明,是農耕時代百越族部落的古越人創造的璀璨文明。1973 年發掘于浙江寧波余姚,出土古跡文物豐厚,包括陶、石、骨、木等。是我國長三角區域新石器時代最初始也是最重要的考古遺跡之一,彰顯了華夏原始文明在歷史起源階段的輝煌成就。河姆渡先民在持續勞作中創造了獨特的生產制造體系和藝術審美范式,其美學風貌和藝術表征包括外在呈現的物質形式,如圖像、紋樣、色彩等直觀表層的視覺元素;以及暗含更深層次的具有象征精神和符號意喻的意識形態領域的文化意蘊,如自然信仰、祖先崇拜、圖騰祭祀、原始精神等內在文明意象。
(一)河姆渡的裝飾藝術美學
河姆渡出土的眾多遺存中,原始藝術品保留豐厚,別具風格。主要涵蓋器表刻畫、牙骨雕刻、陶泥捏塑、陶器色彩和造型規制五種藝術表現形式。③其中以刻畫藝術和雕刻藝術最為典范出色,在線條紋飾、工藝造型、意境布局方面具有獨特的時代美學意趣。
河姆渡器物的刻畫紋飾以拍印繩紋居多,其次是富于流轉變化,效果鮮明,而描繪較易的基礎幾何紋飾,常見于夾雜炭灰的黑陶器表。用簡單基礎的點線面元素,以排列、穿插、轉折、對稱等手法,構成疏密有致、虛實相生的貝齒紋、淺渦紋、重圈紋等圖像符號④。在基本紋樣上,再次相互摻雜交錯、布列組織,轉變出造型生動簡練、線條明快流暢、層次條理分明,具有獨特的節奏韻律和裝飾之美的圖案紋飾。給人樸素粗獷、原始本真的感官享受。
動植物紋(圖1-2)也是常見紋飾之一,題材源于自然物,常見的是禾葉紋、豬紋、鳥紋等。對周圍物象仿照摹寫,并在此基礎上融合改進演變出形象概括的圖案花紋。前期圖像寫實靈動,后期寫意格律,樣式靈巧規整,布局勻稱協調,是純粹的自然主義的藝術手法。代表有:魚藻紋盆、稻穗紋盆、豬紋方缽。紋樣富有區域性的土著氣息和樸素平直、原味十足的地方特色,呈現出原生態、純自然的古拙之美。

圖1 河姆渡文化陶塊植物紋
雕刻藝術是用象牙、骨、木等材料雕刻在蝶形器、手匕、器柄等實用器具和裝飾用品上的原始藝術。材料講究,設計奇巧,寓意深奧。表現方式以陰刻、陽刻的基礎線刻技法居多,間或夾雜圓、浮雕和琢磨等原始早期相對復雜的工藝。農牧時代的審美觀念和相較于采集狩獵時代更為成熟的審美意識在代表作品雙鳳朝陽象牙雕刻(圖2)中得到清晰體現,是古越人審美取向的突破與革新。

圖2 河姆渡文化雙首連體鳳鳥紋
陶塑藝術也是河姆渡原始文化的一大特色(圖3),題材以豬、魚、鳥、羊等動物為主,是孩童玩具或裝飾擺件。多數是在完成制陶后還余有陶泥料而隨性發揮,信手捏下,手法主要是捏塑和堆塑技術,制作粗簡,塑造形象善于捕捉神態特征,變形較為夸張,如豬突出嘴、身,魚突出鰭、尾,羊突出雙角,造型表現張力強烈、感染效果濃重。從僅現的遺存品中可見創作時沒有固定呆板的程式規范,而是直抒胸臆,情感熱烈飽滿,生趣自然,想象奇特,手法大膽且不脫離客觀實在,如陶羊俯地、家豬覓食、游魚嬉戲,獨具一種天真樸素的審美情趣和古稚拙樸的內涵。

圖3 河姆渡文化黑陶塑羊、陶豬
如上,河姆渡裝飾藝術的形式美,主要體現在形制風格、紋飾構成等直觀表現方面,創作主題簡單自然,手法稚嫩粗拙。以古樸粗獷的線條塑形為主,不精雕細琢,更注重對象的輪廓描繪和整體神韻追求。造型天真拙鈍、生動活潑。遺存作品均顯示出濃厚的自然、生活氣息,沒有繁復冗雜的裝飾,功能明確,實用至上的同時也注重與裝飾美觀相結合,明確展現出當時的審美傳統已經從單純的裝飾階段提升至藝術的自發階段。這些作品辯證地反映出河姆渡人以一種原始樸素思維觀念認識自然,作品中表現出來的處世態度及美學情致顯示出一種淳樸素雅、稚拙單純的土著生機,是河姆渡先民主觀審美意志自覺物化的主要表現形式。因而從某種程度上說,史前河姆渡文化的獨特創造藝術稱得上是裝飾藝術,具有豐富的當代美學藝術價值。
(二)河姆渡的原始信仰崇拜
河姆渡屬于原始農牧文明,代表的器物形制、圖像紋樣、色彩遺存等史前藝術,源于人們生產生活、精神情感的感悟和選擇,體現出人對自然的理念,具有重要的象征意味和復雜觀念,其中凝聚了深厚的造物觀念、巫術禮儀等文明元素,承載對原始自然、圖騰的崇拜和信仰,是早期原始人類為謀求生存保佑而寄托精神思想的物質載體,構成了古越族河姆渡部落最初期的原始宗教信仰。
圖騰的信仰崇拜是史前社會奇特的文化征象。作為構筑起人主觀意志與自然神靈之間精神溝通的意識形態產物,在當時生產生活中普遍存在,是先民創造出的一個獨立的精神文化范疇。圖騰作為史前文明,難以獨立依靠抽象概念發揮作用,它的傳承和表意效用,必須通過具體有形的媒介才能獲得實現。藝術具有形象性、公共性、實體性等特點是適合承擔圖騰的載體媒介。李澤厚先生認為“原始社會的紋飾并不單純是形式上的裝飾審美藝術,而是氏族共同體在物質文化上的表現,具有原始巫術禮儀的圖騰含義。”⑤新石器河姆渡先民對賴以為生的自然物象心懷尊崇,蒙昧時代的原始思維將其敬奉為圖騰。原始虔誠的崇敬是祈望精神上的慰藉和滿足,表達了河姆渡人對自然生活的希望與憧憬、對種族繁衍的祈求與寄托。河姆渡是稻作文化的起源,遺存陶器發現的“雙鳥護禾”“雙鳥昇日”的紋飾圖案(圖2),不是單純的裝飾藝術,而是具有嚴格巫術禮法含義。點線的藝術形式暗含了氏族群體在物質文化中的觀念想法,表明先民對稻禾豐收、農業耕作的關切和祭祀,充滿了大量的原始社會的半富含義。鳳鳥紋是河姆渡文明靈物崇拜的典型代表。鳳鳥崇拜作為古老的物態化活動,具有對自然天性、生存本能的贊頌和追求。千年來延續,構成了中國古代沿海地區先民文化生產和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
綜上,河姆渡原始文化體系中富含獨特的藝術意象,包括豐富的裝飾構成、圖像風格、造型規制等,并顯示出蘊含其中的深厚的創造藝術、審美文化、原始禮法等深層文明元素,經挖掘研究其形式語言、類型結構、美學特質、地域文化精神等,以現代審美理念進行解讀,通過具有現實意義的設計改造,復興其視覺藝術形式,可以形成系統而獨特的視覺要素體系,為城市形象注入魅力的文化價值。
三、河姆渡文化的視覺化設計方法
河姆渡文化的藝術美學質樸而原始,意蘊豐富,基礎的幾何圖像中明確可見疏密的節奏和動靜的韻律。在城市形象構建設計中植入歷史文化藝術,需要正確把握城市和文化之間的關系,對應用元素和本土城市情況深入考量,從城市習俗、傳統觀念等多方面進行綜合研究分析。
城市形象的視覺化塑造應該建立在充分體會和尊重文化的基礎上,注重精神內蘊和現代審美觀念的科學融合,而不是單純的拷貝和挪用。通過運用提煉概括、解構重組、優化融合合的視覺化表現手法,重點提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元素符號或總體形態,對其有選擇性地打散分離,運用現代設計的前沿理念和創新手法將零散要素進行重新組合,實施改良設計和創作應用,賦予視覺符號新的設計理念和風格構成,滿足社會主流審美需求。例如河姆渡先民獨特創造的雙鳥朝陽紋、豬紋、禾苗紋等特征鮮明又蘊含原始樸素情感的圖案,對圖像的顯著特征進行局部提煉或整體形象概括,在現代生活和實踐經驗介入的基礎上,發揮現代藝術思維和設計駕馭能力,二次創造出現代化的具象或抽象元素形態,在保留城市傳統優勢形態的基礎上,融入城市特質,完善局部細節,實現創新并有機組合,將紋樣背后的神韻含義以直觀和視覺感知的方式,巧妙轉化并結合出帶有鮮明寧波城市特色的有人文價值且和諧統一的視覺符號,形成系統性、有效應的視覺形象傳播整體。用簡單的圖形達到豐富的視覺效果,塑造出個性強烈、容易記憶的城市視覺形象。在傳承歷史文明的同時彰顯本土地方城市的格調和魅力,切合人文傳統與現代個性相結合的審美意趣和設計語境,讓城市文化形象成為助力城市發展革新的軟實力,強化城市無形潛能。
四、河姆渡文化的在地性重構策略
城市是本土文化的重要表現載體,文化是應對城市生機衰退的核心驅動力,是城市設計更新的靈感內源。城市文化形象是其人文精神、氣質底蘊的綜合反映,對城市的整體發展潛能和競爭實力產生作用。城市歷史文化遺產、市民共同記憶和傳統風俗習慣構成了本土城市在地文化的“原真性”。⑥遵從文化運用的基本規則,多元融合在地文化,用“文化策略”構建起城市更新設計的理論體系,不僅注重技術指引性的設計改造方法,又深植文化在地創生對于城市特質的理論現實引導,幫助定位確切精準的城市形象,促進城市活力發展,推廣城市形象的戰略渠道,具有重要的藝術設計價值、理論文化價值和實踐運用價值。
河姆渡歷史遺產是寧波本土城市所具有的自成體系的文化資源,其歷史性和在地性能使寧波城市視覺形象呈現豐富、獨特的個性。河姆渡文化語境下的寧波城市形象有助于加強城市的人文屬性,區分城市特質差異,提升城市發展空間。從現存遺跡顯示,河姆渡先民在極其艱苦的生存環境中始終保持樂觀的人生態度,乘風破浪,勇敢外遷,開拓文明,在其生產的實用工具和裝飾藝術品中寄予對未來生活的美好憧憬與期望。可見河姆渡文明雖處在安定的新石器早期,卻并不是一個單一守舊、順從安逸的農業文明,而是百折不撓、果敢堅毅、勇于創新,帶有強烈外向性、開拓性的海洋文明,顯示出強大的生存力、創造力和向心力。與當前寧波城市精神中的“知難而進”不謀而合⑦。因此將寧波城市形象根植于本土的河姆渡文化,借助文化引導城市的氣韻格調,對于提升公眾對城市文化的認知,構建文化的情感認同大有裨益,是有效地傳播城市文化信息、精神氣質和歷史文明的互通策略。
五、結語
現代城市的健康、永續發展勢必需要順應時代主流形式,以人文精神作為內涵支撐,才是城市全球化、現代化發展的動力和源泉。從人文、歷史等方面綜合入手,充分挖掘城市自身的特色,保持和提升城市發展的可持續性,賦予城市排他性,使其在一眾城市中脫穎而出。不僅有助于提升城市的內涵特質、文化品位,傳達城市精神,增強文化認同,同時也拓寬了文化遺產資源傳承傳播的載體途徑。立足于河姆渡文化,既考慮當前審美觀念又充分尊重文化內涵,才能創造多元化、立體化、國際化城市形象,在實際的發展中鞏固和強化地域特色,使城市形象獲得具有底蘊內涵的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