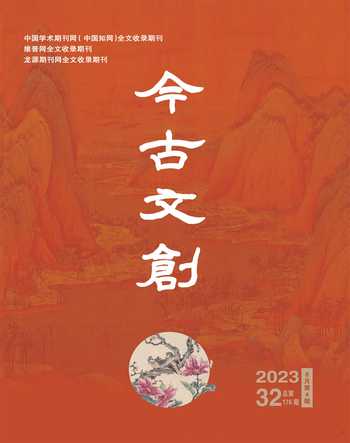疾病隱喻與道德選擇 : 對蘇珊 · 桑塔格《疾病的隱喻》的人文思考
陸欣立 朱夢丹 歸淑婷
【摘要】美國女作家蘇珊·桑塔格的文集《疾病的隱喻》以結核病、癌癥等疾病作為重點敘事對象,探討社會演繹變位下疾病隱喻的獨特表達以及所引發的道德缺位問題。桑塔格將個人的癥候與社會的道德環境交織結合,映射出疾病對人類道德身份與倫理價值的潛在影響。本文擬從疾病本身出發,通過對疾病的隱喻表征、疾病重壓下的道德審判與認知升華以及患者的身份嬗變與道德選擇,分析作品的道德意圖與所指,希冀由疾病剝離出隱喻影子,以此發出疾病外衣下對身體解放的號呼。
【關鍵詞】《疾病的隱喻》;道德;結核病;癌癥;倫理選擇
【中圖分類號】I712?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32-004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2.013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級大學生創新訓練計劃項目“桑塔格的疾病書寫與后疫情時代個體疾病困境的隱喻”(編號:202210332036Z)結項成果。
身處后疫情時代,人類因為這種具有強大傳染性的疾病遭遇了難以愈合的創傷,在罹患疾病時,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種個體社會道德與倫理身份的困境。談及社會現實生活與文學作品中的“疾病”一詞,美國女作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以獨特的視角,結合自己的經歷揭示了疾病對個人與社會、肉體與精神的雙重摧殘。她纏綿病榻,病痛蜿蜒全身,卻叫她以愈發沉著、愈發冷靜的眼光與筆觸洞察造成疾病的社會現實。她在作品中剖析了疾病隱喻的類型,展露人性的善與惡、潔與不潔,傳遞給讀者以獨特且奇妙的閱讀體驗。對苦難的認識、對生命的諦視、對頑疾的反抗,造就了桑塔格清醒又尖銳的文學王國。
21世紀對桑塔格疾病敘事的相關研究日益崛起,近年來不乏高質量的成果。尤其是在經歷大規模世界性流行病后,更是達到新的研究熱潮,相關成果正在大量涌現中。Barbara Clow通過解釋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兩個假設悖論,在“Who's Afraid of Susan Sontag? Or, the Myths and Metaphors of Cancer Reconsidered”[1]中展現隱喻語言在現代“前科學”中以及因果關系的論證中發揮的作用,努力解決現當代醫學診斷和治療中的因果關系的邏輯問題;Yianna Liatsos則是在“Temporality and the Carer's Experience in the Narrative Ecology of Illness: Susan Sontag's Dying in Photography and Prose”[2]中探究了無法治愈的癌癥診斷所產生的時間失調如何阻礙人格和倫理意圖。國內學者張藝在《后經典敘事學的疾病敘事學轉向——以蘇珊·桑塔格疾病敘事研究為例》[3]中嵌入大生命視域文化,為文學的研究范式創新提供一定的哲學基礎和理論依據,激發敘事轉向上的后現代生命意識,拓寬大生命視域的外國文學研究方向;柯英的《〈費城故事〉和〈最愛〉中的疾病隱喻機制》[4]選擇將兩部展現疾病的電影作品與蘇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隱喻》展開互文性解讀,以影視化表達理解疾病的隱喻機制,批判身體成為各種隱喻的載體,我們應當取締疾病和健康的二元對立。鑒于此,本文將試從疾病隱喻的道德意義進行切入,以挖掘桑塔格文字中所表達的疾病的內核意義,進而探索社會“診斷報告”。
一、疾病的隱喻表征與錯位轉向
桑塔格明確亞里士多德的觀點,指出“隱喻”即“是指以他物之名名此物”,說一物是或者像另一不是它自己的物[5]。人類利用隱喻這一修辭手段,賦予了“疾病”更多內涵,將其所帶來的影響從患者個體轉向宏觀世界的道德選擇、政治立場甚至是某種意識形態[6]。疾病的隱喻正一點點地在人們的無限臆想與口口相傳中最終成形,而被隱喻化的疾病,則成了人類想象中的影子和產物。
《疾病的隱喻》誕生于20世紀60年代,當時正處于美國主流文化與反主流文化的碰撞時期。蘇珊·桑塔格在這兩種文化的對立中,堅定地選擇了對“疾病隱喻”的探究。與癌癥多年的對抗和治療之中,她不得不強忍癌癥本身給她身心帶來的強大痛苦,更需要承受由癌癥隱喻化帶來的具有恥辱性的道德審判。作為患者本身,后一種痛苦遠比前者更為痛苦與致命,因為它以道德評判的形式瓦解患者的心性,繼而一步步走向投降、妥協。
論《疾病的隱喻》寫作目的,誠然會提到去疾病的污名化與隱喻化,脫去疾病所蘊含的任何道德意義。桑塔格認為疾病并非隱喻,而看待疾病最誠實的方式——同時也是患者對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盡可能消除或抵制隱喻性思考[5]。把疾病與隱喻二者明確分開,勢必是對人的解放,同時也可帶來撫慰。那么,如若要擺脫所謂的隱喻,首先不可回避。它們務必暴露在陽光底下進行解構。
疾病一旦成為階級地位的象征,便不由會被納入種族或政治的討論范圍。如果說政治事件中沾染了疾病隱喻的色彩,深不可測的邪惡便會浮現出水面。馬基雅弗利把結核病看成是早發現早治愈的疾病,改種疾病是人為可以控制其進程的;類比政治,暴亂亦是如此。
桑塔格從自身出發,借由自己對疾病本身的看法以及付諸疾病之上的隱喻的意義,掀開了當下社會文化中內含的巨大遮羞布:工業社會中節制消費的困難。通過隱喻義,桑塔格實現了對作品內核的多樣化表達,對當時社會中淪陷敗壞的風氣與混亂的倫理秩序發出了猛烈批判。
二、疾病重壓下的道德審判與認知升華
疾病本是在一定的病因作用下,人的一種異常狀態,一種正常形態與功能的偏離。隱喻將疾病從僅僅是身體的非正常,轉換成一種嵌套著一定“意義”的道德批判或政治態度,繼而走向疾病的隱喻。隱喻套在人身上的枷鎖比疾病本身更加致命,且這種枷鎖是隱形的,很難同疾病一樣被療愈。疾病與道德高尚和政治傾向不成關系,然而疾病的隱喻脫離原始的審美領域,躋身道德范疇,進入政治種族圈層,演繹成排斥異己的修辭武器,以掩蓋真相。[7]桑塔格呼吁消除疾病隱喻,將疾病回到疾病本身。
桑塔格在文中提到了結核病、癌癥、梅毒和艾滋病,這四種疾病都是或者曾是人們恐懼、避之不及的疾病,對人類影響極大。桑塔格認為結核病在一開始指向的是折磨性壓抑的、克制的、無沖動的、無力發泄火氣的人。[5]但在19世紀中葉開始,貴族和資產階級爭奪話語權,結核病因此被浪漫地看待,甚至將它當作一種“貴族病”,[5]來提升自我形象。最常見的是在文學作品中,將結核病帶來的身體蒼白和潮紅、情緒的高漲多加描寫,患者大多生活奢華,患病反而使他們更加優雅,帶來的死亡甚至是極樂般的,崇高又平靜。而癌癥恰恰相反,代表畸形和壓抑,身體內的異變和痛苦以及治療中切除身體某個部分讓人們對待癌癥有一種非理性的厭惡,很多人堅持格羅德克劃定的等式:癌癥=死亡[5]。圍繞結核病和癌癥的幻想是夾在自我審判和自我背叛之間的一種形式。梅毒患者,隱喻義被認作是一種上天的懲罰,將梅毒患者集體曲解為是遭到了不正當性關系和嫖妓行為的批判,充滿犯罪感的性污染[5]。艾滋病的情況更為特殊,因為其痛苦無法治愈,傳播途徑被人們曲解成了更多的恥辱,艾滋病逐漸在人們心中成了邊緣人群、亞文化群體的傳染病。
疾病隱喻帶來的道德批判的影響比疾病本身更具“傳染力”。桑塔格指出隱喻帶來了另一種看待疾病的方式,將疾病妖魔化,把錯誤歸咎于患者,用無情的邏輯將其視為犯罪。[5]人們本能懼怕疾病,不免懼怕患病人群。人們懼怕未知,懼怕未被人類征服、具有未知災難的疾病。這等的懼怕和曲解,在疾病的隱喻的幫助下愈發滋長。部分疾病被強行與片面的判斷掛鉤,這樣的理解給疾病的隱喻創造了條件,形成了一種社會認可的疾病道德批判。它無形滲透在醫學、倫理、社會文化等多方面中,由個體的不幸演變為了社會性的恐懼、厭惡和劃清界限。這種隱喻發自個體內心,又從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了反饋,使得它感染了全人類。因為未知和感染力,讓人產生恐懼,從一種道德譴責的態度評論病人,將病人劃分為了不屬于群體的異類,更有甚者,將自己身上所發生、所經歷的不幸歸咎于病人群體。桑塔格在書中指出:“為了強化效果呼吁人們進行理性反應,疾病隱喻被運用到政治哲學里。”[5]在主流媒體關于流行病的報道中,將病毒本體隱喻為“惡魔”“死神”“自然現象”,將對待疾病的手段與治療方式隱喻為“戰爭”“考試”“比賽”。媒體運用這些強烈主觀情感色彩的詞語來隱喻流行病,一定程度上引導提高人們對病毒的認知,即需要警惕病毒、關注病毒,要凝聚人心齊心協力對抗疾病產生的效應。另一程度上,人們的關注同時對病毒產生一定的恐懼,這種恐懼逐漸偏離正確的軌道,擴散為對其他方面的極端恐慌。甚至出于對疾病特性的無知,碎片化的信息和謠言將矛頭直指所謂的源頭傳染者,并成了“公敵”和情緒宣泄口,對病患的隱私進行道德批判和倫理羞辱。一旦有足夠的信息以及“理性人物”的誕生,公眾的理性才得以回歸。即使理性回歸,但對于病毒的恐懼已經深入到觀念之中,面對部分突發情況時,防治成了部分人無視和逃避的工具,死板的條例遮蓋背后最根本的人性,從而將簡單的疾病問題引向了人性道德審判。因而我們呼吁,讓患病的身體回歸身體本位,使疾病不再分裂和異化人心,使疾病不再與其陰暗的隱喻義畫上等式,擺脫疾病的隱喻對人類理性思想的束縛,重審人與疾病、人與病人之間的道德倫理關系,讓人們睜開被疾病污名化蒙蔽的雙眼,從而重構萬物與世界的客觀聯系,找回人類生命的根本意義,捍衛真相與道德的歸位。
三、患者的身份嬗變與道德選擇
世間每一個人都擁有雙重公民身份,其一屬于健康王國,另一則存在于疾病王國[5],那么疾病可謂是喚醒了蟄居于健康人格之上的潛在倫理身份與倫理意識。愈是嚴重的疾病,愈是加速了患者被迫從他的日常生活中被隔離出來,歸因于可怕的、未知的疾病喚起了人類內心深處那份古老又神秘的恐懼。死亡率極高、難以醫治的疾病被當作是外來的“他者”,患者就如同是掙扎在蜘蛛網上的獵物,難以逃離,不得不服從、順應、接受疾病世界新的規則與法度。這個外來的“他者”進駐病人的身體,占據健康王國的領地,污染一切器官與系統,隨意地流動、回溯、擴散、顛覆。而這一整個過程,陌生而敵意的一切緊緊裹挾著患者的身體,將患者囚禁于疾病王國的迷宮之中,逼迫他們做出身份轉變的選擇。
誠然,人無往不在社會之中,但是人的社會屬性的實現依附于個體與社會的連結。疾病隱喻恰恰割裂了患者與外界的關系網絡,疏遠、抽身,直至難以逾越的鴻溝。借用愷博文的軀體化觀念,“個體的損失、所遭受的不公正、經歷的失敗、沖突都被轉化成關于疼痛和身體障礙的話語,這事實上是一種關于自我以及社會世界的話語和行動的隱喻”[8]。親情關系的變異、友情愛情的離散、社會身份的嬗變,都迫使患者進入一種失根的漂泊流浪狀態。
患者無法達成社會道德身份的認同,根本上是疾病、個人、社會這三者關系的失靈。疾病的隱喻在個體的生活圈與有限的社會網之間來回編織穿越,纏繞著集體想象力的被隱喻化的疾病[5],把難堪的死拉近到人們眼前無限放大,繼而再推遠。時代的外部動蕩與變化,肉體的疾病與心靈的復雜創傷,一步步異化、裹挾著患者。社會成了疾病滋生的溫床,高密度的人口、高強度的工作、高度工業化,種種疾病在頃刻之間迅速擴散。文學作品中的道德選擇,則是無可救藥的頑疾面前,人的理性與自由意志的來回拉扯,必須要對自己的境遇和他人的存在做出一個選擇。推之于現實社會,肆虐的流感病毒,體外的東西占領了病患的身體,使得個體成了異己。囿于隔離的環境之中,人們的同理心與關懷感無法真正對病患做出共情,僅僅關心自己所生活的一方天地,聽不見遠方的聲音,最終走向冷漠。道德給了我們與他人共同生活的規則[9]。而用道德的枷鎖隔絕被虛構化的疾病隱喻的病人,卻是人性的淡漠與自私自利。而破除這般枷鎖的最好方式,是打破疾病所纏繞的一切隱喻含義,直面患者,承認患者合理又正當的社會身份,歸還他們應有的道德身份。
歸根到底,最實際問題在于人類在真正面對重大疾病時,能夠轉變自我中心的舊觀念,去疾病隱喻,使疾病回歸本身嗎?《疾病的隱喻》映射了三種時序:曾經經歷、當下正在面對以及甚至將來無法幸免,各種突如其來的災難考驗,可能已經告訴我們了答案。
四、結語
《疾病的隱喻》以其獨到的視角,圍繞結核病、癌癥等癥候進行論述闡述,對變形的道德化的疾病進行思考與評判。桑塔格通過多種疾病隱喻描繪了倫理缺位下,道德崩塌的社會中個體與群體的對立矛盾,疾病不再留于疾病本身含義,而是加諸于肉體與精神的雙重摧殘。疾病與疾病、疾病與患者、疾病與社會之間的本質關系仍需新的思路、新的解讀范式努力去打破舊有的對立,回歸道德真善本位,實現肉體與靈魂雙在場。
參考文獻:
[1]Barbara Clow. Who's Afraid of Susan Sontag? Or, the Myths and Metaphors of Cancer Reconsidered[J], 2001.
[2]Yianna Liatsos. Temporality and the Carer's Experience in the Narrative Ecology of Illness: Susan Sontag's Dying in Photography and Prose[J],2020.
[3]張藝.后經典敘事學的疾病敘事學轉向——以蘇珊·桑塔格疾病敘事研究為例[J].天津大學外國語大學學報,2017,(24):21-28.
[4]柯英. 《費城故事》和《最愛》中的疾病隱喻機制[J].鄱陽湖學刊,2019,(6):73-82.
[5](美)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疾病的隱喻[M].程巍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20.
[6]郝永華.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中的文化研究關鍵詞[J].溫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06):47.
[7]霍源江.生病也任性:蘇珊·桑塔格與疾病[J].世界文化,2016,(08):38-39.
[8](美)凱博文.痛苦和疾病的社會根源:現代中國的抑郁、神經衰弱和病痛[M].郭金華譯.上海:三聯書店, 2008.
[9](美)羅伯特·所羅門(RobertC.Solomon)&凱思琳·希金斯(KathleenM.Higgins)著.大問題:簡明哲學導論[M].張卜天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