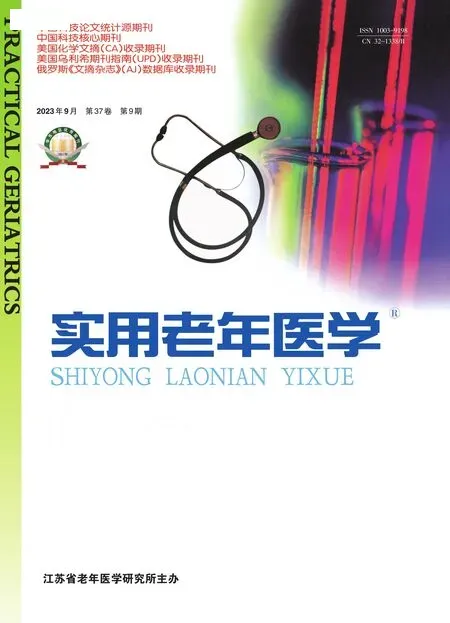不同麻醉方式在帕金森病病人丘腦底核腦深部電刺激手術中的臨床效果
呂坤 曹紋平 王宇航 趙春生 曹勝武
傳統上,深部腦刺激(DBS)是在局部麻醉和清醒鎮靜的情況下進行,然后進行微電極記錄(MER)和術中測試刺激以確定最終電極位置[1-2]。然而,在整個手術過程中,病人必須固定體位且保持清醒狀態。氣動磨鉆發出的巨大噪音會給大多數老年PD病人帶來身體和心理上的痛苦。一些因為缺乏左旋多巴而無法忍受長時間手術的病人可能會要求停止手術,而且部分病人的血壓可能會大幅波動,增加麻醉難度。此外,老年PD病人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心肺功能減退。考慮到這些問題,近期的研究熱點逐漸趨于全身麻醉。全麻不僅可以提升病人的體驗,而且對于不能耐受局麻手術的人有更大的吸引力。部分研究表明全麻和局麻有類似的臨床效果。然而,大多數數據來自不同的中心,導致差異較大。因此,在本研究中,我們選擇了由同一組神經外科醫生進行DBS手術的PD病人,對比分析了手術時間、植入誤差和臨床效果。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納入南京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神經外科2017年10月至2022年10月在局部麻醉和全身麻醉下行雙側丘腦底核(STN)-DBS治療的148例病人。其中全麻組81例,年齡61~81歲,平均(70.4±4.9)歲;局麻組67例,年齡60~85歲,平均(71.5±6.0)歲。所有病人均由多學科小組進行評估,包括2名功能神經外科醫生,1名神經放射科影像醫生和1名運動和肌張力障礙專業的神經內科醫生。納入標準:(1)符合我國2016年發布的《中國帕金森病診斷標準》或者符合2015年國際PD協會及運動障礙學會原發性PD的診斷標準;(2)所有病人進行急性左旋多巴沖擊試驗(acute levodopa challenge tests,ALCT),根據統一帕金森病評定量表第三部分(Unified Parkinson’s Disease Rating Scale-Ⅲ,UPDRS-Ⅲ)的客觀評定標準,最大改善率需>30%。排除標準:(1)癡呆或者精神障礙(MMSE<26分);(2)腦內存在血管性病變或者顱內占位性病變;(3)存在嚴重的共患病或者一般手術禁忌證。在術前1周內完成漢密爾頓焦慮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和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評估并且記錄,所有手術均由同一團隊完成。
1.2 術前靶點定位 所有病人在術前1周內進行頭顱MRI掃描(3.0T,Siemens或General Electric)。主要包含3D-T1(層厚1 mm)、軸位和冠位T2加權像(層厚2 mm)以及磁敏感加權成像(層厚2 mm)序列(susceptibility weighted imaging,SWI),均為連續掃描成像。手術當天在局部麻醉下安裝Leksell立體定向頭架,行多排CT平掃(層厚1 mm)。將CT和術前MRI導入手術計劃工作站(FrameLink),同時設計穿刺針道與進針角度,規避重要結構如腦溝、腦室,以及鈣化灶和 SWI 序列下可見的深部靜脈并獲取計劃框架靶點。
1.3 麻醉流程 對于全麻組病人,用芬太尼(1~2μg/kg)、異丙酚(1.0~2.5μg/kg)和肌肉松弛劑(0.6~1.5μg/kg)誘導麻醉,并在手術過程中用七氟醚吸入維持。將框架和Mayfield適配器連接,使頭部框架的底部與床成45°角。而對于局麻組的病人,由于處于清醒狀態,頸部無法過度彎曲,適當抬高頸部并且在頸部后部放置海綿墊,使頸部肌肉呈放松狀態。然后,給予0.2%利多卡因和0.25% 羅哌卡因1∶1混合局部浸潤麻醉。
1.4 手術流程 根據病人首發病側確定首側植入電極,一般均為對側植入。確定框架靶點后,以穿刺點體表投影為中心做長約8 cm弧形切口,鉆直徑約14 mm的骨孔,切開硬腦膜,雙極電凝小功率處理周邊滲血并撐開蛛網膜,以防止套管針在旋轉進針時因蛛網膜阻力導致的橋靜脈受牽拉出血。緩慢植入套管針,然后立即打入適量生物蛋白膠密閉骨孔,重新形成密閉環境,減少腦脊液丟失和形成大量氣顱。所有病人使用Lead-point微電極記錄系統進行術中單通道MER。從目標靶點上方10 mm處記錄電生理信號,測得STN出現并且穩定2~3 s,信號至少>4 mm。否則應調整針道直到獲得滿意信號。局麻組的病人通過宏電極刺激做術中臨時測試,例如運動癥狀的改善以及不良反應的出現(復試、構音障礙和肢體麻木等)。拔出微電極后,植入永久性刺激電極(Medtronic 3389)并安裝十字定位環。使用術中C臂X光機第一次成像定位選定參考平面,確定電極深度。拔除套管針和電極內芯后分別進行第二次和第三次成像定位,確定3次透視電極深度始終位于同一平面后,使用StimLoc固定于骨孔并再次使用生物蛋白膠封堵。對側電極同法植入。植入顱內電極后,立即于全麻下將入式脈沖發生器(IPG)置于右鎖骨下皮下囊袋中。手術時間定義為從切皮開始至IPG置入鎖骨下囊袋后停止。
1.5 植入誤差和UPDRS-Ⅲ改善率 所有病人在麻醉喚醒后立即行頭顱薄層頭顱CT檢查,確定電極位置并同術前計劃框架靶點圖像融合。記錄術前計劃框架靶點坐標為xi、yi、zi和術后實際植入靶點坐標為xa、ya、za,分別代表相對于前后聯和線(AC-PC線)中點的內外側距離、前后距離和垂直距離。比較2組電極的矢量誤差。術后1個月進行調試開機,開機前告知病人停服抗PD藥物12 h以上。在開機后2 h狀態穩定且未服藥的情況下行UPDRS-Ⅲ評定,并與術前基線評分對比。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本研究包括148例雙側 STN-DBS 植入的病人,共植入296個電極。2組病人的術前基線特征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見表1。

表1 全麻組和局麻組的術前基線特征
2.2 植入靶點誤差分析 計劃框架靶點和實際植入靶點中首側植入電極為第一靶點,對側為第二靶點。全麻組計劃框架靶點和實際植入靶點在x、y、z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在局麻組,無論是第一或者第二靶點,y的差異均有顯著統計學意義(P<0.05),實際植入的靶點更偏向后方,見表2。

表2 全麻組和局麻組植入靶點誤差比較
2.3 手術時間和MER分析 全麻組的手術時間顯著小于局麻組(P<0.01)。見表3。全麻組第一靶點與第二靶點的MER穿透次數差異無統計學意義[(1.45±0.59)次比(1.56±0.50)次,P=0.161],局麻組第一靶點的穿透次數顯著少于第二靶點[(1.55±0.50)次比(1.86±0.82)次,P=0.006]。

表3 全麻組和局麻組的手術時間及UPDRS-Ⅲ改善率比較
2.4 術后效果 全麻組和局麻組術后1個月的改善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331)。見表3。
2.5 并發癥 局麻組病人當日CT檢查發現3例無癥狀腦出血病人,經保守治療后復查未見高密度影。其他所有病人均未出現電極移除、感染和其他手術相關并發癥。
3 討論
STN-DBS手術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病人生活質量,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保證手術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在本研究中,所有病人均在麻醉喚醒后立即行CT檢查,排除顱內出血以及確定電極最終植入位置[3]。2組病人的手術有效性通過植入位置誤差和術后1個月藥物關期的UPDRS-Ⅲ的改善率驗證。提高手術有效性的前提是將電極精準地放置在STN核團的背外側(感覺運動區)[4-5],這是影響臨床有效性的關鍵因素[2, 6-7]。本研究中,局麻組計劃框架靶點和實際植入靶點比較,兩側植入電極的前后距離有顯著差異,這種差異可能主要受到頭部位置和手術時間兩方面因素的影響。在植入顱內電極時,頭部位置和切口相對固定。由于局麻需要保證病人舒適度和氣道保護,因此不可能將頭部位置提高到最佳角度。相反,全麻組頭部位置可以提高到垂直于地面的穿刺點。這保證了操作過程中電極軌跡基本上垂直于地面,最大程度地減少了重力的影響。此外,較低的手術頭部位置會增加腦組織向后移位的傾向,而低的骨孔也會導致腦脊液過度丟失,加重腦組織的漂移,并影響電極植入的準確性。此外,由于局麻組處于清醒狀態,部分病人會因恐懼和緊張導致術中血壓波動較大而難于管理,不能耐受而增加配合難度。此外,術前需要停服抗PD藥物超過10 h,而且局麻組的手術時間也顯著長于全麻組,過長時間停藥或者較長的手術時間會導致部分病人達到藥物關期,從而降低術中檢查配合水平,增加麻醉管理的難度。這些缺點無疑都會導致手術時間的延長,進一步造成腦脊液過度流失和顱內氣體的積聚[8-10],從而引起不同程度的腦組織漂移。而全麻可以提供更好的手術條件,包括更短的手術時間和更好的病人體驗,這使得越來越多的病人選擇全身麻醉[11]。老年PD病人因其耐受性差,共患病較多,全麻技術無疑擴大了部分病人群體。此外,全麻可以更好地控制術中血壓[12],而且全麻可能會減少不良反應,如降低感染和腦內出血的風險[13-14]。因此,手術持續時間和頭部位置對于植入誤差有較大的影響。本研究還發現,局麻組和全麻組術后1個月UPDRS-Ⅲ的改善率(藥物關期)差異沒有統計學意義,這說明雖然植入電極的誤差在局麻組較明顯,但最終不會影響臨床療效。
手術的安全性體現在顱內出血、癲癇、精神癥狀以及感染等方面。本研究局麻組有3例無癥狀腦出血,經保守治療后吸收,全麻組無1例腦出血。由于局麻組過低的手術頭位和過度的腦脊液丟失,在驗證電極植入位置時,需要更多次的MER穿透次數才能到達實際目標靶點位置,這也得以糾正由于頭位和手術時長引起的腦組織漂移,提高植入的準確性。而且重復穿刺可能產生電極植入過程中多個平行軌跡,從而增加微電極引起血管損傷的風險和腦出血的發生率[12, 15-17]。也有研究指出,MER 中使用的微電極比永久電極尖端更鋒利,更可能穿透小動脈[18]。雖然部分研究指出,無論是否采用術中MER,術中CT或者MRI驗證電極植入位置,都可以達到相同的精度[19-20]。但是由于MER可以檢測和放大單個神經元的活動,并且提供實時的神經生理學定位和目標靶點的反饋[21-23],這一特有的驗證方式,使許多學者仍將術中MER作為驗證方式的金標準。
綜上所述,在使用MER驗證電極植入位置時,全麻相較于局麻有更小的植入誤差,手術時間更短且更安全。因此,全麻下DBS值得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