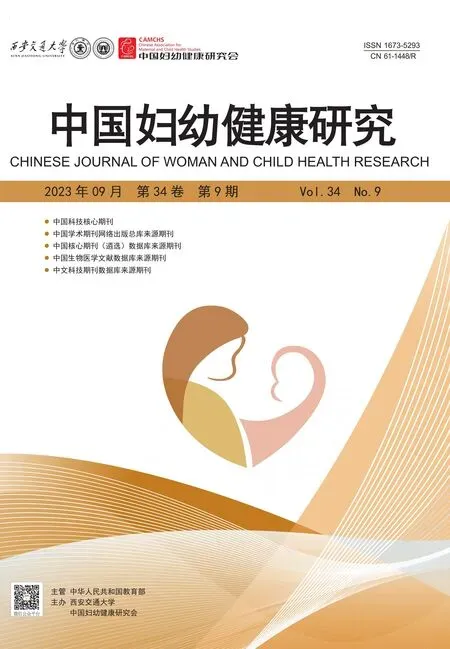胎齡小于32周早產兒經不同抗生素應用策略治療的效果比較及腸道菌群分析
王 慧,張銘濤,溫慧敏,劉新建
(河北中石油中心醫院兒科,河北 廊坊 065000)
隨著近年來孕婦保健意識與婦產科設備技術增強、高齡產婦增多等,早產兒早期干預率隨之升高,且活產早產兒數量不斷上升。而早產兒發育程度較足月兒低,出生后感染率、死亡風險等遠高于足月兒[1]。胎齡<32周早產兒屬于早期早產兒,機體各項功能發育程度相對于晚期早產兒更加不完善,脫落母體后適應環境能力差,大多需入住新生兒重癥監護室(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進行治療,并在生后即開始經驗性使用抗生素,但抗生素使用過度可能導致過敏、二重感染、細菌耐藥性等,進而影響早產兒預后[2]。同時,研究指出,人體嬰幼兒時期腸道菌群的構成與其后期肥胖、哮喘、炎癥性腸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的發生密切相關[3-5],而胎齡<32周早產兒大多因剖宮產無法接觸母親產道的正常菌群,加之抗生素的使用,使其腸道菌群分布與足月兒出現顯著差異,不利于其后期生長發育。因此合理規范胎齡<32周早產兒抗生素的使用策略意義重大。基于此,我院NICU在常規經驗性抗生素應用策略的基礎上進行改進,形成了基于風險評估+感染篩查+監測的抗生素應用策略,從腸道菌群、預后情況等入手,探討胎齡<32周早產兒經不同抗生素應用策略治療的效果,為規范臨床抗生素應用、改善早期早產兒預后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回顧性選取2021年1月至2022年6月河北中石油中心醫院NICU收治的胎齡<32周178例早產兒的臨床資料,根據抗生素應用策略的不同分為對照組(90例)和觀察組(88例)。納入標準:①生后24h內轉入我院NICU,并經系統治療,病歷資料完整;②單胎,于本院分娩,且胎齡<32周;③符合經驗性使用抗生素治療指征;④由同一醫護團隊接生、治療等。排除標準:①合并先天性心臟病、遺傳代謝性疾病等;②同時展開其他研究;③需要應用微生態制劑;④孕婦診斷為臨床型宮內感染;⑤有重大畸形等需外科手術治療等。脫落及剔除標準:①出生后家屬放棄搶救;②非本院產科出生;③住院時間<72h。本研究獲我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核批準(倫理批號:KYLL-2020-22)。
1.2 研究方法
對照組實施常規抗生素應用策略,早產兒出生12~24h后即采集外周血行非特異性感染指標[血培養、C反應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血常規等]檢查,并予以經驗性抗生素治療。然后依據早產兒檢驗結果、具體病情變化調整抗生素的使用:①無論5d內血培養陰性與否,一旦早產兒非特異性感染指標異常或有可疑癥狀均需繼續使用抗生素;②任何1項非特異性感染指標異常均需提升抗生素使用等級、延長抗生素使用時間。
觀察組實施基于風險評估+感染篩查+監測的抗生素應用策略:①對早產兒進行早發型敗血癥發生風險評估,對有早發型敗血癥(生后72h內血或腦脊液培養為陽性)高風險者立即開始予以經驗性抗生素治療,出生后12~24h入住NICU,并采取外周血完成非特異性感染指標(血培養、CRP、血常規等)檢查[6];②有臨床感染癥狀(休克、發熱或低體溫、反應差、激惹、皮膚花斑等)、3d內血培養陽性者繼續使用有效抗生素10~21d;③非特異性感染指標異常、有臨床感染癥狀、3d內血培養陰性者,繼續使用有效抗生素至7d;④無臨床感染癥狀、血培養陽性者,立即采集外周血復查血培養,5d內無感染中毒癥狀且復查結果陰性者停用經驗性抗生素治療;⑤無臨床感染癥狀、3d內血培養陰性者停用經驗性抗生素治療。
1.3 觀察指標
統計兩組腸外營養、機械通氣及住院時間。統計兩組出生后7d、住院期間(出生后至出院的時間)抗生素使用率、使用時間及抗生素使用時間分布(≤3d、4~7d、>7d)情況。
腸道菌群及構成比:早產兒出生后7d嚴格按照無菌操作取兩組糞便標本(量不少于5g),并置于-80℃冰箱保存;未排便早產兒以開塞露加生理鹽水通便;采用實時熒光定量聚合酶鏈式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法檢測腸道菌群含量,主要為乳球菌屬(格氏乳球菌、乳酸乳球菌、乳脂乳球菌等)、腸球菌屬(糞腸球菌、屎腸球菌、鳥腸球菌、希拉腸球菌等)、桿菌屬(腸桿菌、類桿菌、雙歧桿菌等),所用儀器為FQD-16A型實時熒光定量PCR分析儀(杭州博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時記錄兩組乳球菌屬、腸球菌屬、桿菌屬構成比。
預后情況:統計兩組住院期間過敏性哮喘(支氣管激發試驗或運動試驗陽性、支氣管舒張試驗陽性,且出現相關臨床癥狀)、過敏性鼻炎(臨床癥狀噴嚏、清水樣涕、鼻塞、鼻癢等癥狀出現2項以上)、食物過敏(食入過敏原后感覺嘴麻、嗓子癢等,同時根據病史和臨床表現、實驗室檢查明確診斷)、特異性皮炎(皮膚干燥,且伴有劇烈的瘙癢)、支氣管肺發育不良(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BPD)[7]、晚發型敗血癥[8](late-onset sepsis,LOS,患兒出現≥2項血液非特異性感染指標異常、血或腦脊液培養陽性,或出生72h后出現病情變化,或腦脊液檢查呈化膿性腦膜炎改變)、≥2期新生兒壞死性小腸結腸炎[9](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NEC,符合修訂貝爾診斷標準≥2A期者)、≥Ⅲ度腦室內出血[10](intraventricular hemorrhage,IVH,經顱腦B超或顱腦核磁共振成像檢查證實的Ⅲ~Ⅳ度)、≥3期早產兒視網膜病變[11](retinopathy,ROP,隆起的嵴上出現新生血管和纖維血管增殖、纖維血管增殖引起牽拉性視網膜脫離或視網膜全部脫離)、死亡等發生情況。
1.4 統計學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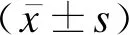
2 結果
2.1 兩組一般資料比較
兩組分娩方式、性別、孕母年齡、使用呼吸機比例、體重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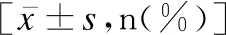
表1 兩組一般資料比較
2.2 兩組腸外營養、機械通氣及住院時間比較
觀察組腸外營養、機械通氣及住院時間短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值分別為6.200、6.341、13.639,P<0.05),見表2。

表2 兩組腸外營養、機械通氣及住院時間比較
2.3 兩組抗生素使用率、使用時間比較
觀察組出生后7d、住院期間抗生素使用率分別為61.4%、64.8%,低于對照組的88.9%、92.2%,且抗生素使用時間均短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χ2值分別為18.116、19.967、20.571、21.680,P<0.05),見表3。住院期間,觀察組抗生素使用時間≤3d占比為54.6%,高于對照組的11.1%;抗生素使用時間>7d占比為21.6%,低于對照組的75.6%,差異有統計學意義(Z=7.355,P<0.05),見表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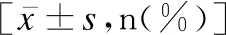
表3 兩組抗生素使用率、使用時間比較

表4 兩組抗生素使用時間分布比較 [n(%)]
2.4 兩組腸道菌群及構成比比較
出生后7d,觀察組乳球菌屬、桿菌屬含量高于對照組(t值分別為4.391、5.485,P<0.05),乳球菌屬、桿菌屬構成比也高于對照組(χ2值分別為6.200、13.639,P<0.05),見表5及表6。

表5 兩組腸道菌群含量比較

表6 兩組腸道菌群構成比比較 [n(%)]
2.5 兩組預后情況比較
住院期間,觀察組過敏性哮喘、特異性皮炎、LOS、≥Ⅲ度IVH的發生率均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值分別為6.593、7.303、3.899、4.582,P<0.05),見表7。

表7 兩組預后情況比較 [n(%)]
3 討論
3.1 胎齡<32周早產兒抗生素應用現狀
胎齡<32周早產兒為早期早產兒,是新生兒中的特殊群體,因其較早與母體脫離,容易導致心肺、神經系統、消化系統等發育程度受到影響,加之機體免疫功能發育不完整,容易出現多種并發癥而影響早期早產兒預后,其中又以院內感染最為常見,而抗生素為臨床遏制感染性疾病發展最有效的藥物之一,因此,NICU中早期早產兒抗生素應用頻繁[12]。此外,臨床醫師為了避免早期早產兒感染對其機體各項功能造成損傷,大多會盡早預防性應用抗生素治療早期早產兒。但抗生素的使用率升高,容易出現一系列抗生素藥物濫用問題,如不必要的抗生素應用、二重感染,或誘導產生細菌耐藥性而導致后期感染性疾病無藥可治等[13-14]。因此,監控和規范抗生素的臨床應用策略至關重要。
3.2 不同抗生素應用策略對胎齡<32周早產兒住院治療情況、抗生素使用率與使用時間的影響
基于風險評估+感染篩查+監測的抗生素應用策略通過評估早發型敗血癥發生風險、檢測非特異性感染指標、臨床感染癥狀觀察、血培養結果等予以早期早產兒不同的抗生素應用,對于無感染癥狀、3d內血培養陰性等早期早產兒停用經驗性抗生素治療,可有效縮短抗生素使用時間、避免抗生素浪費等[15-16]。本研究結果顯示,觀察組腸外營養、機械通氣、住院時間及抗生素使用時間短于對照組,抗生素使用率低于對照組;且觀察組抗生素使用時間≤3d占比高于對照組,抗生素使用時間>7d占比低于對照組,進一步說明基于風險評估+感染篩查+監測的抗生素應用策略在NICU早期早產兒治療中是可行的,亦可顯著縮短其治療時間,有助于減少住院費用,節約醫療資源。
3.3 不同抗生素應用策略對胎齡<32周早產兒腸道菌群的影響
腸道菌群對人體健康至關重要,與免疫調節、營養吸收及代謝密切相關。腸道菌群的定植是一個復雜的過程,而新生兒期是腸道菌群動態變化的特殊時期,其定植與構成受到胎齡、生產方式、治療方式等因素的影響,其中,抗生素的使用可殺滅腸內多種共生菌、影響腸道菌群穩定性等[17]。本研究中,出生后7d內早期早產兒腸道菌群組成主要為乳球菌屬、腸球菌屬、桿菌屬,且觀察組乳球菌屬、桿菌屬含量及其構成比均高于對照組,腸道菌群減少情況較少,分析與基于風險評估+感染篩查+監測的抗生素應用策略的實施可縮短抗生素使用時間、防止其對早產兒腸道內環境的破壞等有關;而兩組腸球菌屬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與既往研究結果存在差異[18],考慮與納入研究對象存在差異、本研究樣本量相對較少等原因有關。
3.4 不同抗生素應用策略對胎齡<32周早產兒預后情況的影響
本研究還發現,觀察組住院期間過敏性哮喘、特異性皮炎、LOS、≥Ⅲ度IVH的發生率低于對照組,提示基于風險評估+感染篩查+監測的抗生素應用策略可改善早期早產兒預后情況。分析原因可能為早產本身為早發型敗血癥最強預測因素,而新生兒早發型敗血癥的臨床表現無特異性,對早期早產兒進行早發型敗血癥發生風險評估時,結合非特異性感染指標檢查給予經驗性抗生素治療是及時控制高風險早產兒病情進展的關鍵[19-20]。此外,血培養為指導抗生素合理使用的重要依據,也是診斷敗血癥的金標準。CRP則為急性時相反應蛋白,可在氣胸、新生兒窒息等疾病中明顯增高。因此,結合血培養、CRP、血常規等非特異性感染指標及臨床感染癥狀來判斷是否繼續使用抗生素或延長經驗性抗生素的使用時間,可進一步合理應用抗生素控制早期早產兒病情進展,同時預防抗生素過度使用對早期早產兒機體產生損害,改善其預后情況[21-22]。
綜上,基于風險評估+感染篩查+監測的抗生素應用策略可縮短胎齡<32周早產兒抗生素使用、腸外營養、機械通氣及住院時間,并降低抗生素使用率,防止腸道菌群減少,進而改善早產兒預后情況。但本研究亦存在一定的不足,如納入對象較為單一、研究樣本量相對較少、缺乏遠期隨訪等,臨床仍需進一步研究以改善胎齡<32周早產兒抗生素應用策略,進而改善其預后、節約醫療資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