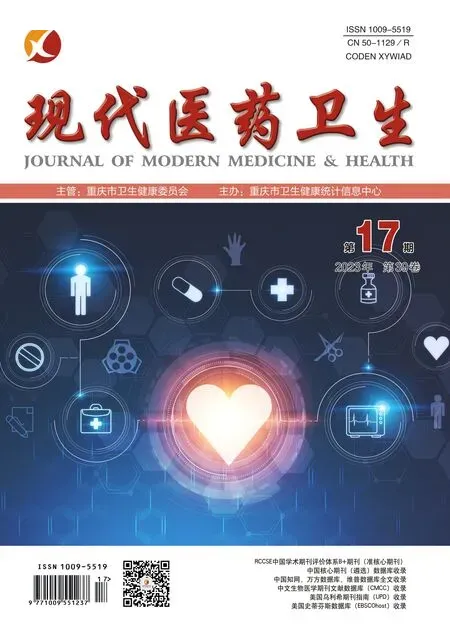基于文獻計量研究國內藥品帶量采購的現狀分析
詹 菊
[遵義市第一人民醫院(遵義醫科大學第三附屬醫院)臨床藥學部,貴州 遵義 563000]
藥品帶量采購是一項有利于民生的政策,最大限度上解決了患者“看病難、看病貴”的狀況,2019-2020年,國家相繼發布了《關于印發國家組織藥品集中采購和使用試點方案的通知》(國辦發〔2019〕2 號)[1]、《關于以藥品集中采購和使用為突破口進一步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國醫改發〔2019〕3 號)[2]、《關于深化醫療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見》[3]等文件,提示我國藥品進入了集中采購時期,隨著2021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動藥品集中帶量采購工作常態化制度化開展的意見》(國辦發〔2021〕2 號)[4]的出臺,標志著藥品集中采購工作的常態化、規范化的進程。但由于藥品涉及的種類多、范圍廣、實施的時間短等,目前仍處于不斷的實踐探索階段。基于此,本研究通過對現有的文獻進行分析,并對開展藥品集中采購的主要研究者、研究機構及目前涉及的方向等問題進行可視化分析,有利于掌握藥品集中采購的進程,預測相關主題的發展方向及趨勢。
1 資料與方法
1.1文獻來源及檢索方法 檢索中國知網(CNKI)數據庫中2010年1月至2022年11月與藥品集中采購相關的文獻,以“帶量采購”為主題,學科選擇“藥學”,將檢索的結果按照reworks格式導出,并命名為“download_XXX”,將導出的數據進行去重復處理。
1.2研究方法 Citespace 是常見的文獻計量研究工具[5],將1.1項下的數據導入citespace 6.1R3軟件,并進行數據轉化。將轉化后的文獻數據導入軟件中進行發文量、機構、作者及研究熱點等主要信息進行定量分析,繪制作者、機構及關鍵詞的共現圖,并對關鍵詞進行聚類、log-likelihood ratio (LLR)分析、引文突現強度等分析。
2 結 果
2.1發文量的分析 共檢索去重復后得到650篇文獻,從結果可見,近5年的發文數量呈急劇上升趨勢,結果見圖1。

圖1 帶量采購文獻的年發文量
2.2作者及機構分析 將去重復的文獻導入到citespace 6.1R3軟件,以時間碎片為1作為標準,分別繪制作者及機構的共現圖(圖中的一個節點表示一個作者或機構,有連線的地方表示兩者之間存在共現關系,且字號越大,表示的文獻量越多),結果見圖2、3。從圖2、3的結果可知,作者和機構的密度分別為0.013 3和0.012 5,表明作者及機構的聯系并不緊密。通過分析發文量排列前10的文獻,目前楊照等[6]、陳昊等[7]、薛天祺等[8]發文量較大,主要研究集中于對政策的實踐與思考。從機構來看,對藥品帶量采購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及健康發展中心等(如中國醫科大學國際醫藥商學院、北京大學藥學院、北京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等)。

圖2 作者共現關系圖
2.3研究熱點及趨勢分析
2.3.1關鍵詞的共現圖及聚類分析 將去重復后的文獻導入citespace 6.1R3軟件,設置K值為25,繪制關鍵詞共現圖并進行聚類分析,計算LLR值,結果見圖4及表1,從高頻關鍵詞來看,除帶量采購及集中采購以外,仿制藥、藥品、原研藥、用藥頻度、公立醫院及醫療機構等關鍵詞的排列均較前,除原研藥以外,其余關鍵詞的中心度均大于或等于0.1,由圖3的聚類分析圖可知,聚類排列前3的分別為#0帶量采購、#1原研藥、#2集中采購;通過計算LLR值,排列前3的聚類ID分別是聚類4、10、7,結果見表1,通過對以上結果的展示發現,從用藥政策層面,目前帶量采購、集中采購、招標采購是目前主要的采購方式,而實行采購的主體為醫療機構、醫院、零售藥店等,除此之外,原研藥、仿制藥、用藥頻度等相關的研究也列入前10的聚類中,表明藥品的質量及合理用藥等是目前研究者較為關注的內容。

表1 關鍵詞的聚類后LLR值結果

圖3 機構共現關系圖

圖4 關鍵詞的聚類分析圖
2.3.2關鍵詞的時區圖 時區圖是以關鍵詞出現的年份為標記點,以出現頻次為累計量,能夠很好地展示該主題關鍵詞的演變及變化趨勢。如圖5中,每個節點代表藥品集中采購的熱點關鍵詞,節點越大表示出現的頻次越多,節點最上方對應的是關鍵詞出現的年限。從圖5關鍵詞的時間線圖可以看出,2018年前,主要是理論的形成階段,2018-2020年是初步執行期,隨著時間的推移,集中采購涉及的藥品種類增加,涉及的面更廣泛,發展更加創新,近2年的主要集中在藥品的管理、藥品的規范化使用、藥品的供應保障及使用情況等方面。
2.3.3關鍵詞的突出強度排名 以γ等于0.5為標準,計算關鍵詞的突出強度,共得到19個突現詞,結果見圖6。由圖可知,2011-2015年的突現詞為基本藥物、閔行模式、招標采購;2015-2017年的突現詞為二次議價、安徽省、聯合體、招標采購、以藥補醫、配送企業、醫保支付,2017-2022年的突現詞為雙信封、低價藥品、陽光采購、藥品采購、藥品價格、冠狀動脈支架及零售藥店。

圖6 關鍵詞突現詞結果
3 討 論
通過分析各年度的發文數量發現2010-2014年屬于研究初期,發文量較少,2015-2018年發文量呈上升趨勢,處于研究的探索期,近5年來,關于藥品集中采購的文獻急劇增加,屬于研究快速發展及實踐探索期。通過對研究機構及作者的分析,發現機構及作者之間存在合作關系,但合作不夠緊密。
通過對關鍵詞的分析,2011-2014年的關鍵詞有公立醫院、采購機制、基本藥物等,該時期主要以省級采購為主,該時期對藥品集中采購機構建設、制度建設、醫療機構、藥品生產經營企業、藥品集中采購目錄和采購方式、藥品集中采購程序、藥品集中采購評價方法、專家庫建設和管理、監督管理與申訴、不良記錄管理等方面作出了明確說明。2015-2017年主要的關鍵詞為集中采購、以藥補醫、采購機制、醫聯體等,該階段主要以堅持以省(區、市)為單位的網上藥品集中采購方向,實行一個平臺、上下聯動、公開透明、分類采購,采取招生產企業、招采合一、量價掛鉤、雙信封制、全程監控等措施,藥品的監管涉及采購的所有過程,切實保障藥品質量和供應,使藥品采購進一步得到規范,但以上2個時期中藥品出現量價脫鉤,招標采購中普遍只招價格不帶量,藥品價格存在虛高,而低價中標的企業卻難易存活的亂象。2018-2019年主要的關鍵詞有仿制藥、原研藥、兒童用藥等,該時期國家為了減輕患者的用藥負擔,保障群眾用藥安全,健全藥品供應機制,提出了“國家組織、聯盟采購、平臺操作”的總體思路和“帶量采購、以量換價、量價掛鉤、招采合一、確保用量、保證回款”的主要原則,有序地實施了藥品集中采購和使用。該時期可看出,在藥品質量方面,對納入集中采購的藥品必須符合質量和療效的一致性,有序地擴大藥品采購范圍,同時,該時期也提出將高價的醫用耗材納入集中采購的范圍。2020年至今,主要的關鍵詞有胰島素、中成藥、中藥飲片、臨床使用等,該時期屬于藥品采購進入規范化、常態化、制度化的新時期,集中采購的品種不斷擴大,包括了一些生物制品及中成藥等,同時該時期很多醫療機構都對集中采購的藥品經濟性方面進行了評價,有研究表明,很多藥品的日均承擔藥費均降低,如抗腫瘤藥[9]、降壓藥[10]、質子泵抑制劑[11]、他汀類藥物[12]、精神病藥[13]等。而對于藥品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方面的評價相對較少,有研究表明,抗菌藥物集中采購后,臨床在選用品種、強度等用藥習慣上發生了改變,耐藥率呈現出一定的變化趨勢,且兩者之間存在相關性,建議醫療機構應制訂與集中采購政策同步、配套的抗菌藥物使用整治方案[14]。除此之外,該時期亦出現了供給風險、供應中斷等關鍵詞,表明這時期,隨著帶量集中采購的數量及范圍的增大,出現某些企業供應不足的情況。未來,有望逐步向零售藥店開放集中采購藥品購銷通道,今后市民可以在藥品購買零差價的集中采購藥品,可降低醫療機構的購藥壓力,為患者帶來更多的便利及福利。
綜上,目前我國的藥品集中采購已經進入了常態化、廣覆蓋、穩步前進階段,最大限度地解決了患者“看病難”的問題,然而該政策執行的時間短,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如從目前的文獻報告來看,由于不同廠家、同一通用名的藥品生產工藝存在偏差,仿制藥與原研藥的藥動學雖然能達到一致性,但在藥效上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性[15]。目前,醫療機構對集中采購藥的藥效一致性及安全性缺乏相關的資料、藥品供應企業存在供應不足情況、對集中采購藥物的綜合評價系統尚不完善等,基于此,作者建議從國家層面制定科學規范的藥品集中采購體系,做好質量、供應、使用三方面保障措施,藥品供給企業,不斷完善藥品生產工藝,保障藥品的質量及供給,醫療機構應及時保證藥品金額的兌付,并充分發揮臨床藥師的能動性,推動集中采購藥物的臨床應用、有效性及不良反應的研究,從多個層面保障廣大人民群眾的用藥安全及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