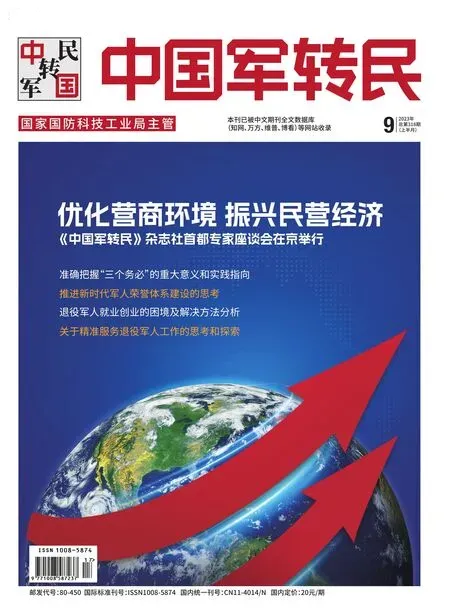由“南陳北李,相約建黨”論中國共產黨建黨的歷史必然
張雪敏 楊梅
一、“南陳北李”的內涵
“南陳北李”是指創建中國共產黨的首領是南方的陳獨秀和北方的李大釗,[1]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史學界公認的說法。以“南陳北李”稱呼中國共產黨建黨的首領,是因為二者在建黨工作中的杰出貢獻。
李大釗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在中國共產黨建黨中的主要貢獻是宣傳馬克思主義,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打下思想基礎。李大釗進入北大擔任圖書館主任之后,利用北京大學圖書館改革的機會,公開地購買了很多馬克思主義書籍,并組織北大學生翻譯成中文供大家學習。還撰寫并發表了大量的文章宣傳馬克思主義。如我們很熟悉的《庶民的勝利》《法俄革命之比較觀》《 Bolshevism 的勝利》等。還發表《團體的訓練與革新的事業》一文直接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做輿論宣傳。關于李大釗在當時中國思想界的影響,章士釗予以了高度的評價:“守常先充圖書館主任, 而后為教授。 ……時北京民主運動正在萌芽,守常志在得北大一席, 以便發蹤指示。 ……守常一入北大,比于臨淮治軍,旌旗變色。”[2]
“南陳北李”中“陳獨秀應屬首位”。陳獨秀比李大釗年長10 歲,成就在前,社會影響力更大。辛亥革命時期陳獨秀就創建報紙、組織岳王會;武昌起義后,他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在安徽很有政績;“二次革命”中,他又主持安徽獨立抗袁。最重要的是,他創建了新文化運動的主陣地—《新青年》雜志,使民主與科學觀念深入人心[3],也使自己成為當時中國進步勢力的旗幟。陳獨秀深得李大釗愛戴,當共產國際找到李大釗商量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組織事宜時,李大釗毫不猶豫地向共產國際推薦陳獨秀作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陳獨秀在會見共產國際代表后,于1920 年8 月上旬成立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之后,信約李大釗在10 月份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立。之后陳獨秀又委托劉伯垂和董必武在武漢建立黨組織、信約毛澤東在長沙建立黨組織、還親赴廣州建立黨組織,要求已經加入黨組織趙世炎在法國建立黨組織,委托王樂平在山東建立黨組織等。可見,在中國共產黨建黨中,陳獨秀是最重要的組織者。
經過多方籌劃,一般認為,1921 年7 月23 日,全國各地共產主義代表在上海法租界李漢俊的家里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告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全國性的政黨正式成立。
二、“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內因說和外因說爭論
關于中國共產黨建黨,中國大陸基本采用“內因說”,國外則比較傾向“外因說”。雙方爭議的“點”在于:共產國際代表魏金斯基來華之前,“南陳北李”有沒有相約建黨。
“南陳北李”相約建黨一說最初來源于高一涵。高一涵在1927 年5 月22 日中山大學追憶李大釗的演講《報告李守常同志事略》中提到,1920 年1 月李大釗送陳獨秀從天津轉上海的途中兩人商議了建黨的事情。
肯定說認為高一涵與陳獨秀是老鄉,兩人一起在日本時同是《甲寅》雜志的編輯。回國后,陳獨秀創辦了《新青年》,高一涵是《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高一涵與李大釗在日本一起創辦“神州學會”,同為《民彝》雜志的編輯。之后三人同時是北京大學的教授。高一涵發表演講時正值中年,健康狀況良好,當時在場三千多人,且有許多著名人士和知名人物,不存在高一涵作為一個嚴肅的政治學學者在這種莊嚴的場合胡編亂造的可能。[4]再有就是,五四時期的北大學生、和李大釗共過事關系密切的朱務善也說過與高一涵相類似的話[5]。
否定說認為這是高一涵的道聽途說,不可信。日本學者石川禎浩根據1920 年2 月13 號高一涵從日本寄給陳獨秀和胡適的信,以這個時候高一涵正在日本,但對“南陳北李”相約建黨一事的描繪生動逼真仿佛小說一般,因而懷疑純屬捏造。旅英學者李丹陽則根據黃埔軍校政治部蘇聯顧問納烏莫夫發表于《廣州》1927 年第1 期的《中共簡史》,將1918年李大釗發起的馬爾格時學說研究會作為中國最早的共產主義團體,再聯系歷史學家金毓黻所言“李大釗擔任北大圖書館主任之后,就與蘇俄人有來往……其中常來常往的有兩個俄國人”。這兩個俄國人據李丹陽考察,一個為舊俄駐北京的外交人員,一為俄共人員。從而推斷出與蘇俄人員的聯系是李大釗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關鍵因素[6]。依據2021 年3 月31 日北京大學發布的《李大釗年鑒》,李大釗進北京大學的確切時間是1917 年12 月。按照李丹陽的邏輯,1917 年12 月之后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因為李大釗與俄國人的往來關系,一切都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之下了。爭論雙方為什么要摳這個細節呢?石川禎浩在他的書中寫的很清楚,他把它看成事關中共誕生是蘇俄“輸出革命”的結果,還是近代中國革命運動發展的必然產物[7]的關鍵證據。也就是說,爭議雙方關注的根本不是這件事情的細節本身,而是背后的意識形態立場。不過因為這個細節本身的可承載性的緣故,爭議雙方試圖賦予的責任顯然超出了它的承載能力。

三、“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歷史必然
湖北大學田子渝教授認為,關于“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細節討論,否定說“沒有也無法否定中共創立是近代中國社會發展到五四時期的必然產物這個歷史事實, 正如1921 年7 月至8 月間舉行中共一大的時間有其偶然性, 但中共一大遲早必定會舉行的那樣”。肯定說也只是“內因決定說”的一個證據而已。從中華民族救亡史上來說,鴉片戰爭之后中國人的自我救亡就沒有停止過。以十月革命和巴黎和會為契機,中國人選擇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的必然。從中國政黨史上來說,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中很多源自于中國國民黨,這些原國民黨人觀念轉變之后建立新黨也在情理之中。從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來說,新文化運動馬克思主義宣傳中有大量介紹和辨別歐美社會黨的文章,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水到渠成。[8]
關于中國共產黨的建黨,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這樣表述的:“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和我國“五四”運動的影響下,在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幫助下誕生的。”肯定了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建黨的幫助,但明確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俄國革命與五四運動的影響”是中國共產黨建黨的前提。
(一)從空間維度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來看
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途徑的空間維度主要有三個:日本、法國和俄國。三個維度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樣的。日本路徑主要進行馬克思學說一般理論性傳播,法國路徑主要進行工人運動經驗傳播,俄國創立主要為中國革命提供了一個現實的實踐“范式”[9]。蔡元培先生說:“西洋的社會主義,二十年前才輸人中國 。一方面是留日學生從日本間接輸人的…… ;一方面是留法學生從法國直接輸入的”。[10]蔡先生在文中并沒有提俄國,因為俄國這個傳入途徑是最晚的。直到十月革命后,中國才開始比較多地關注俄國。
甲午戰爭之后,在張之洞的推動下,5、6 年間,留日學生就猛增至萬余人。[11]“1896 年至 1911 年間,中國留日公費自費生不下 2 萬人”[12]。中國共產黨早期發起人和創建人中,很大一部分有留學日本經歷。“南陳北李”都是。留學生們受到日本社會主義思潮多大影響呢?我們以李大釗為例。日本研究李大釗的著名學者后藤延子認為李大釗很多文章是以日本學者堺利彥的文章為藍本的[13]。李大釗自己在文章《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明確注明,該篇文章所用參考書報中包括茅原華山的《人間生活史》[14];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直接注明“以上的譯語,從河上肇博士”[15]等。
受工讀主義、泛勞動主義影響,在蔡元培、李石曾、吳稚暉等人的推動下,大量中國學生赴法國勤工儉學。由于組織者對當時法國的就業形式,以及學生自身的復雜情況估計不足,導致學生們來到法國后,短短兩年時間內,先是因為就業困難發動了“二二八”運動,接著因為北洋政府以全國印花稅、全國實業購料權、滇渝鐵路建筑權等做抵押秘密向法國貸款購買軍火的消息在法國泄露發生“八一三”事件,為奪回里昂中法大學的就讀權發生“中法大學事件”。
這些學生一般在國內就接觸過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書刊雜志,多多少少受到一些影響。來到法國之后,勤工儉學的經歷使他們親身體驗了工人階級的境遇,一些學生還參加過法國當地工人1920 年的五一節罷工游行,法國工人運動的馬克思主義傾向,必然會影響勤工儉學生。[16]在此基礎上,三次運動的實踐使學生們意識到,工讀主義、泛勞動主義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對于大多數的底層民眾來說,真正能夠指引他們改變個人與社會的,只有馬克思主義。因此,此后勞動學會和工讀世界社的成員“不約而同地轉向了馬克思主義”[17]。
(二)從時間維度的中國工人運動史來看
為反抗外國侵略者奴役 ,早在1858 年四五月間,香港澳門的“為洋人教書、辦理文案及一切雇工人等”2 萬余人“辭退”“告歸”回到廣州。[18]1882 年,為爭取與廣東籍工人平等工資待遇,開平煤礦直隸籍工人罷工[19]。到辛亥革命前后,中國工人運動的范圍越來越廣。1905 年“抵制美貨”運動,香港、廣州、上海、南京、蘇州等地的工人都參加進來。1911 年辛亥革命高潮中,京漢鐵路的工人,上海的工人,甚至當時張家口的工人,都紛紛聲援。及至一戰到五四運動前,據不完全統計,1914-1919 年5 月期間,全國共發生罷工108次[20]。1919 年,上海工人階級在當時已逾 51 萬,占全國工人總數的 1/4 強,占該城市人口的 1/5。[21]這一時期,工人還和農民結合起來一起反抗,如湖南龍山銻礦工人,為抗疫礦警強殺礦工,與附近數萬農民聯合起來暴動[22]。頻繁的罷工,豐富了中國無產階級的斗爭經驗,也加強了全國各級各領域的無產階級的聯盟。但工人罷工的成功率只有1/7。[23]
世界工人運動的一般規律是由自發走向自覺。中國工人處于世界罕見的殘酷壓迫下,反抗是必然的。地域越來越廣泛、參與人員越來越多的罷工標志著中國早期工人的覺醒 。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以及一戰中“華工”的陸續回國,中國工人運動走向自覺是歷史的必然。
(三)從組織維度的中國早期共產主義組織創立史來看
早在1917 年,惲代英就在武漢建立了以“自助助人”為目的的互助社。1919 年底受“新村主義”影響,互助社骨干惲代英、余家菊、林育南等人將互助社改造成具有新生活體驗性質的“利群書社”。1921 年發展成具有共產主義性質的共存社,這是在武昌獨立開展的建黨活動。毛澤東、蔡和森等于1917 年醞釀組建學會,1918 年在長沙河西蔡和森家成立了新民學會。1920 年,利用譚延闿、趙恒惕提倡湖南自治,毛澤東成立文化書社,成為當時湖南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同時廣泛團結了湖南各界進步知識分子和進步人士,為湖南共產黨組織的建立奠定了組織和干部基礎。
處于信息相對閉塞狀態的四川,吳玉章與楊闇公等大概在1922-1924 年[24]獨立地成立了“中國青年共產黨”。“中國青年共產黨”的綱領和章程基本具有無產階級政黨的本質,代表無產階級的基本利益。“中國青年共產黨”雖然后來解散,黨員或轉入中國共產黨,或轉入社會主義青年團,但其“在思想發動和干部培養上均為四川建黨做出了積極的貢獻”[25]。
在海外,新民學會的創始人之一蔡和森,留學法國后把新民學會的工作發展到了法國。1921 年7 月,蔡和森、趙世炎和李立三準備成立“中國少年共產黨”。蔡和森被遣送回國后,周恩來、趙世炎和李維漢共同組織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雖然這個“中國少年共產黨”到底是一個黨組織還是一個團組織存在著爭議。但是不影響它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獨立創建的早期共產主義組織的性質。
綜上,“南陳北李”相約建黨是因為中國已經具備了創建共產黨的基本條件。共產國際選擇在中國建立支部,也是因為中國已經具備了基本的條件。從歷史唯物主義來看,沒有共產國際的介入,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也是遲早的事情。這是歷史的合力作用的結果,不是某個個別外因能夠決定的歷史進程。毛澤東說:“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大的作用,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需要,是因為同中國人民革命的實踐發生了聯系,是因為被中國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系,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26]
在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的今天,我們固然不能忘記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但更加不能妄自菲薄,無視我們先輩在救亡圖存,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道路上奮發圖強、不懈探索的歷史和精神。這是我們民族自信的底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