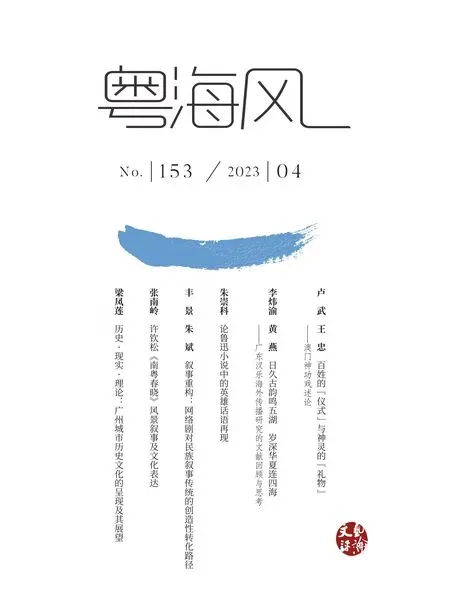百姓的“儀式”與神靈的“禮物”
——澳門神功戲述論
文/盧武 王忠
說起戲曲,就不得不談被譽為“南國紅豆”的粵劇。2009年粵港澳聯合將粵劇成功申報為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它是大灣區一張生動鮮活的文化名片,也是聯結粵港澳三地民眾情感的紐帶。粵劇主要以劇院粵劇、私伙局粵劇(民間自發組織的曲藝社)、神功戲粵劇三種方式存在。時至今日,粵劇已成為澳門本地文化的重要印記,其在澳門依然活躍的表演形式主要是神功戲。整體來看,有關澳門神功戲的研究較為稀缺,幾乎都被囊括在粵劇研究中,或泛泛而談,或一筆帶過。神功戲粵劇的傳承與發揚是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共建人文灣區”的重要舉措。澳門目前仍有七間廟宇的神誕保留著上演神功戲的傳統,在傳統習俗式微的現今,這份堅持尤顯難能可貴。
一、神功戲在澳門的發展論述
粵劇在澳門起源于何時已無從考證。早在400年前,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便在著述中論及澳門的一種戲劇表演。他在1582年首次抵澳,“他(利瑪竇)說的戲劇表演,極可能就是粵劇的前身。”[1]最遲到19世紀30年代,粵劇在澳門已十分普及并深受民眾歡迎。[2]中國戲曲現代學術研究的開創者王國維揭示了中國戲曲和巫覡祭祖的關系,認為戲曲脫胎于宗教儀式、巫術舞蹈與神靈崇拜。依據澳門議事廳、澳督的諭令以及報章記載,澳門戲曲特點之一便是酬神演劇多。據1852年的《中國叢報》所載,澳門的蓮峰廟、火神廟、媽閣廟、土地廟、金花娘娘廟等處都有戲曲演出,一次演出通常持續四日到七日不等。[3]

圖2 農歷四月初八譚公誕,譚公廟前架起的花牌和彩旗。
千百年來不同的國家、地區和民族都會有一些類似祭天祭神的活動,這是戲曲的發源,戲班對天地鬼神的敬畏更為虔誠,無論沿海地區還是內陸均如此,神功戲就產生于這樣的背景。神功戲這個名字實際是廣東班的叫法,一般農村碰上大祭或者神的誕辰,就得請戲班來演神功戲。神功戲又稱酬神戲,“神功”的意思是神做的功德,是百姓為酬謝神恩、祈福禳災而舉行的一連串活動。神功戲按籌辦性質可以分為神誕慶典、太平清醮、盂蘭打醮、廟宇開光、傳統節慶等。神功戲在澳門主要以神誕慶典的形式存在。為神靈的誕辰舉辦慶賀活動,從來不是澳門地區獨有的儀式,不論南北地區,賀誕總是離不開出巡儀式、表演娛樂和大擺宴席,仿如一場為神靈而設的“嘉年華”。當然,由于各個地區環境不同,內容也有差異。雖然澳門地區賀誕的規模遠遜于內地,但儀式更為原汁原味,百年的傳統一直在戲棚之中傳承。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流之地已有400余年,當中最為人稱道的,莫過于眾多中式廟宇與西洋教堂兼容并存的盛況,作為嶺南地區的華人社會,供奉佛祖、觀音、天后、北帝、關帝、女媧、呂祖、土地、太歲、三婆、魯班、金花、濟公、包公、華佗、醫靈、華光、財帛星君、譚公、康公、石敢當等神祇的廟宇、宮殿、神龕一應俱全,出現了“一廟供諸神”的奇觀。
澳門神功戲歷史悠久,關于神功戲活動的記載有較直接的文獻可考:沙梨頭土地廟大殿內撰于嘉慶年間的《重修澳門沙梨頭社稷神壇碑記》、公局新市南街關帝廟刻于道光年間的《重修三街會館碑記》、十月初五日街康真君廟的《澳門康真君廟創建暨奠土各收支數總列碑記》《康真君廟奠土喜捐醮戲金碑記》(時間不詳)均有記錄,河邊新街福德祠保存有一塊光緒年間由“演戲公司”贈送的木匾,蓮溪廟也有道光、咸豐年間演戲值理的賀匾,這些都是佐證。澳門賀誕酬神的歷史,早在17世紀時已傳到歐洲,1695年意大利旅行家杰梅利·卡雷里(Gemelli Carreri)游歷中國后,回國編寫了《環球旅行記》,其中記錄了在澳門上演的一場大戲。[4]1839年在澳門旅居的法國畫家奧古斯特·博爾杰(Auguste Borget)曾詳細描繪澳門各消費層次的市民觀賞神功戲的情形,他寫道:
允許在廟宇附近搭戲臺……和尚們常常在廟院里一邊抽著煙斗,一邊看戲……社會各階層的人混雜在那里,有乞丐,有瞎子,有海員,有游客,甚至于還有穿著豪華的闊佬。在這狹小的空間里大家熙熙攘攘擠成一團……觀眾對戲極其有興趣,倒不是鼓掌和嘈雜聲說明了這一點。[5]
中國人太喜歡看戲了,有的人找不到座位,就爬上了戲臺的竹棚上。后面來的人則要那些已經爬在竹棚上的人再爬高一點。這樣竹架上像戲院里的包廂一樣擠滿了人。盡管他們需要使盡全力才能使自己停留在那危險的地方,他們還是全神貫注地看戲。[6]
神功戲是市民的文娛消遣,時至今日依然如此。每年的神功戲,吸引眾多街坊前去觀看,澳門神誕已成為澳門民眾的狂歡節。神功戲及所衍生的各種游戲、歌舞等民俗活動,凸顯了神誕與神功戲的世俗化和娛樂化。澳門的神功戲往往與舞龍舞獅、飄色巡游、攤位游戲、敬老宴會等同場舉行,神圣信仰背后是民眾世俗的、喜慶的娛樂和狂歡,澳門各時期神功戲活動的興盛在文獻中均有記載:
照得本澳前數日華人建醮慶鬧,經有中外數萬人之眾前來看會,所見多是華人。因此次四方雜處,中外云集,幸藉平安,并無憂心之事。[7]
連夜澳中各商戶虔奉關壯繆、包孝肅、華元化先醫、康真君各神牌像,巡游全澳,自十四晚而止。每夜燈光燦然,明星萬點,皆系各行店備燭助慶,遣伴隨行。[8]
十四晚在火船頭曠地內,某八九行迎致小獅,在此跳舞,焚燒炮竹至數千萬響,計時約一打鐘之久……于時旦見火光一片,金鼓喧騰,并炮竹聲而震耳……圍而觀者至數百人,皆拍掌而喝彩。[9]
由此可見,澳門神功戲具有深厚的群眾基礎。據史料記載,蓮溪廟、蓮峰廟、康公廟、火神廟、包公廟、金花娘娘廟、石敢當廟、藥王廟等都曾舉辦過神功戲。目前澳門主要有七間廟宇的神誕仍在舉辦神功戲,包括沙梨頭土地廟和雀仔園福德祠的二月初二土地誕、凼仔北帝廟的三月初三北帝誕、媽閣廟的三月廿三天后誕、路環譚公廟的四月初八譚公誕、大三巴哪吒廟的五月十八哪吒誕、新橋蓮溪廟的九月廿八華光誕。其中百姓對土地和媽祖信仰尤甚,土地與海洋正好反映當地百姓對生存生產的基本欲求,文獻記載:
沙梨頭土地廟前搭起了高大的七彩牌樓,四周張燈結彩。中午,眾街坊善信扛著整只燒豬,帶備三牲酒醴、庶饈餅餌和香燭紙錢等祭品,到土地廟虔誠上香酬神賀誕。[10]
查舊日到廟賀誕之燒豬,每逾三四百只之多云。而海上漁民,以天后為海神,故對天后誕,更為高興。當澳門漁業興盛時期,媽閣海面,帆檣千百,密泊如織。蓋漁船出海捕魚,雖至遠亦必歸來賀誕,燈籠串炮,矚目喧鬧。[11]
慶賀活動通常會持續幾日,其中又以神靈的誕辰之日最為熱鬧非凡,上演的神功戲劇目繁多,故事性、審美性與思想性兼備。中國百姓具有“樂天”精神,所創作的戲曲也往往具備樂觀色彩。體現在神功戲中,一方面要安排一些喜慶熱鬧場面,另一方面則喜好大團圓結局。內容上大多包含善惡到頭終有報、有志者事竟成、有情人終成眷屬等主旨以符合傳統戲曲“勸人倫,成教化”的道德追求,這些是民眾期待、信賴因果循環的結果,既可以滿足百姓的娛樂需求,又可以增強他們的生活信心,引人向善。劇目大致可以歸納為4種:一是演繹經典傳說,如《七月七日長生殿》是唐玄宗與楊貴妃愛情悲劇的演繹;《斷橋》是白素貞和許仙人妖之戀的演繹;《將相和》講述了廉頗和藺相如的傳奇佳話;《六國大封相》則講述戰國蘇秦游說六國合縱抗秦的故事。二是弘揚傳統美德,宣揚忠、孝、仁、義、禮、信等傳統美德體現的是神功戲的教化作用,“百善孝為先”的傳統觀念在劇目中尤為凸顯,如《目連救母》《寶蓮燈》《仕林祭塔》等。三是蘊含美好祝愿,如《祭白虎》寓意著“驅邪避兇”,《香花山賀壽》寓意著“健康長壽”,《天姬送子》寓意著“人丁興旺”,《跳加官》則由“天官”來賜福百姓,天官手中的條幅上書寫著吉語,除了有傳統的“加官進爵”“步步高升”外,條幅內容會隨著社會變遷而變化,例如清朝時有“一品當朝”,民國時期又有“民國萬歲”“天下太平”等。四是娛人市井劇目,時過境遷,人們不再恪守舊有的儀式,神功戲的劇目和場次也逐漸發生變化,原有的慶賀劇目也會被替換成較為世俗的市井劇目,“酬神”的宗教色彩越來越弱,“媚俗”的娛人成分逐漸增加,如展現寶黛之戀的《情僧偷到瀟湘館》等,娛神的功利色彩已經被置換為娛人的現實目的。
二、澳門神功戲的功能與特征
(一)神功戲的功能
1. 愿望的寄托
澳門百姓的信仰是多神信仰(polytheism)與泛靈信仰(animatism)的復合重疊,無論是儒道釋諸神,還是民間創造的本土神,甚至是西方教派的神,一律都拜。百姓運用戲曲的重要目的是把自己的生活、人生和神圣化的他者聯系在一起,將美好愿望寄托在神靈身上。人們希望通過神功戲來趨利避害、祈福禳災,反映了他們希望過上幸福美滿生活的美好愿望與追求。馬林諾夫斯基(Malinowski)認為人類文化的發生是“出于因功能的增加而引起形式上逐漸分化”,且“一物品之成為文化的一部分,只是在人類活動中用得著它的地方,只是在它能滿足人類的需要”。[12]因此我們可以認為神功戲的產生是為了滿足廣大百姓的信仰需求,在濃墨重彩的神功戲曲中,在異彩紛呈的賀誕儀式中,人們把自己的愿望隨著笙歌一同送至神靈面前。神功戲作為一種媒介,象征性地向神靈祝賀,并且賜福給請戲者和觀眾,讓社會文化的需要和個體的需要都得到滿足。在原始巫術思維的影響下,祈福是人類向神靈禱告以求諸事順遂、福壽延年的一種信仰;禳災則是人類通過一定的儀式解除面臨的災難、厄運的一種信仰活動,祈福禳災本質上表現了人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福”在中國是一個十分豐富的概念,除了長壽、安康、好運,還涉及子嗣、功名、財富等。神功戲祈福禳災的功能,在劇目《八仙賀壽》可見一斑,根據記載,賀壽唱詞如下:
漸漸下山來,黃花滿地開,一聲漁鼓響,驚動眾仙來……(漢鐘離)門外雪山頂寶,(呂洞賓)金盆放滿羊羔,(張果老)天邊一朵瑞云飄,(曹國舅)海外八仙齊到。(鐵拐李)先獻丹砂一粒,(韓湘子)后敬王母蟠桃,(藍采和)彭祖八百壽年高,(何仙姑)永祝長春不老!
美好寓意除了在劇目情節、唱詞等方面表現出來,還尤其體現在演員的服裝道具上,或者說是“神仙”扮演者的“寶物法器”上,如漢鐘離手持芭蕉扇、曹國舅手持云陽板、鐵拐李身系葫蘆、何仙姑手捧蓮花,它們帶有更濃郁的超現實色彩和浪漫氣息,與后世體現為金玉錢幣等現實財富的寶物觀念有所不同。靈芝、丹藥、蟠桃、仙草、美酒等食物飲品,牙笏、葫蘆、如意、拂塵等器物,甚至仙鶴、麋鹿等動物(坐騎),往往具有超常能力,在信眾看來這些都能夠給他們帶來福氣,驅除穢氣。
2. 獻禮的儀式
戲劇起源于儀式。在西方,從阿爾托到格洛托夫斯基、巴爾巴、謝克納,戲劇與儀式的聯系越來越緊密。格雷姆斯(Grimes)指出,當儀式不再是一種直接的體驗,而變成了模仿、虛構和扮演,或當儀式僅僅成為一種傳統習慣時,戲劇便歷史性地出現。戲劇與儀式的關聯,無論國度,無論民族,可以說殊途同歸。早期中國戲曲和儀式相關聯,如先秦的“方相士”“蠟祭”乃至宗廟大典、禮天祭地等,無一不是戲劇與儀式的融合。我們還可以在其他國家或民族的研究資料中得到一些佐證,如古希臘戲劇源于祭祀“酒神”的節慶活動,俄國戲劇源于祭祀“春神”的儀式表演,日本歌舞伎源于行腳巫女表演的“念佛舞”,等等;又如中國少數民族中藏族的“跳羌姆”、蒙古族的“好德格沁”、羌族的“莫恩那莎”和“克西格拉”,等等。中國作為一個禮俗社會,千百年來禮俗互動是重要表現,神功戲作為百姓酬謝神恩、恭賀誕辰而向神靈敬獻的禮物,在一系列民俗活動中形成了一套無形的禮制。例如,在神功戲中,還伴隨著向神像上香、請(戲曲行業的)祖師爺、投擲圣杯、進寶焚化、為神像“妝身”(清潔并重新打扮)、游神等一系列禮制儀式。
3. 禮物的交換
莫斯(Marcel Mauss)認為原始社會的生活方式是以禮物交換為中心的,形成了人與神、人與物、人與人混融一體的禮物社會和禮物文化。交換與契約總是以禮物的形式達成,送禮和回禮都是義務性的,[13]禮物附帶有贈送者的“一部分靈魂”,“禮物之靈”會迫使受禮者回贈禮物來作為回報,由此可見,禮物交換的實質是雙方間社會關系的互動和精神情感的交流。“禮物饋贈和其他互惠交換在(中國社會)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特別是在維持、生產及改造人際關系方面。”[14]儀式表演中的禮物是雙向的,百姓將神功戲作為賀誕的禮物獻給神靈,向神靈敬奉供品即向神靈傳遞信仰,而神靈則賜給人以福氣或滿足人們的愿望,回饋給信眾尚饗后的供品。經過神靈尚饗后的供品成為新的禮物,信眾相信其具有靈力,分享共食是常態,尤其是和自己的家人,這樣使得每個人都具有神的祝福和靈力,而分食供品的行為實際上是分享神賜的禮物。如同基里亞克人分享熊圖騰餐的意義:“我們吃熊肉不是為了果腹,而是為了使熊的力量轉移到我們身上來。”[15]神功戲被百姓作為“禮”獻給神靈,神靈又將“靈力”蘊藏于金豬、瓜果等供品之中,賜福給看戲的百姓。以交換作為核心,圍繞禮物的流動,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禮物流動圈。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不僅提供了“禮物”流動的土壤,也是“信仰”傳播的中心。神功戲,是戲,是儀,是禮,戲臺和祭臺互相轉位,儀式和戲劇合而為一,祭品與禮品相互交換。神功戲的展演目的是敬神、謝神、祈福,是一場向神靈獻禮的儀式,其與宗教酬神祈福相關聯的儀式過程,實際上是“神為我用”的實用觀念體現。信眾抱著明確的功利性目的而來,獲取與神的交換,信眾一旦祈福成功,則需要經常來朝拜,若不持續來朝拜,等同于接受禮物而不回禮。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也是信仰之間的交流,神功戲作為禮物勾連著人與神,是信俗互動和因果機制的產物,也是集體記憶的物化。

圖3 神功戲吸引市民、游人駐足觀賞,人神共樂。

圖4 農歷二月初二,雀仔園福德祠旁搭起戲棚上演精彩的神功戲。
4. 集體的交流
神功戲整合了宗教儀式、娛樂活動、教育意義、社會互動等功能。在中國宗教祭祀活動中,祭品是溝通人與超自然的重要媒介。祭品作為獻給神靈的禮物,是信眾向神靈傳遞信息,表達思想感情和心理意愿的載體,是人與神進行交換并相互認同的途徑和手段。通過祭品這一象征符號作為橋梁,把世俗與神圣世界有機地連接起來,構建一種和睦共處、相互依賴的人神關系,創造出一個“人神交流”的神圣時空,這套象征體系便是列維·布留爾(Lucien Lévy-Bruhl)所謂的“集體表象”。[16]演戲過程中,祭臺與戲臺共同構建了一個特殊的時空,戲臺上的演出和祭壇前的宗教儀式交相滲透,互相轉位,戲劇和祭禮融為一體,難分難辨,每個人都借助儀式媒介對不在場的神靈進行想象,形成一種特殊的人神交流幻象。除了人與神的交流,還有人與人的交流,傳播“靈跡”使在場信眾們拉近自己與神靈的距離,亦可以展示信仰。靈跡既可以是自身或親朋好友的經歷,又可以是遠古時代口口相傳的事跡。通過向周圍人傳播神靈的信仰,由此獲得群體身份認同。羅伯特·貝拉(Robert Bellah)指出,“只有儀式能夠把我們從對個人利益的追求中拽出來,為一個社會世界(的存在)創造可能。”百姓的愿望最終由個人愿望升華為希望家人和睦,希望社區(村莊)平安,希望國家安泰,回歸真善美的普世愿望,而百姓通過參與儀式進行族群身份的確認,獲得歸屬感,建構共同體。觀看神功戲的觀眾多以老者居多,所以現在的賀誕活動增加了敬老孝親的內容,如設敬老宴、敬老折子戲專場、向長者派發禮物等,社區文化交流和綜合服務的性質更加明顯,而神功戲系列活動也成為當下鄉土自治實踐的典型模型。
(二)神功戲的特征
1. 宗教性
澳門曾先后屬南海郡番禺縣、新會郡封樂縣、廣東省香山縣等地,與廣東有著密切關聯。廣東很早就有戲曲活動和宗教信仰相關記載,如《廣州府志》載:“歲為神會作魚龍百戲,共相賭戲,簫鼓管弦之聲達晝夜”,[17]又如《化州志》載:“各神廟、街市俱張燈結彩,士庶嬉游,下戶婦女亦往觀焉。初十后,每夜奉神出游,鑼鼓喧鬧,燈光如晝,放火花,燒爆竹,打秋千,直至月底方休。自光緒七年后,踵事增華,諸神出游,以三夜而畢……張燈演戲,紙醉金迷,國有長春,城真不夜,亦太平之潤色也。”中國民間曲藝表演,不但與民眾的生活息息相關,而且配合著宗教節令,在這些節慶中,從最早的驅邪祈福、報賽田社的祭祀及一般的神祇的信仰、廟神的慶典,乃至于喜慶婚喪的儀式,戲曲技藝表演都是其中最重要的社會與藝術活動。[18]鼓樂歌舞一直是溝通人神兩界的重要手段,神功戲的生存發展離不開宗教信仰提供的土壤,澳門宗祠寺廟林立,宗教文化濃厚,宗教信徒眾多,有助于神功戲在澳門扎根、流傳。目前澳門主要有七間廟宇的神誕有神功戲,從各主保神祇所屬宗教可知,澳門的神功戲以道教為主,合以佛教色彩。由于神功戲主要是做給神靈看,所以戲棚的搭建位置一般要正對著廟宇,以方便其看戲,為神靈提供最佳“觀眾席”也是神功戲與其他類型戲劇戲曲的重要區別。神功戲的觀眾,他們首先的身份是宗教信徒,其次才是戲曲觀眾。在他們眼里,神功戲和敬神用的香燭、紙錢、鞭炮、金豬、花果貢品等“祭祀用品”一樣具有宗教屬性,也一樣具有“答謝神恩、取悅神靈、祈求保佑”的功能。
2. 藝術性
藝術性也可謂“觀賞性”。戲曲廣泛地調動了小說、詩詞、歌曲、器樂、舞蹈、武術、雜耍、繪畫、雕塑等時間藝術和空間藝術的表現力,將其有機融合,呈現出一場視聽盛宴。視覺上,神功戲化妝的顏色以紅、黑、白、藍、黃為主,

圖5 舞臺正在演出神功戲《六國大封相》。

圖6 神功戲演員正在化妝,做登臺前的準備。
代表著勇敢、忠義、奸佞、兇猛、彪悍的個性特點,通過生旦凈丑等角色的動作
身段、臺詞語氣、妝容扮相或夸張或寫實的呈現,即可知道出場的人物是正義之神還是邪惡之妖。聽覺上,“當民眾在戲臺、戲棚較遠處時,也可由敲擊音樂的喧鬧程度知道主角即將出場,或劇情到達高潮,民眾就及時回來看戲”。[19]人類學家弗雷澤(James George Frazer)提出,“相似律”是巫術賴以建立的思想之一,巫師僅僅通過模仿就能實現任何他想做的事情。[20]通過虛擬手法,神功戲演員既可上達天庭,下至龍宮,又可騰云駕霧,呼風喚雨。如劇目《六國大封相》,在有限的舞臺上,用上下場、繞圓場來處理戲劇的時空關系,用一系列的馬鞭表演牽馬、上馬、勒馬、下馬、拴馬的象征動作。在舞臺上,帥旗代表著千軍萬馬,桌椅代表著山脈城池,一轉身便是十萬八千里的迢迢路程,一云旗便是驍騰戰場上的勇士列陣,時間、空間、地理位置、自然現象等等都可以通過想象表現出來,不可思議卻又惟妙惟肖,所以說神功戲具有和其他類型戲劇戲曲一樣的藝術屬性。
3. 民俗性
澳門神功戲的演出已經與賀誕民俗交織在一起,成為民俗活動的重要部分,甚至是重要步驟。過去的生活中,人們日出而作、日落而休,娛樂活動并不多,特別是農村地區。百日之蠟、一日之澤,神功戲作為民俗活動豐富了人們的生活,也體現了百姓樸素簡單的娛樂需求。“任何民俗符號都是由一個或多個民俗表現體和它(們)所表現的具體的民俗對象與抽象的民俗含義或概念結構而成。也可以說是由民俗表現體和它所表現的民俗內涵這兩個方面的關系,成為民俗符號的基本結構”。[21]寺廟、神像、紙錢、香燭、供品、花牌等,以及熱鬧喧囂的鑼鼓、華美端莊的戲服、五顏六色的旌旗,這些都是神功戲的民俗符號,也包含著祥和、喜樂的節慶內涵,已經形成了“祭祀-科儀-民俗-演劇”的文化景觀。[22]老百姓看社戲的民俗古已有之,正如古詩中所記“簫鼓追隨春社近”“太平處處是優場”,就是說村民看到搭建起來的戲臺,聽到喧天的鑼鼓,便知社日將近;太平盛世又適逢社日,處處都在上演社戲。
4. 集體性
集體性可從神功戲所屬的社區以及文化空間(Community & Cultural Space)中得見。在中國,任何社區/村莊都有一個或多個地方保護神作為集體的象征,對這些神靈的崇拜儀式成為社區宗教生活的中心。神功戲是集體參與的活動,在此過程中,有人是組織者,有人是出資者,有人是聯絡者,有人是觀看者。神功戲的“集體性”體現在:首先,神功戲是百姓集體意識的統一,神功戲的觀眾來自各方,也許素未謀面、互不相識,但他們的目的都非常明確——在神誕之日“獻禮”以求自己所需;其次,神功戲是百姓情感的集體宣泄,百姓一方面希望向神靈寄托自己美好的愿望,另一方則希望自己在現實社會中所犯的錯誤能夠得到神靈的寬宥,通過這一儀式,百姓的需求得到滿足,精神得到解放。在一定的聚居范圍內,根據地方保護神的誕辰來舉辦酬神活動,強化集體成員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即使是漂泊他鄉的人也不例外。演出神功戲的廟宇是文化活動場所,是集體的認同象征和社區的核心組織。
5. 地域性
神功戲具有很強的地域性。這里可以聯系另一種和宗教有關的劇種——“儺戲”。儺戲起源于商周時期,也旨在“酬神還愿”,廣泛流行于安徽、江西、河北等省。儺戲流行地區廣泛而分散,神功戲流行地區則相對集中,主要是粵港澳以及廣西部分地區。神功戲發源于廣府地區,主要由本土劇團出演,由于演出所使用的語言為廣府地區的方言——粵語,神功戲很難向粵港澳之外的地區擴散,影響力也逐步減小。也正因如此,才造就了神功戲在廣府地區獨有的號召力和凝聚力,進一步強化了其民俗性。神功戲作為一種特殊的粵劇,具有地域性的特征。
6. 商業性
馬克思將“藝術”和“生產”聯系起來,首次提出“藝術生產”的概念。神功戲既是粵劇表演,又是藝術商品。神功戲劇團的演出可以看作是藝術生產,能夠給劇團帶來收入,而支付酬金給劇團來唱神功戲,可以視作藝術消費,這一點,作為藝術的神功戲與作為商品的“物”相差無幾。各個劇團外出演出,首要目的是追求最高的商業利潤,因此,每個劇團都會打造自己的“招牌戲”來充分發揮神功戲的“商品”屬性。所謂“招牌戲”也就是劇團獨有的拿手好戲,或劇情獨特,或編排精彩,或由名伶出演,用獨特的“看點”來吸引眼球,觀賞性高于其他劇目,以招徠更多觀眾,彰顯賀誕活動的盛況,更好地提供服務,滿足客戶需求。根據記載,以前在上演劇目《跳加官》時,若適逢達官貴人及土豪鄉紳前來看戲,就會臨時增加戲碼,“天官”手中的條幅會是“生意興隆”或“某某人萬歲”來迎合大人物,以此“討封”(紅包打賞),商業色彩明顯。
三、澳門神功戲的保護與啟示
(一)對“人”的保護
對“人”的保護主要側重于對神功戲“從業者”“傳承者”的保護,神功戲離不開薪火相傳。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澳門就有很多專業的大佬倌(演員),因為澳門市場較小,他們后來都到香港尋求發展。而后,改革開放促進了省港澳的文藝交流與繁榮,《華僑報》載:“今春接連有兩個戲班來澳,在永樂戲園登臺賀歲”,[23]形成了“曲來曲往,人來人往”的局面。1945年成立的“黑鷹”文娛體育會和“雀聯”體育會是澳門最早的曲藝社團,“黑鷹”在1989年、1999年土地誕期間受禮聘至雀仔園演出神功戲,期間寒風冷雨,不阻觀眾熱情。[24]而后“黑鷹”特設粵劇組面向民眾展開培訓,《華僑報》載:“隨著曲藝愛好者的要求日增,該會將增設粵劇組,請上粵劇界資深人士盧冰女士為培訓導師……該粵劇組歡迎有興趣者參加。”[25]1992—1995年,澳門粵劇團體由十余個發展至六十余個。[26]澳門粵劇業余社團眾多,直到2004年澳門粵劇曲藝總會成立,才改變了澳門業余社團沒有統一組織的狀況。時至今日,澳門神功戲本土專業劇團仍沒有得到充分發展,主要還是邀請廣東、香港的粵劇團來唱神功戲。澳門每年的神功戲,除了得到坊眾、善信、企業的支持外,還得到了市政署、文化局、旅游局、澳門基金會、霍東英基金會等政府部門和社會機構的支持,這對于神功戲的保護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27]如1989年澳門文化學會(文化局前身)曾舉辦粵劇化妝課程、1990年澳門文化司署曾舉辦粵劇表演形體課程等,要堅持“政府搭臺,百姓唱戲”的實踐方針,提高神功戲的“附加值”。
(二)對“神”的保護
對“神”的保護即對神靈“信仰”的保護和對地方“人情味”的保護。現在的神功戲賀誕,多增加敬老內容,設敬老宴和敬老折子戲專場,當然,如今的戲棚內已少見有售賣小食和各種小玩意的流動小販,戲棚外也不再有賭局。上演神功戲不僅僅是對鬼神天地的敬畏,也是對傳統的敬畏,神功戲體現了民眾崇尚自然、天地合一、社會和睦的生活習慣及態度,蘊含著中華文化的世界觀、倫理價值道德觀和審美意識,多演繹國泰民安、鄰里和睦、父慈子孝、美好生活等正向主題,借此向百姓傳遞價值觀念和教化向善。
(三)對“戲”的保護
對“戲”的保護即是對神功戲“文化”的保護。隨著社會變遷,神功戲不斷發生改變,廟會民俗活動與商業逐利行為之間的矛盾沖突逐漸顯現。現在的神功戲劇目大多經過簡化,如劇目《送子》,根據酬金多少又分《大送子》《小送子》,《大送子》從七仙女上場眺望凡塵開始,到董永高中狀元游街,再到七妹與董永結合,被逼回到天庭,最后將孩子送回董永等一系列劇情;《小送子》則只有兩人上場飾演七妹和董永,重點演繹交還孩子的橋段,情節相較更為簡單,出場人物也少得多。可以看出,神功戲已經逐漸被簡化成儀式化的“軀殼”。神功戲要守正創新,勿受浮躁的社會風氣侵蝕,在傳承發展時要保留原有的藝術表演特色及基本唱腔,在傳承中要去其糟粕,挖掘整理優秀劇目和表演技藝,要積極發展新劇目,汲取現代藝術創意,創新自身的傳承方式與管理模式。
澳門的奇妙之處在于,一個個老舊街區中,在高廈樓宇間,往往靜峙著一所古老的廟宇,氣定神閑地歷經人世變遷,可謂沉默的時代見證者。廟宇代表著所處社區中人們的共同愿望:營營役役的人,希望一本萬利、生意興隆;遭逢疫病災禍的人,希望慘痛消除、雨過天青;要向大海討生活的漁民,祈求風平浪靜、逢兇化吉、滿載而歸……為此,需要形形色色的神祇、法力無邊的大仙。在祭祀祈福的同時,人們理解到相互間的艱苦和危困,由此知道守望相助、福難同當,廟宇由此確切地將社區的人們凝聚、團結起來。人們在祈求神靈的同時,亦知道要適當酬謝神恩,以示飲水思源、不忘其初,于是就有了各種神誕節慶。“還神”,更是對平日辛勤勞作的慰勞,因而舉辦起各種賽會、巡游等活動,甚或請來戲班,在廟前搭棚唱曲演戲,請神靈觀看,娛神娛人。神功戲具有“愿望的寄托”“獻禮的儀式”“禮物的交換”“集體的交流”等功能,上演的劇目或演繹經典傳說,或弘揚傳統美德,或蘊含美好祝愿,集宗教性、藝術性、民俗性、集體性、地域性、商業性于一體。斗轉星移,時過境遷,神功戲作為粵劇獨特的表現形式,我們應該從人、神、戲三方面予以保護,讓神功戲在澳門更好地扎根、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