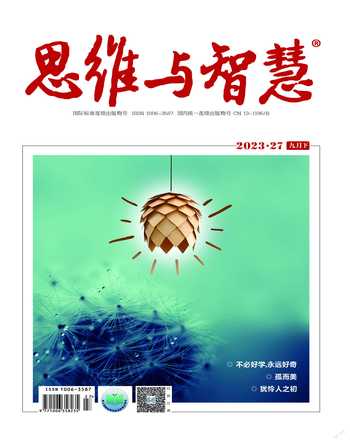閑適的蘇童
遲子建
蘇童與我一南一北,雖然相識(shí)較早,但交往寥寥,只是在一些筆會(huì)上可以見(jiàn)到他“老人家”。所以對(duì)他的印象,只能是浮光掠影。好在蘇童是個(gè)極其隨和的人,所以不會(huì)在意我沒(méi)有“濃墨重彩”地寫他。從他的作品中我感覺(jué)到,他似乎也不大喜歡濃墨重彩。
未識(shí)蘇童前,我讀過(guò)他的《桑園留念》,作品散發(fā)著的優(yōu)雅、傷感的氣息很符合我的審美胃口,對(duì)它分外喜歡,我至今還記得作品的一些細(xì)節(jié),如女主人公多年以后大著肚子從橋上經(jīng)過(guò)的情節(jié)。蘇童的小說(shuō)從一開(kāi)始就成熟于他的年齡,富有滄桑感。蘇童以他的楓楊樹(shù)故鄉(xiāng)作為他文學(xué)創(chuàng)作天空的黝藍(lán)的底調(diào),這決定了他的文學(xué)的豐富和純凈。他的“亮相”引得文學(xué)界的滿堂喝彩,不足為奇。
蘇童曾在《鐘山》做過(guò)編輯,曾經(jīng)編輯過(guò)我的一部中篇《沒(méi)有夏天了》,所以我該稱他為“老師”的。他那時(shí)大約精力充沛,不但寫出了一大批令他大紅大紫的作品,而且在做編輯上也是兢兢業(yè)業(yè)、一絲不茍,這大約也可以看出蘇童為人為文的“誠(chéng)懇”。最早見(jiàn)他是哪一年我已經(jīng)記不得了,蘇童看上去有點(diǎn)“靦腆”,在公眾場(chǎng)合的話語(yǔ)似乎也不多。他的形象,可以用如今比較時(shí)髦的一個(gè)詞來(lái)形容,那就是“酷”。他的“靦腆”,使他相貌上的“酷”得到了最好的收斂,所以蘇童才成為“書生”,而不是演員。
我與蘇童開(kāi)過(guò)幾次筆會(huì),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貪吃”,我與他一樣有“貪吃”的同好,所以我非常不喜歡和他鄰座,兩個(gè)饕餮之徒都虎視眈眈地盯著美味佳肴,它被“消滅”的速度可想而知了。不過(guò),蘇童的吃相很文明,而且他也懂得謙讓,是一個(gè)有品格的“貪吃”的人。我知道他“貪吃”,有一次我就給他講我如何在副食商店買了大骨棒,把它們放到大的鋼精鍋里用文火煮它幾個(gè)小時(shí),你在這邊可以從容地寫作,等到了飯時(shí),骨頭湯只剩奶白色的小半鍋,你可以加上各種調(diào)料,洗一把碧綠的菠菜放上去,美美地吃上一頓。這菜做起來(lái)不需大操大辦,省時(shí),既解了“饞”,又補(bǔ)充了營(yíng)養(yǎng)。蘇童聽(tīng)完我的敘述,果然饞得聲稱“要流口水了”。
筆會(huì)上的蘇童非常喜歡打牌。他與兆言和格非湊在一起,會(huì)打得昏天黑地的,全不把優(yōu)美的風(fēng)景放在眼里,也不想著該出去享受一下大自然的雨露陽(yáng)光。所以我曾戲謔他們要在青山綠水間把自己給打傻了。蘇童還特別的“懶惰”,那一年我們?nèi)S山,我們?cè)缫呀?jīng)到頂峰,兩小時(shí)后,蘇童才姍姍登臨,一臉的痛苦狀,抱怨這山太高。我說(shuō)他這做派很像一個(gè)地主,大約要有幾個(gè)長(zhǎng)工抬著滑竿,再有幾個(gè)丫鬟拿著搖扇為其驅(qū)熱,他才來(lái)得愜意。當(dāng)然,這些都是玩笑話了。
也許是同齡人的緣故,我很關(guān)注蘇童的創(chuàng)作,他的作品既是寫實(shí)的,又是浪漫的。他的新作,我只要能見(jiàn)得到的,一定要讀的。我喜歡他的小說(shuō)。比如發(fā)在《收獲》上的《兩個(gè)廚子》,《天涯》上的《一九七三年深冬的一個(gè)夜晚》,這些作品都是蘇童的近作,我覺(jué)得它們非常扎實(shí),洋溢著濃濃的生活氣息,可感可觸。所以,在報(bào)紙上看到有關(guān)蘇童作品的評(píng)論,說(shuō)他的近作不如從前,我覺(jué)得這是不客觀的。要知道,蘇童走紅的那些年,很多人也未必認(rèn)真讀了他的作品,而是跟著媒體人云亦云。而現(xiàn)在認(rèn)真讀一個(gè)作家的作品才敢來(lái)“發(fā)言”的批評(píng)家也越來(lái)越少了。文壇已經(jīng)相當(dāng)浮躁了。當(dāng)然,一個(gè)作家一直保持著創(chuàng)作上旺盛的激情是不現(xiàn)實(shí)的,誰(shuí)都有創(chuàng)作的高潮和低谷。我們用不著懷疑一個(gè)優(yōu)秀的作家,用不著為著一個(gè)作家極個(gè)別作品的“平淡”而大驚小怪。
蘇童和兆言同在南京,他們的身上,都有一種非常可貴的文學(xué)品質(zhì),那就是閑適。無(wú)論是他們的為人還是為文,都可以讓人體會(huì)到那種寵辱不驚、揮灑自如的氣度,這決定了他們的寫作一直悠徐從容、不急不躁。看來(lái)是江南靈秀的山水和深厚的文化底蘊(yùn)滋養(yǎng)了他們。
還有兩件小事值得一提。有一年,我因自己的一本書被出版社惡意篡改而與之對(duì)簿公堂,法庭需要一些作家提供的關(guān)于這類事對(duì)一個(gè)作家“名譽(yù)權(quán)”的影響,我給蘇童寫了一封“求助信”,他很快寫來(lái)了與之相關(guān)的文字,并說(shuō)他的作品也曾有過(guò)類似遭遇,提醒我打官司要“酌時(shí)酌情酌力而定”,使我一直心存感激。還有一次,我們?cè)诤D蠉u參加《天涯》的筆會(huì),有一天傍晚一行人在海邊散步,李陀先生忽然指著前方的蘇童說(shuō):“你們看他,像不像一只虎頭鞋?”李陀是東北人,他把蘇童與憨頭憨腦的虎頭鞋聯(lián)系在一起,的確十分傳神和精妙。我們大笑起來(lái)。蘇童大約聽(tīng)到了這話,他回過(guò)頭怪聲怪氣地問(wèn):“你們笑啥哩?”
(蘇格拉沒(méi)有底摘自微信公眾號(hào)“清溪舟上人” 圖/槿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