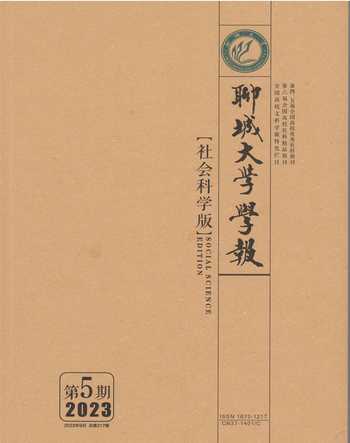論張煒的自我形構(gòu)與文學(xué)敘述
摘 要:張煒是中國當(dāng)代文壇不可或缺的一位作家。張煒因其文學(xué)創(chuàng)作在文學(xué)史與文學(xué)思潮中位置的“含混性”,而成為學(xué)者不斷闡釋與言說的對(duì)象。只有回到文本,將張煒放到時(shí)代與文學(xué)交織的大網(wǎng)之中,在各時(shí)代的共時(shí)場(chǎng)域與張煒自身創(chuàng)作脈絡(luò)的歷時(shí)場(chǎng)域之中考察,才能全面揭示他創(chuàng)作背后的學(xué)理性邏輯。張煒經(jīng)由早期“流浪”形成的知識(shí)分子主體品格貫穿其創(chuàng)作始終,并使其處于與時(shí)代的“共名”與“張力”之中。無論是早期對(duì)于人性的書寫,還是80年代與啟蒙的合奏,或90年代被動(dòng)加入“道德理想主義”隊(duì)伍,抑或新世紀(jì)后對(duì)于底層的關(guān)注,張煒始終堅(jiān)守著知識(shí)分子的道德良知,在魯迅思想的延長線上注視現(xiàn)代人性與人類的精神,探索實(shí)現(xiàn)國家與民族現(xiàn)代化的方法。考察作為知識(shí)分子的張煒的心路歷程,可以為反思知識(shí)分子與時(shí)代的關(guān)系提供一份個(gè)例。在當(dāng)下文學(xué)創(chuàng)作深受資本與市場(chǎng)影響的背景下,這種反思尤具現(xiàn)實(shí)價(jià)值與意義。
關(guān)鍵詞:張煒;自我形構(gòu);文學(xué)敘述;知識(shí)分子;時(shí)代
中圖分類號(hào):I206.7? ? ? ? ? ? ? ?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 ? ? ? ? ? ? ?文章編號(hào):1672-1217(2023)05-0122-09收稿日期:2023-07-20
作者簡(jiǎn)介:李雪(1997-),女,河北邯鄲人,蘇州大學(xué)文學(xué)院博士研究生。
張煒是當(dāng)代文學(xué)中極具創(chuàng)造力的作家之一,以其創(chuàng)作之豐、體量之大、時(shí)間之長而蜚聲文壇。綜觀張煒五十多年的創(chuàng)作生涯,可將其大致歸為四個(gè)發(fā)展階段。從1973年《木頭車》,到《聲音》《一潭清水》等作品的發(fā)表,可視為張煒的早期創(chuàng)作階段。這一時(shí)期張煒以書寫人性見長,筆下多為蘆青河畔的田園風(fēng)味與浪漫情感,有孫犁抒情小說的痕跡。從80年代中期發(fā)表《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憤怒》到《古船》,可視為張煒創(chuàng)作的第二階段。張煒一改早期對(duì)人性善的贊揚(yáng),轉(zhuǎn)而向歷史與現(xiàn)實(shí)的深處挖掘,揭示現(xiàn)實(shí)的惡與歷史的輪回,作品的復(fù)雜性開始凸顯。90年代張煒發(fā)表《九月寓言》《柏慧》《家族》等小說,標(biāo)志著他的創(chuàng)作進(jìn)入第三階段。這一時(shí)期張煒放棄對(duì)惡的直面批判,投身“野地”與自然。新世紀(jì)后,張煒以長河小說《你在高原》的發(fā)表為標(biāo)志,進(jìn)入創(chuàng)作的第四階段。這一階段包括之后《半島哈里哈氣》《尋找魚王》等兒童文學(xué)創(chuàng)作。張煒以更加沉潛的姿態(tài)注視現(xiàn)代語境下的種種亂象。考察作為知識(shí)分子的張煒在不同階段的文學(xué)表現(xiàn)及其文學(xué)創(chuàng)作與時(shí)代的關(guān)系,對(duì)于全面揭示張煒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蘊(yùn)含具有重要意義。同時(shí)也為我們考察知識(shí)分子與時(shí)代的關(guān)系打開了一扇窗戶。
一、早期“流浪”與知識(shí)分子的主體生成
張煒早期小說以書寫人性見長,《聲音》(1982年)、《一潭清水》(《人民文學(xué)》1984年7月號(hào))等小說敘寫古樸、寧靜的田園景象與清新的人性。這些創(chuàng)作與他童年近乎流浪的生活經(jīng)歷緊密相連。在張煒看來,流浪是個(gè)體生命存在的一種獨(dú)特體驗(yàn),“生命的全部奧秘就囊括在這種奇妙的流浪之中”①。因此,張煒將“流浪”視為其文學(xué)的八個(gè)關(guān)鍵詞之一。這種流浪固然指代肉體的位移,但更為重要的則是精神隱喻方面的“流浪”。聯(lián)系張煒父親的被審查,他被迫游走于海邊林野、在學(xué)校被議論與被侮辱的經(jīng)歷,可知他長期處于被時(shí)代放逐的環(huán)境之中,與恐懼、歧視、孤獨(dú)為伴。①恰恰是這種孤獨(dú)的生存體驗(yàn)塑造了張煒獨(dú)立思考的品格,一種真正的知識(shí)分子主體意識(shí)的生成。陳曉明就注意到張煒小說始終有一個(gè)第一人稱“我”,并指出“他的那個(gè)貌似抒情的‘我,其實(shí)是一個(gè)不斷自省的‘我”。②這是深層“流浪”帶來的主體意識(shí)與反省意識(shí),是在自我經(jīng)驗(yàn)的意義上展開的寫作。當(dāng)然,這種“自我經(jīng)驗(yàn)”只能是相對(duì)意義上的,作家不可能真正離開自己所屬的時(shí)代創(chuàng)作。張煒正是一位在某種程度上不受時(shí)代“規(guī)訓(xùn)”但又與時(shí)代密切相關(guān)的作家,他童年的生活體驗(yàn)與生存經(jīng)驗(yàn)成為日后創(chuàng)作的精神源泉。
孤獨(dú)的“流浪”生活滋養(yǎng)了張煒對(duì)自然大地的愛與對(duì)惡的批判。張煒自小見識(shí)了太多“惡的力量”,故地的莽林、建筑、人文遺跡、動(dòng)物等的消失,引發(fā)了他的思考。這不僅是自然環(huán)境的變遷,更是時(shí)代變化與人性復(fù)雜的映像。在他早期的創(chuàng)作中,《山楂林》寫煤礦開采對(duì)自然大地造成的不可挽回的傷害,阿對(duì)和爺爺不能阻擋現(xiàn)代洪流的浩蕩向前。在稍后《柏慧》《外省書》《九月寓言》等小說中,張煒皆表達(dá)了對(duì)于現(xiàn)代化發(fā)展的反思,對(duì)于自然被破壞的痛惜。評(píng)論家將張煒的這類創(chuàng)作稱為自然文學(xué),對(duì)此張煒曾自道:“文學(xué)在我這里就是文學(xué),它們不會(huì)從題材上區(qū)分得這么清楚。作家關(guān)心的主要是人性,是生命中激越的詩意。是社會(huì)的不公平,苦難和愛情。”③因此,張煒自覺地站在弱小者、被迫害者一方,呼喚人性善。
面對(duì)物欲縱流與環(huán)境污染,張煒書寫與歌頌人性美。短篇小說《達(dá)達(dá)媳婦》敘寫純真勤勞的達(dá)達(dá)媳婦對(duì)婆婆的愛。《看野棗》講述大貞子自愿到大海灘上看野棗,不計(jì)前嫌幫助三來。《聲音》敘寫二蘭子與小羅鍋兒之間朦朧的愛情,二蘭子并未因割牛草而放棄對(duì)生活的向往。從創(chuàng)作風(fēng)格上看,張煒早期創(chuàng)作中彌漫著浪漫抒情的筆調(diào),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孫犁《鐵木前傳》抒情小說的血脈因子,以及俄國作家屠格涅夫《獵人筆記》散文化小說風(fēng)格的影響。與同時(shí)期以人倫關(guān)系破裂來表現(xiàn)人民苦難與歷史浩劫的“傷痕文學(xué)”思潮相比,張煒筆下的達(dá)達(dá)媳婦、大貞子、二蘭子等純善人物形象呈現(xiàn)出時(shí)代主題下的另一美學(xué)現(xiàn)象:即不同于反面的對(duì)“假丑惡”的直接控訴,從正面表現(xiàn)人與人性“真善美”的一面。但是,張煒在創(chuàng)作中并沒有過于以理想化的姿態(tài)來想象人性,他也注意到對(duì)災(zāi)難制造者的刻畫。三來(《看野棗》)、盧大麻子(《絲瓜架下》)、“民兵連長”(《操心的父親》)等人物是他小說中惡勢(shì)力的代表,張煒看到他們以“正當(dāng)性”面目行惡的荒誕性,并嚴(yán)厲批判之。這些“偽善”的人物其后又以趙炳、趙多多(《古船》)之類的“惡人”形象出現(xiàn)在張煒的創(chuàng)作之中,但日后他對(duì)于歷史的反思與復(fù)雜人性的洞察卻更為深刻。
張煒踐行著自己的文學(xué)立場(chǎng),不跟風(fēng)。他曾自言:“沒有什么‘歷史的潮流是經(jīng)得住推敲的……我們總是格外尊重和注意那些逆潮流而動(dòng)的人,希望聽到他們未被喧囂淹沒的聲音。”④張煒本身就是一個(gè)與時(shí)代潮流保持一定距離的人。從1974年《槐花餅》始,其后《花生》《夜歌》《下雨下雪》《蘆青河告訴我》等小說中頻繁出現(xiàn)“蘆青河”意象,被評(píng)論家合稱為“蘆青河”系列小說。短篇小說集《蘆青河告訴我》(1983年)是他1980-1982年間創(chuàng)作的。聯(lián)系時(shí)代文學(xué)思潮可知,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傷痕文學(xué)”與“反思文學(xué)”以鮮明的問題意識(shí)——揭示封建蒙昧主義給普通中國人生活和心靈帶來的巨大傷痛——在文壇上產(chǎn)生巨大“轟動(dòng)”的時(shí)期。此時(shí)張煒正承續(xù)孫犁與屠格涅夫的浪漫抒情風(fēng)格,在童年的“蘆青河”上呼喚人性與清澈的田園牧歌。其后,文學(xué)仍延續(xù)著對(duì)社會(huì)問題的關(guān)注。蔣子龍以《喬廠長上任記》掀開“改革文學(xué)”的大幕,張煒的短篇小說《一潭清水》雖然也寫到了農(nóng)村“改革”,但是與文壇上流行的“改革文學(xué)”卻是不相及的。“改革文學(xué)”以其“在場(chǎng)性”的特點(diǎn)揭示改革過程的艱難,進(jìn)而為實(shí)現(xiàn)國家的現(xiàn)代化發(fā)展鼓與呼。如《喬廠長上任記》塑造“開拓進(jìn)取”的“新人”形象,帶領(lǐng)工人為社會(huì)主義事業(yè)奉獻(xiàn)力量。而張煒主要將“改革”作為小說的歷史背景,質(zhì)在探索人的精神在時(shí)代變遷中的“起伏”。隨著現(xiàn)代化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張煒在《秋天的思索》(1984年)、《秋天的憤怒》(1985年)中表露了更多的憂思。也是從這時(shí)起,張煒的創(chuàng)作風(fēng)格開始不同于早期贊揚(yáng)古樸自然的“蘆青河”,轉(zhuǎn)而批判世間的“惡”。
這一時(shí)期的張煒在文壇上多少顯得有點(diǎn)特立獨(dú)行。宋遂良最先注意到張煒早期創(chuàng)作的與眾不同之處:“他(指張煒)不像這個(gè)時(shí)期涌現(xiàn)的大多數(shù)青年作者那樣以寫‘問題小說嶄露頭角,他不追求重大的題材,也沒有迎合時(shí)下流行的一些藝術(shù)習(xí)尚,他鋪開一張白紙,獨(dú)自魅心魅意地去寫他熟悉的動(dòng)過感情的生活。他歌唱美的自然,美的心靈,讓我們感受到生活的芬芳,人間的純樸。”①正是童年“流浪”的生活體驗(yàn)促使張煒從時(shí)代潮流中“掙脫出來”。或許有一天張煒身體的流浪會(huì)終結(jié),但只要他還堅(jiān)守著知識(shí)分子的獨(dú)立品格,他的精神流浪就將永遠(yuǎn)“在路上”。這是他自我主體建構(gòu)的內(nèi)在需要,也是他注視“現(xiàn)代”丑惡現(xiàn)象的一種策略。雖然相比于張煒稍后的寫作,他的早期創(chuàng)作略顯單薄,但預(yù)示了一個(gè)人文知識(shí)分子的創(chuàng)作“底線”,這將伴隨張煒創(chuàng)作始終。在“蘆青河”之后,張煒向歷史的深處開拓,以長篇小說《古船》在文壇上聲名鵲起。
二、啟蒙語境下的歷史批判與現(xiàn)代反思
從中篇小說《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憤怒》起,張煒創(chuàng)作進(jìn)入第二階段。《古船》是這一時(shí)期的代表作,也是張煒的成名之作。《古船》醞釀?dòng)?980年下半年,起稿于1984年6月,定稿于1986年7月,同年10月在《當(dāng)代》第5期發(fā)表。評(píng)論界不再把《古船》看作是“蘆青河系列”。“《古船》是張煒創(chuàng)作的一個(gè)里程碑,它標(biāo)志著張煒的創(chuàng)作已經(jīng)跨入了一個(gè)新的階段”,即從早期對(duì)自然環(huán)境的贊美到對(duì)社會(huì)歷史、人性的深刻挖掘。②但是對(duì)于張煒來說,這是否意味著他的創(chuàng)作完全轉(zhuǎn)向了呢?如果《古船》是張煒“基因突變”之作,那么是怎樣的契機(jī)促使他的轉(zhuǎn)向?如果他沒有完全轉(zhuǎn)向,那支撐張煒前后創(chuàng)作的內(nèi)核又是什么?這促使他的創(chuàng)作與同時(shí)代思潮之間又處在怎樣的張力之中?
《古船》開創(chuàng)了文學(xué)史上新的歷史敘事模式。1949年以后的“革命歷史敘事”中,類史詩敘事與類傳奇敘事具有宏大敘事與史詩氣派相結(jié)合的“革命美學(xué)”特征,突出典型人物的塑造,強(qiáng)調(diào)對(duì)于社會(huì)的簡(jiǎn)單描摹。《古船》率先突破五六十年代所確立的這種宏大革命歷史敘事,代之以家族歷史敘事模式。小說以洼貍鎮(zhèn)上隋、趙、李三家的家族沖突來結(jié)構(gòu)文本與反映歷史,敘述時(shí)間橫跨20世紀(jì)40年代到80年代——中國社會(huì)大變革如火如荼展開的時(shí)期。在《古船》之前,歷史即是主流政治意識(shí)的體現(xiàn),個(gè)人經(jīng)驗(yàn)的歷史書寫模式至90年代方才取得合法性。《古船》開創(chuàng)了以作家個(gè)人經(jīng)驗(yàn)來書寫歷史的模式,這種模式影響了其后劉震云《故鄉(xiāng)天下黃花》(1991)、陳忠實(shí)《白鹿原》(1992)、李銳《舊址》(1993)、高建群《最后一個(gè)匈奴》(1993)等一大批小說的創(chuàng)作,在當(dāng)代文壇產(chǎn)生了強(qiáng)大的輻射力。
對(duì)于20世紀(jì)80年代流行的寫作思潮,張煒并沒有盲目跟隨,而是向歷史與現(xiàn)實(shí)深處開掘,理性地審視歷史。《古船》是張煒對(duì)中國歷史與現(xiàn)實(shí)長期思考的結(jié)果。四年的檔案管理生涯也讓他看到了迥異于“主流”的歷史。隋抱樸站在歷史理性的高度上思考四十年災(zāi)難是怎樣造成的,他的懺悔意識(shí)與原罪意識(shí)也是對(duì)于中國民族與歷史的反思。《古船》揭示封建社會(huì)的“超穩(wěn)定結(jié)構(gòu)”給農(nóng)民帶來的苦難事實(shí)。《古船》中的趙炳和趙多多原是特殊年代里災(zāi)難的制造者,然而在改革開放后又掌握了鄉(xiāng)村政權(quán),他們的地位類似于傳統(tǒng)的“鄉(xiāng)紳階層”,處于鄉(xiāng)村社會(huì)權(quán)力秩序的核心位置,但卻幾近抽空了“鄉(xiāng)紳”作為鄉(xiāng)民保護(hù)者的內(nèi)涵,轉(zhuǎn)而成為苦難的制造者。小說中的四爺爺趙炳尤其體現(xiàn)了傳統(tǒng)宗法制與極左思想的結(jié)合,李家與老隋家的災(zāi)難都與他脫不了干系。趙炳在“土改”時(shí)期對(duì)李其生的利用與戕害,以“干閨女”之名對(duì)含章長達(dá)二十多年的控制與脅迫,皆證明他的虛偽本性。趙多多在“土改”時(shí)期作為民兵頭兒制造了很多苦難,改革后,又精于算計(jì)將粉絲大廠據(jù)為己有,以“企業(yè)家”的身份剝削外族工人。在趙炳等人身上儼然存在著封建壓迫力量的影子。然而,社會(huì)主義制度的建立在政治上結(jié)束了幾千年的封建統(tǒng)治,為什么在“文革”時(shí)期封建專制又會(huì)借革命之名還魂呢?張煒揭示出歷史表層之下巨大的荒謬性,傳統(tǒng)小生產(chǎn)方式浸潤下的封建意識(shí),又夢(mèng)魘般地糾纏在國民性格之中,成為中華民族跨入現(xiàn)代社會(huì)的嚴(yán)重阻遏。
《古船》對(duì)中國革命歷史進(jìn)行了反思。在《古船》之前,文學(xué)對(duì)于“土改”的敘述主要突出其正確性與必要性,缺乏理性的反思。建國前描寫“土改”的小說揭示地主與農(nóng)民之間的階級(jí)斗爭(zhēng)與農(nóng)民的矛盾心理。建國后,反映農(nóng)村社會(huì)主義改造的小說聚焦在先進(jìn)與落后、個(gè)人與集體的矛盾沖突上,講述在黨影響下的社會(huì)主義“新人”帶領(lǐng)農(nóng)民走上“金光大道”的故事。新時(shí)期之初中國文學(xué)有著明確的意識(shí)形態(tài)指向,即反思前一時(shí)期“一體化”格局帶來的弊端。對(duì)于“四人幫”的控訴也好,人道主義的提倡也罷,作家總是在時(shí)代要求的契領(lǐng)下進(jìn)行創(chuàng)作。因此,《古船》之前,從歷史理性層面上反思“土改”中存在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文學(xué)表現(xiàn)。《古船》發(fā)表后,批評(píng)家延續(xù)著“高大全”與“模式化”的極端社會(huì)歷史批評(píng)方法,以“階級(jí)斗爭(zhēng)”和“頂天立地的人物”為標(biāo)準(zhǔn)苛責(zé)《古船》。①忽視了《古船》所表現(xiàn)出的異于前一階段的歷史反思性。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古船》的“異質(zhì)性”將會(huì)凸顯出來。
從表面上看,張煒此時(shí)的寫作風(fēng)格與早期清新的人性書寫有天壤之別。但是,如果我們深入張煒寫作的“內(nèi)面”就會(huì)發(fā)現(xiàn),《古船》并非張煒的基因突變之作,依然延續(xù)了他對(duì)人性的書寫與對(duì)實(shí)現(xiàn)國家與民族現(xiàn)代化的探索。《古船》中隋抱樸在痛苦中的自省,對(duì)于人的尊嚴(yán)與自由的呼號(hào),對(duì)于黑暗與丑惡的抨擊,堪稱為一部“中國農(nóng)民心靈痛苦糾纏和自我搏斗的史詩”②。隋抱樸由此成為一個(gè)因別人的不幸而變得多有思慮和憂郁的“哈姆雷特”,同時(shí)他又兼具了以拯救人民群眾為重任的“堂吉訶德”式的責(zé)任感。因此,他承載著“精神的重負(fù)”日復(fù)一日地在老磨屋中思考,在對(duì)《共產(chǎn)黨宣言》和《天問》的反復(fù)閱讀與追問中尋求對(duì)真理的信仰,最終“出山”挽救粉絲大廠與洼貍鎮(zhèn)的“命運(yùn)”。20世紀(jì)80年代對(duì)于中國社會(huì)現(xiàn)代化進(jìn)行美好想象的歷史樂觀精神,在今天看來多少有點(diǎn)過于理想化。張煒并沒有跟隨大流盲目自信,《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憤怒》的開放式結(jié)局,《古船》中四爺爺?shù)膫凰溃刭|(zhì)勘探隊(duì)鉆井造成的“大地震動(dòng)”,“星球大戰(zhàn)”中丟失的鉛桶埋下的憂慮種子,李知常設(shè)計(jì)的“變速輪”機(jī)器剛啟用就染上人血等等,這些人物和情節(jié)預(yù)示了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改革的艱難與歷史的輪回。作為知識(shí)分子的張煒并沒有盲目追隨80年代“主流”參與對(duì)現(xiàn)代化的理想高歌,而是堅(jiān)守知識(shí)分子主體精神進(jìn)行批判與反思。
張煒對(duì)于人性的探索可以說處在魯迅思想的延長線上,接續(xù)魯迅的國民性批判與思想啟蒙。《古船》“對(duì)國民性的刻畫乃‘魯迅之后鮮見者”③。但是,張煒《古船》的批判國民性是基于改革開放的時(shí)代語境。如果說魯迅始終站在被欺侮、弱小的一方,啟蒙主義的先在論使得他的敘事策略集中在對(duì)惡的揭露與鞭撻上,時(shí)代語境使其堅(jiān)持著一種悲觀的絕望哲學(xué),帶有尖銳的批判性。那么,張煒除了對(duì)惡的鞭笞外,也贊揚(yáng)善。對(duì)于“丑、惡”的揭示正如對(duì)于“美、善”的贊揚(yáng)一樣,是他“道德理想主義”的一體兩面。④因此,在塑造了老得(《秋天的思索》)、李芒(《秋天的憤怒》)兩個(gè)思想者后,在《古船》中他又塑造了隋抱樸這一具有救世情懷和原罪意識(shí)的思想者。這種有道德人格的知識(shí)分子形象在其后《柏慧》(寧伽)、《外省書》(史珂)、《懷念與追憶》(老寧)等創(chuàng)作中也頻頻出現(xiàn)。張煒筆下的一系列知識(shí)分子,有著自己的道德立場(chǎng)和原則,獨(dú)戰(zhàn)著失范的科技理性與物質(zhì)欲望。他們是與張煒情感相通的同路人,是張煒的文學(xué)自況。
從整體上看,張煒這一時(shí)期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處在與時(shí)代“主流”的“共名”與“張力”之中。《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憤怒》《古船》與80年代的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具有明顯的同構(gòu)性,表現(xiàn)為對(duì)五四啟蒙資源與話語的征用。《古船》深入到對(duì)歷史和現(xiàn)實(shí)的挖掘之中,指向?qū)Ψ饨▽V扑枷肱c極“左”思想的批判。同時(shí),《古船》可以說是“傷痕文學(xué)、反思文學(xué)、迄今為止的改革題材文學(xué)的一個(gè)合乎邏輯的發(fā)展,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它們的集大成者。”①《古船》對(duì)文化的反思與批判,可以在“傷痕文學(xué)”“反思文學(xué)”中找到某些影子。《班主任》《傷痕》已表現(xiàn)出文化批判與文化啟蒙的色彩,蘊(yùn)含80年代文學(xué)“向內(nèi)轉(zhuǎn)”的力量。在其后反思文學(xué)中得到進(jìn)一步強(qiáng)化,《桑樹坪紀(jì)事》《黑駿馬》《琥珀色的篝火》等小說發(fā)掘人物言行背后的文化支配力量。然而《古船》又表現(xiàn)出與傳統(tǒng)現(xiàn)實(shí)主義不一樣的質(zhì)素。“傷痕文學(xué)”與“反思文學(xué)”在敘述模式與話語表達(dá)上仍保留著“十七年”的某些特色。《古船》則吸收魔幻現(xiàn)實(shí)主義的表現(xiàn)手法,以時(shí)空的跳躍與怪誕寓言的傳說結(jié)構(gòu)文本,這明顯與80年代先鋒文學(xué)又有共通之處。80年代的張煒及其文學(xué)創(chuàng)作可放置于多個(gè)文學(xué)脈絡(luò)與思潮之中,但是又沒有哪一個(gè)思潮能夠完整地體現(xiàn)出他的創(chuàng)作意圖,這本身就說明了張煒此時(shí)創(chuàng)作的復(fù)雜性。而他在文學(xué)史上的不可通約性恰恰是其知識(shí)分子主體精神的體現(xiàn)。在90年代,張煒堅(jiān)守著知識(shí)分子的道德精神,向時(shí)代深處進(jìn)一步開掘。
三、退卻中的堅(jiān)守與“精神原野”的深處
《古船》之后,張煒又創(chuàng)作了短篇小說集《美妙雨夜》《九月寓言》(1992)、《柏慧》(1994)、《家族》(1995)等。其中《九月寓言》是張煒這一階段的代表作。《九月寓言》醞釀?dòng)?0世紀(jì)80年代前期,起稿于1987年11月,完稿于1992年1月,同年5月發(fā)表于《收獲》。它的誕生與張煒重回故地龍口有密切關(guān)系。在“知識(shí)分子被其所創(chuàng)造的歷史放逐”了的90年代,作為知識(shí)分子的張煒并沒有選擇一股腦地?fù)肀虡I(yè)市場(chǎng),而是對(duì)中國的現(xiàn)代化發(fā)展進(jìn)行反思性批判,包括生態(tài)惡化、人性異化、物欲橫流等方面。《九月寓言》不僅書寫了工業(yè)發(fā)展對(duì)小村生態(tài)樣貌帶來的表面影響,而且揭示了現(xiàn)代工業(yè)文明對(duì)于人心產(chǎn)生的誘惑與異化。張煒延續(xù)著前期對(duì)于人性的探索與苦難的敘述,只是小說中人類得以救贖的方式發(fā)生了轉(zhuǎn)變。《古船》中隋抱樸的原罪意識(shí)需依靠?jī)?nèi)省自我拯救,到《九月寓言》,則“只有與其他生命和諧相處并于自然中汲取神秘力量才能使自身得到修正和升華,人類精神才能得到超越。”②從《古船》到《九月寓言》,張煒找到了人性救贖的基本點(diǎn):從內(nèi)省到自然大地。相比于前一階段對(duì)于惡的直面批判,張煒的創(chuàng)作確乎發(fā)生了轉(zhuǎn)變。這一時(shí)期激進(jìn)憤怒似乎退卻,他更加傾向于擁抱大地、自然。但是,我們是否就可以據(jù)此認(rèn)為張煒放棄了曾經(jīng)的知識(shí)分子立場(chǎng),開始退卻了呢?或如批評(píng)家所說他是反現(xiàn)代的、保守的?
90年代隨著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裹挾著物質(zhì)主義與消費(fèi)主義全面撲來,知識(shí)分子階層化與邊緣化。以1993年賈平凹《廢都》發(fā)表為標(biāo)志,商業(yè)時(shí)代對(duì)于知識(shí)分子的侵蝕全面展開。《廢都》中莊之蝶的精神狀況更像是知識(shí)分子在90年代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中的一個(gè)鏡像。張煒面對(duì)現(xiàn)代社會(huì)的倫理失范與知識(shí)分子的精神危機(jī),召喚德性的重建。在張煒看來:“德性將不僅維持使我們獲得實(shí)踐的內(nèi)在利益,而且也將使我們能夠克服我們所遭遇的傷害、危險(xiǎn)、誘惑和渙散,從而在對(duì)相關(guān)類型的善的追求上支撐我們,并且還將把不斷增長的自我認(rèn)識(shí)和對(duì)善的認(rèn)識(shí)充實(shí)我們”。③張煒認(rèn)為人類最終的“救贖”是通過培養(yǎng)人類的“德性”來達(dá)到的,而他所說的“德性”更多存在于本真純樸的自然世界、未受現(xiàn)代污染的鄉(xiāng)野大地上。因此,張煒甘作“大地守夜人”④,在小說中構(gòu)筑一個(gè)理想回歸之地——“野地”,其小說中主人公紛紛奔向自由的野地。從早期的“蘆青河”系列到《古船》,張煒書寫了一系列野地意象,《九月寓言》則描寫了更多奔向野地、融入野地的孩子。這些人物形象共同見證了張煒對(duì)于詩化意境的營造,對(duì)于現(xiàn)代精神家園的追尋。正是在這個(gè)意義上,有學(xué)者認(rèn)為《九月寓言》比《古船》更真實(shí),寫出了人與大地的本源關(guān)系,更符合作家的本真?zhèn)€性。①張煒在野地與大自然中找到了最終的生存根基與精神生活的源頭。
《九月寓言》發(fā)表時(shí)曾引起巨大的爭(zhēng)議,秦兆陽從“真實(shí)性”層面上否定《九月寓言》,認(rèn)為小說“失去了合理虛構(gòu)的現(xiàn)實(shí)基礎(chǔ)”,表現(xiàn)的是“抽象人性”。②而批評(píng)界對(duì)《九月寓言》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反現(xiàn)代性的層面上。批評(píng)家延續(xù)了80年代的現(xiàn)代啟蒙精神,以現(xiàn)代發(fā)展觀看待張煒的小說創(chuàng)作,認(rèn)為他的作品是反現(xiàn)代性的、堅(jiān)守農(nóng)業(yè)文化保守主義立場(chǎng)的。賀仲明認(rèn)為張煒“站立的是絕望、向后的農(nóng)業(yè)文化立場(chǎng)”,他“成為了90年代文化對(duì)80年代精神進(jìn)行戕害的幫兇”。③鄧曉芒認(rèn)為《九月寓言》是復(fù)古、懷舊的反人道主義思想傾向。④黃軼認(rèn)為鄉(xiāng)村也藏有令人絕望的特質(zhì),應(yīng)該辯證地看待。對(duì)現(xiàn)代的反思,不是說要回到“前現(xiàn)代”,而是要批判的繼承。⑤換句話說,黃軼承認(rèn)張煒對(duì)于現(xiàn)代的反思精神,但是“鄉(xiāng)野”本身能否成為或孕生出抵抗的力量卻需要進(jìn)一步思考。
基于以上的梳理,我們有必要追問張煒筆下的“野地”究竟是指什么?這與張煒“道德理想主義”的文化立場(chǎng)息息相關(guān),是我們理解張煒90年代創(chuàng)作及其文化追求的符碼。張煒深受齊魯文化“萬物有靈”思想與方仙道文化的影響,認(rèn)為人與其他物種都是地球上的一員,自然的和諧會(huì)促進(jìn)人與萬物的和諧相處。在《融入野地》中他曾寫到:“我遠(yuǎn)投野地的時(shí)間選在了九月,一個(gè)五谷豐登的季節(jié)。這時(shí)候的田野上滿是結(jié)果。由于豐收和富足,萬千生靈都流露出壓抑不住的歡喜,各個(gè)與人為善。”⑥在九月野地這一空間里,社會(huì)生態(tài)因富庶的大地而得到改善。《九月寓言》書寫了一個(gè)物質(zhì)匱乏但精神富足的時(shí)代。小說中“魚廷鲅”們?cè)谕恋厣峡癖嫉臍g樂,有關(guān)地瓜干的傳說,金祥千里背鰲的故事,皆是富庶九月最動(dòng)人的注腳。張煒筆下的“野地”孕育著生活的本真與生命的真實(shí),與評(píng)論家所說的藏污納垢的民間相去甚遠(yuǎn),而是寓指一個(gè)真實(shí)的精神家園。隨著“工人揀雞兒”的到來,小村被挖空,小村的姑娘被澡堂、黑面肉餡餅、膠靴等現(xiàn)代之物誘惑,丟掉了身為小村人的原則和底線。小村的陷落標(biāo)志著物質(zhì)消費(fèi)對(duì)于人類精神侵蝕的全面展開,而“憶苦”則是對(duì)大地精神的再一次召喚與對(duì)資本、暴虐的抵抗。故而張煒筆下的大地與自然是其90年代人文道德精神的來源,也是其反思現(xiàn)代的精神資源。
因此,我們似可將張煒歸入廣義的“尋根文學(xué)”脈絡(luò)之中。80年代的文化尋根思潮源于人類對(duì)現(xiàn)代化進(jìn)程的迷惘與擔(dān)憂。尋根文學(xué)以“向后回望”的姿態(tài)代替“直接的前瞻”,既發(fā)現(xiàn)傳統(tǒng)文化的魅力(《受戒》《棋王》《北方的河》),又對(duì)傳統(tǒng)文化的劣根性加以批判(《爸爸爸》、《厚土》系列)。90年代文學(xué)界對(duì)于傳統(tǒng)文化的反顧,接續(xù)80年代“尋根文學(xué)”開創(chuàng)的傳統(tǒng)。現(xiàn)代化在極大促進(jìn)經(jīng)濟(jì)增長的同時(shí),也切實(shí)帶來諸多威脅。環(huán)境污染、水污染、人性異化、道德淪喪等負(fù)作用在90年代集中爆發(fā)。因此,尋根文學(xué)脈絡(luò)下的這種回望并非是回到“前現(xiàn)代”的保守主義,或是“反現(xiàn)代”的,而是在文化人類學(xué)的發(fā)展立場(chǎng)上,對(duì)中國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存在的問題發(fā)出警醒與反思。張煒在90年代仍延續(xù)著啟蒙精神進(jìn)行創(chuàng)作。《柏慧》《家族》繼承魯迅的戰(zhàn)斗精神,表達(dá)了張煒對(duì)邪惡的絕不寬容,體現(xiàn)知識(shí)分子的現(xiàn)實(shí)戰(zhàn)斗精神。⑦《九月寓言》向民間汲取精神力量,所表現(xiàn)出來的文化反思特征也不能簡(jiǎn)單理解為“逃離”與“反現(xiàn)代”。陳星宇指出“道德理想主義”本是“新儒家”在1990年代復(fù)興時(shí)所提倡的,它蘊(yùn)含著中國儒家通過自身調(diào)整——“內(nèi)圣”,最終實(shí)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訴求。①也就是說,張煒提倡的“道德理想主義”是在現(xiàn)代性話語范疇內(nèi)的自我質(zhì)疑與批評(píng),最終目的還是要促進(jìn)中國的現(xiàn)代性發(fā)展,是處于“尋根文學(xué)”所開創(chuàng)的反思現(xiàn)代的脈絡(luò)之下。從這個(gè)意義上說,張煒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蘊(yùn)含了對(duì)中國現(xiàn)代化的擔(dān)憂與檢視,這是一種真正的思想現(xiàn)代化特征。②這對(duì)于后發(fā)型現(xiàn)代化國家尤具警醒意義。李航育《最后一個(gè)漁佬兒》(1983)、張承志《心靈史》(1991)等也表現(xiàn)出這種審美現(xiàn)代性特征。
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學(xué)與大眾的娛樂、消遣達(dá)成聯(lián)盟,席卷整個(gè)90年代文壇。作家以輕飄的寫作姿態(tài)逃避精神道義的擔(dān)當(dāng)。以方方、池莉等為代表的“新寫實(shí)小說”,作家以零度敘事的手法書寫個(gè)體欲望與庸俗日常生活。90年代后,自由主義思想攜帶著個(gè)人化、欲望化寫作崛起。陳染、林白女性意識(shí)的私語表達(dá),何頓、韓東對(duì)欲望化的本能敘事,忽略了文學(xué)與社會(huì)大眾的關(guān)涉。其中,王朔以“游戲”的姿態(tài)進(jìn)行創(chuàng)作,在90年代文壇產(chǎn)生巨大轟動(dòng)效應(yīng)。張煒并沒有與以上任一時(shí)代潮流“合奏”,他始終在形而上層面上揭示生存的意義與人性的本質(zhì),從而克服了90年代文學(xué)中一度盛行的把消遣、娛樂作為旨?xì)w的膚淺傾向。90年代,孟繁華提出“新理想主義”,認(rèn)為文學(xué)應(yīng)關(guān)注人類精神處境,除娛樂功能外,還應(yīng)給人心靈以慰藉。③這一時(shí)期的張煒正是在鋪天蓋地的市場(chǎng)潮流之中,堅(jiān)守著他一貫的人文知識(shí)分子立場(chǎng),關(guān)切人類的精神現(xiàn)狀。吳義勤即從知識(shí)分子的當(dāng)代境遇出發(fā),肯定張煒的知識(shí)分子品格與對(duì)物化社會(huì)的批判、對(duì)精神家園的追求。④因此,盡管在90年代,對(duì)于張煒主張的“道德理想主義”多有貶抑之聲,但是歷史已證明,張煒的憂思不無道理。到新世紀(jì)之后,張煒更加堅(jiān)定地發(fā)出自己的“聲音”。
四、思想的沉潛與獨(dú)站“高原”的發(fā)聲
經(jīng)由“流浪”而形成的知識(shí)分子主體身份意識(shí),以及道德理想主義的人文關(guān)懷,使得張煒的思考點(diǎn)始終錨定在對(duì)人的精神的探尋與生存的關(guān)注上。《九月寓言》之后,張煒又創(chuàng)作了《外省書》(2000)、《遠(yuǎn)山遠(yuǎn)河》(2005)、《獨(dú)藥師》(2016)、《艾約堡秘史》(2018)等作品。耗時(shí)22年的鴻篇巨制《你在高原》(2010)是張煒這一時(shí)期最重要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新世紀(jì)以來,隨著社會(huì)現(xiàn)代化弊端的日益顯著、權(quán)力與資本結(jié)盟的猛烈侵蝕,文學(xué)界開始反思90年代作家“逃避現(xiàn)實(shí)”的書寫模式,試圖恢復(fù)文學(xué)“介入”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能力。2004年興起的底層文學(xué)即是一種應(yīng)對(duì)之策。在新世紀(jì)張煒延續(xù)早期確立的知識(shí)分子品格,站在弱者的立場(chǎng)上,書寫底層民眾的苦難遭際與知識(shí)分子的道德理想情懷。與90年代《家族》《柏慧》等作品急峻、激憤的反抗風(fēng)格與戰(zhàn)斗精神相比,這一時(shí)期他的創(chuàng)作則更為沉潛與冷靜。
張煒延續(xù)其早期《山楂林》《古船》《柏慧》等作品表達(dá)的反思現(xiàn)代的主題,警惕現(xiàn)代化發(fā)展進(jìn)程給底層農(nóng)民帶來的苦難。只不過隨著現(xiàn)代化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張煒更加關(guān)注其對(duì)人類社會(huì)、精神產(chǎn)生的影響。《外省書》不僅表達(dá)了現(xiàn)代消費(fèi)主義對(duì)于自然的毀滅性破壞,而且突出了現(xiàn)代技術(shù)與全球化發(fā)展對(duì)于人類社會(huì)生態(tài)的巨大影響。在《外省書》中,史珂是有著強(qiáng)烈道義感的知識(shí)分子,他不愿迎合市場(chǎng)需求寫一些“現(xiàn)代主義”作品——“精液、屁、各種穢物,再摻幾片玫瑰”,得到的也只能是“你別寫了”的呵斥;他不認(rèn)為人類正通過科技實(shí)現(xiàn)自我解放,技術(shù)商業(yè)時(shí)代帶來虛幻的東西,讓人類走入普遍沮喪,因此,他被人看作怪異的“外星人”;他不愿融入充斥著畸形性欲的時(shí)代,在一隅注視著現(xiàn)代人的精神疾病,呼喚著人與自然萬物和諧相處的偉大事業(yè)。所以他從京城回到故土河灣老屋,傍海而居,過著“心遠(yuǎn)地自偏”的生活。與早期表達(dá)的“現(xiàn)代憂思”主題相比,張煒在新世紀(jì)的書寫更加突出技術(shù)、消費(fèi)對(duì)于人類精神的侵蝕。《能不憶蜀葵》《丑行或浪漫》《精神的背景》等創(chuàng)作也表達(dá)了同樣的主題情節(jié)。
《你在高原》是張煒創(chuàng)作的又一高峰。小說集中對(duì)時(shí)代影響下的人類精神進(jìn)行探尋。《你在高原》以寧伽的家族歷史為敘述中心,講述“父輩”(寧珂)在“革命”時(shí)代的經(jīng)歷與“后革命”時(shí)代的不平遭遇,以及“子輩”(寧伽)長大后在平原、山區(qū)等地的求索見聞。①小說以類似于“游記”的視點(diǎn)記錄了諸多的底層苦難現(xiàn)實(shí)。《荒原紀(jì)事》凸顯底層民眾的生存苦難,小說中農(nóng)民的土地被掠奪,現(xiàn)代工業(yè)與淘金者對(duì)人類生存環(huán)境無情破壞,進(jìn)而引發(fā)人類身體出現(xiàn)病變。《鹿眼》《無邊的游蕩》敘述底層農(nóng)村女性的悲劇,她們更多成為物質(zhì)利益的犧牲品。《橡樹路》寫到海邊打工者漂泊無定的苦難生活。張煒在看到現(xiàn)代發(fā)展的同時(shí),從來沒有忘記底層民眾在這一過程中經(jīng)受的苦難。這是由他自小生活經(jīng)歷與獨(dú)立的文學(xué)立場(chǎng)所決定的。《你在高原》中,寧伽是張煒?biāo)茉斓闹艺\于自己內(nèi)心的理想知識(shí)分子,他見識(shí)了殷弓等人的丑惡、商業(yè)資本對(duì)平原的侵蝕,經(jīng)歷了被柏慧背叛的痛苦、與梅子分道揚(yáng)鑣的無奈,但是依然保持內(nèi)心的清潔。通過他的“游走”經(jīng)歷與人物視點(diǎn),張煒向我們揭示了更多殘酷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小桿兒、冉冉、加友、瓜妞是被欺侮、被蹂躪的底層受害者,他們的被欺辱不是如魯迅筆下祥林嫂與封建勢(shì)力的遭逢那般,而是處于商業(yè)與資本的壓倒性優(yōu)勢(shì)狀況下。《憶阿雅》中的林蕖,《海客談瀛洲》中的秦茗已,《家族》中的陶明都是被時(shí)代物欲所“擊倒”的人。因此,面對(duì)現(xiàn)代發(fā)展對(duì)人類精神展開全面侵蝕的語境,張煒在新世紀(jì)創(chuàng)作中少了“魯迅式”的激憤反抗,而多了幾分沉潛的味道。在面對(duì)“橡樹路”“阿蘊(yùn)莊”“環(huán)球集團(tuán)”“卡拉娛樂城”等藏污納垢的地方時(shí),寧伽也只能如趕鸚(《九月寓言》)、劉蜜蠟(《丑行或浪漫》)、史珂(《外省書》)等人一樣,不停地“在路上”。
從小說的敘事空間上看,張煒?biāo)坪踉跁r(shí)代面前一直退卻與逃離。譬如,張煒筆下的主人公紛紛逃離城市的喧囂與拙劣的建筑,回到老磨屋(《古船》)、登州海角(《柏慧》)、河灣老屋(《外省書》)、葡萄園(《你在高原》)等空間,與小茅屋、葡萄園、大海朝夕相處。也難怪評(píng)論家在90年代指責(zé)張煒將苦難詩意化、躲避到“野地”。如果我們聯(lián)系時(shí)代語境與張煒的整個(gè)創(chuàng)作生涯來看,可知這是張煒的一種策略:以退為進(jìn)。在八九十年代,現(xiàn)代化一路高歌猛進(jìn),文學(xué)也參與到這一“理想化”的宏圖之中。張煒不愿加入這場(chǎng)“大合唱”,寧愿在曠野上“獨(dú)奏”出屬于自己的“聲音”,以此默默地對(duì)抗被同化。賀仲明認(rèn)為“退卻并不一定就是潰退,它還有另一種內(nèi)涵,就是戰(zhàn)略性的撤退。”②換句話說,退卻的背后是堅(jiān)守。張煒曾自言:“置身潮流之中,被一種慣性推擁著,需要多大的堅(jiān)韌和倔強(qiáng)才能掙脫出來。我認(rèn)為一個(gè)搞創(chuàng)作的人應(yīng)該具有那樣的雄心和力量。”③正是因?yàn)榫哂羞@種雄心與力量,所以張煒才能在眾人沉迷于未來一片光明時(shí),獨(dú)站“高原”之上發(fā)出警醒的呼聲。這在《古船》中所表現(xiàn)的懺悔與反思意識(shí)中已有所體現(xiàn),并在其后的創(chuàng)作中得到進(jìn)一步的表現(xiàn)。
新世紀(jì)以來,在大眾傳媒與影視的驅(qū)動(dòng)下,作家以“利”為目的追求短、快的創(chuàng)作效益。在這樣的時(shí)代語境下,張煒能夠沉潛20多年寫出《你在高原》,這本身就說明了他所堅(jiān)守的主體精神。從創(chuàng)作內(nèi)容上看,雖然張煒的創(chuàng)作與新世紀(jì)的底層寫作有共謀之處,但這并不是他有意識(shí)地加入“主流”的結(jié)果,而是在張煒自身創(chuàng)作脈絡(luò)的延長線上。早在《一潭清水》《古船》《九月寓言》等小說中就可以找到影子。《你在高原》之后,張煒創(chuàng)作的兒童文學(xué)《半島哈里哈氣》《尋找魚王》等也處于這一脈絡(luò)之中。
五、結(jié)語
作為知識(shí)分子的張煒處于與時(shí)代“主流”的“共名”與“張力”之中。從表面上看,張煒的寫作內(nèi)容、風(fēng)格與時(shí)代“主流”錯(cuò)位而行,但是,作為知識(shí)分子的張煒卻處于與時(shí)代的“張力”之中。張煒以道德理想為基點(diǎn),基于各個(gè)時(shí)代特點(diǎn)選擇不同的藝術(shù)方式和寫作風(fēng)格,形成所謂的張煒的文學(xué)“轉(zhuǎn)向”。70年代末80年代初,當(dāng)大多數(shù)作家以“問題小說”蜚聲文壇時(shí),張煒在蘆青河上以孫犁的浪漫抒情筆調(diào)贊揚(yáng)人性之善。80年代,文壇上“傷痕”與“反思”的聲音大行其道之時(shí),張煒以《古船》加入到啟蒙主義的批判隊(duì)伍之中,深入對(duì)歷史與現(xiàn)實(shí)的反思、對(duì)惡的批判。90年代,文學(xué)與大眾的娛樂、消遣達(dá)成聯(lián)盟,文人放棄任何擔(dān)當(dāng)。張煒堅(jiān)持著知識(shí)分子的品格,在廣義的“尋根”脈絡(luò)下發(fā)現(xiàn)了“野地”,以此抵抗被時(shí)代“收編”與發(fā)出警醒。新世紀(jì)隨著現(xiàn)代化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在資本與市場(chǎng)結(jié)盟的語境下,張煒獨(dú)站“高原”之上發(fā)出內(nèi)心的“聲音”,對(duì)于底層民眾的關(guān)注與時(shí)代“主流”形成共謀。可以看出,作為知識(shí)分子的張煒始終堅(jiān)持著對(duì)于“真”的恪守與“善”的追尋,對(duì)于“洋野蠻”(商業(yè)擴(kuò)張主義)和“土野蠻”(封建專制主義)的批判,這是經(jīng)由早期“流浪”而形成的知識(shí)分子品格的體現(xiàn),是處在魯迅思想的延長線上。
2016年張煒在接受訪談時(shí)說:“我提防在潮流中走向模仿和依從,提防自己失去原則性。因?yàn)槿硕际擒浫醯摹N蚁M约耗茏鲎粤⒑妥詾榈膶懽髡撸M(jìn)行獨(dú)立創(chuàng)作并排除外界干擾。我希望自己成為一個(gè)冷靜和安靜的人,這樣的人會(huì)有一點(diǎn)原則和勇氣。潮流來了,先要站住。有原則的人才能謙虛,而不是相反。”①張煒以他的“德性”之火點(diǎn)亮?xí)r代的精神荒原,默默地充當(dāng)著商品經(jīng)濟(jì)社會(huì)“廢墟”之中的精神“拾荒者”。因此,張煒恰如本雅明筆下的游蕩者,是一個(gè)有充分主體意識(shí)與基本原則的知識(shí)分子,而并非一個(gè)看熱鬧的、個(gè)性模糊的“人群中的人”②。
On Zhang Weis Self Formation and Literary Narration
——Reflec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ectuals and the Times
LI Xue
(School of Arts,Suzhou University,Suzhou 215123,China )
Abstract:Zhang Wei is an indispensable writer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world. Zhang Wei has become an object of continuous interpretation and discourse by scholars due to his ambiguous position in literary history and literary trends. Only by returning to the text and placing Zhang Wei in the intertwined web of time and literature, and examining the synchronic field of each era and the diachronic field of Zhang Weis own creative context, can we fully reveal the rational logic behind his creations. The intellectual character formed by Zhang Wei through his early“wandering”runs through his creation and puts him in a“co name”and“tension”with the times. Whether it is the early writing of human nature, the ensemble with enlightenment in the 1980s, the passive addition of“moral idealism”in the 1990s, or the focus on the lower class after the new century, Zhang Wei has always adhered to the moral conscience of intellectuals, observing modern human nature and the spirit of humanity on the extension of Lu Xuns ideology, and exploring methods to achieve modernization of the country and nation. Examining Zhang Weis mental journey as an intellectual provides a case study for reflect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ectuals and the times. In the current context where literary creation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capital and the market, reflecting on it has particularly practical value and significance.
Key words:Zhang Wei;Self-construction;literary narration;intellectual;times
[責(zé)任編輯? 唐音]